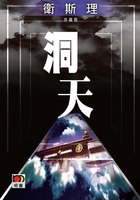刘长乐顿顿,继续说,告诉大家一件压在我心底十多年的秘密吧,可以说,这是一片阴影,它笼罩我心头这些年,今天,我想揭开它。我初中时候的班长,他个子高,身子壮,为人蛮横,他用高压手段统治我们整整三年。这三年,我挨过打,受过欺负,我不敢说,不敢反抗,告老师没用,老师不可能时刻监督班里每个人的一举一动,甚至有时候还会偏向班干部。所以这些年,就是到了现在,我只要想起来,心里的阴影面积丝毫没有缩水,为了不让大家重蹈我当年的覆辙,为了让大家在一个民主和谐宽松友爱的环境里专心学习,愉快成长,我希望从我带的第一届学生开始,尝试着去作改变。
刘长乐的话赢来了热烈的掌声。
学生们已经相处两周时间,算是有了初步的认识了解,在这样的基础上,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高一(5)班的班委。
刘长乐对新的班委班子是满意的。尤其班长和体育委员,从个头到举止,到亲和力,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都是没得说的。特别是班长,一看就是从小经过历练的,就任班长的一番即兴演说,朴素真诚,热情大方,获得了热烈掌声。
掌声中,刘长乐的目光在腊志东身上停留了一小会儿。这个学生没能进班委,是有一点遗憾,不过既然是民主选举,就得尊重。他已经接受了他那天到办公室来给自己内心留下的不悦。那不悦像一道浅浅的影子,已经淡了,消失了。腊志东当什么都不合适,身体,他太单薄,性格,不明朗,甚至有些胆怯。这学生其实就是扔进人堆里会很快被埋没的那一类,但愿学习能够好一些。至于他提出调座位的要求,还是暂时往后推推吧,等掌握了全班更多的信息后,再进行综合考虑调整。
星期日下午返校前,腊志东跑到母亲跟前嘟囔着什么。父亲腊学民将摩托车推出来等在门口,透过半开的门他看到儿子肩头斜斜地挎着大书包,里头塞得太满,也重,书包带子绷成直线,让人担心马上就会断掉。腊学民打着发动机,摩托突突突吐气,像一头不耐烦的急性子叫驴。
腊学民用脚踩着刹车片,也不耐烦了,说,冬冬你快些儿,有啥磨蹭的!
屋里应了一声,不是儿子,是女人,这一声应答,像一块土坯子隔着门帘扔了出来,溅起一片尘土。腊学民揉着眼睛,心里不痛快了,本来不想说的话忍不住顶了上来。他干脆灭了火,提高嗓门说,快叫他出来,磨磨蹭蹭的,一个大男人家咋跟个女娃子一样啰唆!
他的气其实是冲着女人撒的。果然,女人搡着儿子的后背,半推半哄从门里弄出来,腊学民一看娘儿俩那拉拉扯扯的阵势,心头一捧无名火轰一声就爆了起来,喊:你放开他,放开!他不会走路吗?长得墙头一样高了,还像吃奶的娃娃一样哄着,你准备哄他一辈子吗?
腊学民冲女人发了脾气。
女人笑呵呵的,一直把儿子按到摩托后座上,还拍了拍书包,冲男人一龇牙,说,娃才十六嘛,能有多大?在我心里他就是个碎娃嘛。
腊学民狠狠加了把油门,一股子黑烟往后喷出,似乎要把这个唠唠叨叨迷糊不清的女人给淹死。
儿子的身子在车后硬撅撅的,他坐得挺直,随着颠簸,腊学民感到儿子的身子像一个轻飘飘又干巴巴的麦草捆子,在行进中这草捆子一仰一仰往后倒,始终不往腊学民的身上靠近。不知道他的手抓在哪儿,要不抓牢,一头倒栽下去,不摔死才怪呢。他这是做啥怪呢,非得和老子拉开一定的距离?难道离近点老子能吃了你!
腊学民像年轻二杆子一样重重加了把油门,摩托车被注了兴奋剂,嚎叫着冲完最后一段村道,喷着粗气,期待在眼前平展展的公路上放开了狂奔一气。但是腊学民及时捏住刹车,减小油门,速度骤然突降,车后的人颠起老高,扬起又跌下。摩托车喘息着挣扎几下,终于屈服了,匀速前进,车轮沙沙沙向前,汇入正途。
身后的儿子始终和父亲保持着距离,剧烈的颠簸中也没有吭声,没有惊叫,身子还是硬撅撅的,就是不往他身上靠。
腊学民情绪忽然有些低落,像一个捉弄别人的孩子,计谋得逞了,但是发现自己并没有从中找到想象的快乐。他丧气地吐一口气,腾出手把头盔的透明罩子往下拉拉。秋风大,虽然还没到冷的季节,但车速到了七十码,风劲就有着透骨的力量,凉意顺着骨缝钻。不敢小看这秋风,骑摩托车这些年,他已经种下了病根,肩胛、膝盖、前额,一到刮风天气就隐隐地疼。疼倒还罢了,骨髓深处痒痒的,说不出的难挨,据说是早期风湿病的表现。都是这些年骑着摩托来来去去走学校种下的病。今年上了五十,他看重保养了,开始顾救自己,再不敢跟前些年一样耍二杆子了。现在他只要出门,不管路程远近都不怕麻烦地武装自己,头盔、护膝、皮外衣,包得严严实实,穿戴整齐。儿子跟他前些年一样,甚至比他刚学摩托那会儿还彻底,他一点顾救都不做,单溜溜一身家常衣裳,就这么出门上路了。风一灌,全身透,一把嫩骨子,现在年轻没有啥,等到了他这个年龄,各骨帽儿都是病,后悔都来不及了,真是年轻不懂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