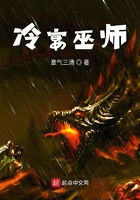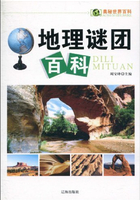当日便与汉中太守苏固签订了城下之盟。苏固承诺不杀张修。厚赉我军将士。偿其“抵命费”黄金、白银各五百斤,帛缣二千匹,蜀锦、蜀丝各千幅。其珠翠古玩、名士字画、奇珍异宝也搜刮了不少。苏固还应允供给吴岳盐每月二千石,统统是最低价收购,至于开放市场,令我军自由出入等等,更签得他名声大臭。
连我都没想到会如此顺利,是夜便急速北归。在汉中的这一笔财发得不小,辎重逶迤得比来时还显丰富。要不是我赶得紧,便拿得还要多些,不过这也成为急行军的大负担,士卒推着装满财宝的大车,初时还兴高彩烈,过了几天就已变得怨声载道。
此次行军我根本也没加意堤防羌人的动向,原以为回到峄醴,必然还赶得急。七月戊寅,尚在南郑。己卯,已过沮县,至沔水尽头东狼谷。
武都郡治下辨,出洛阳凡一千九百六十里。郡内七城,下辨、武都道、上禄、故道、河池、沮县、羌道。盛时户二万一百零二,口八万一千七百二十八。此际遍地凋零,人丁单薄,哪有往日气象?疾速通过东狼谷后,触目尽是广袤的原野、丘陵,无所人烟,只闻狼迹蛇踪,令人感慨万千。
我见天色尚早,准备再走一程。小清纵马上前,道:“夫君光顾着赶路了,士兵们都很累呢。而且,这些天没见峄醴来报军情,恐怕会有变化。”
我听她提醒,方才恍悟过来,“那就准备扎营休息吧。多派哨马,往西北、西南两路打探。”
军卒们陆续闻得将令,都坐在地上长吁起来。待他们纷纷造营、安栅之时,我望望天际荒芜的土地,突然有种疲倦与绝望的感觉袭来,望望四周,竟没来由地紧张起来。我唤着小清名字,道:“你觉得什么不对么?”
小清脸上很平静,但眼神霎时间充满了担忧,“没什么呀,夫君好象有不详的预感呢。”
心中那种恐慌开始成倍地增长起来。隔了片刻,我决然地俯身在地下,侧耳趴在尘土中聆听,大地传导着极是轻微的震动,象是火车在遥远的铁轨上所滚动发出的颤悸一般。
小清吃惊地望着我,似乎想到了什么。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顿时更加明白我所听到的轻响决不是耳鸣。众军士看着我,犹疑作色,露出惊惧不定的表情。而小则清大声喊叫,命令卫队集合。传令兵纷纷吹响长角。
我来不及穿甲胄,便翻身上马,冲到旁边的高坡上了望。天哪!西北、西南两面一带天际黑压压地不知涌出多少军马,似乎正朝这里开来!我大叫:“敌人,西北、西南方向有敌人!快上马,准备应战!”
未及搭成的营寨中的军卒顿时乱成一团,有的已躺倒在地准备享受片刻小憩的,也立刻跳起来穿靴披甲,人呼马嘶中,有执旗持戟的战士寻找着自己的队伍,更有些甚至还未来得及穿鞋,便冲向队伍,除了最先集中的铁甲士卒大部妥当,其余的部队无不凌乱不堪。
稍顷,天边传来鼓角声响,大地隆隆的马蹄的震动更使我们惊慌失措。我大感恼恨,没料到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睡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恨得咬牙切齿。小清、卢横策马围来,皆是不知如何是好。我急令全军结阵,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稳住。稳住就有希望,就可以伺机突围,但我们缺少长戟手和盾牌兵,甲胄也并不完备。形势危如累卵。
没多久,敌军的喊杀声遍野而至。宗稠率前锋千余勇士猛突西北面敌军,但只是象石沉大海一般,毫无起色。我心下一沉,感觉天空似乎都变得异样灰暗起来,忖道:老子一世勇名,便在这一仗断送了!不过我死得其所,即使全军覆没,也不能让对手好过。
弃剑换枪,强打精神地舞动两下,“众军,冲突出去!我们不能困死在这里,我颜鹰当率勇争先,为弟兄们搏杀出一条生路!”
于此时,我也只能这么说。在军心混乱的情况下,只有作出表率,鼓舞士气,才能不溃,从而争取活命机会。
小清上前护我,被我拒绝。我眼中闪现出无论如何也要冲出去的神色,毅然决然地往宗稠苦战的方向冲去。士兵们齐声吼叫,跟随冲杀,但两翼的敌军骑兵,象毒蛇一般死死咬住,令我军施展不开、动弹不得,死伤加剧。
更何况,我军已是疲惫之师。敌军精勇恐怕数倍于我,又以逸待劳,此战孰胜孰负,清清楚楚。我大骂自己糊涂,怎么能不早点察觉呢?明明与峄醴失去了联络,还不想想是否有敌军作怪,仍是埋着头往前狂奔,便正好在阴沟里翻了船!
小清双手执矛,左右开弓。但她再勇猛无匹,一时又哪里杀得光这样多敌军呢?徘徊良久,我们四周的敌尸都能堆成小山了,却只往西北突进了百余步。卢横刀头卷刃,混战中恰逢一敌举刀劈来,他暴喝一声,将废刀掷出,这才突过去抢了那人兵器,将其硬生生砍成两段。
铁甲卫队布阵精妙,战斗能力极强。敌人多半往我这里施压,却得不到半分便宜。不过是时惨叫声、怒骂声和光刀剑影的呼啸声此起彼伏,让人脑中绷紧了弦,只知拼命杀敌,哪还想得了其他?因此我并没有立刻指挥突围。
攸地,敌军阵前不断有人以蛮语狂叫。小清色变道:“果然是赤脊族麻奴!他说有人能生擒夫君者,赏金十万,立刻升为部族统领。”
“我好香么,人人都抢着捉我。”我苦笑道,心神一乱,顿时有敌从后面射来一支暗箭,正中后腰。还好我甲衣隔着,倒无大碍。众军却惊慌地高叫起来。我正欲借此机会激励士气,便放声大笑,拔出箭矢高叫道:“区区一支羽箭,焉能伤得了本帅?众军,活捉赤脊族族长麻奴者,赏金十万,立刻升为将军!”
小清、卢横皆是又惊又佩地看着我,而敌人大现惧色,还道我刀枪不入呢。也可能是我在羌族中威名太盛,前几次与赐支、神海签盟之事令人记忆犹新罢,所以铁甲卫队鼓勇而前,反倒变成了往敌军阵势冲击的势头,令人大感安慰。
麻奴也必定不是寻常之人,惊慌了片刻,眼见族人慌乱,便提剑杀了几名逃跑的士兵。我在阵后观见,暗叹一声,道:“卢横,你杀出围去,向峄醴禀告,命司马恭不得与战。能生离多少,就带多少人走吧。我有清儿,过几日便会回来。”
卢横大震,长声道:“卢横不走!主公莫要心急,我们还有几千军卒,不至就戮,但能杀出重围,令主公生离,卢横纵死无憾了!”
我提枪拼杀,一面叫道:“每次都不听我的话,是不是眼里没我这个主公?现在敌军被我缠着,你正好与宗稠会合,从西北突围。老子与夫人绝不会有事,但切切记着,命司马恭不可与战!”
卢横仍是不肯走,大刀怒横,连斩敌人十余名。我又气又急,突地横剑颈上,“你到底走不走?你若不走,我自刎给你看!”
卢横慌乱交加,竟不顾危险,跳下马来拉我的手,“主公万万不可!!卢横愿遵……将令……”
小清从旁杀了多人,命其上马快速离去。我叫道:“众军弃下财物、辎重,想活命的,便跟卢将军回去!”
卢横拭泪,仰天长啸,道:“主公若有不测,我卢横便杀光天下所有羌人,再一死以报主公知遇之恩!”
铁甲卫队狂呼着继续搏杀,随着旗号往西北冲突。身边只十余名亲兵均存死意,不肯离去。羌兵队见了满道财物、辎重,忽地阵势大乱,拼命抢夺,连将官都收拾不住。我与小清对望一眼,只觉心境说不出的悲凉:是时候了!
她毅决地道:“我不会让你死,相信我!”
我点了点头,她丢开一支矛,单手将我拎到她的马上,“抱紧!”回首又朝身边诸死士大叫,“各位,我们往南冲出去!”
敌军万千军卒重重围堵。小清矛枪疾舞,如风轮一般,挑开无数剑戟流矢,振奋精神,在敌阵中来回冲击,杀贼百余。十余名骑兵齐声怒吼,疯狂打杀。但我心中有数,这情形决不可能长久,而且我也感到她伤得越来越多,连马儿都惨遭屠戮,连声惨嘶。战至片刻,身边已无一名亲兵,她身体每每中箭、中枪,便是一阵震悸。我心下哀苦,低声唤道:“清儿,清儿……你让我死罢!”
小清愤怒地娇咤一声,矛枪忽地挑刺几名弩手,将其囊中箭矢抓起大把,狠狠往敌阵中摔去。她的劲道惊人,弩矢所过之处,敌军东倒西歪、死伤遍地。羌敌见她只有一人,却如此神勇,惊为天人,反而不敢过分逼近。不知杀了多久,待黑幕降临,小清终于冲开最后一道防线,往南驰去。
我背上亦中了多支流矢,却更心痛爱人的身体。她是为我在挡子弹啊!
猛听坐马一声长嘶,倒伏在地。小清腾地跃下,弃矛扶住我身子,侧过脸来道:“你没事罢?”
后头追兵甚急。小清见我点头,一咬牙,背起我向南急逃。我听闻耳边风声呼呼,知她奔行快极,顿有一丝歉疚与安慰。心道:我初时与清儿掉进这个世界,好象也是受伤,耳旁也感到风声,情形一般无二呢。
隔得片刻,竟昏昏沉沉地睡去……片刻前的事情顿时恍若隔世。
不知多久,才终于醒来:眼前是个很小的草棚,身上的伤处已被细细包扎过了,动了几下,却并不很痛,于是轻叹了口气。
有人道:“你醒啦。卢横他们已经脱险了,你知道吗?”
我睁眼望去,却令我心神大碎。小清正在一旁裸着上身,若无其事地拔出身体上的断刃、弩矢。可她的身体浸染着斑斑血迹,而脸上左颊,更是有一条五寸长的刀印,皮肉绽裂,惨不忍睹。
我不由大恸,哽咽了几下,喷出一口淤血,“我……我……都是我害了你!这天杀的赤脊人!老匹夫!狗日的──”
我两手捏拳,往地上猛砸,指节迸血!小清抢上前扶起我,柔声安慰道:“怎么啦?你别担心,我没事的。干嘛急成这样,我不会死,我答应你。”轻轻将我揽进自己袒露的怀中,抚摸我的头发,“我真高兴你这样在乎我。就算真的为你死了,我都心甘情愿……”
我捂住她的嘴,哭道:“你若死了,我就给你殉葬。”望着她脸上那长一条刀伤,不禁轻轻碰触,悲从中来,“都是我不好,都是我害了你……”
“你别哭了。”小清柔声道,用手指擦擦我嘴角的血迹,又吻了吻我的额头,“都是我吓着你了。别担心,伤口很快就会复原的,那时什么都瞧不出来。”
她这样说更加令我心悸。这辈子,我已经欠她太多,恐怕用生命去偿还,也还不干净了。我咬牙切齿,想到我应该去报仇血恨!杀尽羌贼。但转瞬间,又强自平静下来,哽咽道:“都是我的错。我疏于防备,却给麻奴这狗日的制造了机会。清儿,你这样不顾自己地把我救出来……可我怎么忍心……”说不出话,只是抱着她受伤的身体痛哭。
她温柔地抚摸着我,轻声道:“只要有你这些话,我做什么都值得了。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比天还高,比海还深。”
我闻言大震,泪眼迷离地抬头看着她,吻她的唇与伤处。我擦净她脸上的血迹,轻舔着那道刀痕。我撕下内衣,帮她包扎身体的伤口。不管她要不要,我都要执意这样照顾她。她让我心碎,让我伤情,让我觉得永远爱她不够。
我含泪搂她入怀,问起诸事。小清轻轻道:“这儿是沮县南面的小聚邑,没什么人烟。我已甩掉追兵,不过他们很可能还会找过来。我们只有两个人,得早些与司马恭他们会合才行。”
我抹干泪水,心中的愤恨与杀气勃然而起,令身体兴奋得颤抖。我阴沉沉道:“这一仗我所失去的,一定会加十倍、百倍地收回来!我要让麻奴这狗贼生不如死,尝尽苦头。我发誓……”
小清伸出小手,轻轻堵在我的嘴边,微笑道:“你别这样吓唬人家好吗。其实打仗呀,难免会有这样的事,你日后纵然把他抓住加以惩罚,又有什么用呢?夫君是个聪明人,千万别感情用事。而且,你若是因为我这样做,清儿会难受的。”
我默然不语,凝视着她,又觉得眼眶发热。我的确是在感情用事,但我讲的都是实话。谁叫他们伤了小清呢?他们可以击败我,杀死我,但他们不能动我的小清。每个人都有自己最脆弱的一面,我最丢不开放不下的,就是我的结发妻子,我永远永远的伴侣清儿。
“我答应你。”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你好好养伤,其他什么都别想。”
小清笑起来,“我真没什么关系,只是损失了点合成血浆……”
我被她不经意的话惊呆了,因为我想到她是靠着血浆才能活下去的。可是每一次受伤,她的寿命就在损耗呀!她见我吃惊地呆望她,泪眼模糊,便又赶忙安慰我道:“其余伤重的时候才渗出一点,对我身体没有害处的……”
我搂着爱人默默地流泪,这一刻分外珍贵。我们心心相印,已经不需要更多的言语了。我不知道与她相拥了多久,可我愈来愈下定了决心,不能让她再有什么意外,不可以再令她为我去玩命、去拼杀。绝不再让她冒险了!
翌日晨,当我一觉醒来,见她没事一般为我正烤着野兽,不禁心中苦叹起来:清儿不会渴、又不会饿,又不需睡觉,那她到底有什么要的?有什么我可以满足她的?恐怕只有那缠缠不绝的爱情罢。但愿她不要厌倦我,不要讨厌我。
走过去正要亲她,才惊讶地发现,她脸上的刀伤已然隐去大半,只有一条淡淡的白色痕迹残留着。她见我喜出望外的样子,羞涩地笑道:“有什么好看的?是不是我脸上刀伤还特别碍眼呢。”
我温柔地亲了亲她,道:“我希望你早些复原,变得容光焕发。又希望你别太早康复,这样我就可以照顾你啦。心中真是很矛盾呢。”
小清咯咯地笑道:“原来夫君也有为难的时候。快来吃,已经烤熟了。”
我闻得香气,问道:“是什么东西?”
“獐子罢。”小清答道,“这儿漫山遍野都是野生动物,不费气力就捉到了。我已经留了一半,你如果吃不下就扔掉罢。”
我休息了一晚,又兼昨日拼杀整天,肚里早饥馋得久了,拿起熟肉便大嚼起来。清儿静静坐在一边看着我,脸上浮现出满足的表情。我嗯嗯地道:“你不吃一点?”小清笑起来,摇摇头。“每次都这样问我,是不是我不吃你就很难受呢。”
“看人进餐,总有点怪怪的感觉,”我解释道,“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特别假客气,见了面打招呼也是问‘吃了没有’?所以吃东西,实际上是人际交往的一部分,例如培养感情,增进交往等等。我深受如此教育,习惯改不掉了。每次吃饭让你这样看着,我又觉得满意,又觉得失望。”
小清理解了我的用意,笑道:“你满意什么,又失望什么呢?”
我深深地看着她,“我看见你,就说不出的满意,那已经不需要用言辞来表达了。但我却失望你不能和我一起吃东西,甚至不能和我一起入睡。有时候晚上醒来,发觉身边少了你,那种空虚寂寞的感觉真是很难过呢!”
小清面色飞红,嗔道:“你别用这样好色的眼光看着我嘛。我只是不习惯躺着,这种程式会想我想起接受脑部移植的情形。”
我跟她坐在一起,柔声道:“不是告诉你别再想了吗。以后我要你跟我一起,乖乖躺到天亮。只有搂着你我才睡得安稳哩。”
小清更是羞涩不依道:“你只是想自己舒服罢了,人家才……不要呢。”
我哈哈大笑,一时阴霾尽去。我抱着她,靠着树,仰望着天上的云彩,悠悠然地道:“真想立刻就归隐田林,再不出山了。我颜鹰已经挣得够了,那时若见好就收,回到羌地去,又怎么招致昨日的惨败呢?”顿了顿,非常不舒服地拍拍脑袋,“都怪我太得意忘形了。从南郑那么招摇地出来,大包小包地带着财物,真以为自己百战百胜呢。嘿嘿,老子却是犯了最低级的错误,一路竟连个探子也没派,差点就要了我半条老命。”
小清道:“别责备自己了,财宝丢了是小事。只要不让大伙儿丢了命就行。到最后你逼着卢横他们离去,却留下自己作为掩护。那一刻我更加敬重你了。我知道我绝不可以让你死。”她眼波轻转,又笑着抬起头吻我,“好在你没事,不然可叫清儿怎生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