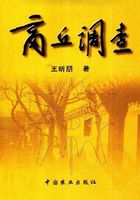我们家乡老话说“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本村有个老太婆,外号叫“京油子”、“老鸨子”,有六十多岁,论乡亲辈分我应当喊她二奶奶。她住在我们村西头紧把边的台阶上,墙边用石灰刷上大白圈,据说可以吓唬狼,不让它爬墙。她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孙子和我差不多大。她是个开赌场的人,什么坏事都干,还贩卖过人口。她经常去北京,听人讲她把亲生女儿也卖到北京的窑子里去了,用这钱给小儿子娶了媳妇。
我在村子里只见过她小儿子,没见过大儿子。我父亲赌钱就是在她家里,因为她尽做坏事,村里很多善良的庄稼人都恨她、骂她。有一天,她突然来我家了,一定没有好事。她长着一脸横肉,腮帮子上的肉往下垂着,穿一身黑衣裤,扎着裤腿脚,手拿着个大烟袋,挂着烟袋荷包。家中只有我和妈妈,她装做关心的样子说:“我那可怜的侄媳妇,你的命苦啊!没人没势的,连块土坷垃(土地)都没有。一个人还带着四个孩子,可真不容易呀,日子难过呀!我听说你这孩子给过人家,你舍得?”“不舍得有啥法子!没吃没喝的,给人家总比在家饿死强。”“你要真舍得给人,倒不如带到北京去换点儿钱,你好过日子。”我妈立刻把脸沉下来,心如刀绞似的难过,果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慈祥的母亲一反常态,严肃地说:“二婶子,你说这话就差了,你的关照我心领了。我是孩子多,日子也不好过。家里穷养不活,把她送人都行,可有一条,她愿意要,我愿意给,两厢情愿,她绝不能虐待我的孩子。她待我家孩子好,我送给她;她若待我孩子不好,我要回来。我要是使了人家的钱,孩子就是人家的了,我还能要得回来吗?二婶子,我人穷志不穷,我再穷,没有饭吃,全家饿死我也不能卖人口。”听了我妈一席话,老婆子马上改口说:“你老嫂子别恼,我可是为你好,我可没有坏心啊,是看你们一家子没着没落的。”边说边灰溜溜地走了。
我在里屋听着她们说话,开始害怕极了,只恐怕我妈被她油嘴滑舌地说动了心,我正揪心地听着,听到妈妈的一番话,心里高兴极了,我妈真行!人正、心正、说话也正,以正压邪,句句有理,铿锵有力,坚决果断,真是理直气壮,几句话就把老太婆赶走了。
在万恶的旧社会,像妈这样的妇女太少了,她真是有主见、有责任心、有正气、有能力的好妈妈。我太佩服妈妈了。
从此,我心里踏实了,妈不会卖我,即使给了人,待我不好还可以要回来。妈妈在我眼里可真是女强人。
算起来那年我八岁,论虚岁是九岁。又到了春季,吴村二月二有庙会,妈说带我上庙去,到庙会可以看戏,心里美滋滋的,很高兴。我兴高采烈地走在母亲前头,想早点儿到庙上。我家离吴村八里路,晌午前走到吴村南头一个亲戚家里,给我介绍一个叫九瑞的姑娘,她大概有十四五岁,说是我表姐。其实论亲戚我应该叫她妈表姐才对呢,这我以后才知道,当时为了使我不产生怀疑、暂时能待下来才这样说。
九瑞带我玩,还给我换上一套薄花棉衣、花裤子,我心中也想:为什么给我新衣裳?又为什么待我这样好?心里纳闷又说不出是怎么一回事,有点儿疑惑也就高兴不起来。接着给了我个白皮球,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在家时看财主家的孩子们有球打,而我没有,但我也不羡慕,我自己会纺线,拾点儿红棉花,纺点儿线,自己缠了一个圆蛋,结上棱子皮花纹也能打。今天有皮球了应当高兴,可我也没什么表示。吃过中午饭,我在院子里打球,好多人围着看我打球,都夸我打得多,打得好。受到了赞扬,我就得意地一个劲儿地打球,只顾玩,不知道妈妈已经从后门走了。看到其他小孩打得也挺好,可没有人夸他们,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事后想想才知道这是大人们设的“计谋”。
为了让我能活下去,能吃饱饭,妈又忍痛第二次把我送给了别人。她是个坚强的人,虽然心里空落落的,但不管遇到什么事,她总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妈妈的心有一半留在了我这里,她只能硬着头皮,心如刀绞,强挣扎着离开吴村回到家里。
老爷儿快落山了,我想起了要回家,开始找我妈,妈妈却不见了。我问他们:“我妈上哪儿了?”他们说妈回家了,对我来说这真是晴天霹雳,我撒腿往外跑,连声叫着找我妈。他们一帮人追上我,拦着我说:“追不上了,早走远了,明儿再回吧!”我非要追,那个年轻妇女就背着我满街走。我不停地说:“我要找我妈,找我妈……”她边走边说:“天黑啦,明儿再找,九瑞叫你九叔去追吧!听话,我明早送你……”
开始我和九瑞姐姐睡,以后就跟着那个年轻女人睡觉、吃饭。那年她只有二十五岁,嫁了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不生养(不会生孩子),就想要个孩子给她做个伴儿,也许她就安定了。
他们俩口子待我挺好,老头是想用孩子把年轻媳妇给拴住了,好死心塌地的跟他过日子。他们家没种庄稼地,是看园子的,有两间矮小的土坯房。那院子挺大,有二三亩地,院子里有口井,大概靠种菜生活吧,吃用怎么来的我不知道。这个年轻女子是从口外买来的,是个巫婆,会下神。有一天后半晌,她在一个大娘家里的炕上正中间坐着,她前面放了一张小炕桌,桌上铺了一块大红布,烧上香摆上一桌子贡品。她坐直了,用手比比划划,声音也变了,嘴里念念有词地说,某某大仙跟上某某人……触犯了大仙的罪过,要在某某时间、某某地方给大仙烧纸化缘,几天后就好了……她在香上烧了三张黄表纸,把纸灰给病人喝了。她打了个哈欠,好像是醒过来了,她恢复了常态,手也不指划了,声响也像平时了。别人说她有神灵附体,会治病去邪。她把一桌子的贡品拿回来给我吃,还说用那块红布给我做衣裳。
有一天夜里,我被大吵大嚷的声音给弄醒了,我起来坐在炕上,看见那女子在地上打滚,用头乱碰乱磕,老头儿在地上用劲抱着她、按着她,也弄不住她。好不容易老头儿把她抱到炕上,按着她的肩膀,她一抬头看见我坐在炕上就不闹了。她说:“我尿尿!”老头儿说:“你不要乱碰,我给你拿尿盆儿!”那女子答应着,两眼傻呆呆地看着我,披头散发。我觉得事情尚未平息,可能是觉得我在这儿不好发作,老头儿就把我送到二大娘家去睡了。以后的情景我就不知道了。
从此以后,这女人一直有病。有一次,老头和他二嫂(就是把我送去的二大娘)说起那天半夜发生的事时,老头儿说:“头碰到地上咯嘣、咯嘣地响,第二天早上看也没疙瘩,也没有红肿,好像什么也没有碰过。当时房上咔嚓咔嚓响,她说她的神来了,她在屋里乱闹,就把凤菊吵醒了,我把凤菊送您这儿来,怕她受惊。”
老头儿很发愁,和他二嫂商量怎样能使她的病好起来。后来,他们把我和那女人一起送到他大姐家住着,说是离开这家出去散散心,叫大姐照看并开导开导她。听村里人风言风语说,有几个坏人想算计她。她病得越来越厉害,起不来床,老头儿把她接走了,仍把我留在他大姐家。
他大姐家有个孙女比我大两三岁,知道我是客人,什么事都让着我,和我一起玩。等我再回到他家时,那女人被装进棺材了,最后人是什么样子也没看到。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她很可怜,年纪轻轻的,眉眼长得也挺漂亮,年仅二十多岁,让她跟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生活,多么不公平啊!她心里一直很苦闷。亲戚们本想要我来给她做伴、解闷,拴住她的心,使她不再想千里之外的家,谁知我很倔,从来也不叫他们,也不和他们说话。老头儿的大嫂常来跟她谈天,想让她高兴。她人很巧,会做衣裳,还会自己砍树根做鞋楦子。我想这女子很不甘心跟这老头儿种菜、浇园、看畦,所以就装神弄鬼的给人看病、驱鬼,借故发泄自己的愤怒。她常说冤鬼、冤神附体了,就大哭、大闹一场,以此来排解心中的郁闷,平时却跟好人一样。
她去世了,我对他家没用了,没有人拿我当人看,也没人管我了。老头儿一天到晚茶不思、饭不想,唉声叹气地发愁,总和他二嫂说“心里结了个疙瘩”。大家都劝他:“人死不能还阳,想开点。”我吃、穿都无人过问,一天到晚听他们唠叨个不停。他也不做饭,我几天不吃饭也没人知道。不知为什么,我发起疟疾来,冷起来浑身发颤,烧起来热得没法活,渴了自己爬到水缸边喝凉水,又想家,但不知怎么能回家,心里难过极了,有苦也无处诉。
妈妈为了我能活命,不得不狠心将我送人,要不是为了活命,她怎么舍得把自己的亲骨肉送人。况且妈妈很喜欢我,觉得我比哥哥姐姐都聪明。送走我后,她白天强打精神做活儿,晚上常和姐姐念叨我,暗暗掉泪。时间长了,不知养母对我可好,借到吴村赶集来看我,又不敢直接来,先到她表姐家问问情况,我表姨才赶紧告诉妈:“吴家的女人死了,你赶快看看孩子怎么样了。”妈妈才来接我回家,二月二日去他家,五月初我就回到了自己家。
我见到妈就放声大哭,由于病饿交加,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只剩一口气了。我生怕妈不带我走,抓住妈妈哭得喘不上气来,直到听妈妈说:“跟我回家,不用哭了!”我才慢慢地不喘了,心里很高兴,终于可以回家了。妈妈带我回家后,疟疾病不断发作,又无钱买药,后来打听到一个偏方:用一个铜子买了绿豆大小的一块铊僧(做砒霜剩下的底子,比砒霜毒性小点),把它放在挖去枣核的红枣里,合上后埋在灶火膛里烤糊,碾成粉状用水冲着喝了,谁知道吃完果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