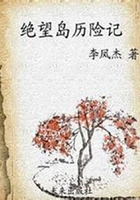冬天到了,地里已没什么活可干。春秋夏是活催人的季节,而冬天则是人找活干的时候。不想闲着,好办,可以搞农田基本建设,铲高垫低,修渠补埝;可以搞点副业,做豆腐漏粉条,烧砖瓦织苇萡编炕席,只要想干,活多的是。这些活有个特点,就是可干可不干,可急可缓。人们干干停停,停停干干,聊着天,逗着乐,优哉游哉,这是农村最自在的时节。心闲长头发,手闲长指甲,狗闲乱叫唤,人闲生事端。有好事者看三队的白生金日子过得舒坦,就嫉妒上了。妒生恨,恨生恶,一发而不可收,非要打打他的主意不可。他们拉白旦当贫协代表,和他们一起整白生金的材料,说白生金是漏划富农,要把他从上中农的档档提拔到富农的阶级队伍里。白旦不知就里,以为自己当了官,便高高兴兴地去参加专案组的工作。他一进专案组,正好赶上他们给白生金罗织罪孽。贫协的白主席,也是专案组组长,打着节拍,念着顺口溜,征求大家的意见:
白生金,不是人,
心肠要比毒蛇狠。
土地占了几十亩,
骡马牛羊一大群。
吃了白的喝辣的,
穿了金的戴银的。
高墙大院深又深,
就像一口大血盆。
白生金,日你妈,
你把百姓给的扎。
长工两头不见天,
短工一个要顶俩。
干起活来鬼吹火,
吃起饭来耍麻达。
辣子无油开水和,
稀水米汤黑面馍。
奉劝乡亲擦亮眼,
饿死不给他扛活。
念完顺口溜,组长问白旦:“你看说得对不对?你爸给白生金家干过短工,他给你说过没有,当年是不是这个样子?”
白旦先是摇摇头,忽觉不妥,又点点头。组长说:“看,怎么样,白旦他爸就是证人,他还能赖掉,这回这富农成分给他划定了。”
“白旦他爸早死了,算什么证人?”有人当场提出不同意见。
组长说:“咋不算?他爸虽然死了,可把话留给了娃,贫农的后代还能胡说?”
白旦说:“我还没说话哩么,啥胡说不胡说,不沾边么。”
“对对对,你还没开口哩。你这就说,你爸给你是咋说的?”组长这才想起,应该从白旦嘴里抠出些证据来。
白旦觉得这帮人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日闲杆杆哩。人家早都把地交了,现在跟大家一样过苦日子,还整人家干啥,太不厚道了。有工夫想想自己的日子咋过吧,何必拿别人开涮。整了人家,自己就好过了?鬼也不信。不利己又何必整人呢,白旦觉得自己上当了,不该当这个贫协代表,不该卷到这个是非里来。可是他不能明说,省得给人抓了典型。现在就是这样,敏感得很,一定要左左左,就是左到牛屁眼里,也没人敢说你个不字。谁敢说句真话,谁敢客观一点,那你准触霉头,轻者挨批,重者查你三代。听说有个左撇子举着左手呼口号,竟被抓了现行,说他想打倒左派,挨了批,游了街。白旦不傻,胆子再大,脾气再坏,也不要在这方面找霉头。就是有意见,也不能明说。他突然谨慎起来,想了想,截至目前,他只摇了一次头,点了一次头,一句话也没说,没什么辫子给人抓的。可是组长不放过他,非要他说点什么不可。他想了想,就说:“行,我揭发两件事,是我爸告诉我的。”
“看看,到底是贫农后代,阶级觉悟高,斗争最勇敢,革命最积极,就是好么。你说,大胆揭发。”
白旦说:“豁出去了,揭就揭。旧社会,白喜亮和白云天都给白生金家打短工。有一回,两个人吵了起来。白喜亮个子低,仰着脸骂;白云天个子高低着头骂。白云天看着白喜亮骂道‘日你妈’;白喜亮朝着天还道‘日你妈’。白生金看到了,小声说:‘等吧(男子生殖器·方言)高一点点,还要日天哩;你看他,支桌子,摞板凳,最多只能日眼睛,还想日天哩,够得着么。’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到了白喜亮耳朵里。白喜亮不答应,说这话比白云天骂他的话还难听,就去找白生金闹事。白生金哈哈一笑说:‘他们懂个啥,我是夸你哩么,你咋就不识个好歹哩。’白喜亮问:‘啥?夸我哩?那咋叫夸嘛?’白生金说:‘咋不叫夸?你听啊,我说鼓上蚤一点脚,还要上天哩。砸桌子,抡板凳,叫你断腿瞎眼睛。你知道鼓上蚤是谁不知道?’白喜亮说不知道。白生金说:‘梁山好汉,地煞星,那就是个小个子,身手好生了得,是个英雄人物哩。我的意思是,白云天别看你个子大,你不一定是白喜亮的对手。你说,我这不是夸你哩么。’白喜亮一听高兴了,不知道自己在东家眼里还是个英雄,有这么高的地位,于是高高兴兴地走了。”
组长泄了气:“你倒是说了个啥,这跟剥削人欺压百姓有何相干?”
白旦说:“咋不相干?鼓上蚤是什么人?贼么。他把贫下中农比成了贼,这不是恶毒攻击革命群众是什么。”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赶快记下。这算一桩,还有呢?”
“还有一件:咱们南边四下村,过去村子穷,光棍多。有一天,我爸陪白生金去四下村办事。白生金问我爸,你知道四下村为啥穷,为啥光棍多不?我爸说不知道。白生金说,主要是人懒。你看他们写村名字都偷懒,本来是四夏村,可是人太懒,写着写着就写成四下了,要往下走。下就下呗,好好写也行。可是还不知足,那个‘下’字都懒得写上边的那一横,而是用‘四’字下边的横代替,两个字放在一块像‘四八’。懒不说,还咒自己死吧,能不穷吗?你再看,还是这俩字,上边的四字大得像个簸箕虫(土鳖),下边那个八字,小得像两个虱子。簸箕虫日虱子,扣着弄哩,还一下弄两个,谁敢把女子嫁给他。”
说到这里,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收都收不住:“这狗日的生金,真是个蔫蔫怪,他咋能想得出来?”
组长也笑得前仰后合,不过收得要快些。笑完后他问:“白旦,你都把人逗死了,你说这有啥用吗?”
白旦一本正经地说:“咋没用?你说这是不是宣传封建迷信,迷惑贫下中农哩?说你受穷不是因为他剥削,而是因为你自己太懒造成的。咱贫下中农懒吗?这不是恶毒攻击是什么?”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赶快记下,这又是一桩。”组长很是高兴,想不到今天的收获如此之多。一高兴,就给大家提前放了工。
下了工,白旦回家路过五保老人田会会门前,就拐了进去。他把顺口溜背给田会会听,老人一听就笑了:“这里头没啥干货么,就靠这能给人划成分?胡闹哩么。”
白旦问:“你不是给生金家干过长工吗,你说说生金这人咋样。”
“其实生金人不错。我干长工,不是人家雇的我,是我找上门要给人家干的。你知道,叔不是个健全人,连个家都没有,一个人过日子艰难得很。我就去找生金他爸求情,想住在他家给他帮工。说是我帮他,其实也是人家帮我呀!生金他爸不拿事,就到生金跟前给我说情,生金就把我收下了。从此以后,我就算有个家了,能吃口热乎饭,能穿上干净衣服,能有活干。其实人家可以不雇人,生金一身的好本事,除了农忙时节要雇人帮忙外,平时生金一个人就能把活干完。”
“哦,原来如此。那吃黑馍,吃水和辣子是咋回事?”
“哈哈哈,胡说哩。你知道吗?咱农村人磨面时,都要收些二三遍的细白面擀面条包饺子用。收了细面,后头的面自然就黑了,谁家不是这样?生金自己吃的也是黑馍。光说人家的馍黑,你咋不说人家给你吃的油泼面又白又筋又光呢?没良心。再说那辣子,只用水和过一次。为啥用水和呢?这是有原因的。那一天,生金老婆把油用完了,打开一罐新油,发现里边钻了不少蚂蚁,吃不成了。没办法,马上要开饭了,就赶紧用开水烫了些辣子。给大家吃的时候,生金还专门做了解释,大家当时都觉得没啥。几十年过去了,又把这事提出来,没事找事哩么。”
“照你这么说,他们这样整也确实无聊。我就不明白,白主席为啥要这么上劲地整人家?”
田会会诡笑着不说话,似有难言之隐。白旦试探着问:“是不是有啥秘密,不便说?”田会会还是笑,不想说。白旦说:“给我透透,不要紧,我烂到肚子里不给人说,你还信不过我?再者说,你要是不说,等你走了,不就成了千古之谜了吗?多可惜。”
田会会指着白旦的眼睛,说:“你保证不对外说?”
白旦点点头:“绝对不说。”
“好,我告诉你。”田会会讲述了当年的一件秘事:
“有一年夏收,白生金雇了些短工收麦子,白主席的父亲就是短工中的一个。有一天,大家在地里割麦子,到了饭口,白生金就让白主席的父亲回去把饭挑到地里。白主席的父亲四十来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他回到生金家,生金老婆正在锅台上做饭。他在人家身子后头色眯眯地看着人家,看着看着就忍不住了,扑上去把人家抱住,又是掀衣服,又是摸奶子,还把人家掀倒在地,压在人家身上亲人家。生金老婆也是有点力气的女人,一把把他推开,拿起菜刀要砍他,把他吓跑了。他跑后就没敢再回去干活,饭还是我送到地里的。”
“哦,原来是这档子事。后来呢?”
“后来生金老婆把这事给生金说了,生金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就叫了两个亲戚把白主席他爸打了一顿。你想,这是丢人的事,生金就警告白主席他爸,不准对任何人说起此事,要是他乱说,就撕了他的嘴。所以,到现在都没有几个人知道。白旦,这么多年,我给谁都没说过,现在也只给你一个人说了,你可不能到处乱说啊。”
“放你一百个心!我乱说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嘛,我是瓜子?”
“不说就好。这回你明白了吧,白主席整人家,是公报私仇,给他爸出气哩。还有,生金会过,日子总比旁人过得好。就有人眼红了,盼着他家出点什么事,心里就平衡了。这人呀,真是个怪物,人家好过了他不高兴,总要说点什么;人家过烂了他笑话,也要说点什么。各过各的日子,人家过好过烂关你屁事。说长道短的,你的日子就好过了?”
白旦说:“就是的,这些人就是好事,心眼也太多了,简简单单的多好,非要生出些事端来,真他妈不是东西。他给他爸出气,还叫这伙人帮他,也太精了。这号事我干不来,明儿不去了。”
“不去?那你咋跟人家说呢?”
“这有啥难的,就说没能力,只会干活养牲口,干不了那动脑子的细活。”
“我看可以。嘿嘿,看不出你小子还蛮有心眼的。”
白旦回到家里给秋香说了白主席整人的事,秋香也觉得有些过分,赞成他退出专案组的打算。秋香说:“咱不干那缺德事,回来吧,能干的活多着呢。人家要问,就说咱是老粗,干不了细活,挣那工分心里愧得慌。还有,现在是冬天,还能抽出空干点正经事。等一开春,想干也没时间干。咱们家的粮食可是挨不到麦收时节的,就是有救济粮发下来,也还有一两个月的缺口。现在粮食还不算紧张,市面上可能便宜些,咱们得提早下手,别等青黄不接时再买,那价就大了。我想让你到北山跑一趟,拿我织的格子布换些玉米回来。我打听了,北山人喜欢咱们这里的家织土布,舍得粮食。你跑两趟,一趟换个七八十斤,省着吃,两趟就够了。你看咋样?”秋香说得有板有眼,白旦只有点头应承,哪有不同意的道理。
秋香又说:“你去问问白平哥,听说他早年在北山要过饭,他一定熟悉那里的情况。问问他,去北山路怎么走,该注意啥,有没有熟人。要知山中事,须问打樵人嘛。”
“对对对,得问问,我这就去。”
白旦来到白平家问事。白平说:“那里粮食确实便宜,只是卡得严,不让出山。有粮食可以交给国家,由国家调剂,不准私下买卖。可是,谁不想把粮卖个好价钱?缺粮的人多了,国家救济得过来?不可能。于是,黑市交易就泛滥起来,想管也管不住。粮食倒是好买,只是路上有卡子,运出来不容易。好多人运粮食,半道上就被没收了。为了安全起见,有些人就想了其他法子:农闲时,干脆拖家带口到北山吃粮,不用往回运了。在那里,可以给人家帮工,可以找活干。白吃饭不说,还能挣俩零花钱。你不行,娃们家正上学哩,去不了。”
“卡得那么严?有没有闯关闯过来的?”
“闯过来的多了,卡得再严也有漏洞,他们还有打瞌睡的时候。卡住谁谁倒霉,卡不住是你走运呗。度饥荒要紧,你去试试吧,放机灵点,卡住的一定是你?我看不见得。”
白平说得对,度饥荒要紧。在城里买粮食,也有被没收的可能。怕没收,就不买了吗?还是去吧,但愿自己是那幸运的一个。他说:“我去。把你那辆自行车拾掇拾掇,借我用几天,没问题吧?”
“这有啥说的。我这车太实惠了,德国造,质量好,不耍麻达;样式老,看上去就是一堆废铁,给贼贼都不要。你只管骑着去,安全得很,没人打你的主意。”
两人说话间,贫协白主席找上门来:“白旦,到处找你,你钻到这儿干啥,咋不到队部上班去?走走走,大家都等着你呢。”
白旦说:“我跟田仓说了,我当不了贫协代表,让他另选人干,我不干了。你去找他吧,说不定新人都选下了。”
“啥干得了干不了,你不是干得挺好么,为啥不干了?这工分挣着多轻松,动动脑动动嘴,风不吹日不晒,到哪儿找这种好事呀?你别瓜了,换啥换,走走走,我给田仓说,不换人了。”说着,就去拉白旦。
白旦是真心不想干的,他往后躲着不走,说:“我真干不了,享不了这份福,待在那儿身上难受,你就饶了我吧。”
白平说话了:“白主席,田仓昨天就把人换了,你再让白旦去怕不合适。你让人家的脸往哪儿搁?你还是找田仓问问看换的谁,换谁谁去不就行了。”
“真换了?”
“换了,就是不知道换的谁。”
“那我去问问。白旦,你等着后悔吧。”白主席撂下话,颠儿颠儿地走了。
白主席一走,白平就说:“其实生金是个嫽(好)人,不知道为啥跟人家过不去。定成分是有硬杠杠的,想咋定就咋定,那不乱套了嘛。”
为啥要整,白旦是知道的,但有言在先,他是不能乱说的。于是说:“瞎整呗,现在就是这形势,不闹出些事端来,咋能向上头表明他们立场坚定、警惕性高嘛。”
白平摇摇头,显得很无奈,说:“唉,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让人家折腾吧,看能折腾出白馍来,还是能折腾出银子来。不说人家了,你回去准备准备吧。我把车子拾掇拾掇,你啥时走,啥时来推。到时候我把路线给你画出来,你到山里找我那几个熟人,让他们帮你办,免得吃亏。”
白旦谢过白平就回了家,他让秋香把要带的土布准备好,一两天内就可以上路了。秋香扯了两丈布,叠好,用包袱包了,说:“两丈足够了,换个百十来斤玉米不成问题。准备哪天动身你说一声,我给你烙几张白面饼,带到路上吃,能撑到山里就行。山里有的是吃的,不用把石头往山里背。回来的时候把干粮带足,检查站不至于连干粮都没收吧?”
白旦脸一沉,道:“看你说啥哩,我还没动身呢,就没收没收的,多不吉利。我看还是别去了,省得给你这乌鸦嘴说中了,白跑一趟不说,还把布也折进去了。”
“呸呸呸,是我胡说哩,打嘴。”秋香边说边拍着自己的嘴,打得“啪啪”响。白旦拉住她的手,笑着说:“哎呀,开个玩笑么,你就当真了。你要真能说那么准的话,就给咱说一句捡狗头金的话,那咱不就发财了?”
秋香也觉得没什么,笑笑了事。
其实很简单,没什么好准备的,就是骑上自行车,到百十里外的北山换点粮食而已。第二天白旦就出发了。本来应该一大早动身,晚上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可白旦偏等到中午才走。白旦有自己的打算:北山属另一个县管辖,两县以沟底的河流为界,从沟底到沟上,两边都有十里长的坡路。北山县的检查站就设在沟底河上的桥边。白旦想在沟底住一夜,摸摸检查站的活动规律,看看能不能找到冲关的最佳时机。白旦算过,中午动身,不慌不忙,晚上刚好到沟底,所以等到中午时分才上了路。
太阳落山时,白旦就到了沟底。这里很热闹,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很像一个小镇子。他从一家烧饼铺子里讨了碗开水,蹲在一个避风处,拿出秋香给他烙的白面饼嚼了起来。吃饱喝足,天已擦黑。他寻了孔废弃土窑,发现这里可以直接看见检查站,便于观察动静,于是决定在这里过夜。他拾了些干草铺在地上,困了可以躺下打个盹。又拾了些干柴火,半夜冷时可以烤烤火。很快,夜深了,零散的店铺都打了烊,只有车马店那边还有灯火,时不时传来说话声和牲口的叫声。检查站的门头上挂着一盏马灯,亮亮的,把站前的马路照得通明,却不见有人出入。他们也是人,也要睡觉,也怕冷。这不正是冲关的好时机吗?好,明天晚上的这个时候,就是我白旦通关的时候。只要闯过检查站门口,顺利骑上前边那个慢坡就算成功了。再往前就是一段下坡路,他们就是想追也追不上,也追不成了,因为那已出了县界,不归他们管了。
他正得意地想着,忽见三个人骑着自行车飞一般地从眼前闪过,车后驮着百十来斤粮食。三个人冲过检查站,冲上慢坡,快到坡顶时,用力蹬骑了几下就上到了坡塄上,一转眼就没了影,他们闯关成功了。原来这么简单,看来人们说得那么邪乎,不过是传说罢了。突然又有一人驮着粮食冲了过来,车速极快。不好,前轮压着什么了,车子直打晃晃。车速太快,不好控制,总是摇摇摆摆扳不过来,三拐两拐,“哐”的一声就撞开了检查站的门,冲了进去。里边的人喊了起来:“干什么的!”紧接着,就听双方嚷嚷起来。嚷嚷了半天,就见这倒霉蛋蔫耷耷地推着自行车出来了,车后座上的粮食给人家没收了去。
这一切,白旦看得心惊肉跳。那人撞门时,他竟闭了眼不敢看,心里骂道:“这挨千刀的,自己主动送粮上门,人家不想没收也得没收了。”待到这人出来,白旦却又同情起来。他赶过去把这人叫到土窑里,两人围着火堆聊了起来。通过聊天,白旦了解到,这人叫田兵,是个运粮闯关的老油条了,每年冬天都要闯他个二三十回。田兵说,给生产队干活,一冬天也就挣九百个工分,按每个工分一分五的收入计算,也就值个十来块钱。运一次粮少则挣个五六元,多则七八元。辛苦点三天可以运一次,吃不了苦,就五天运一次。一个冬天下来,能挣个二百来元,一年的花销就有了。
白旦问:“给人抓住了怎么办?就像这一回,这不全赔了?”
田兵得意地说:“咋能让他抓住?抓不住几回。你看见了,这回是我自己找上门的,要不然,还不是顺利过关。没收一次,跑三趟就赚回来了,总的算下来还是值得干的。”
“把粮运回去咋处理呢?老卖粮食,还不给生产队抓了现行?”
“你看你老实的,我能在自己家叫卖吗?县上的黑市上到处都有人收购,粮一到,就有人包圆儿了。咱把钱一拿,就开始跑下一趟了。”
“哦,是这么回事。我老婆上回在黑市上买了一百多斤玉米,原来这粮食就是这么来的?哎呀,这也太不容易了。”
“如今干啥容易?挣的都是血汗钱,吃的都是自己的肉。”
白旦又问:“明天准备咋办,回家?”
“咋能空着手回去,再进山弄粮去。现在在半道上,回去多可惜,这趟不能白跑了。干脆咱们一起走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白旦早有这个想法,只是没好意思说出来。田兵一说,他自然高兴:“好好好,我正这么想着呢。我是头一回,你路熟人熟,跟着你心里就有底了。”白旦把白平给他画的路线图拿出来给田兵看,又说了自己要找的熟人。田兵说他就是活地图,用不着。白平介绍的熟人几年前就死了。卖粮点多的是,价钱有行情,都差不多,用不着找熟人。
天亮了,两个人结伴踏上了进山的路。中午时分,就到了一处卖粮点。山高皇帝远,这里好像没有山外管得严,卖粮点甚至挂了幌子,毫无藏掖躲闪之意。田兵好像是到了自己的家里一般,又吃又喝又吆喝的,好像他是当家的。没多大工夫,田兵就买好了粮。主人的孩子帮他把粮袋捆到了车后座上。白旦是用布换粮食,办起来比较麻烦。首先是要给布作价,作了价才可算出能换多少粮食。粮食价是有行市的,布价就没准了。白旦和对方讨价还价,始终定不下来。田兵把主人叫到一边小声说了几句,主人回来就笑呵呵地说:“好了好了,看在老田的份儿上,就按你说的办,一尺八毛,两丈给你换一百斤玉米,这回满意了吧?好好谢谢老田吧。”
白旦笑了,谢过老田后又说:“袋子里少装四斤吧,给我换成四斤干粮,我和老田路上吃。”
主人点点头说:“知恩知报,人不错。”又对儿子说:“娃儿,按他说的办。”
按白旦的意思,主人的儿子装了粮,又帮白旦把粮袋捆在了车子上。
田兵说:“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咱们就走,半夜就可赶到检查站。他们都睡了,轻轻一冲就过去了。”
白旦说:“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
两人吃过饭,和主人聊了一会儿就出发了。一个时辰不到,就到了沟沿上,下来就是十里长坡。这段路好走,下坡多,上坡少,省力气,速度快。两人有说有笑,不知不觉就走完了大半路程。前面横着一道梁,先上后下,一上一下就是五里路,翻过这道梁,就是沟底了。天已黑了下来,两人停了车,钻进路旁的一个土壕里避风休息。田兵点了纸烟抽,又递一支给白旦。白旦说抽不惯纸烟,随手装了锅旱烟抽了。
白旦问:“老田,你常一个人走夜路,害怕不害怕?”
田兵想了想说:“有怕的,有不怕的。什么妖魔鬼怪,狼虫虎豹,一点都不怕,就怕两种声音:一个是‘打劫,把东西留下,快滚。’这是土匪说的;一个是‘站住,你犯政策了,粮食没收。’这是干部说的。土匪劫道,只是听说,没遇到过。干部扣粮倒是常见,我自己也让扣过几次。”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人比野兽、比妖魔鬼怪厉害。人不怕鬼不怕野兽,人就怕人,对不对?”
“就是这意思。鬼是虚的,是人自己吓自己;狼虫虎豹虽厉害,但没心眼,好对付,其实它们是怕人的,不愿意跟人作对。只有人最可怕,不好对付,好起来像太阳,温暖得很,坏起来像蛇蝎,狠毒得没法说。”
“有道理,人整人不露声色,人吃人不吐骨头。”
休息了一阵子,田兵说:“走吧,该动身了。翻前边这道梁,是要费点力气的。翻过梁,就该闯关了,都不是轻松活。”
他在路旁的大树上折了两根树枝,自己留下一根,一根给了白旦。白旦问:“要棍子干啥?”田兵说:“拿着,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两人骑车到了梁下,下坡突然改上坡了。借着下坡的冲力,加上他们的奋力蹬骑,也没走出多远就骑不动了,白旦只好下车推着走。田兵也下了车,他把木棍的一头插进车把的钢管里,另一头就搭在了车后座的粮袋上。他来到车后,手扶木棍,半趴在粮袋上往前推,看上去是那么协调自然,没走几步就赶上了白旦。他对白旦说:“伙计,用棍子把住车头,在后头推,省劲。坡又长又陡,像你那么推能把人累死。”
白旦照着做了,果然轻松了许多。再轻松,也是推着重物爬山,没走多远,两人便是大汗淋漓。隆冬时节,寒风凛冽,身上虽冒着汗,裸露在外的手和脸还是觉得冷风刺骨。寒风从脖子、从裤脚嗖嗖地往里钻,冷风吹湿汗,冰凉冰凉的,人不由得打着激灵,甚是不适。寒风又卷带着黄土和沙粒,从脖颈,从裤管往里灌,更是让人感到异样的难受。白旦干脆把棉衣脱了,想着这样就可以不出汗,就可以少受一种罪了。田兵看见他这样便说:“出点汗不要紧,别脱衣服,受了风寒可不是闹着玩的。要不这样,咱们歇歇再走。弄点火,烤着火擦擦汗,把挨身子的衣服烤干了再走。反正天还早,半夜到凌晨五点以前,都是冲关的好时机,误不了事。”
两人在路旁的破土窑里歇了。田兵点了一堆柴火,干柴烈火,火苗蹿得老高。白旦脱光了上衣,又赶紧把棉衣穿上,把被汗水浸湿了的衬衣在火上烤。他不无感慨地说:“他妈的,这真不是人干的活!一回就把我跑得认了卯,饿死也不跑第二趟了。老田啊,我真佩服你呀,一个冬天能跑几十趟。你这一身苦比我大多了,你挣的可真是血汗钱呀!”
“唉,有什么办法,一大家子人要吃要喝,不这么干咋办呀!别的咱也不会,就是有一身的好苦力。有智吃智,没智吃力么。”
烤干了衣服,两人又上路了。推上坡梁已是半夜时分,下了梁就到了沟底。田兵停下不走了。白旦问:“咋不走了?”
田兵说:“先看看动静再说。”
白旦朝检查站那边瞭望,发现检查站外边有几个人走动,就问田兵:“那几个人是不是检查站的人?”
田兵说:“不知道,小心为妙,等没人的时候再过。”
就这样,他们又等了十多分钟。当确认确实没人的时候,田兵说:“走吧,可以过了。”又叮嘱白旦说:“放坡的时候一定要稳,不一定要多快。但是过检查站门前的时候,一定要快,用时越短越安全。过了检查站就该上坡了,要把吃奶的劲用上使劲蹬,最好能骑着过坡塄。只要一上坡,就万事大吉了。”
白旦不住地点头,心里却有些发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闯过这一关。田兵交代完毕,就率先骑上车放坡,白旦紧随其后。趁着下坡,两人朝着检查站方向冲了过去。快到检查站时,田兵突然加快了速度,虽说是在平路上行驶,可速度比放坡时还快。白旦不敢怠慢,紧蹬几下跟了上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检查站的门开了,里边走出来一个人。这人迷迷糊糊的,看见田兵白旦闯关,第一时间竟没有什么反应。白旦有些害怕,慌乱中放慢了车速。田兵急了,喊道:“快过,愣啥愣。”
这一喊,同时惊醒了检查站的迷糊人。那人下意识地喊道:“站住,不许跑。”随后就追了上来,边追边喊:“有人闯关,赶紧追呀。”
田兵到底是老手,闷着头只管蹬车,上坡的速度也没慢多少,利利索索地上了坡,逃脱了。白旦就不一样了,恐惧感让他卸去了一半力气,蹬到半坡,车速已降了不少。直行已经很费力气了,他只好走“之”字路,曲线行驶。后边的追兵越来越近,远处还有援军陆续赶来。白旦还在用力挣扎,快到坡顶时,车速降到了零,一歪一拐,连人带车倒在了地上。
检查站的人用电筒照照自行车,照照白旦,说:“你这老东西劲还挺大,差点让你给跑了。”其实白旦没多大年纪,还不到四十岁,只是不修边幅,胡子拉碴的,晚上看上去像个老头而已。白旦连人带车被带到了检查站,不用说,处理结果还是留下粮食走人。
谁也不会想到,白旦竟硬了起来,非要把粮食带走不可——粮留人不走,人走粮不留——跟检查人员较上劲了。检查人员说:“你违反国家统购统销政策,不抓你的现行就不错了,你还敢要粮食?”
白旦说:“这粮食就是我们一家五口的命,命都不保了,还怕你抓典型?你不给我粮,我就不走了,吃你们的,住你们的,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反正回去也得饿死,还不如留在你们这里寻条活路。”
检查人员气得冒烟了:“咋,你想耍死狗呀?”
白旦不紧不慢地说:“我倒是想耍活狗,可想活就得吃,你把粮食给我没收了,活狗耍不成了,只能耍死狗。随你怎么说,不给粮食不走人。”
田兵逃脱后,在前方不远处等白旦。左等等不来,右等等不来,天都大亮了,还不见白旦的面。他寻思,就是给人家抓住没收了粮食,人也早该回来了。他不敢往下想了。同路不舍伴,他要拐回去找找白旦。他把粮食寄存在一户人家,骑着车子原路返了回来。一路上看看这里,瞅瞅那里,又想找到白旦,又怕找到白旦。真的在路上找到了,那麻烦就大了,还不如让人家抓去扣粮好。一路寻来,就寻到了检查站。
白旦惊奇地问:“你怎么来了?赶紧走赶紧走。”白旦怕检查站把田兵当成他的同伙抓了,逼田兵把粮食交出来。
田兵不怕,捉奸捉双,抓贼抓赃,这道理他懂,现在他只身一人,谁也把他怎么不了。他让白旦跟自己一起走,可白旦拗上了,就是不走。没办法,他只好自己回去了。
就这么着,白旦耗上了。一连几天,跟检查站的人抢吃抢住,弄得人家毫无办法。白旦也不愿意这么做,他明白,再好的政策也不能做到让人人满意,可再坏的政策也不能让人活活饿死。他不相信这事没有通融的办法,他相信这事最终会得到妥善处理。他忘不了秋香坐在织布机里的样子:织一阵,哭一阵;累了,就趴在织机上打个瞌睡,醒了再织,再哭。他忘不了秋香晕倒在纺车前的情景。可怜啊!一想起这些,他就心疼,就伤心,就愧疚。这是用秋香的血汗换来的一点救命粮,能让它就这么没了吗?天理都不容啊!他就是豁出命,也要把失去的粮食夺回来。
白旦一走好几天回不来,秋香急了。她跑去问白平,白平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给她宽心。秋香后悔了,为什么非要到北山换粮呢?图那点便宜干啥,要是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得了,她把肠子都悔青了。正着急间,消息来了,公社打电话通知村上,让村上派人去沟底检查站领白旦。电话还说,白旦太不像话,赖在那儿不走,闹得人家检查站无法工作,要求领回后对其进行批评教育。白平得知消息后颇感意外,想不到白旦还是个人物,敢跟官家论短长。秋香也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双手合十,念念叨叨。只要人好好的,就算白家烧高香了。
村上派治保主任白栋和民兵连长白林一同前去领人。说好路费先由个人垫付,待把人领回后由白旦报销,因为这是为他的事发生的费用,自然应由他承担。白栋白林坐公交车赶往沟底,劝说白旦回家。
白旦说:“回去可以,但村上得给我把粮食要回来,否则免谈。”
白栋无奈,只好找检查站负责人交涉。他把白旦家的情况向人家做了介绍,想唤起人家的同情心,然后请求人家通融。
这负责人说,自己没有这个权力,粮食已上交了,自己帮不了什么忙。又说,没收了的东西想要回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还是走吧,别再纠缠了。我们不是没有办法治他,实在是看他可怜,不忍心。好好劝劝他,在这里闹没用的,赶紧走吧。
白栋白林只好再做白旦的工作,磨了半天牙,连劝带吓唬,终于说动了,白旦同意跟他们一起回去。这事到此就算解决了。
回到家里,白旦感到对不起秋香,向秋香道歉。
秋香用手封住他的嘴不让说:“快别说了,安安生生回来就好。都怪我贪图便宜,把你支了出去,我都后悔死了……”
白旦也伸手捂秋香的嘴,不让她说这些话。他自己伤心得都要哭了,只好绷着嘴往回憋,话都说不出来,两行热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几天来,白旦没睡过一个囫囵觉,累、困、惊、惧,忽冷忽热,弄得他筋疲力尽。到了家,精神一放松,忽然觉得身上像抽了筋似的,一下子就瘫软了,还有些发烧,身子沉得一步都挪不动。趁孩子们上学、秋香出去干活的清静之时,他美美地睡了一觉,从早上九点多一下睡到下午六点。要不是白林来找他,他可能会一直睡下去。
白林是为讨要路费来的。白栋觉得白旦的损失已经够大了,自己垫的那点钱不算什么,就不要了。白林不行,他不愿意给白旦垫钱,所以就来讨要。他向白旦说明来意,白旦一下就恼了:“不是我叫你们去的,我掏不着这钱。谁让你们去的,你就找谁要去。说实话,不是你们死乞白赖地叫我回来,我是不会回来的,说不定我已经把粮食要回来了。就是因为你们把我拽了回来,我才损失了那么多。不找你们赔就不错了,你反倒来找我要,真是岂有此理!”
白林愣了,想不到白旦会这么说话,太不讲理了。他说:“你讲不讲理?要不是你出事,我们能去?我们不去,你能回来?恐怕现在你早就让人家抓走关起来了。”
白旦毫不退让,说:“实话跟你说,我根本就没想回来。他想关只管关,关了也得管我饭吃,三天一洗澡,六天一会餐(注:农村有传说,说监狱里的生活就是这样),比在家里挨饿强多了。”
白林觉得白旦就是个搅屎棍子,不想跟他纠缠,就说:“废话少说,临走时队上就是这么交代的,回来后叫你报销路费。我只管要我的钱,你把钱给我,有意见找书记说去。”
一提队上,白旦就来气,他提高了嗓门说:“少跟我提队上,要不是队上,我还到不了这一步。他们要是把秋香母子接纳了,工分我也挣了,秋粮我也分了,年终分红我也领了,我还有必要上北山吗?都是队上把我害的。他不认我,我为啥要认他?他爱咋交代咋交代,关我屁事。”
白林也来了气,嗓门更大:“胡说八道,队上待你不薄,你不够吃怨不得别人,谁让你娶个黑女人(黑人黑户之意),养个带来子……”
“谁说我是带来子,我日你妈!”白林话音未落,丁五斤就冲了进来。他边冲边骂,冲到白林跟前就抡起拳头打起来。
秋香随后也冲了进来,质问道:“我怎么就是黑女人了,你给我说清楚?说不清就撕烂你这臭嘴。”说着就朝白林脸上抓去,三人缠斗在了一起。
秋香五斤原本不在家,可白林赶的这个点不对,正是学生放学、社员收工的时候。五斤放学回来,就听得屋里有人高声争吵。他来到屋门前偷听,想知道他们吵什么。秋香在外帮工也回来了,他们就一起听。当白林骂他们是黑女人带来子时,他们就冲进来了。
白林给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蒙了,防备不及,竟被这对母子所控制,只有招架之力,没有反制之策。他只顾抵挡,却不敢还手。他知道,对方是女人和孩子,一个大男人动手打女人孩子是不合适的,更何况自己大小还是个干部,就更不应该了。白旦在一旁窃笑,心里说:活该,看你还胡说不。他也知道白林不敢还手,所以,既不当帮手,也不去拉架,任由秋香母子撒野。秋香见白林并不还手,也就知趣地收了手,顺手又把儿子拉过一边。骂也骂了,打也打了,气也出了,秋香的心情也好了许多,她想,该收场了。可怎么收呢?她灵机一动,警告白林:“白林,告诉你,我们母子不是好欺负的。以后你再胡说,我跟你没完。”说完,拉着五斤去了另一个屋子。
白林钱没要上,反窝了一肚子气,挨了一顿打,心里实在是憋屈。他瞪着白旦,气吁吁地说不出话。白旦收了笑容,一本正经地说:“白林,你听哥给你说,这钱我真的出不着。你看是这样的,啊,检查站拿我没办法,就给公社打电话叫把我弄回来。弄回来干啥?还不是想让公社收拾我呗。公社让你们去领人,就是要收拾我么。你们合伙要治我,还叫我掏钱,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这是其一。队上说叫我报销,只给你们说了,却并没有给我这个要出钱的人说。有这样办事的吗?这是其二。第三,没经我同意,队上凭啥花我的钱?别忘了,你们出的是公差,不是给我办什么事。既然是出公差,凭啥叫我一个平头百姓报销?没有这个道理嘛,你说是不是?所以说你还是找他们吧,把我的话一字不落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还坚持让我出的话,就让他们来和我说。”
“哼。”白林没说话,气呼呼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