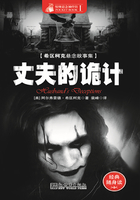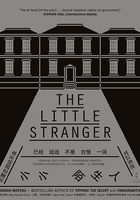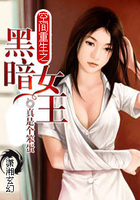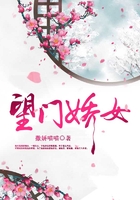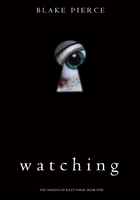由于要参加今天的评报,所以我把同城几家主要竞争媒体的当日报纸都找来看了一遍。每家报社每天都会有类似的会议,大家各有眼珠盯牢的几家媒体,如果别家有的新闻自家没有,叫漏稿,责任可大可小,严重的能让相关记者立马下岗;如果自家有别家没有,当然沾沾自喜一番,奖励嘛,一些铜钱而已,多数时候只有口头表扬。重罚轻奖,皆是如此。
所以开会前一小时,我把《新闻晨报》《青年报》《东方早报》《解放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扫了一遍,于是就看到了以上这则新闻。
这则新闻我们漏了。
不过在我看来,这算不上是重大新闻,也不是条线上必发的稿子,属于别家的独家新闻,是他们记者自己发现的稿,总不能不让别人有独家新闻吧?虽然领导们总是这样想,但小兵如我们,还是觉得,该给别人一条生路走……如果真有份什么好新闻都不漏的报纸,那别家报社就不是都不用活了?而且《新民晚报》是每日上午截稿,相比我们这些前一天晚上截稿的早报而言,本来就有先天优势,报道比他们晚一天是常有的事。
再说,评评报而已,有必要得罪平日在报社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吗?
所以,评报时轮到我说话,我只以一句:“今天《新民晚报》有篇关于历史遗迹的独家稿,我们要是以后能多些这样的发现性稿子,报纸会更好看。”轻轻掠过,丝毫没有加罪于谁的意思。
可是头头儿自有头头儿的想法。如果是新来的头头儿,想法就特别多。
评报会开完,蓝头让我留一下。
蓝头姓蓝,是新来的头儿,所以叫蓝头。职务是副总编。这是个分管业务的副总编,于是我们分管业务的变成了两个副总,职务重叠,谁都知道这其中涉及报社高层的权力纠纷。
蓝头初来乍到很卖力,磨刀霍霍,已经有许多不走运的记者编辑挨刀子了,被他叫住,让俺满心的不爽,不过我在报社也算是老记者,功名赫赫,听得见得多了,心一横,谁怕谁。
话是这样说,好像心还有点慌,一点点,真的只有一点点而已。
“想和你说晚报那篇独家稿的事。”蓝头满脸笑容地说。
我看着他点了点头,一副成竹在胸的老记派头,好像我是领导似的。
“别人有独家稿不怕,但我们得跟上,有时候,先把新闻做出来的,不见得是笑到最后的。”蓝头开始娓娓道出他的计划。
原来他想让我去做一个深入调查,把这两幢大楼的底细翻出来,扩大影响,力图通过媒体的影响力,最终把这两幢大楼保留下来。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同时也展现了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也展现了我们《晨星报》的力量”。有句话我知道他没有说出来:“这也展现了我蓝头的英明领导。”
“我虽然刚来不久,可你的报道我看了很多,你是《晨星报》的骨干,这个专题报道就交给你了。”他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
“没问题。”我拍胸脯保证,心里暗笑,看看,这蓝头还知道哪些人能动,哪些人不能动,哪些人要捧在手心里不是?
深入报道是件细活,我打了个电话,和居委会说好明天下午去采访,而明天上午,我打算去一次上海图书馆。如果那幢大楼真如《新民晚报》报道里说的那么有名,上海图书馆一定有它的资料。要想把大楼保下来,这类能证明其珍贵性的资料是不能缺少的。再说,引用一下资料,我的稿子也好写。
第二天一早九点,我就到了上海图书馆。我是那里的熟客,早就办了张特许阅览证,可以查阅那些不对外开放的文献资料,他们管宣传的几个人我都认识,最关键的是,几个古旧文献书籍的分理员我都熟。虽然他们的内部网络可以查书目,但许多时候没人指点还是有无从着手之感。
也巧,刚走进上海图书馆的底楼大堂,就看见分理员赵维穿堂而过。
我把他叫住,然后递了根“中华”过去。我不怎么抽,但好烟是一直带着的。
“算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不准抽烟,说吧,这次又要查什么?”赵维推开烟,很上路地说。
“呵呵,还是你了解我。”我笑着把烟收回去。
“没事你还会上这儿来?”
我把事情一说,赵维指了指VIP休息室,扔下一句“在那儿等着”就走了。
坐在沙发上等了大约十分钟光景,赵维拿着一本厚厚的硬面精装本过来。
《上海老建筑图册》。
“1987年出的书,里面老建筑用的基本都是从前的老照片,对建筑的介绍也相当详细。”赵维说着翻到其中的一页。
“看,这就是那四幢楼,当时日军轰炸后不久拍的,珍贵的照片,文字资料也挺多的,你慢慢看,要扫照片的话去办公室,反正那里你也熟,我还有事,不陪你了。”
“你忙你忙。”我嘴里说着,眼睛却紧紧盯在这页的照片上,一瞬间的惊诧,让我甚至忘记对正快步走出休息室的赵维应该有的礼貌。
我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张令人惊叹的照片。
那简直是一个奇迹,这张照片所呈现的,是近七十年前的一个奇迹。
我猜测着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是那场轰炸过后的一小时,还是一天、两天?不可能更长的时间了,因为照片中的画面上,四处是废墟和浓烟,见不到一个人。
当年日军轰炸过后,上海像这样一片废墟的地方很多,但在这张照片里,残屋碎瓦间,却突兀地耸立着四幢毫发未损的建筑。
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在高处,取的是远景。遥遥望去,四幢明显高出周围破烂平房的大楼,分外显眼。
在刹那间我甚至以为,当年日军轰炸机投下一颗颗重磅炸弹时,这片街区张开了只有在科幻小说中才听说过的能量防护罩,所以毫发无伤,否则,以周围建筑被炸损的严重程度,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这当然是个可笑的念头,真有保护罩的话,怎么四幢楼四周和之间的平房都塌了,就只留了这四幢楼在?可是,照片上所显示的状态,显然比保留下一片街区更为荒谬和不可思议。
我随手翻了翻前面几页,发现其他建筑取的都是近景,而且照片只占整页的一半左右,只有这张照片取的是远景,而且占了一整页。我翻到后一页,果然,后页上是四幅比较小的大楼近照,以及文字资料。想必当时的编者也觉得这张取远景的照片极为神奇,所以才给予特殊待遇。
我翻回前页,凝神仔细看这张照片,四幢大楼的排列很奇怪,每幢大楼都相隔了一段距离,最前面两幢,后面一幢,再后面一幢。
我总觉得这排列有问题,翻到后面的文字介绍,果然看到这一段。
“当时孙家四兄弟建造四幢大楼,以孙家长兄的大楼为中心,其他三幢大楼呈‘品’字形围在周围,每幢大楼之间的距离有五六百米。”
我翻回去一对照,果然是“品”字形。
不知不觉间,我的眉头已经皱了起来。当年这里并不是租界区,凭什么日本飞机周围炸了一圈愣留了这么大一片盲区?
不对,不是一片盲区,而是特意留了四个点没有炸!
见鬼了,以今天美国人的精确制导技术,都不能保证精确到这种程度,当年的日本鬼子,就算是有心不炸四幢楼,也不可能做得这样精确,这样漂亮啊。
文字介绍里也提到了这四幢楼得以保存的原因,和报道里基本一致:住在楼里的外国人打出了外国旗子,日本飞行员看到了,就没炸。
很多事情只要有人给出一个答案,大多数人就不会再去深究,眼前就是个例子。而作为要进行深度报道的记者,我当然不能延续这种思考的惰性。
只是不论我如何地思索,疑点越来越多,答案却想不出一个。
首先,那是什么国旗;其次,为什么那些外国人不待在租界里,到底有多少外国人,多少面旗,如果四幢楼里都有旗升出来,那么多外国人怎么会聚集到这里来?
即便以上都成立,可是在飞机上的飞行员竟能注意到下面的小旗?就算注意到了,在那样的战争状态下,日本人高昂甚而嗜血的战争意志下,还能因为这小小的外国旗子就放过这四幢建筑?
再者,也是最奇异的地方,即便日军飞行员决心放过这四幢楼,他们是怎么做到,把四幢楼周围的建筑都炸得稀烂,而四幢楼却分毫无损?难道说那时他们的飞行员,凭肉眼制导,就能把精确度控制在十米之内?
这些无解的问题在我脑海中盘旋了许久,我忽然失笑,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一个难以解释的奇迹,难道不是让这幢大楼保存下来的最好理由吗?只要稍加炒作,每一个看了报道的人都会认为,这四幢当年在日军的炸弹下神话般屹立不倒的大楼,在今日的和平年代里,难道连半数都保存不下来吗?四幢楼平凡无奇的外观,建造者有钱人孙氏四兄弟没有显赫的身份,这些都将不再成为问题。
复印,然后扫描,该干的都干完以后,我把书还了,愉快地走出上海图书馆。报道的主线我已经找到,文章该怎样布局已经心中有数,接下来只要找一些经历过当年战火的老居民,让他们叙说一些当年“神话”发生的细节,就大功告成了。据资料上介绍,孙氏四兄弟当年购下这四块地皮时,曾和地皮的原主达成协议,四幢楼建成后,拨出一些房间给原主居住,所以有一些老百姓在大楼建成后又搬回去住了。从这点上来看,虽然不知道孙氏兄弟是做什么买卖,此等行径倒颇有“红色资本家”之风。
下午,在裕通路85弄弄口,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残存的两幢大楼之一。在进入之前,我站在门口拍了张照,从新闻的角度讲,我需要一张今天的照片来和六十七年前的照片进行对比。
和之前在书上看到的那四幅大楼近景一样,如今站在了它面前,除了灰色的外墙让大楼显得老旧之外,没有什么区别。这实在是一幢极其普通的老楼,毫无建筑上的特色,和美学、艺术之类的扯不上边,唯一有点特别的,是这幢三层楼的层高很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五层楼。如果不是找到了那张老照片作为切入点,我实在找不出阻止它被拆除的理由。
“三层楼居委会”就在这幢大楼的一楼,周主任不在,接待我的是一位姓杨的副主任。他很热情地向我介绍大楼的情况,只是他所说的我大多已经了解。过了半个多小时,我才有机会打断他的话,问起目前住在楼里的老居民有多少。
“从那时候就开始住到现在的老人啊?”杨副主任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想了想,告诉我这样的老住户已经很少了,楼里的住户大多是“文革”前后入住的,以前的老住户搬的搬死的死,毕竟已经过了六十多年。
“这幢楼里是没有了,后面那幢楼里还住着两位。二楼的老张头,还有三楼的苏逸才苏老先生。都是八十开外的人了。”
我注意到杨副主任称呼中的细微变化,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却有着两种不同的称呼语气。看来他对那位老张头并不是很尊敬。
“苏老可真是个大善人哪,这些年人前人后做的好事不知有多少,听说他前前后后给希望工程捐了几十万,去年老李家的女婿得了肝癌,他就悄悄送了三万块呢。老张头可就不一样了,孤僻得很,不太愿意理人。”杨副主任开始向我介绍这两位老人。
“老张头,他叫……”我写稿子的时候可不能这么称呼老人家,与其当面问这位孤僻老人的名字,还不如现在就问个清楚明白。
“他叫张轻。不过老实说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有些奇怪,不管怎么说,那么多年都是一个人过的,没有娶妻生子,那么多年来楼里也没人见过他们的父母或亲戚,就那么一个人住在楼里。而且他们都不怎么谈过去的事儿,不知会不会对你说。”
八十多岁的单身贵族?我也不禁愣了一下,这可真是罕见,而这里还一下子就出了两个。不谈过去的事……我又想到了那张照片。
压下心中的疑惑,我起身向杨副主任告辞,还没接触前没什么好想的,说不定他们愿意向我这个记者说些什么。
“你往弄里多走一段才能见到那幢楼,离得挺远的。”杨副主任提醒我。
我忽然想起一事,问:“听说原来四幢楼是以一幢为中心呈‘品’字形排列,现在剩下的这两幢是哪两幢?”
“你现在要去的那幢三层楼,就是位于中心的那幢。这幢是外三幢中向着西北面的一幢。”
当我沿着裕通路85弄向里走的时候,我才明白刚才那句“挺远的”到底有多远。直到走到弄底,不,应该说是穿出这条弄堂,走到普济路的时候,我才看见另一幢“三层楼”。算一下距离上一幢有一两百米远。
我用手搓着额头,这情况还真有那么点奇怪。
从中心的一幢到边缘的那幢就要这么远,那边缘的三幢之间的距离,岂非要三百米甚至更多?算算位置,如果那两幢被拆去的“三层楼”还存在的话,一幢该在民立路或共和路上,一幢该在汉中路附近。
其实在看那张照片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这几幢楼之间的距离挺大的,现在实地走一走,才想到,这之间的距离,已经大到不合逻辑。
四兄弟建造四幢大楼,难道不该是紧贴着建在一起的吗,为什么隔那么远?要是四兄弟关系不好,又为什么要在同一片地域建房子,而且房子的式样还一模一样?真是横竖都说不通啊。
把额头来回搓了几遍,我走进了这幢“中心三层楼”。
这大楼从外到内都建造得十分平民,一楼的采光并不好,虽然是下午,但走进去,一楼的许多地方还是笼罩在阴影中。我顺着木质楼梯向二楼走去,脚下的木板发出“吱吱”的声响。
如果是我的话,一定把大楼造得小一些,只建两层,但却能造得比现在好许多,若是拿四幢楼的建造费合起来造一幢,就可以造得相当豪华,四兄弟住在一起也绰绰有余。
这样想的时候,我踏上了二楼。
老式的大楼是没有门牌号的,张轻住在哪里,只有靠问。
“请问张轻住在哪里?”我问一位从左边门里出来的老太。
“张轻啊。”老太操着宁波口音,皱着眉头,似乎想不起来。
“就是老张头。”
老太恍然大悟,随手指向右前方紧闭着的一扇朱色房门。
没有门铃,我敲响了房门。
“谁啊?”过了一会儿,门里传出低沉而混沌的声音。
门“吱”地开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矮小精干的老人,身子瘦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但一双眼睛却很有神,头发花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十多岁。
“您好,张老先生吧,我是《晨星报》的记者那多。”我拿出记者证。
张轻扫了眼我手上的记者证,问:“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您是从这幢楼建好就一直住到现在的老居民,最近这幢楼面临被拆的危险,《新民晚报》昨天已经做了一个报道,我们报纸也想跟着报道一下,希望能让有关部门改变主意,把这两幢仅存的‘三层楼’保存下来。”
“你去问居委会吧,我没什么好说的。”老人丝毫没有让我进去详谈的意思。
“可您是老住户,有些情况居委会不了解,只能来问您,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只半小时就好。”我微微弯着腰,脸上笑容可掬。
“你想了解什么?”老人低低地说,依然挡在门口,一动不动。
“我在上海图书馆里查到一张照片,就是1937年日军轰炸以后,四幢楼依然无损的照片,这简直是个奇迹,我完全无法想象那是怎么发生的,所以……”
老张头的眼珠忽然收缩了一下,他扫了我一眼,眼神在瞬间变得十分凌厉,让我的话不由得微微一顿。
“没什么好说的,我要睡午觉了。”
朱红色的门在我面前关上,我竟然连门都没能进去。
没奈何,只能上三楼去。
问到苏逸才的屋子,我摁响了门铃。
开门的是一位略显富态的老人,头发眉毛雪白,脸上的皱纹,特别是额上的皱纹深如刀刻。
“您好,我是《晨星报》记者那多,能耽误您点时间吗?”我改变了策略,先进去再说。
“哦,好的,请进。”老人微笑着把我引进屋子。
屋里的光线很好,这间屋子有十五六平方米,没有太多的家具摆设,最显眼的就是四面大书橱。靠窗的八仙桌上摊着一本墨迹未干的绢制手抄本,毛笔正搁在旁边的砚台上,看起来已经抄完了,正放在太阳底下晾干。我看了一眼,应该是佛经,最后一页上写着“圆通敬录”的落款。
我注意到手抄佛经的同时,苏逸才已经开始把佛经收起来,放入书橱。随着他的动作望去,我不由得一愣,那书橱里几乎放满了这样的手抄本。
“您向佛吧?”苏逸才招呼我在八仙桌前落座的时候,我问。
苏逸才笑了一下,问:“你刚才说,你是晨……”
对于这张新兴报纸,像苏逸才这样的老人不熟悉是很正常的,我忙复述了一遍,把记者证拿出来。苏逸才摇摇手示意我收回去,看来这位老人要比二楼那位好相处得多。
“您是在这幢大楼里居住时间最长的居民之一了,来这里是想向您了解一些大楼的掌故。毕竟这幢大楼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如果拆迁太可惜了,希望通过媒体的努力,可以把‘三层楼’保存下来。”
“说到居住时间最长,这里可不止我一个啊。看来你已经在二楼碰过壁了吧?”苏老呵呵笑道。
我也笑了:“我连张老的门都没进去。”
“其实老张的人挺不错的,就是性子怪了点儿。你想问些什么?”
我心中大定,看起来面前的这位老人是最好的采访对象,肯讲而废话好像又不多。希望他的记忆力好一些,能提供给我尽可能多的细节。
“1937年那次日军轰炸之后,‘三层楼’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闸北最高的建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三层楼’有了纪念价值。我在上海图书馆看见一张照片,是那场轰炸之后不久拍的,那场面太神奇了,周围一片废墟,而‘三层楼’却得以保全。我非常好奇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这番话说完之后,我心里却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苏逸才脸上的微笑已经消失了。
“太久远的事情了,我老了,已经记不太清楚啦。”
“据说是当时住在楼里的外国人打出了旗子……”我试图提醒他。
苏逸才的脸色一肃:“对不起,刚才是我打了诳语,并不是记不清楚。”
我心里一喜,看来他向佛之心还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可苏逸才接下来的话却让我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但是,那是一段我不愿意提起的回忆,所以,只能说一声抱歉啦。”
走出“中央三层楼”,我向居委会所在的“三层楼”走去。一无所获,却反倒激起了我把事情搞清楚的好奇心。
两次碰壁并不能堵住所有的路,对我这样一名老记者而言,还有许多寻找真相的办法。
老张头和苏逸才的奇特反应,使我开始觉得,六十七年前的那场轰炸,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不仅保下了这片建筑,更让当事人噤若寒蝉。
回想起来,围绕着“三层楼”的不正常现象已经很多了,除了在日军轰炸中幸存这最大的疑点之外,看起来孙氏四兄弟也有问题,为什么造了这四幢相隔这么远的大楼,为什么是“品”字形……
回到居委会,杨副主任忙了半天,终于找出了我要的资料。
虽然眼前“三层楼”里的两位老居民都对当年的事绝不透露,但我没有忘记,还有两幢我没去过的“三层楼”。
就是那两幢已经被拆除的“三层楼”。
那里面应该也住着一些见证过当年情况的老人吧。
居委会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虽然那两幢楼里的居民已经搬迁,却还是留下了他们的新住址和电话。
我又得到了三个名字。
钟书同,杨铁,傅惜娣。
没想到,竟然看到了钟书同的名字。从居委会提供的资料来看,我并没有搞错。就是他,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还听过他的关于三国历史的一次讲演,非常精彩。钟书同却不是因为拆迁才被迫搬的,他本来也是住在中间那幢三层楼里,七八年前买了新宅就搬出去住了。
这位九旬老人是中国历史学界当之无愧的泰山北斗,他对中国历代史都有研究,而其专业领域,也就是对两汉,尤其是从东汉后期到晋,即俗称的三国时期的研究,更是达到了令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惊叹的高度。他采用的许多研究方式在最初都被认为不合学术常规,但取得的丰硕成果使这些方式在今天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所采用。许多学者谈起他的时候,都以“他几乎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形容他对那段历史的惊人了解。
所以,很自然的我第一个就打电话给他。
可惜,我在电话里被告知钟老去巴黎参加一个有关东方历史文化的学术会议了,要过些时日才能回来。失望之余,我不由得惊叹,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位老人已经有九十二岁高龄了,竟还能乘长途飞机参加这样的学术会议。
无奈之下,只能联系另两位的采访。
说起来真是很惨,我们《晨星报》报社在外滩,而杨铁搬到了浦东世纪公园,傅惜娣则在莘庄。也就是说,从报社出发,不管到哪里我都得跑十几二十公里。
不过从好的方面讲,我跑那么远来采访你,你也不好意思直接把我轰出去吧,总得告诉我些什么。
世事总是那么的出人意料,对杨铁和傅惜娣的采访,除了路上的奔波不算,竟然非常顺利。
而两次极为顺利的采访,却为当年所发生的一切,蒙上了更阴霾厚重的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