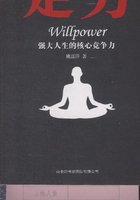皇家珀斯医院传染病分院比“黄金时代”大得多,弗兰克最初被送到那里进行康复治疗。1893年,天花病流行起来。在此期间,传染病分院开始运营。它最初是一家帐篷医院,设在珀斯郊区未开垦的灌木林带里。不祥的是,一个新的城市公墓很快就在它附近被设立起来。随着医院的发展,它的病房在那片灌木丛里伸展开来,出口与走廊相连,成了一座长楼。一旦用惯了轮椅,弗兰克就飕飕地在走廊里穿行。他拜访病房和厨房,追逐他喜欢的护士,和病人聊天儿。那些病人坐在走廊上,看着鸟儿飞进黑黢黢的树林,又飞出来。
在康复期间,他很想知道他为什么还活着。
绝大多数患脊髓灰质炎的病人都是单身的年轻人。他们侥幸活了下来,兴致很高,喜欢讲和疾病有关的黑色幽默笑话。弗兰克是他们中最小的,很快便承担了传递消息的任务,他还为轮椅篮球赛呐喊助威,帮助设计每天例行对护士搞的恶作剧。这个瘦弱、面色苍白的淘气鬼,在那么一小段时间里,成了他们的吉祥物、丘比特和小兄弟。哪里都有他。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让人对他生不起气来。他轻易就能明白某种东西,就像他体内有个开关被打开了。在后来的岁月里,他认为这是独特的“魔力”。
有时候,在斑驳的光影里,那种等待的感觉,以及无穷无尽停停走走的陌生人,会让他回想起小时候在维也纳的难民收容所里度过的时光。他已经获救了,但尚未回归现实生活。在关于生活的课程上,他已经远远落后了。他热爱自由。而且,他正像是已经获得了可以延缓长大进程的授权一样。
一天,他进一步深入探索医院的老旧部分,他设法通过了沉重的大门,进入了一个未知的病房。病房里有四个带孔的大盒子。它们排成一排,宛如船坞里的潜水艇,它们幽灵般的、有节奏的呼吸声弥漫在整个房间里。弗兰克在门口待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地。他清楚地明白这些声音来源于哪里、为了什么——它们是代替呼吸的铁肺,是困住你的“棺材”。除了死亡,这是脊髓灰质炎带来的最糟糕的东西。
他的额头上渗出了一滴汗。一种幽灵般的被监禁、无助的感觉刺穿了他的身体。他回到房间,回到他的床上,默默地躺了下去。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餐的盘子刚被收走,他发现自己马上又转着轮椅去了铁肺病房。
那个地方有一种特别庄严的平静气氛。弗兰克知道,那是早上洗刷、喂饭的混乱后的短暂平静。在房间的那一端,专门有一名护士在照看一个病人。一颗头颅从距门最近的盒子里伸出来,它脱离了枕头,就像一个盛放在盘子里的头颅。弗兰克瞥见了一个又高又白的额头、一只干净的大耳朵、一个罗马人般的鼻子和下巴。那侧脸明明就是一个成年男人,但却有着男孩般纤细的脖子,那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会长。
“你是要进来吗?”那个人平静地说,不过没有转头,“到这儿来,我们聊聊。”
弗兰克转着轮椅进去,停在他的旁边,“你是怎么看见我的?”
年轻男子把他的眼睛往上翻了翻。在他头的上方悬着一块长方形的镜子,那镜子倾斜了一定的角度,正对着走廊。
“往后稍退一下。好了。你多大了?”
“快13岁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
“随便看看。你在干什么?”
“写诗。”
沉默了一会儿,弗兰克说:“但是你没有……”
“我在脑子里写。”
“诗的题目是什么?”
“雪原。”
“雪?在澳大利亚?”
“实际上写的是天花板。”
“写天花板的诗?”弗兰克声音有点儿扭曲,默默吞下其他问题。
“我已经写好了头几行。”
“说来听听吧。”
诗人顿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
昨夜,
雪定然来过了,
这就是全部,
我现在能看到的。
“不押韵啊!”
“你为什么觉得必须押韵?”
“在学校里……”弗兰克的声音弱了下来。
诗人微微一笑,呼吸了一下。“亚述人冲下来像……狼在羊圈……他那穿紫袍的军队……铠甲金光闪闪。”
他吟诵得很快,呼吸间吞吐着奇妙的韵律,像一支儿歌。
“我们就是这么学的。”
“当然是这样……你叫什么名字?”
“弗兰克·戈尔德。”
“看啊,拜伦勋爵……在一百……四十年前……写的那首诗,你再也……不必……写那样的诗了。顺便说一下,名字真好……戈尔德,很……贴切。”
他的名字叫沙利文·贝克豪斯,弗兰克开始每天都去拜访他。正式的拜访时间很严格,每周两个下午,时间从正午到下午1:30。为了每天选择正确的时间进入那个病房,弗兰克用尽了他所有的技能——直觉、观察、经验——来进行合适的拜访。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发觉,护士是知道他来这里的,但她们默许了他的行为。或许是因为沙利文和她们说起过他,弗兰克猜。
他们的谈话常常是关于诗歌的。沙利文如同一个老师,弗兰克是学生,尽管弗兰克现在还没有一丝作诗的想法。实际上,当艾达和迈耶互相引用匈牙利语的诗歌时,弗兰克会感到很厌烦——尤其是艾达那略显神圣的声音。他觉得她对音乐和文学的尊崇是做作的、有意为之的,她将它们看得比其他任何事儿都重要。
“诗歌不需要夸张,”沙利文说,“也不是为了炫耀什么。它听起来就像是有个人在说话,它完全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美国的诗歌发生了重大变革,一场新的运动正在兴起。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人中汲取了经验——罗森博格、萨松、欧文。他们并未赞美战争,而是简单地、一点儿一点儿地谈论那些和他们一样的战士的经历。不论在哪里,他们都从未停下自己的笔触,哪怕是在地下掩体里、在船上、在火车上,甚至是在医院里。”
“一旦你习惯了你的处境,”他说,“你的想象力将再度得到自由。”
沙利文总是在写诗。那些诗是关于什么的呢?弗兰克很想搞清楚。
“朋友、航海、夏季的河流、在学校的最后一天……从前写的大多是这类怀旧的或是临时创作的诗。但如今似乎总是在写关于现在的诗,过去仿佛变得极其遥远。”
弗兰克的第一印象是对的。沙利文在学校里是个学生会长。沙利文在一所男校就读,他是学校赛艇队的队长,在一个名为“河流的首领”的比赛中,他们曾以微弱劣势败北。接下来,沙利文被确诊患上了脊髓灰质炎。他曾打算毕业去大学读英语专业,(学英语?我们所有人都会,还用学吗?弗兰克想。)航海是他的挚爱。他有三个兄弟,一个比他大,另外两个比他小,他们一起住在带着花园的房子里,那房子就在天鹅河的尽头。沙利文刚满18岁。
“我父亲打算等我出院了给我买一个助力器,这样我就能远行了,也可以再次游泳了。”
在此之后,弗兰克的脑海里形成了一幅图画,他把这幅图画与沙利文联系了起来。那是数年前他从火车上瞥见的一个场景。当时,他和他的父母准备去看望住在中部地区的匈牙利朋友。画面里有一座带着宽阔走廊的两层房屋、一块斜坡草地,柳树的叶子拂过橄榄绿的水面,小码头上小船晃动。穿短裤的孩子们跳上小船又跳下去。那就像旧式绘画中的一个场景。当然了,那不是沙利文的房子,沙利文的房子其实是在城市的另一边。但是,这个场景一直徘徊不去,宛如一支曲子或一阵芬芳。只要他看到或想到沙利文,他就会想起这个场景:水面上的太阳、摇晃的小船、蹦蹦跳跳的细腿孩子。
探望沙利文的还有沙利文的父亲。他利用闲暇时间进进出出,肯定没有谁会阻拦他。他个子很高,长腿,斑白的头发向后梳着,注重礼仪,穿着一套迈耶会欣赏的套装,有时候也穿一件有着金纽扣的蓝夹克。护士长有一次亲自把他领了进来。“你这个淘气鬼,走吧。”她微笑着对弗兰克说,露出了牙齿。弗兰克感觉被冒犯了,立即转着轮椅离开了。沙利文的父亲什么时候来,弗兰克就什么时候离开。当有人来探望某个病人时,其他人就离开,这是所有病人都会遵守的一种礼貌,护士长难道认为他不懂吗?
但是,贝克豪斯先生已经背对着护士长了,正朝着沙利文弯下腰。“你怎么样,老伙计?”他低声说。他一贯如此,眼里没有别人。
有一次,在沙利文的支持下,或许还受到了沙利文的鼓动,他转向弗兰克,而弗兰克正在忙着想他的告别词。“那么你就是楼上最小的病人了,”他和蔼可亲地笑着说。他的发音非常标准,几乎和英国人一样。“一个新澳大利亚人。”
“是的。”弗兰克说。
“弗兰克·戈尔德。你来自哪儿啊?”
“匈牙利。”
“哦。”贝克豪斯先生点了点头。弗兰克感受到了这个男人的冷淡目光。
“你什么时候来的澳大利亚?”他微微一笑,眨巴着眼睛,尽量不去看沙利文。
“在1947年。”
“喜欢珀斯这个地方吗?”
虽然似乎有必要给沙利文的父亲说实话,但弗兰克还没想好怎样概括他的经历。
“喜欢。”在这位父亲痛苦而绝望的烈焰的炙烤下,弗兰克的魔力就像清晨的露珠一样消散了,他没办法说实话。沙利文父亲的内心似乎一直在说:为什么我的儿子要这样?为什么我的儿子不能坐在那里?
“好孩子!”他又把脸转向沙利文了。沙利文总是有一个笑话或病房生活的轶事讲给他的父亲听。
弗兰克明白了沙利文背负的巨大责任。我干吗要拒绝它呢?他一边想,一边转着轮椅离开了。他知道,他父母把他失去的双腿当成他们又一个不得不承受的不幸。我拒绝成为他们唯一的光,我想成为我自己活着的理由,弗兰克想。虽然迈耶每个星期来一次传染病分院,有时候艾达也是如此,但他宁可他们永远也不来探望。他现在已经和沙利文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魔法的世界。
有一次,当他给艾达提起沙利文的名字时,她皱起了眉头。“贝克豪斯?那是个德国名字吧?”
“我不知道!”他不耐烦地摇摇头,“他是个澳大利亚人。”
“也许是个瑞典名字,”艾达若有所思地说,“你怎么拼它?”
“‘apposite’(适当的)是什么意思?”弗兰克问她,想换个话题。
“它的意思是……完全不同……在另一边……你懂的。”
“不是opposite,是apposite。”他再次摇摇头,眼睛看向了别处。
有传言说,沙利文的父亲是州长助理,是坐着配有专门司机的车来探视的。弗兰克开始在走廊上等,等着观看贝克豪斯先生离开病房。贝克豪斯先生低着头,耸着肩,夹克飞扬,迈着从容的大步走向车道的尽头,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有一辆黑色的大哈博车停在那里。
沙利文说,只有当他孤单时,他才能过上他真正的生活。
“因为你是个诗人?”弗兰克问道。
“当然不是!每个人的生活不都是如此吗?”沙利文说,“看看艾迪。”
沙利文这样称呼照顾他的护士,这个名字是他偷偷起的。
“她的面庞如此文雅、开朗,你注意到了吗?她总是在为别人考虑。”弗兰克注视着那个平淡无奇、满脸雀斑的“艾迪”,扁平的身材,短腿,她不是他们总关注的那个漂亮护士,但是,艾迪是一个爱笑的人。
“我会幻想她独自一人待在自己房间里的样子,”沙利文继续说,“她坐在床上,脱下鞋子,慢慢卷下长筒网丝袜,我相信那时她看起来会很美。”
“我们其实是死于孤独。”沙利文说。
沙利文一向和善,但有时候弗兰克到来时,弗兰克不说话,他躺着不动,只是眨眨眼睛表示欢迎,随后便直勾勾地看着前面。第一次这么做时,他用嘴向弗兰克示意,“我在工作。”
如果弗兰克在那里坐的时间够长,沙利文会在每次呼气的时候说一句诗,弗兰克把它们记在他的处方笺上。
事实证明,
我们坚强,
就像蟑螂。
弗兰克浑身发抖,他还是觉得自己太脆弱了。他仿佛听到了甲壳“嘎吱”的声音,如同脆弱的骨头正在裂开。就像所有的生物那样,人的肉体也很容易被彻底毁灭。
“别担心,戈尔德。”沙利文说,“我会接着写的,铁肺是个好编辑。”
有一次,他非常冷淡。当弗兰克问候他时,他连眼睛都没有睁开。“他昨晚遭了不少罪。”当弗兰克进去时,护士长宾尼对他说。
弗兰克一直等护士离开,才朝他俯下身去。“你怎么样?”
沙利文睁开了一只眼睛。
“不能抠我的鼻子,不能挠我的睾丸,不能擦我的屁股。不过除了这些,一切都称心如意,戈尔德。”
他闭上了眼睛,咧开嘴笑了,仿佛一切对他都没什么。
沙利文的病情逐渐好转后,终于不再待在铁肺里了。他被绑在一个躺椅上,一直绑到脖子,随后就可以和弗兰克一起在走廊里坐着,椅子挨着椅子,刚开始只能坐五分钟,然后十分钟,再然后半个小时。阳光正好,空气清爽。他们坐在那里,对世界感到心满意足,就像两个已近暮年的老人。“最后,我终于学会了如何生存下来。”沙利文说。
他说起脊髓灰质炎侵袭他的那一天。每个人发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他发病时恰逢那场著名的“河流的首领”划艇比赛。一开始他感觉自己全身发抖,但他认为那不过是因为神经紧张。比赛正在进行,他的船领先对手一个船头。突然间,他的力气消失了,再也没办法继续划了,就像拉着铃的铃绳忽然断开一样。他们最后排在了第三,比赛结束后,他觉得太热,颤抖得太厉害,于是认为游泳之后也许会好些。他不在乎这是不是出格,直接一头扎进了河里。然后,他发现他的腿动不了了,他举起手求助,可所有人都觉得他在开玩笑。等他们把他拖到艇上的时候,他已经呼吸困难了。
他异常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在他看来,那段记忆有一种美感。在学校的生活过得太开心了,他有两三个关系很好的伙伴。他相信,他们会成为他一辈子的朋友。
他们把他平放在艇上,向岸上送去。他看到灼热的阳光穿透了他的眼皮,也感受到照在他身体上的热度,耳朵里满是男孩子们涉水时水飞溅起的声音。他听到了他们的沉默,就在那时,一首诗闪进了他的大脑,道尽了这一切。那是一首长诗、大诗,题目是“我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他现在写的一切都是它其中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弗兰克的发病经历不太有诗意,他一点儿都不想说。在他的记忆里,发病的那段时间,他感受到的是自己家庭生活的喧嚣、苛刻、过分亲密,如同一出悲喜剧。他刚开始头痛得目眩,拒绝起床。艾达冲他喊叫说她要迟到了,有可能丢了她在女帽店的新工作。迈耶上早班,早就走了。艾达火急火燎地走了,然后又从公交站点回来,想最后检查一下他的额头。接下来,她疯狂的喘气声充满了他们小小的房子。她在迈耶的衣服口袋里找硬币,骂他每当需要的时候都不在。她沿着街道跑向电话亭,去给科恩医生打电话,也不管前门还大开着。
然后,迈耶奇迹般地出现了。弗兰克像一个婴儿般躺在他的臂弯里,被抱向了救护车。迈耶被晒成褐色的脸在那时变成了浅灰色,艾达的脸色也是煞白。人们远远地看着,其中包括扎内蒂一家、其他邻居和路人。他们的脸模模糊糊的,宛如梦境。
这将教会他们一些事情,他曾经想。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超然和无动于衷的感觉。教会他们什么呢?不要指望他会成为他们的全部幸福!他拒绝成为他们唯一的光。
他此时想,有一天这一切也将成为一个梦。在阳光的照射下,他闭上了眼睛。
“我们正在好转。”他对躺椅里的沙利文说。
“也许这只是暂时缓解?”沙利文反问道。突然,沙利文的背部开始出现严重的痉挛,弗兰克赶忙去找艾迪。
一天晚上,弗兰克醒了,房间里很热、很黑,外面还打起了雷,闪电劈开了天空,大雨倾盆而下。他躺在那里,想起铁肺是靠风箱工作的,风箱连接着病房窗户外面的一台大电动机。
他的轮椅被放在了病房的门边,他没办法够到。他索性从床上滑到地板上,用肘部撑着越过了冰凉的油地毡,通过房门,到了走道上。当他费力向黑暗中看时,倾盆而下的雨水溅到了他的身上。他发现到处都没有生命活动的迹象,难道所有人都忘了铁肺里的病人?
在接下来的一道闪光里,他看到了一群白色的身影。那些身影就像幽灵,在如注的大雨中行进。他看出那些女人是护士。她们从宿舍跑向了铁肺病房,她们身上穿的短睡衣全都湿透了。当他看到那群护士时,他就知道铁肺里的病人将安然无恙。他精疲力竭,勉强撑着回到自己的床上。第二天上午,在铁肺病房,他才了解到,她们竟然一连三个小时用手给那些风箱打气。
不久,医院里有传言说,一些病人将被允许回家度过周末。只是,沙利文不在其中,因为他再也离不开铁肺了。而弗兰克也不在其中,因为他不想离开沙利文。
“我正在缓慢地变成别的某种东西。”弗兰克在处方笺上写道,为了沙利文。这是他的新诗的第一行,诗的题目是“痕迹”。
我们把悲剧留在了家里,
留给了我们的母亲和父亲。
“我父亲想刊印我的诗。”沙利文说,“就一小部分,不是现在这些诗,是我过去写的那些,关于朋友和航海之类的,押韵的那些。他想把它们称为‘青春’,我想把它们称作‘我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但他不听我的。我希望结尾用另外一首诗,虽然我还没写完。”
他闭上了眼睛,一会儿又睁开,看着弗兰克说:“这最后一行是送给你的,戈尔德:到最后,我们终将成为孤儿。”
第二天上午,在病房的早餐盘发出的“锵锵”声中,弗兰克听到一个护士对另一个护士说,一个铁肺病人昨天晚上去世了。
弗兰克急忙去够他的轮椅,他的盘子无意间被打落到地板上。
“嗨,小家伙!”“你这是怎么了?”当他转着轮椅下到走道上时,其他病人这样喊道。
沙利文的铁肺不见了。
“我正要去告诉你,”艾迪说。她的鼻子和眼睛红通通的,帽子也歪了,肩膀下垂。“他有一点儿流鼻涕,不想喝茶,突然就发起高烧来。”她的拇指和食指“咔嗒”一声碰到一起。“他离开了,沙利文就这样离开了。”她站在弗兰克面前,扣着自己的双手,然后又松开了。
一行诗句进入弗兰克的头脑。
啊,你为什么这样站在我面前,
扭着你红彤彤的小手?
“它在哪儿?”他朝着原来放着铁肺的地方做了个手势。
“正在维修,熏蒸消毒。需要这样,弗兰克。”
沙利文的父亲和护士长走过了病房。沙利文的父亲面色苍白,拿着个袋子。当他看见弗兰克时,他停下脚步,低下了头。“我亲爱的孩子已经失去了他的生命。”他说。他的言行举止是在对他儿子的朋友表示尊敬,一种官气十足的致意。他抬起头,向前走去。
沙利文失去了他的生命,但他仿佛还活着,只是没了他的肉体。
弗兰克的绝大多数亲属都在战争中被谋害了,但他对他们的死亡从来没有感觉。他怔怔地躺在床上,从口袋里掏出处方笺,打开,翻到沙利文让他记录下的最后几行诗句。
我必须找到一个,
能够呼吸的地方,
那是诗人的故乡,
是我们心中最深的执着。
“不过是些笔记,戈尔德。”沙利文曾经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弗兰克在接待大厅的电话亭里给迈耶打了电话,当时迈耶在上班。“一个男孩儿去世了。”除此之外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他感到头晕、发烧。他试图完成一首诗,沙利文的诗,《我在世上的最后一天》,现在轮到他接着写了。他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医院的走道像流动的动脉,流过厚重的、有着微弱的呼吸声的黑暗房间。除了这些,还有跳动的阳光、俯冲的鸟儿、灌木丛神秘的阴影。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生活和这个悸动的世界,他顽强跳动着的小心脏不过是其中微小的部分而已。
他没挂电话就离开了。他上了床,拉上帘子。熟悉的黑暗在那里等着他。他直挺挺地仰面躺着,睁大眼睛,手臂放在两侧,缓慢地呼吸着,仿佛也死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