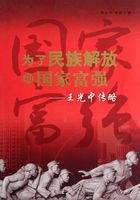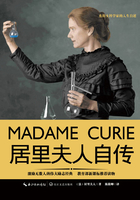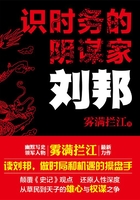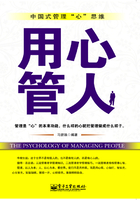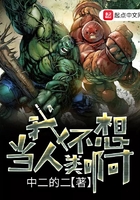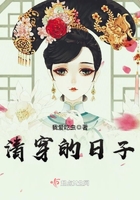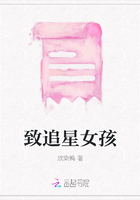袁克定在杨度对面坐下之后,先代表老爹向他说了一串早已编好的、甚表赞赏的言语,然后说:“杨先生虽远离官场,但杨先生对国事的见解,家父常常赞不绝口,久有相识之意,只是无缘。今日杨先生就任宪政大事,家父十分高兴,故派克定先来问候,有方便之日,自当请先生光临寒舍与家父畅叙。”
杨度跟袁世凯并无交往,但对袁世凯其人却不欣赏。他认为袁世凯不是科班人物,心中无知识,只凭机遇和权术上攀。但是,就凭他这样一个人物,能够连连高升,且军权势大,如今又入了军机,成了国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也得算他能耐。袁克定跨进门的时候,杨度就在“掂量”袁世凯这个人,他虽一时尚难知他的斤两,但是,他业经敬服他的立身,敬服他的仕途通畅。再听了袁克定一片奉承,又见人家如此身份能够如此礼贤下士,心里早已甜滋滋、乐融融了。再细想想,他原想投靠的张之洞,此人虽德望不一般,但毕竟年老体弱,老态龙钟了,再加上几年并未展示多大的雄心和才华,充其量,算个吃老本的人。相比之下,无论年富力强还是雄心抱负,自然都差袁世凯几筹,他终于改了主意,说“承蒙宫保厚爱,晳子(杨度字)万分感激。宫保的为人为官,晳子早已倾心敬服,此番任职宪政,便想待稍事安顿,即到宫保大人府上去请教。不想,大公子先临舍下,晳子不日即登府求教。今后事无巨细,晳子一切听从宫保,还请宫保大人多多提协。”
袁克定见谈话投机,见地相一,也就不免多说了几句,然后告辞——就这么一趟,袁世凯圈里又添了一位干将,不仅在目下成了袁的得力助手,且日后更是大展宏图,成了袁世凯想当皇帝的“筹安六君子”之首,为袁氏称帝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成了袁家天下“十三太保”之骨干。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立宪、立宪,在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主宰者和他们的权臣面前,倒是成了一件“怪物”:皇室及他们的王公贵胄,是想着借立宪之名,苟延残喘,维持权势;贵胄中的失宠派,想通过立宪,以便抓权;大臣中的某些要人,也都是想借此机会捞取更大的权力。
入了军机的袁世凯对于立宪之事,仿佛比别人用的心思都多。他想通过立宪捞更多的权。可是,他却又觉得果真立宪了,皇权削弱了,他仿佛要倒霉了似的。前天,儿子向他禀报了拜见杨度的情况,他很高兴;但在他准备接见杨度的时候,又获得了一个十分可怕消息——袁克定说完了杨度的事之后,又吞吐着说:“大爷,外边对立宪的事风声很大。”
“我听到了。”袁世凯说。
“有些话传得很不好。”
“怎么不好?”
“有些满族大臣说,说是……大爷……”
“说我怎么样?”
“说是大爷你通过立宪,阴谋夺权。”
“混账话!”袁世凯甩了一下马蹄袖。
袁克定说:“他们说,汉族大臣觉得自己无法用武力夺取皇权,便搞起了合法斗争,企图通过立宪运动,来夺取皇帝特权。并说,这股夺权势力的带头人就是大爷你。”
袁世凯怒气冲冲地站立着,仿佛想明白了一件事。“怪不得这阵子妖风四起,立宪的风声愈高,满族亲贵反汉族大臣的风潮也愈高。原来根源在这里。”他对儿子摆摆手,说:“好了,你去吧。”
袁克定走后,袁世凯心里更不安了:“这个议论若是传到老佛爷耳朵里,老佛爷偏信了,可对我不利呀!”许多年的亲身体会,那女人毕竟是女人,恨谁了会杀了谁,袁世凯怕惹不起她。于是,便匆匆去见奕劻,诚诚恳恳地对他说:“务请大人在老佛爷面前把话说透,据慰亭所想,实现君主立宪,乃是缓和民主革命危机之策,只有这样做,才能保持我大清王朝根基万代。”
奕劻也劝慰他说:“朝中紊乱,人心不齐,说什么的都有。任他们说去吧。闲言碎语误不了大政。你来了,我倒是想问问你,按照形势,当务之急是什么?咱们应该拿个主意。”
袁世凯一听奕劻这话,正中了心思——他是想通过立宪扩展势力的;要扩展势力,就必须对立宪有所作为。袁世凯趁机说:“大人所想极是。我觉得,当急要办的,是该建议朝廷组织几位宪政方面的专家,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开办宪政讲座,讲解立宪精神。让那些对立宪一知半解或根本就不了解的王公大臣都懂得立宪是怎么回事。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胡言乱语自然会少了。”
“是件急事。”奕劻说,“就是这些主讲师,不知好不好找?”
“这不难。”袁世凯胸有成竹,“现在已经有了宪政编查馆,那位提调杨度就是个‘立宪通’,由他主讲十分合适。”
“好,那就找个机会,向上边推荐一下。”
不久,慈禧便做出决定,在颐和园开办了一座“宪政讲座”,由杨度做主讲。
六
慈禧搞立宪,本来就是一件装模作样的事,不得已而打出的一个招牌。
真干,她是不干的。王公大臣中对立宪也是各持一说,议议而已。杨度做了主讲,去拜见张之洞,张之洞盛气凌人地对他说:“中国推行宪政,绝不能走西方之路,必须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在本国历史上找根据,千万不能标新立异,违背历朝的规章制度。”“历朝的规章制度”与立宪有什么关系,这位老朽没说明,杨度也没有领会具体。有一句话杨度是听明白了,那就是“不能标新立异”。
杨度去拜见满族大臣,他们都明白地表示:“立宪的目的,必须做到巩固和扩大君主的特权。”而杨度所悉知立宪,又恰恰是在限制君权,他有点忧虑了。
最后,杨度来到袁世凯面前。一阵寒暄之后,便谈及立宪问题。袁世凯不隐蔽观点,他同时也觉得杨度早晚是他的人,他要指挥他,他同时为他的后路着想。他说:“中国宪法,必须吸收东西方各国立宪所长,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不宜墨守成规,故步自封。”
杨度点头应“是”,但他心中却在嘀咕:“富国强兵?是富‘君主’的国,还是富‘民主’的国?这个袁军机告诫‘不宜墨守成规,故步自封’,那个张军机却告诫‘不能标新立异’,究竟孰是孰非?”杨度暗自笑了。“袁大人呀袁大人,我认识你了:你对奕劻说的是君主立宪,要保大清王朝的君主‘万世一系’;转脸又要我不墨守成规,这岂不是旨在变更皇权吗?”他转念又想:袁世凯算是英雄,有应变能力。
宪政主讲就是这样的心态,开起讲来会怎么讲?可想而知了。
立宪既是潮流,朝廷不敢阻挡,唱高调也得随着唱。五大臣出洋考察,朝中设立“宪政编查室”,颐和园开办宪政讲座,这还觉得不够又接着派出达寿等三人考察团赴日、英、德考察政治;更命溥伦等人为资政院总裁,筹备立宪资政院,还命各省筹备成立谘议局,各府、县成立议事会。一时间,立宪问题成了举国上下的大事。朝廷当成大事办了,下边闻风而动,官僚地主摇旗呐喊,绅商农工也纷纷请愿。到了1908年9月,清政府还堂而皇之地颁布了包括二十三条条款的《钦定宪法大纲》……人们一见这部大纲,通通傻了眼。原来那上边规定:“预备立宪之期为九年。”这就是说,朝廷打算用九年的时间做准备,准备就绪了,再实行。
“九年何其遥远?!那个老女人还能不能再活九年?!”人们明白了:《钦定宪法大纲》,乃缓兵之大计也!
天有不测风云。
1908年,是大清王朝流年十分不利的年头,立宪风潮真真假假闹腾得国人不安之际,朝廷中“哀”事连连:11月14日,皇后到瀛台去见皇帝,竟发现光绪皇帝死了;满朝文武尚未转过神来,慈禧皇太后也死了——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傀儡皇帝死了,实权太后也死了。别管死得多么蹊跷,都得算作国家大哀。
皇帝死了,国中不能一日无主。根据太后的遗命,以醇亲王载沣的三岁儿子溥仪为嗣皇帝。嗣君年幼,不能亲理朝政,载沣以摄政王的名义代行皇帝的职权。
朝中这迅雷不及掩耳的变幻,使许多王公大臣都慌了神,下一步究竟会是一局什么样的棋,虽然都说不明白,但谁也不能不想想自己的前程。
袁世凯似乎比所有人更慌张。
载沣是皇族的守旧派,视权如命,对汉人成见颇深,尤其是对袁世凯这样终日要揽权的人,简直是疾恶如仇,早就明处暗处干着维护皇权的动作。当年,袁世凯受到慈禧太后信任,去训练北洋新军,载沣便极力反对,他认为那样做是大权旁落。明处向慈禧阻拦,拦不住,便伙同铁良、良弼极力解除袁的兵权,而想由皇室自行统领。事未能成,他便嫉恨袁。原来这个载沣倾向德国的。早年,他以“谢罪专使”的身份到过德国,德皇威廉二世竟十分优厚地接待了他,待之以友好国家亲王之礼。载沣受宠若惊,低三下四地向威廉二世请教“强国之策”。威廉正有意拉拢清政府,想日后做他的附庸,便毫不含糊地说:“作为君主国家,兵权必须由皇室总揽。这便是‘强干弱枝’的政策。若干不能强,国家难盛,皇室便谈不上安危。”从那之后,载沣便认准了袁世凯。“有朝一日,我非杀了他不可!”
袁世凯耳目众多,自己又精明透顶,载沣的内心他早已了如指掌。如今,载沣摄政了,袁世凯感到未日即将到来。袁世凯刚愎自用,从来都是自以为是,但逢到大难时,他也去求人。不过不是求部下,而多是去求外国人。英国公使朱尔典,便是他的靠山之一。形势危急,袁世凯匆匆去拜见朱尔典。
朱尔典也算是中国通了,1871年来到中国,1906年升任公使,在中国三十多年,甚知中国的军政。朱和袁世凯是在朝鲜相识,也有三十年了,交往甚密。载沣摄政,这个外国人也看到了袁世凯的危难处境。
“军机大人阁下,我等候你多时了。”
袁世凯心里一惊,“公使阁下知道我会到这里来?”
“知道,知道。”这个黄头发老外自信地点点头,说,“我是你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朋友就得知心。不知心算什么朋友?”
“朝中的事情……”
朱尔典摇摇手。“我知道,知道。对你不利,极不利!”不待袁世凯说话,他又说:“你,处境相当危险。载沣是个狠毒的人,他会采取手段,消灭他的政敌。”
“那怎么办呢?”袁世凯焦急了。
“现在尚无万全计策。”英国公使眨了眨泛白的碧眼珠,说:“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事大事小,一走便了’。我看阁下还是走出北京为好。”
“走出?!”袁世凯摇摇头,“他们早已布下严阵了,走不出。”顿了一刻,又说:“走出去了,又怎么办?”
“走出去就有办法。”朱尔典说,“只要有一段时间,事情就会有转机。”
“阁下可以帮我走脱?”
“你愿意走?”
袁世凯不甘心坐以待毙,他点点头。
“有地方去?”
“可以先到天津。”
天津是直隶总督的驻地,总督杨士骧是袁世凯的人,杨的弟弟杨士聪正做着京津铁路督办。
英国人撅了下小胡子,点点头。“那好吧,现在你就化装一下,我送你出去。”
在英国人和杨士聪的帮助下,袁世凯连夜逃往天津,住进法租界的利顺德饭店,准备伺机逃往日本。
袁世凯逃走的消息传到宫中,摄政王载沣气得眼睛都直了。“我要抓回来,杀了他!”
载沣要抓回一个逃逆,那是易如反掌的。可是,气怒一阵之后,他还是冷静下来。“袁世凯毕竟是一个庞然大物,杀他还得费一番工夫。”
载沣虽然比袁世凯小了二十多岁,但他毕竟在宫中长大,见多识广;何况,载沣的见识又多是在朝政风雨飘摇之际积累的,他深懂各种关系。国难当头,人心惶惶,杀了袁世凯会不会更乱?他心神不定。
载沣把张之洞找来,请他对此事发表意见,想争取他支持。张之洞虽然跟袁世凯不睦,但自己毕竟也是汉人,并且与袁世凯同进军机。思索一阵子之后,说:“袁世凯在此时出走,实不应该。但是,国家遭逢大故,不宜深戮旧臣。否则,人心不安呐!”
“你把我的意思用军机处名义密电各镇统制,看他们什么意见?”载沣交代。
军机处的密电发往北洋六镇了。隔日,即由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联名发来回奏。回奏十分简单,但却十分坚决:请将臣等先行革职,以免士卒有变,辜负天恩。
好一个“士卒有变”:这无疑是等于以兵保袁。载沣明白,中国的军队统归六镇,而六镇之将,全归袁世凯。杀了袁世凯,六镇必反,后果更不堪设想。
就在这时候,英国公使朱尔典也频繁地出入宫中,开展他的软硬兼施的保袁外交活动。载沣为难了——载沣要杀袁世凯,原因很多,袁世凯兵权大揽,早为载沣所疾;除掉汉族权臣,是载沣的皇权集中的策略关键。另外,其兄光绪帝之死,一股传言甚嚣尘上,都说是慈禧授意袁世凯干的,这又增加了他的嫉恨。但是,传言终是传言,何况国内国外又那么多阻力,载沣只得摇头作罢。
在朱尔典的周旋和担保下,袁世凯只好回到北京。不久,他便奉到上谕:
袁世凯患有足疾,着即回籍养疴。
袁世凯被革职了,他成了平民百姓。其革职的原因,竟是因为他三十多年前跟随养父袁保庆在南京坠马伤足!于是,人们当作笑柄议来议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