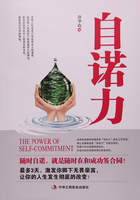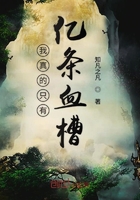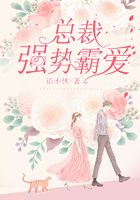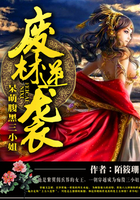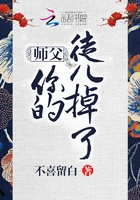职业评论家的产生有着特定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与文学体制化、商业化、批评新闻化、人情化、刊物圈子化等关系密切。正因为有着这诸多原因,我们不能指望这些评论家去职业化,也许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从事职业化的评论同时,多一点业余评论家的自由从容的心态。——如果他们真的认为评论不仅仅是一种职业,同时还担负一种责任与使命的话。——这样,我们才可以说,职业批评家也可以写出好评论。[67]
文学在借助新闻传媒宣传、传播、推销自己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使之更加靠近、适应大众传媒时代对文学的需求。一是作家写作方式的变化,创作成为一种职业,作家成为自由撰稿人,大众的文学消费需求制约着作家的创作,而这种需求往往是通过大众传媒反馈给作家的。换言之,大众传媒的发达,使靠写作谋生的作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注文化市场、关注读者。二是发表、出版方式的变化。过去作家往往将发表、出版作品局限在某些纯文学报刊和出版社范围内,而它们常常得不到大众传媒的青睐;为了走向大众文化市场,今日许多作家瞄准了那些被大众传媒看好的报刊和出版社,纷纷在此“亮相”,因此也就有更多的机会被宣传、推销。三是内容文体的变化。大众传媒关注、看好的往往是那些内容贴近现实生活,文体不拘一格,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的作品,由此导致文学走向通俗化,许多长期从事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创作的作家也创作了类似“布老虎丛书”这样“雅俗共赏”的作品,而有的小说作家从写小说一开始就瞄准了影视市场,企望其作品能被制片人、导演看中,搬上银幕、荧屏,所以小说从内容到文体都更接近电视剧和电影。有的作家干脆直接给制片人写电视剧,从而获得了比创作文学作品更高的知名度和更丰厚的经济报酬。文化散文、生活随笔、新闻小说、戏说历史……各种文体应运而生,传统文学意义上的文体界限已被打破,跨文体写作盛行,大众文化市场和新闻传媒已经和正在创造着新的文学文体。四是文学刊物的变化。近年来许多纯文学刊物纷纷改头换面,重新粉墨登场,其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在保持一定文学性同时,使之具有新闻性、大众性、综合性、娱乐性。《作家》就是一个代表,这家刊物公开声明:要办成中国的《纽约客》。也许不要多久,传统意义上的专供纯文学作品发表的刊物已不复存在,我们看到的只是大众传媒发达时代的报纸和杂志。而“网上文学”的兴起,使众多的网民们则连报刊也不用阅读,就可以了解、欣赏文学。以印刷文化作为载体的文学除了借助现代传播方式、途径传播、推销自己,似乎别无他途。
就这样,新闻传媒在制造了大众文化神话的同时,又粉碎了文学神话。作为大众文化的制造者和代言人,新闻传媒与文学消费关系日益密切,其对文学走向文化市场,赢得大众读者具有不同替代的作用,而文学在今日已不可能拒绝文化市场和大众读者,因而文学的新闻化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文学的新闻化是商业文化市场与新闻传媒合谋的产物。
二、文学能够拒绝新闻化吗?
在大众传媒发达与文化消费的时代,文学与新闻传媒的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如前所述,文学要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进入文化市场,必须借助新闻传媒;而文学一旦过分依赖新闻传媒或者被其控制,就必然要以文学特性的丧失,文学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作家自我的丧失为代价。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文化的精神会在新闻的嘈杂声中消失。”[68]他认为:“大众传媒的精神是与至少现代欧洲所认识的那种文化的精神相背的:文化建立在个人基础上,传媒则导致同一性;文化阐明事物的复杂性,传媒则把事物简单化;文化只是一个长长的疑问,传媒则对一切都有一个迅速的答复;文化是记忆的守卫,传播媒介是新闻的猎人。”[69]米兰·昆德拉这里所谓“文化的精神”也包括文学的精神,它在本质上是个人化的、独立的、自由的、超功利的和具有永恒性的,而新闻传媒在本质上是同一化的、受制约的、现实的和流行的,其出发点是现实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大众的趣味时尚。文学之于新闻传媒的意义、价值,不在于它的美学理想、艺术风格、对人生的形而上的探索和个人化的心灵世界,而仅仅在于它是一种文化现象或一个社会事件。新闻传媒关注的是文学的非文学方面,包括作品出版和发表的背景、内幕,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和引发的事件,以及作家的秘闻,等等。正由于如此,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都不是靠传媒而成为优秀的,它们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是通过时间与读者的检验而获得的。反之,由于它们本身所反映和表现的内容与形式常常是与传媒精神不同的超越具体时空,指向人生存在永恒与艺术发展未来的方面,因而在当时往往被新闻传媒所冷落,新闻传媒甚至与官方意识形态、大众时尚合谋,对其加以围攻、扼杀。西方自有新闻传媒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惠特曼、普鲁斯特、劳伦斯、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伟大作家的作品都遭遇过类似的命运。中国的情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正由于如此,从来伟大的和优秀的作家都是拒绝新闻化,拒绝成为传媒中的“新闻人物”。他们恪守的箴言是:“作家要靠作品说话”,“作家的自我仅仅存在于他的作品中”,由此而使自己与那些在传媒中频频出现的官员,大亨,体育、歌唱、影视明星等“公共人物”、“大众情人”划清界线,不愿意在传媒的喧嚣中丧失自我,在短暂的新闻效应之后被遗忘。因为“被新闻控制,便是被遗忘控制。这就制造一个遗忘的系统,在这系统中,文化的连续性转变成一系列瞬息即逝、各自分离的事件,有如持械抢劫或橄榄球比赛”。[70]川端康成得知自己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第一个反应竟是对妻子说:“不得了,到什么地方藏起来吧!”对此后而来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不间断的采访、拍照,他感到极大的厌烦和倦意。[71]古今中外大凡优秀的作家都视文章为寂寞之道,喜爱孤独的。在没有传媒和传媒不发达的时代是这样,在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他们也能这样,如钱锺书拒绝接受《东方时空》的采访。英年早逝的王小波生前默默无闻,他自觉地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多次声称:“信不过话语圈”。——这“话语”当然包括新闻传媒。尽管传媒聚焦他的去世,但那主要是着眼于一个具有某种新闻效应的文化事件,真正使王小波在死后获得读者和社会承认的是他的小说和杂文。
然而,事实却是:在这文学消费的时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正在被新闻化。君不见,在新闻沸沸扬扬的炒作中,一部平庸的作品成为“精品”或畅销书,一个平庸的作家(甚至算不上作家)成为世人关注的“名人”。原本了无生气的文坛变得热闹起来,走向“繁荣”。新闻传媒近年来如此钟情于文学,并非要守护某种“文化的精神”,而是出于商业文化宣传的需要,迎合大众趣味时尚的需要,它关注的是当代文学的时尚效应、名人效应、商业效应、新闻效应,而非文学自身的精神。它在解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时,又以商业消费的意识形态来解构文学,企图将其纳入以大众文化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这种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概括为:主体的消失、深度的消失、历史感的消失、距离的消失。哈贝马斯则称“后现代主义是中产阶级品味庸俗者的大逆流”:
陈腐不堪的内容与不真实的图景结合为一,板滞的习俗与高科技相拼凑融合,通俗文化的废墟跟高度个人化的、以消费主义方式装饰起来的荒诞之物掺杂结合。文明的垃圾堆用塑胶掩饰起来,普遍的实质溶化成自恋,一种完全失去个性、变成陈词滥调的自恋。[72]
在新闻传媒所给人带来的名利的诱惑下,当代众多的作家已经或正在加入后现代文化消费的大合唱。他们身为作家,却不甘寂寞,一心要成为影视明星式的新闻人物,所以不仅对新闻传媒的关注做不到疏离、拒绝,反而投其所好,频送秋波,自觉地要使自己新闻化。于是,或是以新闻传媒关注的热点、焦点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主题、内容,创作中自觉迎合商业文化消费趣味、需要,以期赢得青睐;或是竭力给自己的作品进行包装,以迎合传媒的宣传口径;或是借助新闻传媒,通过他人吹捧自己和自我推销;或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屎里觅道地制造事件、争端、官司,使自己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这种种向新闻传媒献媚的“诗外功夫”,使这些人在大众文化市场上名利双收,这是传媒对他们的回报。然而,传媒是个靠不住的朋友,一旦他们无法通过上述途径、方式成为传媒关注的热点和新闻人物,新闻传媒就会遗弃他们,他们也就很快地被遗忘。所以,他们得不断地追逐热点、制造事端,使自己始终处于新闻传媒视线之内。当然,也有一些人是靠他们的作品成名的,或者说,在新闻传媒关注他们前就获得了社会和读者的承认。但是他们禁不住成名后被传媒关注的诱惑,从不情愿到半推半就到越来越自觉地主动接受采访,频频出现于电台、电视上,大谈自己经历,参与各种事端,成为与政府官员、企业家、影视明星等公众人物相媲美的“电视知识分子”。与此同时,他们的创作越来越成为一种重复性的技艺批量生产,原先的那种体现文学精神的形而上的思考与个人对人生、生命的独特感悟淡化乃至消失了,代之的是后现代式的“怎么都行”、“削平深度”、“零度写作”。正应了米兰·昆德拉的话:“小说家一旦扮演公共人的角色,便把自己的作品置于危险之中。”
由上可见,文学的新闻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家主体人格的丧失和对大众文化的媚俗。除此之外,文学批评的缺席和失语也是一个重要的缘由。在文化市场业已形成、文学已进入文化市场的今天,文学批评远没有形成一种能预先影响、引导文学创作导向和大众文学消费需求的力量和机制,而文学批评做不到的,新闻传媒却能做到。如前述新闻式的评论,它既可以控制作家的创作方向,也可以左右读者的文学消费需要,文学要在文化市场中生存和发展,便不得不依赖新闻传媒的宣传、炒作、包装。而文学生产与消费一旦被与商业文化关系密切的新闻传媒所控制,必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人为性、随意性、投机性、突发性和标准混乱、价值错位。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的缺席和失语,文学生产和消费之间缺乏一种正常的、准确的、健康的供求关系运行机制,文学家与读者都被传媒制造的“文化信息噪音”所迷惑、所左右,前者为迎合传媒需要而生产,后者的消费需要受传媒左右。在这种情形下,文学要想拒绝新闻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文学:拒绝新闻化”的命题除了向当代作家人格提出追问之外,也在呼唤着不受传媒左右的、真正意义上的、坚持文学特性和价值标准的文学批评。
三、电视文化时代的文学的不可替代性
当代社会大众传媒的发达是以电视文化为标志的。我们生活在电视文化中心的时代。“回家看电视”,几乎成了一句世界通用的口头语,电视涌进家庭,使它已成为每个家庭与每个社会成员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电视以其直观性、形象性、迅捷性、大众化、娱乐性、综合性的特长,和兼容新闻、艺术、娱乐、社会服务和公共教育等多种功能,几乎征服了所有的人,同时也深刻地、全方位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难怪美国作家戴维·哈博斯坦将电视称为这样一种设备:“在我们生活的那些能感觉到的和不能感觉到的方面,它都比报纸、广播、教堂更重要,更有支配力,而且在70年代飘浮无定的美国,电视常常比家庭更重要,比政府更有影响,更有力量。”
电视占据我们精神文化生活最重要的位置是其所创造、传播的大众娱乐艺术。据有关机构调查,我国电视观众约8亿,其中文艺节目收视率为60%,每晚电视文艺节目观众高达4亿。多数人看电视的第一目的是娱乐消遣,每晚8~10时的电视观众人数最多,这个时段主要播放的是电视剧,被称为电视的“黄金时间”。人们读书看报的时间越来越少,文学作品日益受到了冷落。那种因为一篇小说、一首诗而街谈巷议的“文学热”已成明日黄花,代之而起的是由电视激发、产生的流行歌曲热、MTV热、小品热、电视剧热。其中尤其是电视剧,始终是人们的宠儿。它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生活中最流行、最广泛、最共同的话语,它包容、抹平、拆解了种种文化上的差异。一位大学教授与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妪可以就一部电视剧找到共同话题;而不同频道在相同和不同时段播放的不同题材、内容的电视剧则又可以满足各类人的各种文化消费需求,使所有的人无法拒绝电视文化,而日益冷落以文学读物为主体的印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