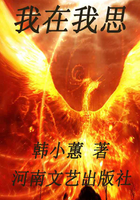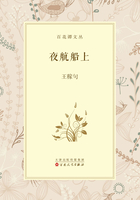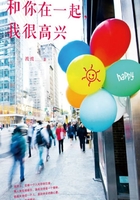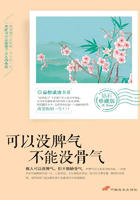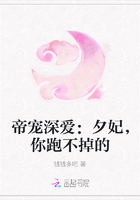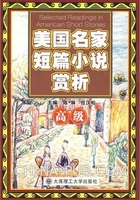吃过早饭,瑞年拿了那本早已经读过无数遍的德国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却心神恍惚地半天也看不进一个字去,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忽然有一种极其强烈的不安和不祥的预兆。窗外不知何时又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这是1937年7月7日的上午,瑞年不知道,此时,远在故国的宛平城外,中日双方正酝酿着一场空前的激战。
临近中午,瑞年穿戴整齐地出了门。几天前他就和近藤敏夫、李海潮等人约好,今天到千代田的九段军人会馆小聚。
五年多以前,瑞年高中毕业之时,鄂泰贝勒给他定下了和正红旗满洲伊尔根觉罗氏家的淑娟小姐的婚事,终于导致了他和父亲之间有史以来最激烈的冲突,最终让他跨海东去。
虽然那位伊尔根觉罗氏的淑娟小姐和瑞年也算得上是同校的校友,但当时南开的学生男女不同校,故而两人虽然名为高低年级的同学,却从来未曾谋面。
在福晋舒穆禄氏她看来,伊尔根觉罗氏家的淑娟小姐和儿子简直就是一对金童玉女,天作之合,她甚至觉得,这是自己嫁到尼玛哈家以来,丈夫鄂泰办过的最令她称心如意的一件事了,不想瑞年就是不肯答应这门亲事。
“你真的是想急死你阿玛,急死额娘啊?!”
福晋舒穆禄氏顾不得一向的矜持和端庄,急赤白脸地跺着脚冲着儿子发狠。
鄂泰在遭到儿子断然否决了他一手策划的婚事之后,无奈之下搬出了自己的福晋这个救兵,他知道,儿子从小最亲近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生母福晋舒穆禄氏,另外一个则是他的乳母李郑氏。早在几年前瑞年刚进中学李郑氏就告老还乡回河北三河县老家去带自己的亲孙子去了,眼下唯一能劝说儿子的也只有福晋舒穆禄氏了。
瑞年虽说是生性刚烈,但却是个至纯至孝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违逆父母意愿的,可这次硬是铁下心来违逆了母亲的劝说,虽然他一向爱戴着母亲。儿子因为那些霸占着东北的东洋鬼子而拒绝留学东洋虽然让鄂泰贝勒觉得恼火,舐犊情深的他还尚可容忍,儿子毕竟是自己的,况且尼玛哈家族到了他这一代可说是人丁不旺。福晋舒穆禄氏十六岁进门,直到二十岁才开怀,生下了瑞年之后便偃旗息鼓再无生育,以至于期盼着多子多孙的他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娶回来三个侧福晋,还把几个丫头收了房,日夜耕耘,到头来却只有三福晋生下了一个女儿婉如,其余一干妻妾全都成了不下蛋的母鸡。这可真是老天不开眼!抱怨之余,对于瑞年这个自己唯一的子嗣传人,鄂泰就看得更重了,因此尽管儿子忤逆得过了分,死活不肯去日本念书,老贝勒还是舍不得真的跟他着急上火,可这回是关系到儿子的婚姻大事,关系到他尼玛哈家族的香烟后代,他不能再不较真了,否则真就要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他那个御赐的贝勒爵位了,这次鄂泰贝勒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由着儿子了。他声色俱厉地当着全家人的面宣布,如果瑞年不答应和伊尔根觉罗氏家的这门亲事,就甭打算去北平上学,甚至甭想走出马场道上的贝勒府大门一步,而且说到做到,立刻就命人把儿子房里的窗户用碗口粗的木条钉死,门上也加上了一把硕大的铜锁。瑞年就这么被父亲关了起来。
瑞年被父亲老贝勒鄂泰关起来可急坏了福晋舒穆禄氏,她先是声泪俱下地规劝丈夫未果,又转而再次恳求儿子瑞年向鄂泰服软认错,却还是遭到了断然拒绝。这下这位原本就不善言辞和心计的福晋彻底没了辙,只剩下干着急的份了,最后还是她那个机灵的贴身大丫头给福晋出了个主意,让她搬出了那位鄂泰贝勒想不买账都不行的主儿,来化解这父子之间的矛盾。
爱新觉罗?载泓出现在鄂泰府上,着实让老贝勒爷吃了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隐居多年的老爷子竟然会突然大驾光临,而且一开口就把自己骂了个狗血淋头。
说起载泓,来头可不小,这位年近七旬的老爷子是大清开国之君努尔哈赤的嫡传后裔,光绪皇上没出五服的兄弟,就连溥仪按辈分还要尊称他一声“皇叔”。只可惜老爷子的爷爷当年得罪了咸丰皇上,被褫夺了皇族和旗籍,贬为庶民。直到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念及自幼和载泓甚笃的私交,撺掇溥仪恢复了载泓一家的皇族身份和旗籍,生性耿直的载泓却坚辞不就,三代人的沉浮荣辱已经让他看破了尘世浮华,别无所图了。宣统逊位之后,载泓便到北京西山找了个小小的道观清修去了,从此再不与皇室和过去的族人们往来。这么些年,几乎就没了他的音讯,这个时候这位老爷子忽然冒出来,怎么能不让鄂泰吃惊呢?
载泓一身道士装束,虽然没有挽起发髻,却也颇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不过多年的清修似乎并未改变这位前满洲贵胄的火爆脾气,刚一落座他就拍桌子打板凳,高声大嗓地数落起鄂泰的不是来了。
“你个猴崽子,长本事啦?敢关我的外孙?反了天了你!”
载泓的话让鄂泰两腿战栗,冷汗哗地一下顺着脊梁沟就淌了下来,看来今天这老爷子是专门兴师问罪来的,这通臭骂大概是躲不过去了。
载泓其实和福晋舒穆禄氏压根没有血缘关系,他和瑞年的外祖父,也就是福晋舒穆禄氏的父亲年轻时是八拜之交的结义兄弟,并且是福晋舒穆禄氏的挂名义父,所以,瑞年也就成了他口中的外孙。
载泓骂过鄂泰之后,立时三刻地逼着这位“干女婿”把关着的瑞年放了,并且回绝和伊尔根觉罗氏家的这门亲事。
“这事就这么定了!”
老爷子载泓一脸的不容置疑,让鄂泰进退维谷。虽说载泓现在不过是一介平民,可他老人家毕竟是曾经的皇亲,而且和溥仪的生父载沣私交深厚,据说溥仪幼年尚未进宫之时,没事就骑在他的这位族叔肩膀上去逛厂甸,简直比跟他的生父载沣还亲近呢,鄂泰贝勒即使有十个八个胆子也不敢得罪这位老爷子啊。唯唯诺诺间,鄂泰叫人把关着的瑞年放出来给载泓请了安。瑞年谢过这位干姥爷之后,载泓笑吟吟地拉了他的这个多年不见,已经出落得仪表堂堂的干外孙坐在身边,上下打量,前后观看,那份慈爱让瑞年都有点浑身不自在了。
“好小子,不愧是咱满洲人的种儿!”载泓攥了拳头捶打着瑞年的胸膛,眼里满是爱怜和赞赏,“咱满洲人是马上得来的江山,孩儿啊,你也让你爹一步,去日本,进士官学校,学武去吧!”
瑞年权衡再三,也想不出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了,无奈之下只得答应了去日本留学的事,不过,心里却打定了主意:先离开这个家,离开那眼看就要套在自己脖颈间的婚姻枷锁,而后再图发展。瑞年打算先到日本混上一段时间,然后找机会到欧洲去游历,给鄂泰来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到时候阿玛鞭长莫及,估计也就只能顺水推舟地由着他了。他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压根就打错了算盘,从他踏上东瀛的土地那一刻起,一切就都变得身不由己了。
瑞年被迫答应赴日留学离开了他来到人世间十八年来从未离开过的父母和家,在父亲专门安排伴随他东渡的一个幕僚的陪同下来到了东京。原本打算相机而动,借留日的机会给父亲来一个金蝉脱壳,远走高飞,瑞年却没有料到,老奸巨猾的父亲早就料到,或者早就提防了他的这一招,不仅特地安排了随侍的幕僚,而且叮嘱他的那个忠心耿耿的手下,一到日本就联络上其时驻东京的“满洲国”大使馆,借机把瑞年地护照骗到手,立刻更换成“满洲国”的护照,让瑞年糊里糊涂地就成了“满洲国”的子民,也因此再难实现他游历欧洲的愿望。瑞年这才明白,自己虽然冲出了父亲禁锢他的那个房间,却被阿玛放进了另外一个囹圄中桎梏起来了。盯着手中的“满洲国”护照,瑞年恨得咬牙切齿,从此竟然再不肯给父亲传去只言片语的问候,在他看来,父亲不仅侮辱了他的人格,也侮辱了他的情感,更侮辱了他曾经努力维系着的对父亲的感恩和父子亲情。
虽说是被迫进了陆士,但瑞年在陆士的学习成绩却是始终令校方和同学们刮目相看的,不管他对日本,对陆士是多么抵触,但既来之则安之,瑞年可不想让那些永远自我感觉良好,早早地就以日军精英自居的陆士同学看低自己,他要让他们瞧瞧,中国人走到哪儿都是好样的。从陆士预科到本科,整个陆士四十九期的学员里,能跟瑞年在成绩上一较高下的大概也就只有那个近藤敏夫了。
进了陆士的瑞年虽说没有明确宣布和鄂泰断绝父子关系,可心底里却已经几乎割断了他们的父子之情,他只是偶尔给那让他记挂着的母亲写回一封家书,或是拍一份电报,但却绝不会寄到家里,而是通过在天津的中学同学转交。他却不知道每每接到他的来信,母亲都会含泪拿给父亲看,而老贝勒看过之后,多半会一个人躲在书房内整宿整宿地黯然神伤。瑞年就这么隔着大海和父亲僵持着,直到1934年春末夏初之时他突然接到父亲从国内委托一个挚友捎来的一封书信,近两年来凝结在他们父子之间的那块坚冰才慢慢地消融开去。
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执政”溥仪终于重登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就任了“满洲国皇帝”,其时,作为前清重臣的鄂泰贝勒也接到了出席登基大典的邀请,兴高采烈地赶往了“新京”,但谁也没料到,这位临行前还欢欣若狂的贝勒爷,却只在新京短暂地停留了一周的时间,而后就怒气冲冲,捶胸顿足地返回了天津,甚至连溥仪委任他的“满洲国参议府”的要职也坚辞不受。
“现在想来,还是瑞年当初说得对,看得远,小日本压根就没一个好东西,可怜咱们的宣统爷啊,比起当年被老佛爷垂帘听政时的光绪爷还不如啊!”
鄂泰为参加溥仪的登基大典来到新京之后,亲眼目睹了日本人在“满洲国”的骄横跋扈,甚至在溥仪的“登基大典”过程中,他还亲眼看到负责警卫任务的日本关东军的普通士兵像呵斥奴才一般地训斥前来出席典礼的几位前清重臣。那几位老爷子全都是鄂泰的前辈,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几乎是至尊无上,仅次于宣统皇上的。愤愤不平的鄂泰当时便忍不住骂了街,而让他更想不到的却是他曾经的挚友熙洽竟然几乎跟他翻了脸,没完没了地责怪他不知轻重,在皇上大喜之日添堵抹黑,是对“日满亲善”的大不敬云云,气得鄂泰差点吐了血,要不是看在祖宗情分上,等不到“登基大典”结束,他就立时三刻地返回天津了。
鄂泰贝勒回到天津,一跨进贝勒府的大门,就捶胸顿足地嚎啕起来。这趟新京之行,让这位曾经对“满洲国”,对“帮助”大清复国的日本人充满幻想的鄂泰彻底明白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效忠了十几年的宣统爷,如今早已被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彻彻底底地成为了一具傀儡,鄂泰贝勒彻底死了寄望于溥仪的复国之心。痛定思痛,思前想后一番,鄂泰终于放下了他的“父为子纲”的架子,给远在日本的儿子瑞年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家书,在信中,他对儿子表示,他再不会逼迫儿子去效忠那个如今不仅连身上穿的制服都效仿日本天皇,还竟然不顾祖宗,廉耻全无地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迎回来顶礼膜拜的宣统爷了。鄂泰还表示,如果儿子想回国,那就回来,如果他想去欧洲学习,他这个做父亲的也会全力支持,总之,一切都任由瑞年自己决定。
瑞年现在终于明白了父亲转变的原因,为他很高兴父亲终于认清了日本人的险恶用心,认清了溥仪的不可救药,为他们父子和好欣慰之余,也不由得心生感慨:父亲鄂泰贝勒万万也不会想到当年被他逼迫东渡求学的儿子,此时却打算继续留在日本学习了。
如果说父亲鄂泰的转变源于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人的骄横跋扈,溥仪的软弱无能,那么瑞年决心留在日本继续他的陆士学业,则要归功于潜伏于“满洲国”军界的国民党人王家善。当时,供职于“满洲国”军界的王家善被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进修,虽说和正在陆士预科学习的瑞年并不同班,但两人很快就相识了。最初,瑞年对这个来自“满洲国”的“汉奸”很是不屑,以至于王家善几次试图和瑞年交往都被他冷漠地回绝了,直到后来王家善向他坦露了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迹,瑞年才恍然大悟,并且从此和王家善成了挚友。
王家善听瑞年说父亲鄂泰改变了态度,同意他回国或是远赴欧洲,很诚恳地和瑞年长谈了一次,他对瑞年表示,与其这样半途而废地回到国内或者去欧洲留学,远不如在日本陆士完成学业,一来可以学到先进的战争理论,二来可以进一步了解日本国情和军情,为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做准备,到那个时候,今天的所学必将为国所用,又何必逞一时之气,争一日之短长呢?王家善的话深深打动了瑞年,于是,他出乎父亲和所有人的意料,留在日本继续陆士的学业,却不料鄂泰竟在不久之后撒手人寰,临终前父子俩都没来得及见上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