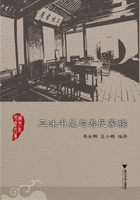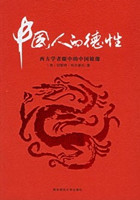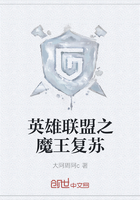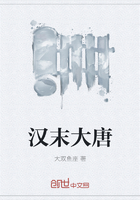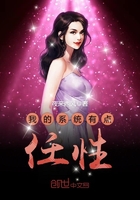“天下间四只脚的除了桌子之外,广东人没有不能吃的东西。”我们享有如此“美名”。固然是食胆甚大,但也是因为岭南的生态环境本来就很多样,聚集了不少北方罕见或者早已绝迹的生物,比如大象。反正要杀,那就千万别浪费,潮汕人和广府人秉持物尽其用的传统美德,不只宰象割牙,就连它的肉也要想尽办法炮制。每次捉到活象,我们的祖先“争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不仅火烤红烧,听说糟渍的味道也不错,切条生炒还行。等到象鼻不好找了,后来的香港人就开始吃象拔蚌,那条“象拔”起码长得像真象拔。岭南还有华南虎,香港最后一次发现老虎是1947年11月,一位主教在沙田看见了它,而且当年还有不少其他目击者的报告。至于现身香港的最后一头大象,恐怕就是几年前马戏团带来的吧。
2012.5.11
葵的消失
中国名山丽景数之不尽,我们很容易就会产生一种幻觉,以为它们由古至今都是旅游胜地,浑然不觉这些自然风光原来也是历史的造化,有些会被淘洗淹没,有些会被后人发掘。
比如张家界和九寨沟,对今天的香港旅行团来说,这两个地点大概要比华山还热门;可是回到两百年前,张家界的名字说不定许多人连听都没听过呢。更极端的例子是千岛湖,数十年前它根本不存在,因为这是一座水利工程形成的人工湖。另一方面,有些名山却莫名其妙地降了格,原来是无人不知的“国家级景点”,现在则成了地方上的游览好去处。就拿浙江天目山来说吧,魏晋以来就吸引了无数骚人墨客,李白苏轼更曾为它赋下千古名作。在那长达一千年的中国“中世纪”里,它的地位恐怕要比黄山还高;不过,如今去天目山游玩的旅客数量又怎比得上黄山呢?还有一些地方干脆是彻底沦落,变得寂寂无闻,只余最专业的访古癖才会不辞劳苦地觅其芳踪。
名山若此,名菜亦然。
前两天重读汪曾祺先生散文,有《葵·薤》一篇。汪先生很好奇古诗里头时常提到“葵”,并说它可以拿来做羹,是种很常见的好蔬菜;但到底什么是“葵”呢?只知道它肯定不是向日葵,也不是秋葵和蜀葵,因为这几种植物好像都不太能够下汤。终于,他在清人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与《植物名实图考长编》里头找到了答案,原来“冬苋菜”就是“葵”。四川、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还很流行冬苋菜,而且就是取叶做汤,吃起来像莼菜一样滑利,正如古人形容。
那么“冬苋菜”和我们广东人常吃的苋菜又是不是同一回事呢?恰巧我也有吴其浚这两部书,是台湾出版的精装小开影印本,但翻遍家中而不获。于是我又上网搜寻,似乎也看不见两者关系的佐证。最后我在明人朱的《野食》里分别找到苋菜与“冬葵”的图录,发现它们的吃法都是采叶水煮,口感也极其相似,只是样子长得不太一样。
先撇开“葵”与苋菜究竟是不是同一回事这点不论,引起我注意的其实是朱说“冬葵”叶乃“百菜主”这句话。因为汪曾祺先生引述吴其浚,也说他“把葵列为蔬菜的第一品”。不只如此,更早一点,元朝王祯亦在《农书》称“葵”为“百菜之王”。既然古人这么喜欢“葵”,老在诗文里称颂它的美好,后人又怎么会几乎忘记了这种菜的存在呢?汪先生叹道:“不知怎么一来,它就变得不行了。明代的《本草纲目》中已经将它列入草类,压根儿不承认它是菜了!葵的遭遇真够惨的!”的确,别说今天的中国北方很少人知道“葵”,哪怕是还在吃它的南方人也往往视之为“野菜”(事实上,香港乡郊道旁也能见得它的踪迹),而非大规模种植大规模销售的农产;从前它却曾是整片神州大地最常见的百菜之王呀!
汪先生猜这是因为白菜取代了“葵”,将它挤下历史舞台。可在我看来,这个解释还不够,我们更应该追问白菜之所以代替“葵”的原因。想了半天,我只能说这是人类口味的变化。比起“葵”的潺滑,今人更欣赏白菜的爽脆;比起古人水煮熬汤,现代人更喜欢大火炒菜。你一想到蔬菜,首先联想到口感是软滑还是鲜脆呢?这么一问,答案大概就出来了。
2010.10.8
在北京吃面
不要误会,我好像老是逆潮流而行,说北京的坏话,嫌它住得不好吃得不行。不,不是这样子的。我是喜欢这个地方,才为它担忧,怕它被当前浮躁功利的心态拖垮。其实除了那些名气很大的“时尚热点”之外,还是有些躲在胡同里的新派餐馆是不错的,正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其实是用不着花大力气宣传的,食客的口碑自然会引来更多的食客。
不过要是有朋友去北京,我还是建议他们去找些传统的地道口味,比方说炸酱面。
不知是偏见,还是我家的口味养成,我一直觉得“北方”面食要比我们广东的强(所谓“北方”,我用的是广东人的说法,凡是在广东以北就叫做“北方”)。我不是不喜欢广东面食,云吞面、虾子捞面与蒸河粉、炒河粉皆我所爱;但你看今天香港满街面档,有多少家没有那中人欲呕的过重碱水味呢?大好岭南风味,如今都给人败坏了。结果现在要吃一碗好面,还是苦心搜索,舟车劳顿特意去找,完全不是我国面食的本色。吃面,原来应该是件很随意的事,街上走着走着肚子饿了,闻到香味看见店招,就坐进去点一碗面,趁着汤热面不烂的时候呼噜呼噜迅速吃完,然后钱一丢拍拍屁股就走,潇洒怡然。所以这种东西就该像便利店一样,“总有一家在你附近”,根本用不着食经指南,它应是大部分人都不会做坏,随便哪一家都吃得过去的民生必需品。可是,今日香港离此境界实在远甚。
而且我们视野狭窄,对广东以外的面食明明一知半解,却要指指点点。例如香港一位杂志食经专栏作者,平常看来识饮识食,语多挑剔,我也喜他不买账。但最近见他苛评一家新开的上海面馆,就真是大跌眼镜了。首先声明,这家名店近年的水平确实不稳,它的香港分店我也没试过,所以我无意为它辩护。问题是那位食家说他们把面和料分开上,再让客人自行把那小碗菜料倒进面里是“玩花招,不实际”,这就太过离谱了。要知道上海面食一向如此,这本是苏州人吃面的方法,寻常得紧,所有面都是清汤阳春面,其他一切菜码酱料皆另分小碗,叫做“浇头”,您自己看着下。无论是鳝糊、黄鱼,还是三鲜,莫不如此,有何稀奇?又有何“花招”可言呢?
还是说回北京的炸酱面吧,基本上大街也好,陋巷也好,真没有一间不能吃。这就和你到了意大利,很难碰上很难吃的pasta一样。这才是懂吃面的地方。要是真要找家最有名的,我推荐海淀区甘家口的“海碗居”。这家倒真是有“花招”了,店面陈设强装老北京风味,服务员一个个“小二”打扮,客人进门就欠身大喊:“来了,您呐!”客人坐下来之后就有人一路吆喝“奉茶”一路用白抹布擦桌,走的时候自然是“送客”、“走好,您呐”,热闹得紧。
不过他们的面真是实在。首先面条够劲道,有嚼头,但又不失滑溜(再提示一点,很多人以为所有北方面条都是拉面,大错特错,炸酱面用的就一定是切面)。其次炸酱,黄酱虽然也是“六必居”货色,但肉丁肥瘦匀称,炸得很香。其他如黄瓜丝、青豆儿也都清新爽口。到了最后,还送上一壶“面汤”,也就是煮过面的那锅水。北方人讲究“吃原汤,化原食”,吃完一碗面后再喝面汤,饱腻尽消,肚子受用。不信的话,下回您试试。
2007.12.29
火锅
今年省麻烦,除夕夜里吃火锅。虽然这不是我家的习惯,但传统上不都说“围炉”吗?所以我们还算按规矩过了一回中国年。
说起火锅,还真是一样很有中国特色的吃食,与西方世界的饮食文化截然不同。而第一个发现这种中国特色的,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却是法国人类学大宗师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
这位几乎与“结构主义”同名的老人去年年尾刚过一百岁生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固然要亲自登门贺寿,各大报刊则以头版发布他寿辰的消息,有些电视台更不惜拨出全天候的节目时段回顾他一生的成就。一来,这是法兰西的高贵传统,大家崇拜学术明星就和崇拜刘德华一样(尽管不是人人都能读懂那些硬邦邦的巨著,但起码也得装一下,好比香港office lady一定要学会LV的正确发音);二来,这是因为这位人类学家实在厉害,洞察到不少文化里头的根本结构。
那么,他对中国饮食文化发表了什么很厉害的见解呢?其实也不多,一句话说完,那就是“中国菜几乎是共时的”。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这就算很厉害吗?
且容我先用他老家的法国料理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都知道,以法国菜为首的西式料理上菜是一道道上的,除非在某些特别场合,否则绝少同时上全一桌菜。不仅如此,一顿饭里的每一道菜都应该尽量不重复。所谓不重复,指的是它们的基本元素,例如材料和烹调手法,头盘出过烤田鸡腿,主菜就不该让它再来一回。而且上菜的程序也有讲究,正常情况下,海鲜鱼贝不能排在牛扒羊腰前面,否则就乱了口味了。这种情况就叫做“贯时性”,各种元素按顺序一一列出。
中国菜则不然,出过的材料还可以再出,冷盘用过豆干不碍大盘再用一次;使过的手法也还能再使,吃完油炸凤尾鱼不妨接着再上炸响铃。更妙的是,这一切东西都可以同时上桌,红白黑黄七彩纷呈,煎炒煮炖样样不缺。还得注意,一般中菜根本没有所谓“配菜”这回事。比方芥兰炒牛肉,你说这是芥兰配牛肉,还是牛肉在配芥兰呢?所以中菜菜单的洋文翻译特别难,因为我们实在很难用西餐菜单里的那个“with”去形容各式各样主客不分的中菜。
或许是从此得到灵感,另一位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于是判断日本火锅是种“没有中心”的“共时”文化。可是在我看来,中国火锅不是走得更远吗?日本人吃火锅单调得很,牛肉就是牛肉,鱼肉就是鱼肉,绝不轻易混搅。哪像我们广东人,生蚝鹅肠共冶一炉,不讲究顺序,也不分别荤素禽畜,什么东西都往锅里丢就对了。这才是最中国的中国饮食,“没有中心”,是因为没有配菜;你怎能判断一锅火锅的主角是什么,配菜又是什么呢?
火锅是最极致的团圆,取消了前菜和主菜的分别,从头到尾只有一种烹调的技法,吃的过程和烹调的过程合二为一,所有食材共时出现共时享用,每一种东西都染上了别的东西的味道,是彻彻底底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农历新年吃火锅,谁曰不宜?
2009.2.13
羊肉串
一
北京朋友告诉我一个“段子”。话说街上有个肤色白皙的汉子叫卖羊肉串,喊着“羊肉串儿”的时候刻意变声,把结尾那个“串儿”拉得又长又高,活脱脱一个维族人讲话的调子。然后来了几个小伙子,呵斥他:“这是干什么?正经点说话!”于是那小贩立刻满脸堆欢,换上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口音普通话:“嘿嘿!大哥大哥,来几串呀?”原来这小贩是汉人,为了显得正宗地道,故意用维族人的口音叫卖羊肉串,结果一眼就给人看穿了。这个故事不像虚构;要是编造,它应该更戏剧化一点,更搞笑一点。就算是编出来的,它也寓言般呈现了某种现实。
现实就是维吾尔人卖烤羊肉串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他们的吆喝就如无数传统民间小吃小手艺一样,形成了固定的标志;你一听那种腔口那股韵律,便知是卖羊肉串的来了。所以哪怕是汉人经营羊肉串,也得学着维族人的模样。现实的另一面是卖羊肉串的汉人越来越多,以往街头巷尾常常见到的维族人小摊早已不知退隐何方。
回想十多二十年前,北京还没有今天这等气派摩登,宽大的马路也不多。在稍具规模的公共汽车站等车,很容易就看到站旁一两个维族人推着辆脚踏车,车尾架着一截被刮开了的竹子。那段开口竹竿原是精巧易携的廉价小烤炉,里头烧炭,上面能铺一排羊肉串。虽然其时已有固定店铺售卖电炉烧烤的铁插肉串,但大家还是喜欢这些原始简陋的竹签烤肉,那种炭香是电炉烧烤没法比的。
它是我当年在内地旅游最难忘的小吃之一。肥瘦相间的羊肉,其油脂被明火烧出一阵焦香的羊膻,隔条马路都闻得到。而孜然,就是判定它正宗与否的关键了。不知何故,汉人处置肉串往往不肯多下孜然,风味远逊维族原版,凡知味者不取。
如果拿它下酒,那就更妙了。外公晚年归乡,每年冬天我都要去河北省的河间市看望他。年轻乡亲常带我去夜市喝酒,只见一整条街的上空烟雾缭绕,底下全是一摊摊的烤肉串,火光如星,异常灿烂。我们围坐在低矮的小桌旁,和邻桌一样喝酒吃肉,肉是三十串三十串地叫,酒则一斤一斤地喝。再冷的天,有这羊肉白酒顶住。如果气温实在太低北风实在太大,还可以坐进废弃大巴改成的室内“餐厅”,紧闭窗门。奇怪的是,好像从来没人担心窒息中毒的问题,毕竟每张桌子都供着一只用来保温加热的小炭炉,炉上油脂烤得嗞嗞响。唯一令人不快的,是下得车来从头到脚由里至外一股羊膻味,好像自己就是一头刚刚烧好的全羊。不过,到了那时候,每个人早已喝得酩酊大醉,又有谁会在意身上的气味呢?走回家的时候,大伙踩过满地竹串,撞倒几个空酒瓶,一路引吭高唱莫名的曲调,不知今夕何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