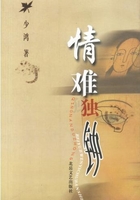“我和贝戈特的相识,”他又转头对父亲说,“对他,对我,都不能不说是一件尴尬的事(也是另一种方式的趣事)。几年以前,贝戈特去维也纳旅行,当时我在那里当大使。梅特涅克公主将他介绍给我,他到使馆来并希望我邀请他。既然我是法兰西的驻外使节,既然他的作品又为法兰西增光——在某种程度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微不足道的程度上——我当然可以抛开我对他私生活的不满。然而他并非独自旅行,所以他要求我也邀请他的女伴。我这人不爱假正经,而且,既然我没有妻室,我完全可以将使馆的门开得大一些。然而我忍受不了这种无耻,它令人作呕,因为他在作品中却大谈德行,甚至干脆教训人。他的书充满了永无休止的、甚至疲疲沓沓的分析,这是我们私下说,或者是痛苦的顾虑、病态的悔恨,以及由于鸡毛蒜皮的事而引发的冗长的说教(我们知道它值几文钱),而在另一方面,他在私生活中却如此轻浮,如此玩世不恭。总之我没有回答他。公主又来找我,我也没有答应。因此我估计此公对我不抱好感。我不知道他对斯万同时邀请我们两人的这番好意作何评价。或者是他本人向斯万提出来的,这也很难说,因为他实际上是病人。这甚至是他唯一的借口。”
“斯万夫人的女儿也在场吗?”我趁离开饭桌去客厅的这个机会向德·诺布瓦先生提出这个问题。这比一动不动地在饭桌上,在强烈的光线中提问更便于掩饰我的激动。
德·诺布瓦先生似乎努力追忆片刻:
“是的,一位十四五岁的姑娘吧?不错,我记得在饭前别人把她介绍给我,说是主人的女儿。不,她露面的时间不长。她很早就去睡了,要不就是去女友家了,我记不清楚。看来你对斯万家的人很熟悉。”
“我常去香榭丽舍街和斯万小姐玩,她很可爱。”
“啊,原来如此!的确不错,我也觉得她可爱,不过,说真心话,她大概永远也比不上她母亲,这句话不至于刺伤你热烈的感情吧?”
“我更喜欢斯万小姐的面孔,当然我也欣赏她母亲。我常去布洛尼林园,就是为了碰见她。”
“啊!我要告诉她们这一切,她们会很得意的。”
德·诺布瓦先生说这话时,态度与其他所有人一样(虽然为时不长)。这些人听见我说斯万是聪明人,说他父母是体面的经纪人,说他家的房子很漂亮,便以为我也会以同样的口吻来谈论同样的聪明人、同样体面的经纪人、同样漂亮的房子。其实,这好比是神经正常的人在与疯子交谈而尚未发现对方是疯子。德·诺布瓦先生认为爱看漂亮女人是理所当然的事,认为某人对你兴奋地谈起某某女士时,你便应该佯以为他堕入情网,和他打趣,并答应助他一臂之力,因此,这位要人说要向希尔贝特和她母亲谈起我(我将像奥林匹斯山的神化为一股流动的气,或者像米涅瓦[48]一样化身为老者,隐身进入斯万夫人的沙龙,引起她的注意,占据她的思想,使她感谢我的赞赏,将我看做要人的朋友而邀请我,使我成为她家的密友),他将利用自己在斯万夫人眼中的崇高威信来帮助我。我突然感到无比激动,情不自禁地几乎亲吻他那双仿佛在水中浸泡过久的、泛白发皱的柔软的手。我几乎做出了这个姿势,以为觉察者仅我一人。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要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在他人眼中的地位作准确判断确非易事。我们害怕自视过高,又假定人们生活中的众多回忆已经在他们身上占据极大的场地,因此我们举止言行中的次要部分几乎不可能进入谈话对方的意识之中,更不用说留在他们记忆之中了。其实,罪犯的假定也属于这同一类型。他们往往在事后修改说过的话,以为别人无法对证。然而,即使对人类千年的历史而言,预言一切都将保存的哲学可能比认为一切将被遗忘的专栏作家的哲学更为真实。在同一家巴黎报纸上,头版社论的说教者就某件大事、某部杰作,特别是某位“名噪一时”的女歌唱家写道:“十年以后有谁还记得这些呢?”而在第三版,古文学学院的报告常常谈论一件本身并不重要的事实,谈论一首写于法老时代的而且全文仍然为今人所知的、但本身并无多大价值的诗,难道不是这样吗?对短暂的人生来说,也许不完全如此。然而,几年以后,我在某人家里见到刚巧在那里做客的德·诺布瓦先生,我把他当做我所可能遇见的最有力的支持,因为他是父亲的朋友,为人宽厚、乐于助人,何况他由于职业和出身而言语谨慎,但是,这位大使刚走,就有人告诉我他曾提到以前那一次晚宴,并说他曾“看见我想亲吻他的手”。我不禁面红耳赤,德·诺布瓦先生谈论我时的语气以及他回忆的内容,使我愕然,它们与我的想象相去万里!这个“闲话”使我明白,在人的头脑中,分心、专注、记忆、遗忘,它们的比例多么出人意外,使我赞叹不已,就像我在马斯贝罗[49]的书中头一次读到人们居然掌握公元前十世纪阿苏巴尼巴尔国王邀请参加狩猎的猎手的准确名单!
“啊!先生,”当德·诺布瓦先生宣布将向希尔贝特和她母亲转达我的仰慕之情时,我说,“您要是这样做,您要是对斯万夫人谈起我,那我一生将感激不尽,一生将为您效劳!不过,我要告诉您,我和斯万夫人并不相识,从来没有人将我介绍给她。”
我说最后这句话是唯恐对方以为我在吹嘘莫须有的交情。可是话一出口,我便感到它毫无用处,因为我那热情洋溢的感谢辞从一开始就使他降温。我看见大使脸上露出了犹疑和不满,眼中露出了下垂的、狭窄的、歪斜的目光(如同一张立体图中,代表某一面的远遁的斜线),它注视的仅仅是居于他本人身上的那位无形的对话者,而他们的谈话是在此以前一直和他交谈的先生——此处即为我——所听不见的。我原以为我那些话——尽管与我心中汹涌澎湃的感激之情相比软弱无力——可以打动德·诺布瓦先生,使他助我一臂之力(这对他轻而易举,而会令我欢欣鼓舞),但我立即意识到它的效果适得其反,甚至任何与我作对的人的恶言恶语也达不到这种效果。我们和一位陌生人交谈,愉快地交换对过路人的印象,而且看法似乎一致,认为他们庸俗,但是突然在我们和陌生人之间出现了一道病理鸿沟,因为他漫不经心地摸摸口袋说:“倒霉,我没带枪,不然他们一个也活不了。”和这种情景相仿,德·诺布瓦先生知道,结识斯万夫人,拜访她,这是再普通、再容易不过的事了,而我却视作高不可攀,其中必有巨大的难言之隐。因此,当他听见我这番话时,他认为在我所表达的貌似正常的愿望后面,一定暗藏着其他某种想法、某种可疑动机、某个以前的过失,所以至今才没有任何人愿意代我向斯万夫人致意,因为那会使她不高兴的。于是我明白他永远不会为我出这把力,他可以一年一年地每天与斯万夫人相见,也决不会——哪怕一次——提到我。不过,几天以后,他从她那里打听到我想知道的一件事,托父亲转告我。当然,他认为没有必要说明是为谁打听的。她不会知道我认识德·诺布瓦先生,也不会知道我热烈渴望去她家。也许这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倒霉。即使她知道这两点,第二点也不会增加第一点的效力,何况这个效力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因为对奥黛特来说,既然她本人的生活和住宅引不起任何神秘的慌乱,那么,认识她并拜访她的人决不如我臆想的是什么神奇人物。要是可能的话,我真想在石头上写上我认识德·诺布瓦先生这几个字,然后将石头扔进斯万家的窗子。我认为,尽管传递方式粗野,这个信息会使女主人对我产生敬重而不是反感。其实,如果德·诺布瓦先生接受我的委托的话,它也不会有任何效果,反而引起斯万一家对我的恶感。即使我明白这一点,我也没有勇气收回这个委托(如果大使慨然允诺),没有勇气放弃乐趣(不论后果如何悲惨):即让我和我的名字在对我陌生的希尔贝特的家和生活中与她陪伴片刻。
德·诺布瓦先生走后,父亲浏览报纸。我又想到拉贝玛。既然我看戏时所感到的乐趣远远少于我原先的估计,这个乐趣便要求被补充,并且无条件地吸收一切滋补。例如德·诺布瓦先生所赞扬的拉贝玛的优点,它被我一饮而尽,仿佛干旱的草地立刻吸收人们洒在上面的水一样。这时父亲将报纸递给我,指着上面一段小报道:“《淮德拉》的演出盛况空前,艺术界及批评界的名流前往观看。淮德拉的扮演者、久负盛誉的拉贝玛夫人获得她那辉煌事业中前所未有的成功。此次演出不愧为轰动戏剧界的大事,本报将作详细报道,在此只需指出,有权威的评论家一致认为,此次演出使淮德拉这个人物——拉辛笔下最美最深刻的人物之一——焕然一新,并且成为当代人有幸见到的最纯净、最杰出的艺术表演。”“最纯净、最杰出的艺术表演”,这个新概念一旦进入我的思想,便朝我在剧场中所感到的不完整的乐趣靠拢,并稍稍填补它的欠缺,而这种聚合形成了某种令人无比兴奋的东西,以致我惊呼道:“她是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呀!”人们可能认为我这句话不完全出自内心。我们不妨想想许多作家的情况:他们对刚刚完成的作品不满意,但是如果他们谈到一篇颂扬夏多布里昂的天才的文章,或者想到某位被他们引为楷模的大艺术家(例如他们哼着贝多芬的乐曲并将其中的忧郁与自己散文中的忧郁作比较),那么,这种天才的概念会充塞了他们的头脑,因此,当他们回顾自己的作品时,也将天才的概念加之于它们,从而感到它们不再是最初的样子,甚至确信它们的价值,并会自言自语说:“毕竟不坏嘛!”然而他们并未意识到,在使他们得到最后满意的全部因素中,还有他们对夏多布里昂的美妙篇章的回忆,他们将这些篇章与自己的作品相提并论,而前者并非出自他们之手。我们不妨想想那些虽一再被情妇欺骗但仍然相信她们忠贞不渝的人吧。还有一些人时而盼望一种无法理解的幸存——例如含恨终身的丈夫想到已失去的、仍然爱着的妻子,或者艺术家想到将来可能享受的荣誉——时而盼望一种使人宽慰的虚无——因为他们回想起过失,如果没有虚无,他们在死后必须赎罪。我们再不妨想想那些旅游者,他们对每天的日程感到厌烦,但对旅行的总体美却兴奋异常。我们不妨问一问,既然各种概念共同生活于我们头脑里,那么,在使我们幸福的概念之中,有哪一个不是首先像寄生虫一样从邻近的不同概念索取自己所缺乏的力量呢?
父亲不再提我的“外交官职业”,母亲似乎不太满意。我认为她感到遗憾的不是我放弃外交,而是我选择文学,因为她最关心的是用一种生活规律来约束我那喜怒无常的情绪。“别说了,”父亲大声说,“干什么事首先要有兴趣。再说他不再是孩子,他当然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恐怕很难改变。他明白什么是他生活中的幸福。”将来的生活幸福还是不幸福,暂且不谈,当晚我便由于父亲这番让我自己作主的话而感到烦恼。父亲突如其来的和蔼往往使我想扑过去亲吻他胡子上方红润润的脸颊,仅仅怕惹他不快我才不这样做。我好比是一位作者,他认为自己的遐想既然出于本人之手,似乎价值不大,但出版商竟然为它们挑选最上等的纸张,并且可能采用最佳字体来印刷,这不免使他惶惶然。我也一样,我问自己我的写作愿望确实如此重要,值得父亲为此浪费这么多善意吗?他说我的兴趣不会改变,我的生活将会幸福,这些话在我身上引起两点十分痛苦的猜想。第一点就是我的生活已经开始(而我每天都以为自己站在生活的门槛上,生活仍然是完整的,第二天凌晨才开始),不仅如此,将来发生的事与过去发生的事不会有多大差别。第二点猜想(其实只是第一点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我并非处于时间之外,而是像小说人物一样受制于时间的规律,而且正因为如此,当我坐在贡布雷的柳枝棚里阅读他们的生平时,我才感到万分忧愁。从理论上说,我们知道地球在转动,但事实上我们并不觉察,我们走路时脚下的地面似乎未动,我们坦然安心地生活。生活中的时间也是如此。小说家为了使读者感到时间在流逝,不得不疯狂地拨快时针,使读者在两分钟内越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一页书的开始,我们看见的是满怀希望的情人,而在同一页的结尾,他已是八旬老翁,正步履蹒跚地在养老院的庭院里作例行的散步,而且,由于丧失了记忆,他不理睬别人。父亲刚才说“他不再是孩子,他兴趣不会变了”等等,这些话使我突然间看到时间中的我,使我感到同样的忧愁,我虽然尚不是养老院里智力衰退的老头,但仿佛已是小说中人物。作者在书的结尾用极其残酷的、冷漠的语调说:“他越来越少离开乡间,终于永远定居乡间。”等等。
这时,父亲唯恐我们对客人有所指责,便抢先对妈妈说:
“我承认诺布瓦老头,用你的话说,有点迂腐。他刚才说对巴黎伯爵提问会不成体统,我真怕你会笑出来。”
“你说到哪里去了,”母亲回答说,“我很喜欢他,他地位这么高、年龄这么大,还能保持这种稚气,这说明他为人正直又颇有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