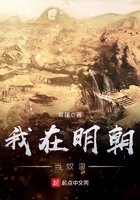那年夏天非同寻常,闷热难当。那年夏天,他们用电刑处死了卢森堡夫妇[1],而我,根本不明白自己来纽约干什么。对处决,我一无所知,想到电刑就直犯恶心。然而,整天报纸里读到的都是这件事——每个街角,每个冒着陈腐之气,散发花生味儿的地铁口,总有报纸的头版鼓起眼睛瞪着我。这件事跟我毫无关系,可我忍不住要琢磨电刑——活生生地,沿着你的神经一路烧过去,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啊!
我想,人世间没什么比这更惨的了。
纽约已经够惨的。暗夜弥散一股假冒乡村湿气的清新之意,刚到早晨九点便蒸发殆尽,犹如一场美梦的小尾巴。街道两旁,花岗石大厦林立,状若道道峡谷,而那谷底在阳光下热气蒸腾,灰蒙蒙犹如海市蜃楼。汽车车顶被烤得吱吱作响,发出闪光。煤渣般的烟尘,干巴巴扑进我的眼睛,钻下我的喉咙。
电台老在播送卢森堡夫妇的事,办公室里,同事们也议论不休。结果我无法把这夫妻俩从脑海中清除出去。头一回看到尸体之后,我也是如此。接连数星期,那具尸体的脑袋——准确地说,是那脑袋的残余部分——总漂浮在早餐煎蛋和火腿的后头,在巴迪·威拉德的脸后头,让我目睹那尸体就怪他。不久,我便觉得自己身上牵着条绳子,绳上系着那具尸体的脑袋,活像个黑黢黢、没鼻子的气球,散发着一股醋酸味儿。
我知道那个夏天自己不对劲。因为满脑子都在琢磨卢森堡那一对儿,琢磨自己当时该有多傻,才会买那么多价格昂贵,穿起来却难受的衣裳。这些衣裳挂在我的衣橱里,活像一条条死鱼。我悔恨交加,自己欢欢喜喜在大学里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小成功,怎么就在麦迪孙大街两侧一溜儿的大理石和厚玻璃墙外,咝咝地烧成了一场空!
照常理,我本该兴高采烈地享受这段时光。
照常理,我正被全美成千上万跟我一样的大学女生们妒忌眼红。她们满心只想跟我一样,在午餐时间去布鲁明戴尔百货[2]买一双7码的黑漆皮鞋,再搭配一条黑漆皮带、一只黑漆皮包,在纽约城里四处招摇。我们十二个人实习的杂志刊登了我的照片——照片上,我啜着马蒂尼鸡尾酒,上身是件袒胸露臂的银线仿缎紧身衣,下身是条蓬松犹如大团白云的白纱裙,站在什么星光大厅[3],被好几个无名小伙围在中间。他们都长着典型骨感的美国脸,或被雇用,或被借来,专为参加拍摄——谁看到这照片,都会以为我正心花怒放。
瞧瞧这个国家发生的奇迹吧,人家会说。一个穷丫头,偏远乡下生活十九年,穷得连本杂志都买不起。可倏忽之间,荣获奖学金念大学,这儿得个奖,那儿得个奖,终于有一天,居然玩转了纽约城,仿佛这座城市就是她的私人座驾似的。
其实,我什么都没玩转,连自己都玩不转了。只知闷头从酒店去上班,再赶着去参加聚会。从聚会回到酒店,再去上班,麻木往复,好似一辆无轨电车。我本该跟多数其他女孩子一样欢天喜地,可就是兴奋不起来。我内心死寂空虚,如同龙卷风的风眼,四周喧嚣迭起,而我无可奈何,死气沉沉跟着转。
我们一共十二个人,都住在这家酒店里。
我们都在一家时尚杂志举办的征文大赛中获奖。我们撰写散文、短篇小说、诗歌与时尚广告参赛。作为奖品,人家给了我们在纽约实习一个月的机会,包揽了所有开销,还提供一堆又一堆的免费福利,比如芭蕾舞演出的门票啦,时装秀的入场券啦,在一家昂贵的明星发廊里做头发啦,还安排我们与自己心仪行业里的知名人士见面,还指点我们如何根据肤色来打扮自己。
他们当时派送的彩妆盒,我至今还留着。这一盒专为褐色眼睛、褐色头发的人设计:一支方形的褐色睫毛膏,小小的刷头;圆圆的一小块蓝色眼影,刚够指尖轻轻一蘸;还有从粉到红的三色唇膏,都排在小小的镀金盒子里,盒子内侧还有镜子。我还留着一个白色塑料的墨镜盒,上面缀满彩色的贝壳、亮片和一个绿色的塑料海星。
我们收到的礼物堆积如山,只因为这是给生产公司免费打广告。我意识到了这点,但也没什么好愤世嫉俗的。天上掉下这么多不要钱的礼物,手舞足蹈还来不及呢。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它们都珍藏起来。再后来,病好了,我又把它们拿出来,至今屋子里还四处摆着。我偶尔也还用用那些口红,上周还把墨镜盒上的塑料海星剪了下来给孩子玩。
是的,我们一共十二个人,都住在酒店里。住在同一侧翼、同一层上的单人间里,一间挨一间,让人联想到大学的宿舍。这不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酒店——真正的酒店,应该是不分男女混住同一层。
这家酒店叫“亚马孙”,只接待女宾。其中多数是年龄跟我不相上下的女孩子,她们的父母财大气粗,却担心女儿会受男人的诱骗,就把她们送到这儿来。这些姑娘要么在凯蒂·吉布斯学院那种时髦高级的秘书学校上学,进课堂还得戴帽子、穿丝袜和戴手套;要么就刚从凯蒂·吉布斯学院那种地方毕业,给公司总裁们当秘书,在纽约无所事事混日子,伺机以待,好嫁个飞黄腾达的男人。
我觉得这些姑娘们个个百无聊赖。我看到她们在露台上,边打呵欠边涂指甲油,努力保持在百慕大度假时皮肤晒出的小麦色,似乎对一切都腻味透顶。我跟她们中的一个闲聊过,她口口声声自己腻味游艇,腻味乘飞机到处飞,腻味圣诞假期去瑞士滑雪,也腻味了巴西的男人们。
这样的女孩子至今让我恶心。我说不出地嫉妒她们。活了十九年,除了这次来纽约,我还从未踏出过新英格兰一步。人生中的第一个大好机会,我却坐着干等,任它像流水般穿过我的指缝。
我想,众多烦心事里,多琳得算一宗。
我从没结交过多琳这样的姑娘。她来自南部的一所专门培养社交名媛的大学,一头淡金色的蓬松长发,宛若一团棉花糖,萦绕着她的脑袋。一对蓝眼睛犹如透明的玛瑙,坚硬明亮,坚不可摧。而嘴边永远挂着一丝冷笑。我说的可不是那种尖酸的冷笑,而是一种开心的冷笑,难以捉摸,仿佛她身边的一干人等,个个笨头笨脑,只要她乐意,随时可以拿人家寻开心。
多琳一眼就把我挑了出来。她让我感觉自己比其他人聪明得多,而她的确幽默机灵。开会时她总坐在我旁边,到访的名人滔滔不绝时,她就悄悄压低嗓门,俏皮话、挖苦话,接二连三。
她说她的学校特别看重穿衣打扮,所有女生都专门挑选和连衣裙一样的料子来定做手袋,这样,每换一身行头,就都有合适的包包来配。这类细节让我大为震撼。从这里,我窥见了从不间断的奇妙精致的奢靡生活,这份奢靡,磁石一般吸引着我。
多琳只为了一件事对我恶语相向:我太舍得下苦功,总在期限前交稿子。
“这有什么好拼死拼活的?”多琳懒洋洋地躺在我的床上,她身披一件浅粉色的丝绸晨衣,用小砂锉打磨着自己被香烟熏黄了的长手指甲,而我正忙着打印一篇对一位畅销小说家的访谈稿。
这是我的另一宗烦心事——我们其他人都只穿浆过的棉布夏季睡裙、絮棉的家居便服,或者也能当泳装罩衣穿的厚绒布长袍。可是多琳,总穿着半透明的尼龙和蕾丝长睡裙,披着裸色的晨衣,晨衣还起静电,包裹着她的身体。她散发着一种难以名状、略带汗味的气息,让我联想起被撕下来揉碎后,香蕨木扇形叶子在指尖的留香。
“你晓得的,老杰伊·茜才不在乎你那稿子是明天交还是周一交呢。”多琳点起一支烟,缓缓翕动着鼻孔,烟雾弥漫,遮蔽了她的眼睛。“杰伊·茜丑得简直像犯罪。”多琳冷冰冰地说,“她那老丈夫靠近她之前,肯定先得把灯都给关了,不然绝对要吐。”
杰伊·茜是我老板,无论多琳如何贬损,我还是很喜欢她。杰伊跟那些贴着假睫毛,珠光宝气,招摇虚伪的时尚杂志编辑不同,她有真本事,脑筋灵光,长得虽不中看,却无伤大雅。她懂得好几种语言,认识圈子里每一位作家高手。
我试图想象杰伊·茜脱下刻板的套装,摘下午餐会必戴的帽子,光着身子和她肥胖的老公同床共枕的模样,可实在想不出。每逢想象男女同床的情景,我就彻底傻掉。
杰伊·茜想给我指点,认识的每一个老太太都想给我指点,但我突然觉得,她们没啥好指点我的。我把罩子合上打字机,“啪”的一声关上。
多琳咧嘴一笑:“真是个聪明姑娘。”
有人敲门。
“谁啊?”我懒得起身开门。
“是我,贝特西。你去不去酒会?”
“大概去吧。”我还是没开门。
他们直接把贝特西拉到了纽约,从乡土气息十足的堪萨斯州。她,还有她那把晃荡过来晃荡过去的金发马尾辫,以及那张甜美的大众情人脸。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她被一个下巴刮得发青的电视制作人叫到办公室,那人身穿细条纹西装,想看看从我们身上能不能挖掘些素材做节目。贝特西便扯起了堪萨斯的雄株玉米、雌株玉米,越说越起劲,那制作人听得都要哭了。可惜啊,他说,这些他做节目都用不上。
后来,《美人儿》杂志的编辑,劝说贝特西把头发剪短,还让她当了回封面女郎。我还不时看到她出镜,扮成家庭主妇,给B.H.雷格牌成衣打广告。
贝特西总问我想不想和她,还有别的姑娘一道,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出手相救似的。可她从没邀请过多琳。私底下,多琳叫她“马大哈女牛仔”。
“你跟我们一起打车走吗?”贝特西的声音从门那边传过来。
多琳摇摇头。
“不用啦,贝特西,”我说,“我跟多琳一块儿走。”
“那好吧。”我能听到贝特西脚步轻轻远去。
“我们去酒会上露个脸,待够了就走。”多琳边对我说着,边在我床边台灯的底座上拧灭了香烟,“然后去城里玩玩。他们安排的那些酒会,和学校体育馆里老气横秋的舞会没什么两样。他们干吗老找一帮耶鲁的男生来?那些男生蠢到家了!”
巴迪·威拉德在耶鲁念书,可我现在一想,他之所以不对头,就因为他蠢。哦,他考试成绩是不错,在科德角海滨度假时,还和一个讨人嫌的女招待眉来眼去,那女的叫格莱迪丝。可巴迪头脑不灵光,一点儿直觉都没有。多琳的直觉就很好。她每说一句话,都像我骨头里的一个神秘声音在发声。
我们被堵在了去剧院看戏的高峰车流里。我坐的出租车车头正挤在贝特西的车尾上,我后头则是其他四个女孩坐的车,整条街上寸步难移。
多琳真是美极了。她穿一条白色无肩带的蕾丝裙,裙子上半部的紧身胸衣收紧了她的腰,突显曲线,突显她丰满的胸和臀,夺人眼球。在苍白散粉之下,她的皮肤散发着古铜色的光泽。
我穿的一条山东绸紧身裙,花了四十美元。当时听说自己有幸入选去纽约,我就大手大脚,疯狂购物。这条裙子剪裁别出心裁,里头无法穿胸罩,不过无所谓。我瘦骨伶仃,像个男孩子,胸部几乎无甚隆起。炎热的夏夜,我也喜欢这近乎赤裸的感觉。[4]。当时听说自己有幸入选去纽约,我就大手大脚,疯狂购物。这条裙子剪裁别出心裁,里头无法穿胸罩,不过无所谓。我瘦骨伶仃,像个男孩子,胸部几乎无甚隆起。炎热的夏夜,我也喜欢这近乎赤裸的感觉。
不过,纽约城褪去了我皮肤上的日晒颜色。我皮肤发黄,简直像个华人。我老是因为裙子和自己奇怪的肤色紧张不安,可和多琳在一起,我就全然放松,一派自以为是,冷眼旁观的派头。
那个身穿蓝色格子棉衬衫、黑色便装长裤,脚踏刻花马靴的男人,一直朝我们的车里张望,他闲步从酒吧的条纹遮阳篷下朝我们走过来。无法自欺,我很清楚他是冲着多琳来的。他在堵塞的车辆之中穿行而过,倚到我们敞开着的车窗旁,魅力十足。
“我说,夜色这么美好,两位美人儿干吗孤零零坐在出租车里?”
他嘴巴大大咧开,牙齿雪白,笑得宛如牙膏广告。
“我们在去酒会的路上。”我脱口而出,而多琳忽然像根木头,一言不发,漫不经心抚弄着手包表面覆盖的白色蕾丝。
“听起来真没劲。”男人说,“不如跟我去那边的酒吧喝几杯怎么样?我还有几个朋友一道呢。”
他朝遮阳篷下几个衣着随便、懒散站立的男人点头示意。那几个人一直在观望这边,见那男人回头,立刻哄笑。
那笑声本该让我警觉的——猥猥琐琐,玩世不恭,充满讥讽。可车堵得毫无移动的迹象,我知道,假如不做反应,眨眼工夫我就会对错失探索纽约的良机而懊恼。我所见到的纽约,一直有板有眼,遵循杂志工作人员的精心安排。
“你觉得呢,多琳?”我说。
“你觉得呢,多琳?”男人咧着嘴,笑说。直到今日,我都想不起他不笑的时候到底什么样。他大概总在笑吧,笑成那样,对他来说,大概天经地义。
“好吧,也行。”多琳对我说。我打开车门。我们刚下车往酒吧的方向走,车流便开始向前挪动。
刹车尖厉地嘶鸣,接着是沉闷的碰撞声。
“嘿,你们两个!”出租车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气得脸都绿了,“你们想跑?”
他刹车刹得太急,后头那辆出租车轰隆擂了上去。我们看到车里的四个女孩手臂乱舞,挣扎着直起身。
我们站在马路边,而男人笑着回身走到车边,递给司机一张钞票,四下喇叭声震耳欲聋,还有人粗着嗓子叫喊。我们目睹杂志的同事们接连前行,出租车鱼贯而过,仿佛一条仅有伴娘的婚礼车队。
“来吧,弗兰基。”男人朝人群中的一个朋友说。这人小个子,一脸不开心,走过来和我们一起进了酒吧。
这种类型的男人我真受不了。穿上高跟鞋,我身高足有1.78米。跟小个男人站在一起,我就得稍稍弓着腰,屁股也撅得一高一低,好让自己矮一点。我尴尬难看,缩手缩脚,像给拉去出演滑稽戏似的。
刹那间,我做着美梦,盼望我们会按身高来配对。那样的话,我就能和起初搭讪的那个男人搭档,他身高超过1.8米。然而,他跟多琳并肩走了,瞧都没瞧我一眼。弗兰基贴着我的胳膊,我装作没注意,在多琳的身旁坐下,紧挨着她。
酒吧灯光昏暗,除开多琳,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淡金色的头发、白裙子,她仿佛是银子做的,吧台那边的霓虹灯也反射在她身上。我则觉得自己渐渐融入阴影之中,变成照片底片上从未谋面的某个人。
“我们喝点什么?”满脸笑容的男人问。
“给我来杯古典鸡尾酒[5]好了。”多琳对着我说。
点酒总让我晕头转向。威士忌和杜松子酒我都分不清,没有哪次能点到自己喜欢的。巴迪·威拉德和其他我认识的大学男生们,要么没钱买高度酒喝,要么对喝酒嗤之以鼻。那么多男生都不抽烟,不喝酒,真令人大跌眼镜。而我认识的似乎都属这一类。
跟我一起的时候,巴迪·威拉德买过一瓶杜邦内甜葡萄酒,这是他喝过的最出格的东西了。他这么做,不过为了显示自己尽管学医,但仍有美感,有鉴赏力。
“我要杯伏特加。”我说。
男人打量起我来:“里头加什么吗?”
“纯伏特加就好。”我说,“我从来只喝纯的。”
我想,要是说加冰,或加杜松子酒什么的,肯定显得傻气。以前见过一张伏特加酒的广告,雪堆之中放着一满杯伏特加,沐浴着蓝蓝的光。那杯酒清澈纯净,宛若冰泉。所以,我觉得喝杯纯的不会有事。那时候,我做梦都期盼,何时能点到一杯美味绝伦的酒。
侍者走过来,男人帮我们四个人都叫了酒水。这个酒吧都市气息十足,而这男人一身农场行头,举手投足轻松自在,我猜多半是个名人。
多琳一直不说话,摆弄着桌上木屑压制成的杯垫,过了一会儿,点燃一支香烟。那男人不以为意,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她——人们去动物园观赏罕见的白色金刚鹦鹉,也是这副模样,巴巴地盼那鸟突然开口,说句人话。
酒送上来了,我的那杯看上去当真清澈纯净,和广告上的别无二致。
沉默在我四周疯长,如同林中密集的野草。“你是做什么的?”我问那男人,试图打破沉默,“你在纽约做什么?”
男人缓缓地把目光从多琳的肩上移开,似乎煞费气力。“我是电台DJ,”他说,“你肯定听过我的名字——莱尼·谢泼德。”
“我知道你。”多琳忽然开口。
“那我真高兴,宝贝儿。”男人爆发大笑,“认识我,对你有好处。我名气大着呢。”
莱尼·谢泼德深深地看了弗兰基一眼。
“嘿,你是哪里人?”弗兰基猛然坐直,“你叫什么名字?”
“坐在这儿的是多琳。”莱尼的手揽过多琳光溜溜的臂膀,在上头捏了一把。
多琳仿佛完全没察觉,不见她有任何反应,我大为吃惊。她一味神情忧郁地坐着,一袭白裙,像个被漂白了的金发黑人女子,小口啜着她的酒。
“我叫艾丽·希金博特姆。”我回答,“从芝加哥来。”说完这句话,我沉着多了。我可不愿那一晚说的话、做的事牵扯到自己,也不愿说出我的真名和故乡波士顿。
“嘿,艾丽,我们跳个舞怎么样?”
这小矮子男人脚踩橙色的麂皮内增高鞋,身上的T恤小得出奇,还罩了一件松松垮垮的蓝运动外套——想到和他一块儿跳舞,我直发笑。要说我有什么看不入眼的,就数穿蓝色衣服的男人。黑色、灰色都好,就连棕色也过得去。蓝色,看着就想笑。
“我没情绪。”我冷冷一句,把身子侧过去背对着他,还把椅子往多琳和莱尼那边移了移。
而这两个人,此刻已亲热得如同老相识。多琳手持细长银勺,从玻璃杯底舀水果块吃。每次她把勺子移向唇边,莱尼又是埋怨低吼,又是猛烈咆哮,好似一头乞食的狗,想吃勺子上的水果。多琳咯咯笑着,只顾继续打捞水果。
我渐渐感觉,伏特加正中下怀。它味道寡淡,却直插胃部,犹如吞剑表演者手中的利剑,为我注满神一般的力量。
“我还是走吧。”弗兰基边说边站起来。
酒吧里头太暗,我看不清他的面孔,却发觉他的声音又高又尖又滑稽。谁都没有理会他。“嘿,莱尼,你还欠我钱呢。记得吗,莱尼,你不是欠我的钱吗,莱尼?”
当着我们两个陌生人的面,弗兰基催着莱尼还钱,岂非怪事?可弗兰基站着不走,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讨账,莱尼只好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大卷绿色的钞票,从里头抽出一张给了弗兰基。大概是十美元。
“闭嘴吧你,快滚!”
一时间,我还以为莱尼这话也是冲我来的。可我听到多琳说:“艾丽不去的话,我也不去。”她说我的假名字说得自自然然,我真佩服。
“艾丽会去的吧?对不对,艾丽?”莱尼对我眨眨眼。
“我当然去。”我说。反正弗兰基已消失在夜幕中,我宁愿跟着多琳,尽量长长见识。
我喜欢观察特殊时刻的人们。交通事故也好,街头械斗也好,实验室罐子里漂浮着的婴儿标本也好,我都会停下脚步,死命看,直到牢记得地老天荒。
就这样,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要是没有这个习惯,很多事可能与我失之交臂。哪怕眼前的景象使我吃惊,弄得我难受,我也从来不动声色,死命硬挺,假装自己一贯见多识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