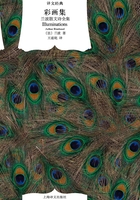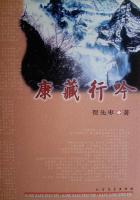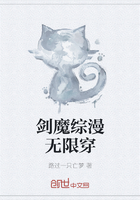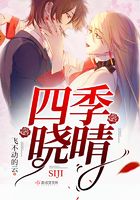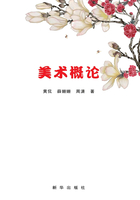在欧洲,凡是对日本电影多少有关心的人都知道日本电影里时代剧和现代剧是有区别的。在电影杂志和报纸的批评、介绍栏中有斜体的Jidaigeki-gendaigeki[20]这种非常流行的概念。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这种事的,也不知道发展过程如何。人们可以谴责我这种无知,说我曾对将日本电影介绍到海外的人们是多么傲慢,同时也可以唤起人们注意这些人的工作是多么孤立艰辛。不过,这现在不是我的主题。外国电影中有没有这种时代剧、现代剧之分呢?当然,与“日本电影”相对,“外国电影”这说法非常不严谨。如果是与日本电影位置对等,那么严格说来,应该一个一个国家地讲。不过,现在为了方便起见或者根据某种程度上人们的见解,这里所说的“外国电影”指美洲、亚洲和欧洲电影。这个意义上的“外国电影”中存在着像日本电影那样时代剧和现代剧的区别吗?恐怕不存在。因为正是不存在这样的区别,所以在叙述日本电影——主要是介绍的时候,人们才使用Jidaigeki-gendaigeki这个词。
当然,我论述的前提是承认日本电影中存在着时代剧和现代剧之分。不过,我发现外国电影里也不是没有区分相当于日本电影中时代剧和现代剧的电影。本文将就安杰耶·瓦伊达[21]进行论述,因此这里就举一个与他相近的例子。最近,我们终于能看到耶尔齐·卡瓦莱罗维奇的《法老》等电影了,这就是一部像时代剧的电影。换而言之,对我来说,外国电影中几乎所有以古代为背景及一半左右以中世纪为背景的电影都是时代剧。之所以慎重地将部分古代背景的电影排除在外,是考虑到比如说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一系列作品是否能算作时代剧;将一半左右以中世纪为背景的电影排除在外,是因为想到比如描写圣女贞德的卡尔·西奥多·德莱叶和罗伯特·布列松的电影。欧洲观众们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呢?当然,我知道那儿并没有一个“时代剧”认识框架。尽管如此,他们有这样一种区分范畴吗?对此的无知显然是由那些在日本介绍外国电影的人的傲慢引起的,应该加以谴责;同时,在远东一个贫弱的岛国里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必须承担着极大甚至令人绝望的困难,我们对此可能加以同情。但现在难道不正是我们传达真相的时候了吗?
我知道一个词——古装戏(costume play),如赛西尔·B.德米尔的作品就可以那么称呼。那么费德里科·费里尼的《爱情神话》又如何呢?在去年威尼斯电影节[22]上,我看完这部电影后说:“什么呀,这不是德米尔吗?”对此,《综艺报》的吉恩·莫斯科维奇一吐为快道:“如果是德米尔,他会让我们感到更愉快!”《爱情神话》究竟能否称得上是古装戏呢?或者能否叫时代剧呢?欧洲观众对电影分类并不感兴趣。电影类型的确存在,例如指南性质的手册上就明确地将电影分类介绍,戈达尔的作品常常被划入喜剧电影。但是,我至少在印刷品上没有发现时代剧和现代剧的区分。
我为什么要紧抓这个问题不放呢?比如,最近的黑帮电影到底是时代剧还是现代剧?如果去了欧洲,被一提起日本电影就将它分为不同类型的批评家们问到该怎么办?我想这种黑帮电影应该划入时代剧吧。最近,每到夏季都会有战争电影——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战中电影——出现,就像是严守规律的妖怪一般[23]。这些又该如何划分呢?在我看来,它们都是时代剧。如此说来,对我而言,所谓现代剧就是以战后日本为背景的电影。这是我的想法和感觉,这种想法和感觉异常吗?我不这么认为。我想,会有人赞同的。
让我们回到欧洲。一个欧洲观众在观看他们国家的电影时会给它们分类吗?我很想知道这一点。
写到这里,我的话题终于来到安杰耶·瓦伊达身上。我们日本人接触瓦伊达作品的机会太少了,一般能看到的作品有四部:《下水道》(1956)、《灰烬与钻石》(1958)、《无罪的巫师》(1960)和《二十岁之恋》(1962)。对他的作品介绍也很不足。佐藤忠男[24]曾前往波兰,对瓦伊达的《一代人》(1955)、《洛托纳》(1959)、《灰烬》(1964)和《一切可售》(1968)做过简要说明。我们通过阿多兰·陶利侬的著作[25]第一次得以了解瓦伊达的《参孙》(1961)、《西伯利亚悲情小姐》(1961)等作品。至于其余的《天堂之门》(1962)、《千层糕》(1968)、《驱逐苍蝇》(1969)、《战后的大地》(1970)等,我至今还不了解内容。但即便是大概了解的十部,我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是以过去为素材。其中以“二战”为素材的电影有五部,《灰烬》和《西伯利亚悲情小姐》讲述的是更遥远的过去的故事。完全以现代为题材的作品只有三部,即《无罪的巫师》《二十岁之恋》和《一切可售》。以我对电影的思考来说,瓦伊达是一个时代剧作家。当然,这是句玩笑话。欧洲人看瓦伊达肯定不一样。陶利侬说,在拍《西伯利亚悲情小姐》时,瓦伊达第一次放弃现代题材,面向过去。这种感觉可能是正常的。实际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以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为题材的《洛托纳》似乎也可以划入“面向过去的电影”范畴。但我没看过这部电影,无法下结论。
在前面这段很长的叙述中,我写了许多貌似大道理的话。其实,我想说的是,瓦伊达的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为什么在我的眼里是现代剧呢?这里面当然有严格的时间问题。《一代人》《下水道》和《灰烬与钻石》被称为瓦伊达的三部曲,拍摄、制作的时间是在1954至1958年间,可以推测当时战争还像现实一样存在于许多人心中。毋庸赘言,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非常鲜明的主题也存在瓦伊达的内心中。“二战”期间,瓦伊达才十三至十九岁。后来,他曾这样回答别人的提问:
佐藤忠男:(……)与你本人的战争体验有关联吗?
瓦伊达:……我有某种情结。……在德军占领期间,我与地下组织有联系,但并没有被关进强制收容所。当时,我刚好去了克拉科夫,没有参加华沙起义。可以说,我错过了那个时代发生的各种事情。我用作品填补了经历中所欠缺的部分。
波勒斯瓦夫·米哈维克:你经历了怎样的战争?战争期间,你在什么地方?
瓦伊达:……我几乎没有参加过抵抗运动。因此,我的战争经历很少。或许正因此,我想在电影中加以弥补。
不能完全相信导演说的话。不要以为他对别人说过同样的话,那就是真实的。不过,他对两个人说同样的话至少可以让我们明白这样一点:瓦伊达在心里已经暗自决定,针对这个问题他要这么回答。只有这一点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回答。一个是他的“战争经历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抵抗运动或地下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他回答中的“经历很少”或“几乎没有”也可以用“完全没参加”这样的说法来代替。按我的推测,可以说他可能就没参加过。但没用“完全没参加”这个说法,是因为他还是想参加来着。另一个是用作品来弥补这句话。话虽然很漂亮,但能用作品来弥补行为上的欠缺吗?这一点上,采访者的追问很不到位。显然瓦伊达本人也一定认为这是无法弥补的。他自身知道无法弥补的作为或不作为,可能成为创作的动机。
但是,仅仅以此动机能创作出作品吗?文学方面也许能,但电影却是做不到的,至少仅仅靠动机是绝对不可能创作出杰作的。过去无法弥补,这是我们面对历史的一种悔恨。对这种悔恨感觉最强烈的是瓦伊达。一般人在面对历史时,最多也只有受害者式的悔恨。我相信,在面对历史时,世界上的国家中波兰是具有最深切悔恨的一个。但即便如此,不,正因如此,一般人也只有受害者式的悔恨。这时,瓦伊达的抵抗运动和地下组织在面对历史时,没有任何作为的行为反而意味着他们具有发挥优势的潜质。尽管如此,这一开始也仅仅是一种悔恨,是一种甚至连受害者式的悔恨都称不上的悔恨。在罗兹的电影大学学习时,当人们叙述自己在战争中的体验时,恐怕瓦伊达悄悄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或许他至多也就开朗地说上一句:“我真的没有参加过战争。”
这种面对历史的悔恨在《下水道》《灰烬与钻石》中被以主体性的悔恨形式呈现出来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1956年发生了波及波兹南的去斯大林化运动、民主化运动,在这些运动中,这一次瓦伊达采取了主体行动吗?
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清楚,既没有文字记录,也没有语言叙述,连佐藤忠男也没有去追问过。我倒不是为了维护我所敬爱的佐藤忠男才这么说。在当时的波兰电影界可能存在着难以涉及这方面情况的某种氛围——我本人只在波兰待了几天就感觉到了。因此,在这种去斯大林化及民主化运动就像地下水流动般活跃期间,我们不清楚瓦伊达做了些什么。但完全可以推测的是,在此期间,罗兹电影大学和电影界毫无疑问是民主化运动的一个据点。1954年出现了几个称作“运动”的创作集团。此前一直由国家直接管理的电影制作开始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这标志着电影领域的民主化运动要比其他领域走在前面。当然,我们不清楚瓦伊达在这中间,特别是在政治上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但是,在1954年,以导演为首的演职人员到一部分演员全都是新人,“在不同的原则指导下,他们制作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新电影”(瓦伊达语),瓦伊达是“将电影当作他们的宣言书的一群人”(瓦伊达语)中的领袖。在此期间,瓦伊达毫无疑问起到了主体性作用。
实际上,这时如果瓦伊达明确地具有非斯大林式的,或更进一步说反斯大林主义式的政治思考,那他就走得有点过了。毋宁说,在从《一代人》到《下水道》再到《灰烬与钻石》的摸索过程中,他可能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反斯大林主义式立场了。倘若进行大胆的推测,或许在完成《下水道》后,即将开始制作《灰烬与钻石》前,他对政治的思考达到了一个顶峰。而且,当他站在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上时,波兰的去斯大林化、民主化运动正开始开倒车。就像是马契克紧紧抱住被击倒的斯祖卡[26]时在他们背后绽放的焰火一样,《灰烬与钻石》之所以美丽又悲伤,是因为对去斯大林化、民主化运动的倒行逆施感同身受的瓦伊达的内心有一股冲动。
也就是说,在面对1945年的一段空白时间里,瓦伊达将1956年自己面对历史的一切都奉献了出来,制作了《下水道》和《灰烬与钻石》两部电影。《一代人》是因此而情绪激昂的习作,《洛托纳》是一部令人感到悲伤的副产品。因此,包括后两部电影在内,它们完全就是现代剧,永远的现代剧,与每年盂兰盆节时像妖怪一样出现的日本战中电影截然不同。不过,我在这儿希望大家注意:瓦伊达制作的现代剧与某国拍着时代剧但认为其中有现代问题的导演绝对不一样。在作为素材的“过去”里存在着我们与历史的关系,这种关系和现在我们与历史的关系重复变换着——瓦伊达的电影就在这种情况中产生。不经过这样一个过程而制作出来的、以过去为素材的电影,无论作者如何强词夺理,也只是花架子。那是真正的“古装戏”[27]。
说起古装戏,我想起这样一件事。陶利侬曾引用普拉祖斯基发表在《电影手册》上的一篇文章,说:“瓦伊达故意让齐布尔斯基[28]穿上流行的窄长裤子。瓦伊达多次在他的想法中强调双重性的一面,也就是说,出场人物尽管坐在小酒馆的椅子上,但他不是喝上一杯带酒精的饮料,而是喜欢喝马基(抗德派)[29]队员水壶里的水。不过,瓦伊达又强调了主人公戴着1958年款浅色眼镜。”陶利侬虽然引用了这一段话,但他并没有理解这段话的含义。他只将这段话当作结果来接受。1945年的反革命抵抗运动者(语言上多么矛盾!)戴着1958年款太阳镜并穿着紧身裤——这不是结果,而是方法。瓦伊达将他的一切都押在这个方法上。
针对佐藤忠男的提问“波兰电影看上去好像在波兰派令人瞩目的活动后基本没什么动静了”,卡瓦莱罗维奇回答道:“他们有时能帮助人们制作出好电影,有时也会陷入危机。”这句话特别奇妙。我曾问过同样的话,也得到过同样的回答。对瓦伊达来说,波兰1958年之后的时间可能不是“帮他制作好电影的时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此后我只看过他的《二十岁之恋》一部电影。相反,这部影片在“现在”中加入了“过去”,是一部优秀的电影。我没有看过他其他电影,没有发言权。但是,看了他的影片之后,我切身感觉到瓦伊达的苦涩心情。
如果以当下的现代为主题,瓦伊达在面对历史时恐怕无法像1956年那样发挥主体性,会有局限吧。即使以战争为主题,那也是非常遥远的事情,恐怕《参孙》被人们批评为“冷漠”也很自然。以遥远的过去为素材拍摄杰作的新方法或许还没有为人们所发现。如此思考,我们可以从瓦伊达的影片志中明确看到他所面临的从内到外的困难。
“如果我是自己作品的制片人,经济能独立的话,我就能拍出第二部《一代人》和《下水道》了吧。”这是1963年1月4日发行的《世界》上发表的瓦伊达回答伊凡娜·芭比提问的谈话,十分悲壮。我们由此会想起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艺术家的命运。但是,作家决不能创作“第二个××”。我不会按字面意思完全相信这句话。瓦伊达的影片志虽然充满了绝望的苦涩,但他没有后退。我想尽早地观看到故事从兹比格涅夫·齐布尔斯基[30]死后开始的《一切可售》这部影片。由于1968年贝加尔莫国际电影节参展作品全都是“平庸的作品”,因此没有颁发带奖金的大奖。许多人为此提出激烈的反对意见,其中,马尔塞·马尔瑭在《电影1968》上大声疾呼:“此次评审委员会如果能评出‘平庸奖’就好了。这么说是因为参加竞赛单元的作品除了《忧郁的高卢人》(米歇尔·库诺[31]导演)和罗伯特·克拉莫[32]的《边缘》,《宴会与客人》(扬·内梅克导演)、《一个女子和另一个女子》也暂且不提,另外还有两部最好的未公开作品:瓦伊达的《一切可售》和日本导演大岛渚的《绞死刑》。什么叫平庸?!”或许有着这样的缘分,可能多少有点感情用事,我发现瓦伊达在《一切可售》后,以从未有过的快节奏连续拍摄了《千层糕》(1968)、《驱逐苍蝇》(1969)、《战后的大地》(1970)等作品。我以为这中间肯定有某种原因,十分期待。齐布尔斯基的死也许在瓦伊达的内心燃起了激情。对那种过早发现历史与自我之间关联的、引人注目的方法,瓦伊达一定在坚持做着两项工作,一是姑且否定之,另一是继续包容。瓦伊达说:“在波兰,对艺术家的要求比在其他国家要多得多。”这有时是荣耀,有时是重任。瓦伊达所处的地方既远离声势浩大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斗争,也远离资本主义国家一再受创却不断产生新突破向前发展的新左翼革命运动;如果没有发生比如1956年的去斯大林化运动、民主化运动——这是瓦伊达与之相关的运动,以快节奏坚持制作电影的行为就有着重大的意义:这里一定会诞生出“像宣告胜利的曙光般闪闪发光的钻石”来,而这是超越波兰国民要求的,甚至是远超波兰国家要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