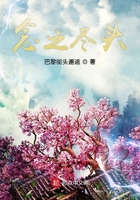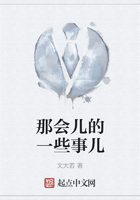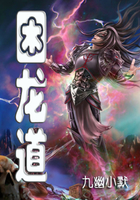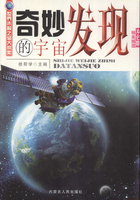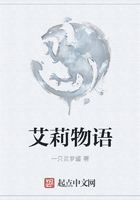01
一个已经几十年不见的人,有一天,突然在大街上与你劈面相逢;或者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有一天,突然成了你的故交挚友,然后你的人生像水遇到了水,或者像水遇到了火,开始出现莫名的变化。我相信,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大家都有。我也有。坦率说,本书就源自我的一次奇特的邂逅。
02
说起我的这次邂逅很有意思。
那是十二年前的事。十二年前,我是个三十岁还不到的嫩小子,在单位里干着很平常的工作,出门还没有坐飞机的待遇。不过,有一次,我们领导去北京给更大的领导汇报工作,本来,汇报内容是白纸黑字写好的,小领导一路上反复看,用心记,基本上已默记在心,不需我亦步亦趋。可临时,大领导更改了想听汇报的内容,小领导一下慌张起来,于是紧急要求我“飞”去,现场组织资料。我就这样第一次荣幸地登上飞机。正如诗人说的:凭借着天空的力量,我没用两个小时就到达北京。小领导毕竟是小领导,还亲自到机场来接我,当然不仅是出于礼仪,主要是想让我“尽快进入情况”。我刚出机场,跟小领导见上面,二位公安同志却蛮横地拦在我们中间,不问青红皂白,要求我跟他们“走一趟”。我问什么事,他们说去就知道了,说着就推我走,把小领导急得比我还急!路上,小领导一个劲地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又何尝知道呢?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次神秘的“带走”,要不就是错误的。我反复跟“二位”申明我的名字,是麦子的麦,家庭的家,不是加法的加。其实,我父母给我取名麦家,首先是孤陋寡闻,不知世上有麦加圣城之说,其次是出于谦卑,也许是要求我谦卑吧。因为,麦家的意思,说白了就是田地的意思,耕作的意思,农民的意思,很朴素的。
“二位”对我名字毫无兴致,他们说,管你是加法还是家庭,我们带的就是你,错不了的。听来有点不讲理,其实全是理,因为是有人有鼻子有眼地指着我喊他们来带我的,哪会有错?那喊他们来带我的,也是两个人,在飞机上,我们坐在同一排,听他们私下交谈,乡音不绝于耳,给我感觉是回到了自己远方老家。我也正是听着“两位”熟悉的乡音后,才主动与他们攀谈起来。殊不知,这一谈,是引火烧身,引来二位公安,把我当个坏人似的押走。
公安是机场的公安,他们是否有权扣押我,另当别论。这个问题很深奥,而且似乎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将如何脱身。公安把我和小领导一起引入他们办公室,办公室分里外两间,外间不大,我们一行四人进去后,显得更小。都坐定后,二位公安开始审问我,姓名、单位、家庭、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好似我的身份一下子变得可疑可究的。好在本人领导在场,再三“坚定又权威”地证明我不是社会闲杂人员,而是“遵纪守法”的国家干部。所以,相关的审问过去得还算利索。
接着,二位话锋一转,把问题都集中到“我在飞机上的所见所闻”之上,我一下子有点不知从何说起。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光荣坐飞机,“见闻”格外丰富、琐碎、芜杂,乱七八糟的,谁知道说什么呢?在我请求之下,二位开始有所指向地问我,其实,说来说去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飞机上从两位“小老乡”的私谈中听到了些什么。这时候,我才有所觉悟,我邂逅的两位乡党可能不是寻常人物,而我的这次不寻常的经历跟我听到——关键是听懂——他们之私谈直接相干。他们认为满口家乡“鸟语”会令人充耳不闻,就如入无人之境,斗胆谈私说秘,不想“隔壁有耳”,听之闻之,一清二楚。
于是,心存不安。
于是,亡羊补牢。
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没从他们嘴里听到什么骇人听闻的东西,他们并非一开始就说家乡话,我也不是那种“见人熟”,加上又是第一次坐飞机,好奇之余,又发现没什么好奇的,等飞机一拔上天,马上觉得无所事事,光傻瓜地坐着,自然戴起耳机看起电视来。我是在摘下耳机时才听到他们在说家乡话,一听到,就跟见了爹妈似的,马上跟他们套亲近,哪知道他们在聊什么。我这样说似有狡辩之嫌,但是天知地知我知,我绝非虚假。
事实上,想想看,如果我有什么不良企图,怎么可能主动跟他们认老乡?再说,既然我要认,又怎么可能听他们说了很久之后再认?再再说,既然我一听到就认,又怎么可能听到什么前因后果?虽说口说无凭,但平心而论,我的说法——没听到他们说什么——不是不值得尊重的。我的谆谆诱导没有枉费心机,又承蒙我领导极力美言,二位公安终于同意放我。不过,必须我保证一点:不管我听到什么,事关国家机密,何时何地都不得外传,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我自然是连连承诺,这才“一走了之”。
03
其实,又怎么能一走了之?
在以后的日子里,此事如团异物,常盘桓在我心头,令我神秘莫测又毛骨悚然。我不能想象,那两位乡党究竟是何等人物,有这般神秘的权威和秘密,连一句话都听不得?我要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但这样的“世面”没见过不说,而且打心里说,也害怕见。离开公安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从口袋里摸出两位乡党留给我的名片,撕掉,丢入垃圾桶里。机场垃圾桶。不用说,这名片肯定是假的,所以也可以说,它们本来就是垃圾。我那么希望丢掉它们,意义不完全是为了丢垃圾,而是我希望通过丢掉这玩意儿,把两位乡党可能给我带来的麻烦统统变成垃圾,见鬼去。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是个平民百姓,最怕出是非。
但我有种预感,他们还会找我。
果不其然,从北京回来不久,我就接到两位乡党的电话(我给他们的地址和电话是真的),两人轮流在电话上向我解释、问候、致歉、安慰,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们那边玩。说来,他们单位其实就在我们地区下属的一个县城郊外,也许是在山里。我以前便听说过,那县上有个大单位,住在山沟里,很神秘的,他们进山之后,县里就没有一个人再进过山,包括原来在山里生活的山民,都举家迁了居。正因如此,所以没有人能说得清,这到底是个什么单位。说法倒是很多,有说是搞核武器的,有说是中央首长的行宫,有说是国家安全机构等等,莫衷一是。这样神秘的单位,有人请你去看看,一般人都容易冲动,我虽然心有余悸,依然不乏冲动。却迟迟没有践行,大概还是因为“心有余悸”吧。
然后是国庆节间的一天,有人开车找到我家,说是有人要请我吃饭。我问是什么人,来人说是他们首长。我说你们首长是谁,他说你去就知道了。这话跟机场公安说的一样,我马上敏感到可能是我的那两位神秘乡党。去了,果然如此,同时还有另外几个满口乡音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总共七八个。原来,这是老乡间的一次聚会,年年如此,已经开展五六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了我。
至此,可以说,我与本书已建立起一种源头关系,以后的事情都是水到渠成。
04
本书讲述的是特别单位701的故事。
“7”是个奇怪的数字,它的气质也许是黑的。黑色肯定不是个美丽的颜色,但肯定也不是世俗之色。它是一种沉重,一种隐秘,一种冲击,一种气愤,一种独立,一种神秘,一点玄想。据我所知,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一些担负某些特殊使命的组织似乎都跟“7”有关,如英国的皇家七处,前东德的七局,法国总统的第七顾问,前苏联的克格勃系统的第七研究所,日本的731部队,美国的第七舰队等。说到中国,就是特别单位701,这是我国仿效前苏联克格勃第七研究所而组建的一个情报机构,其性质和任务都是“特别的”,下面有三个“特别的”的业务局:
侦听局
破译局
行动局
侦听局主要是负责技术侦听,破译局主要是搞密码破译,行动局当然就是行动,就是走出去搞谍报。侦听,就是听天外之音,无声之音,秘密之音;破译,就是解密,就是要释读天书,看懂无字之书;谍报,就是乔装打扮,深入虎穴,迎风而战。在系统内部,一般把搞侦听的人都称为“听风者”,搞密码破译的人叫作“看风者”,搞谍报的叫作“捕风者”。说到底,搞情报的人都是一群与风打交道的人,只是不同的部门,打交道的方式不同而已。
我的两位神秘乡党,其中一位是当时701的一号首长,姓钱,人们当面都喊他叫钱院长,背后则称钱老板;另一位是行动局的一名资深谍报人员,姓吕,早年曾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人称“老地瓜”,就是老地下的意思。两位都是“解放牌”的革命人物,年届花甲,在701算得上是硕果仅存者。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与两位乡党关系渐深,使我有机会慢慢地演变成701的特殊客人,可以上山去“走一走”。
山叫五指山,顾名思义,可以想见山的大致构造:像五个手指一样伸在大地上。自然有四条山沟。第一条山沟离县城最近,大约只有二三公里山路,出得山来,就是该县城关镇:一个依山傍山的小山城。这条山沟也最宽敞,701的家属院便建在此,院子里有医院、学校、商店、餐馆、招待所、运动场地等,几乎是一个小社会,里面的人员也是相对比较繁杂,进入也不难。我后来因为要写这本书,经常来采访,来了往往要在招待所住上几天,几回下来这里有很多人都认识我,因为我老戴墨镜(我自二十三岁起,右眼被一种叫强光敏感症的病纠缠,在正常的白炽灯光下都要戴墨镜保护),人都喊我叫墨镜记者。
后面三条山沟是越来越狭小,进出的难度也是越来越大。我曾有幸三次去过第二条山沟,第三条山沟去过两次,而第四条,也就是最里面的山沟,一次都没去过。据说,那里是破译局的地盘,也是整个山上最秘密的地方。行动局是在第二条山沟里的右边,左边是培训中心,是个副局级单位;两个单位如一对翅膀一样依山而扎,呈扇形张开,但左边的扇形明显要比右边大。据说,行动局平时没几个人,他们的人大多“出门在外”。
第三条山沟里也有两个单位,一是侦听局,二是701机关,两个单位的分布不同于行动局与培训中心——面对面,相对而立,而是分一前一后,前为701机关,后为侦听局,中间地带属双方共享,都为公用设施,如球场、食堂、卫生所等。
因为无乡民进得了山,山上的一切无人糟蹋,年复一年,现在山上树木郁郁葱葱,鸟兽成群结队,驱车前往,路上经常可以看到飞禽走兽出没。路都是盘山公路,发黑的沥青路面,看上去挺不错,只是过于狭窄,弯道又多,很考司机手艺。据说,山体里有直通的隧道,可以在几个单位之间快速来回。我第二次去侦听局时,曾提议钱院长是不是可以让我走一回隧道,老头子看我一眼,未予理睬,好像我这个要求过分了。
也许吧。
不过,说真的,在我与包括院长在内的701人的接触过程中,我明显感觉到,他们对我的心态是比较复杂的,表面上是害怕我接近他们,骨子里又似乎希望我接近。很难想象,如果只有害怕,我这本书将如何完成。肯定完成不了。
好在还有“希望”。
当然,更好在每年还有“解密日”这个特殊的日子。
05
我要说,作为一个特别单位,701的特别性几乎体现在方方面面,有些特别你简直想不到,比如它一年中有个特殊的日子,系统内部都管它叫“解密日”。
我们知道701人的工作是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但职业本身具有的严密保密性却使他们自己失去了甚至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以致收发一封信的自由都没有,都要经过组织审查,审查合格方可投递或交付本人阅读。这就是说,若你给他们去信,主人能否看到,要取决于你在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如果你的言谈稍有某种嫌疑,主人便可能无缘一睹。退一步说,即便有缘一睹,也仅是一睹,因为信看过后将由组织统一存档保管,个人无权留存。再说,如果退回二十年,你有幸收到他们发出的信(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比较小,除非你是他们直系亲人),也许会奇怪他们为什么会用复写纸写信。其实,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们投出的信件组织上必须留下副本;在尚无复印设备的年代里,要让一份东西生出副本,最好的办法无疑是依靠复写纸。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他们离开单位时,所有文字,包括他们平时记的日记,都必须上交,由单位档案部门统一代管,直到有一天这些文字具备的密度消失殆尽,方可归还本人。
这一天,就是他们的“解密日”。
这是一个让昔日的机密大白天下的日子。
这个日子不是从来就有,而是起始于一九九四年,即我邂逅两位乡党后的第三年。这一年是钱院长离任之年,也是我初步打算写作此书的年头。由此不难想见,我写作此书不是因于结识两位乡党,而是因于有幸迎来了701历史上未有的“解密日”。因为有解密日,我才有权进山,去山沟里走走,看看。因为有解密日,701人,严格说是获得解密的人,才有资格接受我的采访。
不用说,若没有解密日,便不可能有此书。
06
我的身份无关紧要,我说过,这里人都喊我叫墨镜记者。我的名字叫麦家,这我也是说过的。我还说过,生活中,邂逅一个人,或者邂逅一件事,这是常有的事。我认为,有的邂逅只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一种形态,一种经历,一点趣味而已,并不会给你的生活创造或带来什么特殊的不同,但有的邂逅却可能从根本上把你改变了。现在,我忧郁地觉得,我与两位乡党的邂逅属于后一种,即把我从根本上改变了。现在的我,以写作为乐,为荣,为苦,为父母,为孩子,为一切。我不觉得这是好的,但我没办法。因为,这是我的命运,我无法选择。
至于本书,我预感它可能是一本不错的书,秘密,神奇,性感,陌生;既有古典的情怀,又有现代的风雅,还有一点命运的辛酸和无奈。遗憾的是,最支持我写此书的人钱院长已经去世,无缘一睹此书的出版。他的死,让我感到生命是那么不真实,就像爱情一样,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完蛋了。鸡飞蛋打,什么都没有了,生变成了死,爱变成了恨,有变成了无。如果说,此书的出版能够给他的亡灵带去一点安慰,那即是我此刻最大的愿望。
此书谨献给钱院长并全体70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