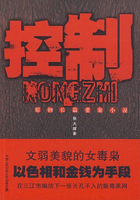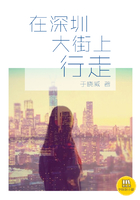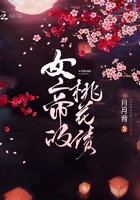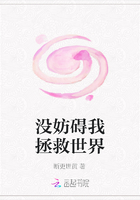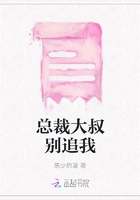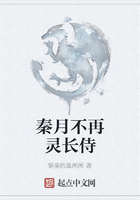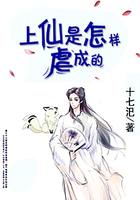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日,党的“十二大”胜利闭幕。
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了。各地报纸纷纷报道当地领导人大张旗鼓传达贯彻“十二大”的消息,全国热气腾腾。可是河北的报纸上,始终没见第一书记露面,就是从外地传来的高扬的讲话中,也没有在什么“指引下”、“照耀下”之类穿鞋戴帽的话。这使某些习惯于按常规思维的同志很不安:作为第一书记,这么大的事,连个态度也没有……合适吗?
态度是有的,它写在河北的大地上。
高扬并不一般地反对开会传达,他只知道目前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开会表态。“十二大”文件已在报上公布,关于传达学习,中央已有要求,他在会议闭幕的当天即召集本省代表做了布置。可是“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在河北怎样实现?河北工农业“翻番”的路子在哪里?
他必须迈开双脚,到河北的大地上去寻找。“十二大”之前,省农委曾建议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这样的会议,如果不是闹派性的耽搁,是早该开的。但是高扬发现关于会议的设想重心不明,路数不清。与其急急忙忙开一个不深不透的会,莫如晚一些,待准备充分之后,开一个卓有实效的会。于是“十二大”一结束,在返回石家庄的途中,他就沿路对易县、保定、定县进行了调查。之后又由石家庄南行,一头扎进了太行山。河北省有五个地区二十四个县处在太行山的怀抱里;主要发源于太行山的海河水系横贯河北大地,左右着全省农业的命运。耀邦同志一九八二年四月视察河北时曾经预言:太行山的面貌不改变,河北要翻身是困难的。高扬决心先啃下这一砣。
太行山,母亲般的山。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她用自己的乳汁养育了人民的军队。“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教儿打东洋”,从这里走出多少优秀儿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高扬受党的派遣,由山西进入太行山,在穷苦农民中间建立党的组织和抗日政府、抗日武装,先后担任过中共河北省邢台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冀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晋冀豫特委宣传部长,与太行人民甘苦与共,度过了整个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一九八二年六月,他到河北上任的第二天,一位老同志去看他时,他说:“快四十年了,走过多少地方,还是常常想到这儿……”现在,高扬象三十七年前告别太行打回东北老家去一样,重又踏上了这片热土……十月七日,当高扬一行十八乘坐的奶油色“面包车”驶出石家庄的那一刻,太行腹地簸箕楼峰脚下的槐疙瘩村上,六十七岁的李占林老汉正在家里手忙脚乱。女儿李绪书刚才风风火火跑进门,说:“爹,省里高书记到赞皇来了!县里让我来接你哩!”
“他可是真来了?”前两个月,从省里回来的人捎信儿说,高书记有空要来“老家”看看,可他说来就能来吗?李占林口里问着,手早不知做什么好了,找衣服,找蝈子。没扣上扣子就跟女儿上车了。
赞皇县委的干部们都在招待所门前等着。人们间他,“老李,你还能认出高扬同志不?”“能……咋不能!”虽是这么说,心里可没底儿。四〇年前后,槐疙瘩是冀西地委的驻地,他是村长,又是党员,他的家便成了地委和八路军的“公寓”,高扬和许多同志都在他家住过。四十年了,谁知还能不能认识呢?
下午四点钟,“面包车”到了。车门一开,一位身着灰色制服,蓄着雪白寸发,戴白边眼镜的老人探出身来。
李占林不由叫了一声:“就是他!”说着蹒蹒跚跚地奔过去,拉住高扬的双手,问:“老高,你还认得我不?”高扬热烈地摇着李占林的双手,笑道:“我还能不认识你呀!”“你可老了……”“是呀,都老了。”两位老人四只手握在一起,走进会议室,坐下来了,还不忍松开……这天,除了和赞皇县委的同志谈工作以外,高扬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交给了李占林。老兄弟俩饭桌上边吃边说,吃过饭边走边说,晚上高扬听完县里的汇报,已经九点多了,李占林忍不住又去了。他们有说不完的话。
“两位老人还健在吗?”那是两位亲同父母的老人,当时有的年轻同志干脆在这儿认了干娘。
“都没了。”
“几个孩子?住的是老屋还是新屋?日子过得怎么样?”
“你不用结记,都比早年强了。”
“那棵黑枣树还在吗?”
“五八年砍了……你还记得哩?”
“啊……”高扬遗憾地说,“那棵树的枣没核儿。”
它立在李占林家几亩薄地的中央,高扬闲时常在那里帮着干活儿。那年月,家有一棵枣树是能救命的呀,换盐吃,换布穿,没粮时,抓俩枣儿也能顶顿饭。
李占林越说越亲,恨不能把几十年的事儿都倒腾一遍。高扬问他以后都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时候退休的,一提这话,老汉眼圈红了。“文革”前他在县里当过畜牧局长、区委书记,七〇年在干校,人家一句话就打发他回来了。临走那天,连个送的人也没有,离家几十里路呢!他夹着铺盖在路边发憨,幸亏有个熟人帮他拦了一辆山西拉煤的卡车,捎了他~段,这才摸黑赶到家。说着,老汉落泪了。
一旁,女儿李绪书忙制止说:“爹,别说这了!”高扬说:“让他说吧。说出来也好消消火,心里痛快点儿。这些年,老干部都受了不少委屈。”
该说的说了,该问的问了,第二天高扬进山去调查,还要亲眼看一看槐疙瘩,不然他心里总不踏实,仿佛他在那里失落了什么。
已是深秋时节,太行山敞开了丰饶的胸膛,慷慨地把财富赐给自己辛勤的儿女。地里的庄稼大半已经收割,路边的柿子也变黄了,农民的脸上洋溢着喜色。毕竟是变了。山沟里有了水库和电站,过去有马也只能牵着走的傍山栈道,如今通了汽车。曾经牺牲了我们几十名战士的长沙村,就在路坡下,如果不是李绪书指点,他已认不出来了……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他希望多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以便唤起那深沉的记忆;又希望一切都变得认不出来……奋斗了几十年,为的不就是这个变化吗?
望着山坡的杂树,他问李绪书:“你说说什么树的叶子能吃?”
高扬住槐疙瘩的时候,李绪书不过四、五岁。那时候地委和八路军干部们每天只有十二小两粮食,还要节余四两救济群众,即便这样,高扬每次从食堂领回的那一份儿,还要分给孩子们一些。如今留在李绪书记忆里的,只有“当当当,吃包包”这句童谣了,因为只要挂在树上的炮弹皮一敲响,她就有菜包包吃。这种亲如一家的感情,如今又被唤醒了,因此她已没有生分的感觉。她调皮地反问高扬:“你说什么树叶能吃?”高扬数点着:“杏叶能吃,杨叶能吃……”
李绪书接口说:“柳叶、柿叶也能吃。”
高扬说:“柿叶可涩呀!”
李绪书说:“是涩,可六〇年也吃了。”
高扬没言语。六〇年,他知道。那时他下放在贵州,和老百姓过的是一样的日子。他不想让后辈人都记得这件事,只愿老同志不要忘了那段教训。
他的目光在山坡上寻找着什么。“怎么看不见羊群啊……”他说。想必当年他是经常看见的,那里有送鸡毛信的孩子,有“王二小放牛郎”。
“‘文化大革命’把羊群都‘砍’了。”李绪书说。
高扬对这一类的回答似乎不大甘心。他仍在寻找。汽车转过一个弯儿,他忽然兴奋地指着前面:“看,我看见羊群了!”
李绪书看了看,对他说:“伯伯,你看花眼了,那哪儿是羊群呀,那是禁坡——封山育林,在石头上刷的白灰。”
“哦……”历史真是太无情了。
槐疙瘩到了。他们下了车,踩着杂木棒子搭成的小桥,过了乱石滚滚的槐河。乡亲们从一家一户跑出来,高扬亲亲热热地和他们握手,打招呼,好象“反扫荡”之后又回村时一样。仔细一打量,已经没有几个认识的人了。
如今五十几岁的老汉,当年也不过是儿童团里的角色。拥挤在狭小山洼里的大部分还是老房子。顺着七高八低的小巷,他还能找到李占林的家。他住的那间只有三根椽子宽的小南屋去年已经拆了,其它三面的老房子还在。他抚摸着墙上的石头,在狭小的院子里端详了许久,“变化不大呀”他说。
周围的几座山,旮旮旯旯他都去过。当年山上的树就不多,如今更少了。“还是穷啊。”坐在门前的蒲墩上,他对社队的干部们说,“这么大的山场,总要发展点什么。种点酸枣总可以吧?干不了别的,用它闹个擀面杖、梳头栊子也好啊!”
许多人都有旅游的经历。作为共和国的普通公民,我们可能会为雄险奇绝的山峰所倾倒;可能面对青碑占庙发一番思古幽情;可能被山区的变化引出一腔感叹,或者对山沟的落后和贫困发一通牢骚;此外,也可以利用山里人的闭塞和诚实,攫取一点廉价的山珍。之后,就可以扬长而去了。我们只是普通公民。可是,假如你是这一方土地的“衣食父母”,你是对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呢?你会是怎样的心情?
“面包车”继续南行。走到赞皇与临城县交界的地方,隔一架大山,那边就是著名的八路军后方基地蝎子沟了。当年,那里有我们的军械所、被服厂、医院,地委也在那儿住过。那是被许多革命者视为“家”的地方。“能过去吗?”高扬问。
“还没通公路呢。”前来迎接的邢台地委的同志答道。
“通电了没有?”
“也没有。”
闭塞,在敌强我弱的游击战争年代,曾经是我们赖以坚持和发展的条件;今天看来却是那样难以忍受。在车上,人们讲了这样几件事:蝎子沟的农民卖一口猪,要八个人抬着,走一天才能送到公社。孩子上学要走十八里路。公社的干部去蹲点,采取抓阄的办法,不然谁都不肯去,因此那里的老百姓很少见到生人。一九八一年地委新来的书记对县里的同志说,他要到蝎子沟去看看老百姓,蝎子沟的人们听到信儿,就整天盼。一天,果然来了个穿制服、提皮包的人,全村人象过节似的,好酒好菜招待,干部整天不离左右。过了两三天,总不见这人做指示,光打听皮毛行市。问他:你是不是地委书记?他说:“我是进山来买皮子的……”
这是个笑话,却谁也笑不出来。“解放三十多年了,老百姓还过这样的日子怎么行!”高扬有些激愤。他对邢台地委的两位同志说:“请你们无论如何要去一趟,别让他们再失望了!公路、电,要限期解决!那里有两千多口人,也该有个学校、卫生所、商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