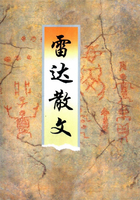现在,我刚刚翻完这部名为《飞向太空港》的长达二十万字的书稿,脑海里“星”“箭”乱飞,满眼皆是黑白。我不得不闭目凝神,企望以此来进入一种“思想”的境界。然而……
又是那个夏日。那个夏目的中午。
灿烂的阳光折射在布满了李鸣生那床头墙角的关于火箭卫星的彩色图片上,氤氲出几许“高科技”的气氛。李鸣生在递给我一个雪花梨的同时,抛出了一个新鲜名词:星空乡愁。他脸上随即浮现出迷茫而遥远的神色。他回忆说:大约是在我三岁的一天傍晚,我肚子实在饿了,可妈妈迟迟不见回家,我只好到路边等。等呀等呀,天渐渐黑了,星星们一个挨一个地亮起来。我抬头望着,突然觉得它们就像妈妈的乳头,在不停地向我闪着诱惑的眼睛。我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想亲近它们的冲动,就像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渴望投入母亲温暖的怀抱的那种感觉。从此,在我和星空之间就滋生出了一种莫名其妙但又深刻有力的情感维系。我常常喜欢独自一人仰望星空;望着星空,我的心中马上就会被一种遥远而又亲近、陌生而又熟悉的情愫涨满,既有怅然迷惘的失落,更有刻骨铭心的神往。似乎冥冥中有神在召唤:回到这儿来吧,这儿是你最古老的故乡。在我听来,这是对整个人类的呼唤。我记得有个外国人就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认为差不多也是一句神谕——他说:“人,不同于猪的地方在于,他要不时地抬起头来仰望星空。”我把人们凝眸星空时生发的这种难以名状的柔情愁绪称之为“星空乡愁”。这种概括也许不准确,但这种情绪我认为是人类共有的,只不过是有人意识到了而有人没意识到或意识强弱的程度不同而已。你有过这种体验吗?
(我翻动眼睛,略做回忆之后,似是而非地晃了晃脑袋。)
我由此进一步联想起另一个问题——李鸣生接着说——我的问题是,当第一个猴子从地上站立起来时,地球上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了梦;那么,人类的第一个梦又是什么呢?当然,这是个荒谬的问题,但确实又是个迷人的问题。让我很费了一阵琢磨。在一个似睡非睡的夜晚,我终于以梦的形式完成了对这个关于梦的难题的猜想。我梦见一位远古人类祖先仰面躺在夏夜的林中草地上目醉神迷于那满天繁星和一勾明月。突然,一只美雉呼啦啦冲天而起,华丽的彩羽也就煽动了这位人类祖先想象的翅膀。他的肉体沉沉睡去,他的思想却缓缓起飞……他做了一个梦——一个飞天梦!
(这真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梦中梦,玄而有味。我赞曰。)
玄吗?其实也不玄。李鸣生继续发挥。全人类各民族的远古神话都是人类飞天梦的文字表述。几千年来,人类飞天梦不仅不死,而且一天比一天更生动、更现实。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标志人类第一次挣脱了地球的束缚,跨进宇宙的大门,从此开始了神奇而迷人的航天时代。
李鸣生激动地站起来,伸出手臂列宁式地比划了一下,做划时代状,转而用更连贯流畅更专业化的语言侃下去——迄今为止,在我们头顶上空昼夜飞旋的卫星已多达3442颗。真可谓茫茫宇宙,星满为患。已故现代航天之父布劳恩早在二十年前说曾预言:“21世纪,将是在外层空间进行科学活动和商业活动的世纪,是载人星际飞行和开始在母星地球之外建立永久性人类立足点的世纪。”事实上,美国总统里根在1984年初就将开拓宇宙空间列入国家战略目标,并命令建立一个永久载人空间站,并计划在1992年送入太空。实践证明,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人类离宇宙母亲的怀抱已越来越近。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母星——地球已伤痕累累,岌岌可危而不堪重负。人口、资源、环境、粮食、能源五大绳索已深深勒进它的脖子。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已成为未来的急迫主题。开拓天疆,走出地球村,是五十亿人的共同使命。宇宙空间必将是人类明天的归宿,更加美好的第二故乡。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对此深信不疑。你呢?
(李鸣生突发提问,我猝不及防只好如实招来:我对此毫无研究,我对此半信半疑。)
李鸣生并不在乎我的信与不信,继续在他的思维轨道上做惯性滑行。他开始踱来踱去。他说,于是,我就老在想,自从人类在地球上站立起来以后,就开始从这一端走向那一端,从地面走向地下,走向海洋,走向高山;不管走到哪里,足迹到处,几乎都有了文学的反映。那么,人类走向太空走向宇宙这一革命性的关乎人类明天的伟大壮举是不是也应该或者说更应该有文学的反映呢?就譬如说在我国,可以有乡村文学、都市文学、军事文学等等,可不可以再来一个“航天文学”呢?而且,作家们都在寻根,寻找自己的优势或寻找自己的位置,那么我的位置又在哪里?我想是不是就在这里,我这一辈子就来做好这一件事,做好这一个梦,一个航天文学之梦。
说完了,李鸣生也平静了,坐下了,两眼直怔怔地望着我,像期待着什么。
这下轮到我站起来了,我奔到他跟前比比划划地侃开了。具体侃了些什么现今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把那天明媚的阳光侃得渐渐暗淡下去了……
是的,相比较而言,“星空愁”也罢,“飞天梦”也罢,都不仅仅是属于李鸣生的。而且,我在这两方面的知识和研究都等于零——人置于星空下的情感究竟如何,我从未细察过,还有待于在某个月明风清之夜去仰望一番、体验一番。至于人类的航天活动到底仅仅是出于人类永无止境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的驱力的一种纯科学实验与探险行为,还是果真关涉到明天全人类的星际大迁徙的革命性壮举,我不敢妄加臆测,姑且存疑。我比较有把握可以说的是,航天文学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也是一件能引起我极大兴味的事。单单就生活层面与文学题材拓展的意义论,航天文学就是站得住的。何况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么多内涵和外延都不甚精确严谨与科学的文学旗号,再扯起一面航天文学的大旗又有何不可?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无论怎样说,航天事业都是迄今为止整个人类最尖端的高科技活动,它集中体现了全人类的聪明与智慧,最高限度地代表了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和挑战的勇气与努力。它将可能造福于人类的广泛性、深刻性、当代性与未来性,恐怕都是别的事业所难以比拟的。它的重要性、超前性与神秘性在当今信息社会的时代里已越来越显示出它(作为文学题材)的分量与价值。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写它,而是如何写好它和由谁们来写的问题。
李鸣生当然可以而且应该是这个行列中的一分子,或者说已经是一个捷足先登者了。航天文学的梦想首先就是属于李鸣生的,而李鸣生也是属于这个梦想的。他们之间的双向选择关系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十七年前,当一列军车拉着那个年仅十八岁的四川小伙隆隆驰向西昌那块土地的时候,一个神奇的梦和它的梦者就已经遇合。
十七年来,李鸣生的航天文学之梦和着西昌这座中国的航天城一起长大成熟。十七年间,他在那里打过山洞,当过计算机技术员和宣传队创作员。他是西昌航天事业飞速发展的目击者、建设者和讴歌者。80年代以来,他就陆续发表了《编写生命程序的人》、《独腿高工》、《航天情》、《航天女》、《月亮城的风采》、《火箭今晚起飞》、《中国卫星司令》、《燃烧的翅膀》等“航天人”系列报告文学、小说数十万字。如果说,在报告文学作家当中有一类是专靠采访写作,而还有一类则是与他所报告的对象具有某种“血缘”联系的话,那么李鸣生正是后者。他是一个有“根”的报告文学作家。他首先是一个航天人。他对航天人的那种理解、对航天事业的那份挚爱,仅仅靠采访是得不到的。这就保证了他能敏锐地及时捕捉住任何一次成功的机会。于是,当我国定于1990年4月7日将在西昌运用“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为国外发射卫星——“亚洲一号”的消息一经发布,他立刻就进入了“临战状态”,兴奋得不可遏止。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当天来系里请假时斩钉截铁地说过一句话:我家里出了天大的事我都可以不请假,但是这次的假,我请定了!
于是,他感动了我们,他成功了——“1990年3月30日上午,我从北京气喘吁吁地登上了飞往成都的飞机。当晚10时许,又爬上了成都去西昌的91次特快列车,开始了闪电式的采访。”
于是,时隔半年之后,我读到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飞向太空港》。
可以预见的是,这部作品将以它锐新的观念、崭新的题材、密集的信息和流畅简练的文笔,以及起伏跌宕的情节和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关于它可能得到的种种好评,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听到。在这里我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较之于李鸣生过往的全部创作,《飞向太空港》无疑实现了一次新的飞跃。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李鸣生首次成功地对一个大型事件进行了全景式的驾驭与表达;二是李鸣生突破了事件本身的局限,力求运用一个超越事件的“高视点”对事件本身进行观照与思考。前者保障了扫瞄的广度,后者提升了立意的高度。
应该说,我国运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美国卫星“亚洲一号”确实是1990年度中轰动中外的重大新闻,它标志着我国航天技术已经拥有了打进国际卫星发射商业市场的雄厚实力与尖端水平。但它的意义又决不仅止于航天领域与科技方面。它的影响力还反射与波及到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诸多方面。从中西方最高决策人,到西昌地界少数民族的平头百姓;从“发射窗口”的气象拼图,到国际舞台的政治风云;从乌可力诸君往返穿梭的洲际游说,到“亚洲一号”的总统待遇的远行;从火箭发展的“欧亚大陆怪圈”,到“中国箭”与“美国星”的苦恋与结合……真是上下三千年,纵横九万里,千头万绪,纷纭复杂,要理出个子丑寅卯何其难哉!
波澜壮阔的大画面迫使李鸣生不得不升高视角,第一次从他的生活基地——西昌跳出来(他前此的全部创作基本上都是拘囿于西昌版图上的“区域作业”),从对“亚洲一号”的仰视到平视再到俯视,广泛采访人事,大量占有资料,了然于胸,烂熟于心;再以“亚洲一号”为织梭,牵引千经万纬,流贯而出,一气呵成;不刻意于结构,却把一幅长卷的布局处理得自然顺畅,从容舒展,疏密相间,张弛有致。这充分表露了李鸣生吞吐与消化大吨位题材的气魄与潜能,是他不断实现宏伟的“航天文学”梦想的一个好兆头。与这种大构架、粗线条基本相适应的是他的简练的不拖泥带水的跳跃的行文。尤其是作为序章的“本文参考消息”,寥寥几则简讯便把当今世界的航天大态势和“亚洲一号”的发射大背景做了一个强劲的推出,真可谓开篇不凡,先声夺人。可惜的是,这种创意与气势并未能贯彻下去,否则,我们读到的这部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将会是另外一副更加新人耳目也更加卓尔不群的魅人面貌。而且,行文也“粗”,忽略进行一些更精细和更见文采的局部描写,以致缺少了一些不应该缺少的精雕细刻的华彩乐章(譬如说发射景观的壮丽图画)。
要看清一个大事件,需要有一个相应高度的观察视角;而要想清一个大事件,同样需要有一个相应高度的思想视点。李鸣生清楚地意识到,面对着“亚洲一号”跨国界的飞行这样一次国际闻的高科技合作行动,仅仅驾轻就熟地沿用自己惯常的或歌颂奉献精神、或弘扬艰苦创业精神、或升华爱国主义精神等思路来进行观照与涵盖,都恐怕是不能够全面和有深度的。他肯定是在对事件的不断介入与不断思索的过程中逐步唤醒与沟通自己的“星空乡愁”和飞天梦想的玄思,最终豁然明朗和树立起簇新的意识或观念,即“我们都是地球人”,也就是一种超越“地球村”的所谓“宇宙意识”,一种终极关怀于人类明天的生存与发展的超前观念。从这样的意识与观念出发,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航天事业看成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把开拓天疆视为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中国箭”与“美国星”经过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弯道终于走到一起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人类的福音。“亚洲一号”的联合发射不过是东西方人民携手合作创造空间文明、走向明天的一支小小的序曲。当然,今天距离明天实际上还是十分遥远的,简直可以不夸张地说,遥远如天上的星辰。关于这一点,在作品的第五部“我们都是地球人”中尤见得分明。从西方专家在中国西昌的土地上发生的那些诸如“伦巴、探戈与辣椒、蒜苗”、“有车不坐要骑车”和稀里糊涂地用汉语唱“跑马溜溜的山上,学习**好榜样”等故事中,人们不难感受到,双方在文化积淀、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有着多么巨大的迥异与落差。这也是作者的一种隐忧和他面对世界发出的一种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