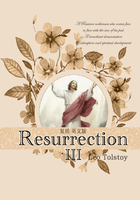“忍字忍,饶字饶,忍字没有饶字高,人不能抓住别人的错不放。婆子想了,娶个媳妇多不容易呀,把她抓走了,谁还给她家当媳妇,叫她孩咋弄?兴许吓她一回她能改哩。从那以后,媳妇不敢那么欺负婆子了。几年后,婆子死了。又过几年,媳妇也死了,埋在婆子的坟边上。晴天白日的,这边埋人的刚走,还没有走出地边哩,‘咔嚓’一个大炸雷,把媳妇的坟劈开,天上下来一条龙,抓了媳妇就飞天上去。”
“龙王爷把她抓走弄啥呀?”
“弄啥?投到地狱叫她受罪,十八层地狱里的罪,排着受一遍。”
讲着讲着,身边就慢慢围上一群人,讲着讲着,下地的人也回来了,凑上来听。大人也都跟小孩一样,这瞎话听季瓷讲了无数遍,还是碰上了就要听完,不听完不走。有人就笑着对罗北京说:“叫你听哩,叫你听哩。”罗北京呵呵笑笑,挖了面端着面盆进灶火去了。季瓷对围着的人说:“不光叫她听哩,叫你们这些做媳妇的都听听,也叫男女老少都听听,做人不能坏良心,一坏良心早晚遭报应,可别想着没人看见,老天爷啥都能看见……中了,中了,都散了吧,回去做饭去,下回听我讲个再烈不能夺人碗。”
夏天一打雷,西芳就害怕,钻到季瓷怀里,季瓷给她说:“不怕,龙王爷只抓干坏事的人。”
“那我上回在队里菜园偷摘了个茄子,龙王爷看见了没?你看这雷打得这么响,是不是来抓我的?”
小小的西芳常常感到心里不舒坦,尤其是雨天的时候,她不能出去玩,在家里看季瓷和罗北京做针线活。下雨天罗北京不出工,和季瓷坐在堂屋门口,一人靠住一边门扇,季瓷把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说,像院子里的雨水不停地淅淅沥沥。西芳和津平在竹床上玩,在东里边、西里边钻,玩着玩着西芳就会扔下津平,缠磨到季瓷身上,猛然蹦出一句话:“奶奶,我心里可不舒坦。”季瓷把几十年前的人或事抛到一边,眼睛还是看着手里的活:“咋个不舒坦法?哪疼?我给你揉揉,哪痒?我给你挠挠。”
“也不疼,也不痒,就是心里不舒坦。”
“你那是作祸哩,吃饱饱的,还有啥不舒坦的。”
罗北京停下手中的活,迷蒙的大眼睛认真地看看西芳的脸。
“你是不是看这雨下个不拾闲儿,心里怄得慌?”
西芳点点头。罗北京大眼睛向她眯起来,笑一笑:“人都这样,天一晴心里就好受了。快了,下了两三天,该晴了。给你二分钱,戴上麦帽,去代销点买几个糖恁俩吃吃吧,一吃就好了。”西芳跑到门后抓麦帽,津平闹着也要去,罗北京说:“地上滑,摔倒了,在家等着,叫你姐去买回来,你吃了,多好的事。”西芳穿上罗北京的大胶鞋,拖拖拉拉地从院子里走出去。
“娘,叫我看,西芳这闺女跟别的小孩不一样,心里道道多,小小的能看懂大人的脸,得哄着她来,顺着她来。”
“唉,我就知是这,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这样的人一辈子都活得比旁人累。”
西芳一个人走在雨地里。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她搞不明白的事,春天来的时候,油菜花开茄子花开秦椒花开桐树花开柿树花开,它们咋就各开各的,不会忘了或者弄错了开成旁的样子,咋就每年准确无误地开成自己的样儿,该开时候开,该落时候落,该结果子的时候它们就忙忙排排地都结了,谁叫它们这样的?奶奶说是该热不热五谷不结该冷不冷五谷不等,为啥不等?等一等又能咋?奶奶过几天梳一回头,把长长的稀疏的头发从右边脖子弄到前边来,拿木梳梳,再用篦子篦,梳得光光的再盘起来在后边绾个疙瘩鬓,把梳下来的头发捋到手里,缠成一小团塞到墙缝里,等着找头发换针的来。她突然想,人的头发在长出来之前,是不是在头皮里盘着,那得多乱啊,人一跑一跳,晚上睡到床上头转来转去,把头皮里面那一团弄乱了怎么办?弄不好我的头皮里已经是乱糟糟一堆了,那可咋办啊?她总为这些事发愁,这就是她常说的心里不舒坦。
吃了糖的西芳,半天之后又陷入那种不舒坦之中,那是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心像在鏊子上焙着,像在石灰水里浸着,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可能天晴了会好,长大了会好。
老天爷是不是把天下漏了,雨咋都停不住。人也都不上工,在自己家窝着,勤快的乘机干家里的活,懒的连天彻夜睡觉。实在没事的,就来季瓷这儿听她说瞎话。漫长的雨天,心里实在没个捞摸,便一个个戴着破麦帽,披着沉甸甸的蓑衣,来到她家的堂屋里,听那听过几十回的瞎话,来得晚的没有蒲团坐,就骨堆到地上,靠着两扇门,靠着桌子腿。
“今儿说个坏媳妇夺人碗吧。”季瓷把手里的麻整好,一缕缕放在腿上,理得多了,再一根根续上去,搓成细麻绳。家里有外人的时候,她就不补她那些破衣裳了,怕人笑话。
“这回是南乡的媳妇,心铁得很,她嫁来这一家,前边留下俩小孩,她是当后娘的。人当了后娘,就要对前面留下的比对自己生的还亲。你想啊,你自己生的有亲爹热娘,可人家前边撇下的,看着你们搂住自己的孩小乖乖小能豆地亲,心里啥味?她可不,有点好吃的就把那俩拿话支出去了,有了活就把自己的俩哄出去玩了。这也就罢了,你还可以说是你的俩孩子小,大的让着小的,也算说得过去。可她看前面那俩总是不顺眼,不是撅就是打,最可恼的是有一回那个大孩正在吃饭,她不知为啥在那撅哩,越撅越气,伸手上去把他的碗夺下来了。恁想想恁想想,世上再赖再铁的人,咋能夺人饭碗哩?”
有听众已经开始抹眼泪了。就像是西芳总要打断季瓷一样,总有那几个人在这个时候开始抹眼泪。回回都有罗北京,回回都有瓦片。
“那小孩他爹哩?他爹咋不管管?就叫这后娘这样?”西芳也同样没忘记她的职责,及时打断。
“他爹有他爹的事,在外当官哩,挣钱哩,养家哩。”
“你说的瞎话儿咋都是男的不在家哩?”
“那要是都在家,当时就管住她不叫她装孬了,我这瞎话儿还咋编哩,咋讲哩。你听不听了?”季瓷又假装生气地问,停下不说了,看了看屋里的人,又看看外面的雨,“天爷呀,你真要把天下漏,这世上又出赖人了不成?恁又生气了?”
“听,听,咋不听,说吧。”西芳把身子拧成个麻花,缠到她腿上。
“听哩,听哩,快点说吧,都张嘴瞪眼听着哩。”别的人说。
“前面撇下的孩也十来岁了,懂事了,想这样在家不中,他到亲娘坟上磕了头,给自己兄弟说,你且在家忍着,小心行事,别惹娘生气,我出去给咱挣功名,挣了功名回来接你走。这孩问邻居叔叔大爷们借了几个钱,出去找了个地方,下苦读书。一考考了个进士。他想,娘再不对,可她也快老了,也该享两天福了。买了油馍馃子回来看他爹娘和兄弟,恁猜猜咋?在家门口碰见一个瞎老婆子,不但眼瞎,嘴还烂,话也说不成,手也抬不起。仔细一看,正是他那后娘。当年他走后,他爹从外边回来,问他儿哩,后娘编排他,说他不听话不服管,偷了家里的钱自己跑了。这是老天爷给她的报应,叫她眼瞎嘴烂手不能端碗吃不成饭,一天进一点稀汤汤。她想死还死不了,她上吊绳就断她投井水就干,就天天这样熬着,活活受了几十年罪。”
门外的雨冷冷地下着,屋里没有一点声音。她每回讲完这个瞎话儿,听的人都不出声,只吓得四处看。
西芳又想听又害怕,想起那瞎眼烂嘴,比龙来抓还怕人,可她过几天就想听,听了后就在心里搜肠刮肚地想我有没有对人操坏心的时候。
屋后自留地里的柿树长了几搂粗,成了村里最大的树。年年夏天,柿树挂上黄色的小花,清早,和西芳一般大的小孩子跑到树下,捡拾掉在地上的柿花,回到家里,拿绳穿个圈,早饭后,脖上统一挂了柿花的小孩们又在大柿树下疯跑着玩。
柿树是西芳家的,西芳身上穿着西安买的衣裳,西芳兜里猛不丁就能掏出一块从西安买回来的糖,西芳说,站好了,排好队,一人咬一小块我手里的糖。小孩们就赶快排好队,西芳手里捏着那个咖啡色的话梅糖,每个人凑上来咬一口,糖越来越小,西芳的手被小孩子的唾沫、鼻涕沾得湿乎乎的。西芳对那个流鼻涕的说,下回把你的鼻涕擦净了再来,要不,不得吃糖。
西芳很快成了村里小孩的权威,最多的时候身后跟着十来个。她开始给他们上课,她让爷爷在家里找了个一面刷蓝漆的三合板,是那年章守信从西安带回的,一直放着没用。章守信给那上面穿了两个眼儿,挂上绳,就是西芳的小黑板了,还给她用小木条刮了个教棍。西芳又叫奶奶去学校问老师要几个粉笔头,季瓷也就扭着小脚去了。大柿树下坐了一片小孩叫西芳教他们识字,识得好的,可以咬一口西芳手里的话梅糖,“咯嘣”一声咬下来,高兴地坐回自己位置上。几根铅笔,一个钻笔刀,这就是西芳的全部财产,她把铅笔分给大家轮流用,几个人合用一支铅笔,钻笔刀由她保管,谁要用了举手请示,她从兜里掏出来,让人家在她的监督指导下把笔削好,她再装回兜里。
“谁要是这学期表现好,我把这块小皮囊奖给他。”西芳的手里举着一块粉红色的香橡皮,“可香了,都来闻闻。”她把那块香橡皮在每个人的鼻子下放一小会儿。孩子们个个抓住她的手,贪婪地闻。
“这皮囊是弄啥用的?”最小的孩子问。
“擦字的,这都不知。你拿铅笔写字,写错了就用这皮囊擦,擦干净再写,皮囊就越擦越小,最后就没了。”一个小女孩说。
“啊,这么好的皮囊,咋能就没了?咋能用它擦字哩?”
“皮囊就是用来擦字的,要不就不叫皮囊了。”
“既然它早晚都是要没有的,那为啥把它还弄那么香,那么好看,谁舍得用它擦字?”
小孩们都不说话,看着西芳手里那块皮囊。
“要是大家都表现好哩?你这块皮囊咋分?”最小的小孩问。
“那就拿刀切开,一人一小块吧。”又有人说。
“肯定有一个最好的,我来选,我说了算。”西芳手里握紧那块皮囊。
孩子们早早晚晚围在西芳身边,白天吃了饭就有人跑来,帮着她拿凳子,拿三合板。有的晚上喝了汤还要来,有的就提出叫我再看看那块皮囊,再闻闻。
西芳心里越来越难过,因为她不知道怎样分这块香皮囊。孩子们一个比一个表现好,对她万分忠诚,她在他们面前说一不二,眼看她承诺的“这一个学期”就要到了。傍晚,她一个人坐在柿树大树冠的外边,痴痴地向西边看。
五六岁的西芳常常在傍晚的时候坐在土坡上看夕阳。按说除了晚上睡觉,孩子们是不给她独处时间的,她说,下课了,你们回家吧,我想一个人坐会儿。孩子们不愿走,围绕她身边,她生气,你们还说要表现好,你们也不能老缠着我吧,你们都不想要香皮囊了?孩子们“哗”的一下散了,但并不走远,躲在柿树后边,躲在菜园子里,远远地看着她,而她,捧住脸,看着天边的夕阳一点点、一点点落下去。这日头是不是落在西安了,是不是刚好落在爸爸妈妈那儿,它把人砸住了压住了可咋办?她知道妈妈去西安后又生了个妹妹,还寄回了相片。爸爸常给爷爷写信,寄东西回来,听说西芳跟着罗北京认了好些字,他就寄回了铅笔、橡皮,还有本子。
西芳突然跳起来,往家里跑。孩子们不知咋回事,也跟着跑回她家。西芳扯住正在院里骨堆着搓绳的爷爷说:“爷,你给俺爸写封信,叫他给我寄回来二十块香皮囊。”
章守信只管搓绳,呵呵笑笑:“好闺女,你爸爸上回寄来的你还没使完哩,咋又要,还要那么多?”
从堂屋拿了蒜臼出来的季瓷说:“你要那么多弄啥?熬胡辣汤喝呀?那东西闻着香,可不能吃哩。”
章守信只当她是胡闹,又“呵呵”两声,只管搓绳。
“我有用哩,你快写吧,快点。”她夺爷爷手里的绳。
“哎哟哎哟,这闺女这么大的劲,你叫我把绳搓完,就是写也得明儿天明了写呀,这会儿黑灯瞎火的,看不见。”
“点上灯,点上灯不就看见了。”她猛地一推,章守信一屁股坐到地上,赶忙用手撑住地,在地上坐稳了,两只手拍着土,还是那样呵呵地笑:“这闺女,说啥一声,哪有那么快的事呀?我得找钢笔吧,得找信纸吧,得找信封吧,还得有时间去白果集上买了邮票,送到那绿箱子里吧……”
“别给她说那么多了,喝汤。”季瓷在灶火门口喊,“想法气人,你明年才上学哩,这会儿要那么多皮囊弄啥,再气人就不搭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