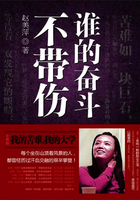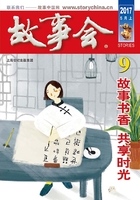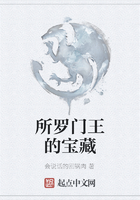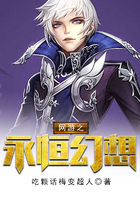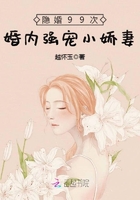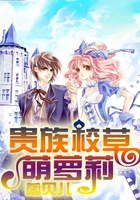第十六章 “短剑”千里追杀 叛国者终进铁窗
瓦努努把以色列的核机密卖给了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把以色列的天给捅了一个大窟窿;摩萨德派出“短剑”小组千里追杀,将他抓捕回国判了18年徒刑;刑满释放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对那些认为我是叛国者的人说,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和欣慰”。
被解雇的“危险分子”
内厄姆·艾德莫尼出任摩萨德第六任局长后,还干了一件让世人震惊的大事,那就是把泄露国家机密的以色列前核物理学家瓦努努捉拿归案。
瓦努努1954年出生在摩洛哥的一个犹太家庭,他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20世纪60年代初,在摩萨德向以色列偷运移民时,瓦努努一家从摩洛哥历史古城马拉喀什搬到了以色列,定居在贝尔谢巴的一个贫民区。瓦努努的父亲靠做一些小生意勉强维持全家的生计。
瓦努努长大成人后加入了以色列工兵部队,成了一名下士。后来,他就读于特拉维夫大学,但因一年级物理考试不及格而退学。21岁时,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广告,是以色列的迪莫纳核研究中心在招收“受过训练的技术员”。瓦努努一见,马上呈交了一份求职报告,他很快被录用了,在迪莫纳核中心接受了速成训练。两个月后,他通过了考试,被秘密地送到了迪莫纳核研究中心。来到迪莫纳核研究中心后,瓦努努按要求在一份保密宣誓书上签了名。该宣誓书的条文规定,凡向任何人(包括同事)泄露其在迪莫纳工作情况的人将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在迪莫纳中心,瓦努努本来会像别的工作人员那样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地工作,然而,性格上的变化使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第一次变化是他与自己的宗教传统彻底决裂。出身于东正教家庭的瓦努努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断绝了与家人的一切联系。
第二次变化是发生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瓦努努本来与众多的摩洛哥移民一样,是一位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信仰贝京和他的利库德集团,主张对阿拉伯人采取强硬政策。但是,他在贝尔谢巴大学哲学系读书时,结交了很多阿拉伯民族的同学,成了贝尔谢巴大学附近的左翼团体的活跃分子,他甚至曾经申请过加入以色列共产党。在贝尔谢巴大学读书时,有许多老师因为拒绝去阿拉伯被占领土服役而遭到了监禁,于是学生们就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以色列当局释放那些老师。瓦努努也参加了这次运动,并且表现非常积极,表现出了一种愤世嫉俗的意识。
同时,瓦努努在大学里还是一位出了名的怪诞人物。有一次在校园里的晚会上,他在表演音乐喜剧时竟然跳起了脱衣舞,当时的情景还让他的同学给拍摄了下来。同时,他还给艺术系的学生当过裸体模特。他曾经和巴勒斯坦的大学生一起打着标语牌,参加过各种抗议以色列政府的活动。当时贝尔谢巴大学的校报上还引用过瓦努努的话——“停止迫害阿拉伯人”。
瓦努努的所有活动和思想言论,引起了以色列情报机关的注意。1985年,迪莫纳核研究中心的一位安全官员曾经警告过他,要求他按照研究中心的要求,检点自己的行为,尽量保持沉默,至少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中抛头露面,或者惹是生非,恣意生事。瓦努努虽然受到了警告,但他仍然一意孤行,我行我素,于是迪莫纳核研究中心便决定开除他。为了避免事情被张扬出去,酿成一种丑闻,核研究中心并没有正式宣布瓦努努为“危险分子”,而是悄悄地在内部对他作了处分,同时向他支付了解聘费。于是在1985年,瓦努努就和另外180 名工作人员一起被迪莫纳核研究中心解雇了。
瓦努努被解雇之后,卖掉了他的旧汽车和小公寓,然后长途跋涉来到了远东地区旅行。在那里,瓦努努对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目标进行了自我反省。
核机密卖了5万美元
瓦努努于1986年5 月抵达澳大利亚的悉尼。在一个犹太教“安息日”的晚上,他信步向有灯光的地方走去,推开了圣·约翰的安利坎教堂的大门。两个月之后,瓦努努终于迈出了他具有决定性的一步——皈依了天主教。瓦努努的这种人生的改变和宗教的选择,不仅是同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家庭出身彻底决裂,而且是与自己的国家以色列作出了彻底的决裂。
来远东旅行的时候,瓦努努的兜里装着一件小小的纪念品,不过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但是,当他与一位古怪的哥伦比亚人相识之后,他便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这一秘密。那个哥伦比亚人名叫奥斯卡·格雷罗,是一位很不安分守己的自由派记者。格雷罗当时由于失业而在当地的一座教堂做油漆工,给这座教堂涂刷栅栏。瓦努努就是在这时候认识了他。交往了数周之后,两个人成为了无所不谈的知己,颇有相见恨晚之意。不久,这位以色列人就向他的这位异国朋友吐露了埋藏心中已久的秘密。
一天晚上,两个人坐在草坪上聊天。瓦努努神秘地对格雷罗说,自从离开以色列后,他就一直携带着两卷彩色胶卷,但不知怎么样处理才好。因为格雷罗曾经是一名记者,对于胶卷这样的事情当然既熟悉又敏感。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犹太人一定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他就迫不及待地问瓦努努,是什么样的胶卷。
当瓦努努说这是他在迪莫纳核中心上夜班时偷偷拍摄的照片时,格雷罗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作为自由派记者,这位哥伦比亚人本能地产生了获利的欲望。他没有问瓦努努是如何将照相机偷偷带入迪莫纳核研究中心,又是如何将胶卷带出以色列的,而是马上想到,这个瓦努努即将会成为一只生出金蛋的母鸡。
格雷罗马上告诉他,他的经历完全可以卖钱,而且是可以卖一大笔钱,终生享用不尽。格雷罗这个想法对瓦努努立刻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他仿佛听到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那句经典的咒语。经过与自己良心的较量,他最终认定以色列的秘密是不道德的,应当予以揭露——于是,他终于念出了那句“芝麻,开门吧!”
经过一番策划之后,格雷罗将自己指定为瓦努努的“文字代理人”,他们一道与数家国际出版机构联系,表示愿意提供一条耸人听闻的内幕消息。但是他们所到之处却没有一个人相信,眼前的这个瓦努努竟然曾经是以色列核工程的一名工作人员。美国的《新闻周刊》杂志和澳大利亚当地的大小报纸都拒绝购买他们讲述的故事。最后,他们找到了一家愿意让他们试一试的买家,那就是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这家报纸决定给他一次机会。
《星期日泰晤士报》是出版业巨头鲁珀特·默多克经营的一张自负盈亏的报纸。澳大利亚就是鲁珀特·默多克的出生地。鲁珀特·默多克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将他的一位资深记者彼得·霍纳姆派往悉尼,以便与这位以色列人会晤并且评估他那奇特的故事的真伪。霍纳姆曾经获得过物理学学位,具有这方面的鉴别能力。他以一位行家的眼光同瓦努努和格雷罗进行了多次交谈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肯定了这个犹太人的故事绝不是“天方夜谭”。他又仔细看了瓦努努的那些照片,更让他大为震惊。
于是他就向瓦努努开价5万美元,独家刊登他的故事和那些照片,最终出版一本书。霍纳姆把他的想法向报社进行了汇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老总也同其他具有商业头脑的出版商一样,觉得那个格雷罗夹在中间是个多余人,就很想摆脱这个所谓的“中间人”。于是,彼得·霍纳姆就以“有必要将瓦努努和他的照片带往英国作进一步的调查”为由,把那个格雷罗给甩开了。
1986年9 月11日,瓦努努和霍纳姆从悉尼飞往伦敦,格雷罗到机场为他们送行。这时瓦努努并不想和格雷罗分手,就对他说:“三个星期后我一定回来找你。”但是令瓦努努和霍纳姆没有想到的是,格雷罗等到他们的飞机起飞后,却乘坐了另一架班机跟随他们来到了伦敦。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老总和那些编辑们都十分清楚,现在他们手中掌握的就是一枚以色列的“原子弹”。如果这颗“原子弹”真的能够爆炸,一定会震惊这个世界。
瓦努努让《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老总和编辑们看了那些照片,然后对他们说,这60多张照片都是自己亲手在以色列的迪莫纳核研究中心拍摄的,有的还是在一栋被他称为“麦昌2 号”的大楼内拍摄的。
说到“麦昌2 号”,瓦努努神秘地告诉他们,在迪莫纳核研究中心的2700名雇员中,只有150 人持有进入“麦昌2 号”的安全许可证,而他就是其中之一。他进一步透露,为什么“麦昌2号”会这么神秘呢?就是因为“麦昌2号”是个地地道道的地下核炸弹制造厂,它就在内盖夫大沙漠底下。
那些照片清晰地显示出“麦昌2号”鲜为人知的秘密。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它那深入地下六层的详细草图,还可以看到局部的走廊、实验室、储藏室以及控制面板的画面。在一组仪表的上方,有一个清晰的希伯来文标牌,表明这里是“第九十五小组”。瓦努努对那些英国编辑说,那里有很多这样的工作小组在承担分离一种放射性元素钋的工作,所以照片中有用希伯来文写的“放射性”警告牌。有的照片上还有一种金属的球体,瓦努努说这些都是炸弹模型。
瓦努努声称,有资格进入“麦昌2号”的人,除了以色列国防军的那些高级军官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外,另外就只有以色列总理。其中有一个地方是迪莫纳核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都熟悉的地方,叫做果尔达阳台——当年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就是站在那里观看下面的生产车间的。
此时,《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那些人完全相信了瓦努努所提供的那些照片和他描述的真实性。因为他所说的这一切,同当年法国的一些报道完全吻合。而以色列的迪莫纳核研究中心就是法国人帮忙建造的。“麦昌2号”就是当年法国派往以色列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挖掘的,那些制造核弹的设备也是由法国人安装的。
瓦努努所提供的照片和一些数据还表明,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法国提供的26兆瓦反应堆显然已经被以色列人提高到150兆瓦。瓦努努的情报有力地证实了一些外国政府和它们的情报机关的怀疑以及国际新闻媒体的报道,以色列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已经远远超出其所承认的核能力。同时他们也确切地知道了,以色列迪莫纳核研究中心额外使用的铀,一部分是从美洲的纽梅克公司搞来的,另一部分则是在1968年从地中海上的“普卢姆巴特”号劫获的。
《星期日泰晤士报》请来了英国的一些核工业专家和物理学家研究那些照片,最终证实犹太人瓦努努并没有撒谎。然而就在这时,那个让《星期日泰晤士报》想甩开的所谓的“中间人”格雷罗,做出了一件让瓦努努本人和《星期日泰晤士报》都想象不到的事——在没有获得任何一方同意的情况下,他竟然一个人找到了另外一家报纸来抢先披露这件事。
格雷罗这时已经意识到了,无论是瓦努努本人,还是准备隆重推出这个新闻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这时都已经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他对自己被抛弃的做法感到十分的不满,就找到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竞争对手《星期日明镜报》,向该报披露了这一惊天内幕。《星期日明镜报》当时根本就不相信格雷罗,不过,从竞争的角度出发,《星期日明镜报》认为这倒不失为一个攻击对手的绝好机会,于是就拿出几千美元买下了格雷罗的这个“故事”,并利用他所提供的几张瓦努努拍摄的照片,配上一篇轻描淡写的文章,在报纸上把这件事给捅出来了,其目的无非是想以此来嘲笑《星期日泰晤士报》这样一家既有声誉又有口碑的大报,竟然轻信一个犹太流浪汉的一派胡言来小题大做,以此达到欺世盗名的目的。
就这样,在《星期日泰晤士报》还在策划之中,还在等待新闻官员的态度时,《星期日明镜报》抢先一步,在自己的报纸上率先披露了有关以色列核机密的新闻,一时间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反响。事后,《星期日明镜报》对自己的歪打正着居然还感到有点不知所措。
有关以色列核机密的新闻和照片见报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瓦努努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他知道自己肯定会成为以色列特工追捕的对象,顿时感到恐惧万分。
瓦努努的恐惧是很有道理的——当以色列驻伦敦大使看到《星期日明镜报》后,立即报告了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佩雷斯震惊不已,下令务必将这个瓦努努逮捕归案。
邂逅神秘的美丽女郎
以色列自从有了铀以后,拥有核武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但是在此之前,以色列官方却一直是守口如瓶,从来就没有公开承认过,而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大媒体尽管也在寻寻觅觅,但一直也找不出具体的证据来证明以色列的确拥有原子武器。而英国的《星期日明镜报》现在却是言之凿凿,称以色列的武器库里已经有了原子弹,并且还配有清晰的照片。如果以色列现在还想否认,那可就难了。
不久,以色列总理佩雷斯也亲眼看到了那张《星期日明镜报》。为了控制机密再次泄露,佩雷斯总理又电告以色列驻伦敦大使,要他请求英国新闻界在刊登出这种新闻之后,最好是能低调处理,不要再度张扬。哪知《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却认为,既然以色列总理如此关注,那就证明瓦努努所说的一切都真实可信,于是就决定在自己的报纸上以更大的篇幅,再一次更加全面地渲染一番,把瓦努努提供的那些照片刊登出来。1986年10月5日,《星期日泰晤士报》以头版的位置登出了一篇文章,巨幅醒目的标题是:《昭然若揭——以色列核武器库之秘密》。文章披露,在迪莫纳核研究中心的地下藏有一座6层的秘密核工厂,这个工厂每年生产40公斤钚,足以生产10枚威力相当于当年美国投在长崎的原子弹……
佩雷斯见到这张《星期日泰晤士报》后,立即把摩萨德局长内厄姆·艾德莫尼召来了。当艾德莫尼赶到总理办公室时,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拉宾和国防部长沙米尔已经坐在那里了。佩雷斯指着《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瓦努努的照片,命令摩萨德马上逮捕瓦努努。他对拉宾和艾德莫尼等人说:“既然我们已经无法制止机密泄露,那么,我们就只有坚决惩罚泄露机密者。无论他在哪里,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们都要将他抓回以色列审判。这将告诫其他的叛国者,所有出卖以色列的人最终将难逃法网。”
对于瓦努努其人其行,艾德莫尼早就有所闻。当瓦努努还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就已经被澳大利亚的安全情报局给盯上了,觉得他是一个危险分子,并且在当时就通报了摩萨德。1986年秋天,摩萨德收到了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发来的一份简要材料,材料说一位以色列人正在实施一项特殊的诱惑计划,企图引诱新闻媒体重金购买他的一则“秘密”。澳大利亚情报局认为这个以色列人的“秘密”一定涉及国家安全,于是就通知了摩萨德。后来得知瓦努努要去伦敦的消息后,澳大利亚情报局又通知了英国的MIS 情报局——因为通过摩萨德前几任局长实施的“外围战略”,这几家情报部门已成了同一行当中的盟友。所以当瓦努努和霍纳姆离开澳洲前往伦敦时,两名摩萨德特工也尾随其后,跟着他们来了伦敦,对瓦努努进行监视。
但是,现在要到英国去逮捕泄露机密的瓦努努,却是非常艰难。佩雷斯本人也非常清楚,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的尊严是十分敏感的,所以摩萨德的逮捕行动无论如何都不能触犯英国法律,否则,“铁娘子”的愤怒会给以英合作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雷佩斯和拉宾等人又再三叮嘱艾德莫尼,不能因为这次抓捕行动而得罪了英国人,给以色列造成外交上的障碍。
不过,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情报机构之一的摩萨德,似乎还没有不可能做到的事。艾德莫尼接到命令之后,立即采取行动。摩萨德的两名特工在以色列的一家木器厂找到了在那里工作的瓦努努的哥哥阿尔伯特,问他是否收到过瓦努努的来信。一位特工不加解释地对阿尔伯特说:“如果收到你弟弟的来信,就把它交给我们。”
然后,他们又马上用密电指示那两位前去跟踪瓦努努的特工人员,立即同摩萨德驻伦敦情报站取得联系,再通过他们与英国情报局合作,掌握瓦努努最近的一切行踪,并且马上再派出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连夜乘飞机飞往伦敦,去执行这项抓捕任务。
1986年9月的一个夜晚,艾德莫尼亲自挑选的特别行动小组出发了,他们的目的地就是伦敦。
就在瓦努努的照片再次见报之后,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就知道以色列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不但会找报社的麻烦,同时也会对这个以色列人下手,于是就把瓦努努给保护起来了,并且每隔一两天就将他的住处更换一次。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因为这个瓦努努对他们还有用途。一旦日后要和以色列政府对簿公堂的时候,这个瓦努努就是最好的证人。只要他能开口,就可以证明自己所报道的并不是造谣惑众,无中生有。
1986年9 月24日晚上,一位身材修长、过早秃顶的男子在霓虹灯和电影院彩灯的映照下,穿行在伦敦市中心的莱斯特广场。这位男子就是瓦努努。这是瓦努努搬到蒙巴顿饭店的第二天,经过多日紧张的等待和孤独的生活,瓦努努在用过晚餐后就去了离蒙巴顿饭店不远的伦敦莱斯特广场散步。瓦努努欣赏着眼前那流光溢彩的灯光,感受着黄昏后广场宁静的气氛,慢慢地,他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几分钟前,几天来一直陪着他的人还极力劝慰他少安毋躁,并且不同意他到莱斯特广场这样游人密集的地方去。但他是那样的执拗,因为连日来禁闭般的生活,憋得他快要发疯了。
这时,瓦努努信步来到了广场边上一家迪斯科舞厅门前。迪斯科舞厅那疯狂的乐曲让瓦努努感到周身肌肉发紧,同样疯狂变幻的灯光也让他感到热血奔涌、血脉贲张。但是瓦努努此时注意的却是站在门口的一位高高的、胖胖的、嘴唇肥厚的金发女郎。女郎那美丽、艳媚的眼睛以及轻佻的嘴唇似乎不经意地吸住了瓦努努射来的目光。她那透着娇媚的微笑、极富线条美的身材和那一身入时的打扮,像一颗磁石,深深地吸引住了瓦努努那颗孤寂的心。瓦努努不禁心潮起伏,随即走上前去,和那位女郎攀谈起来——这位女郎就是摩萨德女特工“辛迪”。
“辛迪”的真名叫谢里尔·本托夫,她是摩萨德“短剑”小组中一名出色的女特工。谢里尔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漂亮异常。在美国上完大学后,谢里尔不远万里来到以色列,专攻希伯来语。
在学习期间,谢里尔结识了一名摩萨德特工,两人一见钟情,共浴爱河。为了支持爱人的事业,谢里尔也加入了摩萨德。据说,谢里尔的智商高达140,看东西过目不忘。由于表现出色,她常常得到上司的肯定和嘉奖。谢里尔非常敬业,有一回,上司问她如果任务需要,她会不会同一个陌生人上床,谢里尔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如果任务的成功需要我施展‘美人计’,那么我将不在乎同任何一个陌生男人上床。”
谢里尔说到做到。莫迪凯·瓦努努向英国媒体泄露了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顶级机密后,摩萨德就派谢里尔出马,化名“辛迪”与瓦努努接近。摩萨德特别行动小组已经完全掌握了瓦努努在英国伦敦的行踪,一直在等待抓捕他的机会。
当时瓦努努才三十来岁,而且还是一个未婚男子。所以对于漂亮异性的渴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于是,一见到这个美女后,瓦努努就主动进行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叫“莫迪”,在澳大利亚时他的朋友就这么称呼他;但在以色列,他却叫莫迪凯。
女郎对瓦努努的这番表白似乎很感兴趣,于是就和瓦努努交谈起来。她说她叫辛迪,是到此孤身旅行的美国人,是一位美容化妆师。瓦努努请她跳完了舞,又与她漫步在莱斯特广场,他们一边走一边聊天,就像是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侣一样。
那天晚上分手时,瓦努努把自己旅馆的电话号码给了辛迪,他们相约不久再次见面。回到蒙巴顿饭店的房间后,瓦努努就急于想再次见到这个美丽的金发女郎。晚上他独自睡在饭店的床上时,眼前总是浮现着她那美好的倩影。
仿佛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第二天,辛迪就主动打来了电话,约瓦努努到泰晤士河北岸的泰特美术馆见面。瓦努努一接到这个电话,就像听到了一种天籁之音,他一直在等待和她再次见面的美好时光。
从此,瓦努努就与辛迪频频约会起来,俨然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并且一次比一次亲热。
在一次约会时,辛迪试探性地对瓦努努说:“亲爱的,我发现那家《星期日泰晤士报》好像是在耍你,看来他们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是那么的需要你。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当时,瓦努努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做法已经有些不满,那家《星期日明镜报》率先披露了这个新闻不仅不付钱,反而加剧了他的惊恐。而《星期日泰晤士报》事后还吞吞吐吐地说,当时之所以不急于发表那些材料,是想看看以色列的“反应”。
“他们的确不相信我。你的感觉没错。”瓦努努说。
“亲爱的,那你还有什么犹豫的?我们彻底离开《星期日泰晤士报》,离开他们,离开伦敦吧。”辛迪乘机这样建议他——特别行动小组为了不同英国发生外交上的麻烦,决定换个地方对瓦努努下手。
辛迪对瓦努努说,她有个姐姐住在意大利,她希望瓦努努能陪她同去看看姐姐,她还告诉瓦努努说:“如果我们到了罗马,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而在伦敦我总觉得不够踏实。”
尽管《星期日泰晤士报》曾一再告诫瓦努努“不要出国,不要乘飞机,也不要住任何要求出示护照以证明身份的饭店”, 但是他此时已经让这个美丽的辛迪迷住了心窍,把报社的那些叮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手掌上写着“我是在罗马被劫持的”
1986年9月30日,辛迪和瓦努努一同登上了飞往罗马的英国航空公司504航班。在希思罗机场,瓦努努又像在悉尼甩掉格雷罗那样给《星期日泰晤士报》打了个电话,说他要“出城”几天,并保证几天后就会回来。但是从此以后,伦敦的这家《星期日泰晤士报》再也没接到他的电话,直到四十多天以后,他们才听到了有关瓦努努被捕的消息。
英国航空公司504航班在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着陆后,一名自称是辛迪姐姐的男朋友的意大利男子在机场迎接他们,然后他们驱车来到郊外一栋公寓。瓦努努刚一进门,就遭到了两名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摩萨德特工的袭击。特别行动小组的特工们将瓦努努按在地上,给他注射了一针强力麻醉剂,然后就把他捆绑起来。他们又在瓦努努的嘴里塞满了布条,然后用一块强力胶严严实实地封上了。
当天晚上,几个彪形大汉抬着一个巨大的麻袋上了一辆小货车,驶向意大利的拉斯佩齐亚港口。当瓦努努再次苏醒时,他已经身在海边。摩萨德特工用担架把他抬上一艘军用小艇,然后驶向一艘游艇。在游艇上,瓦努努连续七天都被他们铐在床上,直到抵达以色列海岸。游艇一靠岸,瓦努努就被等在那里的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的工作人员带走了。瓦努努在离开以色列多年之后,以这样的方式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这可是他当年去澳大利亚旅行时始料不及的。
对瓦努努的公开审理并不像一般的案件那么简单。一直到1988年3月24日,瓦努努才被宣判因犯有叛国、间谍和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尽管瓦努努在法庭上多次表白,“我不是一个卖国贼,并没有企图毁灭以色列国的故意”,但最终并没有改变他的刑期。
当时,对于瓦努努的拘留和审讯都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但是,在一次乘坐戒备森严的警车前往耶路撒冷地区法院出席判决前的听证会时,精神振奋的瓦努努将手掌贴在车窗上,他在手掌上写着“我是在罗马被劫持的”。瓦努努手掌上的字迹成了各国记者们关注的目标。许多人都认为摩萨德触犯了意大利的法律和尊严,结果差一点引起同意大利的一场官司。
瓦努努被判处18年徒刑的事实告诉人们,以色列对叛国者从来是毫不留情的。
但不管怎么说,被以色列视为国家级高级核心机密的核话题,由于瓦努努事件成为人们公开议论的话题了。同时,在逮捕了瓦努努后,以色列政府始终向外界隐瞒了一个事实:瓦努努间谍案其实是一宗跨国绑架案。
18年以后旧事重提
关于瓦努努的话题并没有结束——18年以后的2004年4月21日,瓦努努终于刑满释放了。当他走出监狱的大门后,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对那些认为我是叛国者的人说,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和欣慰。我非常高兴我成功地完成了那些事”。铁窗生涯后,瓦努努宣称,他今后依然不会“退让或屈服,道歉或忏悔,装聋或作哑”。
瓦努努在铁窗内度过了整整18年。据说,就在他刑满即将被释放的几个小时前,以色列安全部门还在就到底释放还是不释放他进行磋商,原因就在于瓦努努怀揣着以色列的绝对机密。虽然瓦努努坦言已经没有更多核秘密可以泄露,但以色列政府对他仍然不放心。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他被释放的前一个星期还表示,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瓦努努被释放后仍将受到严密监视,他的护照也可能会被没收。
后来有消息说,瓦努努已经提出放弃以色列国籍,申请前往美国生活,但至今还没得到以色列政府的许可。对于那些摩萨德特工们来说,他们的下一步行动也许就是继续监控这位18年前的泄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