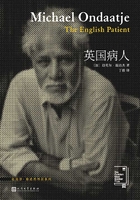他们紧跟在张老师他们后边,绕过东闸口,来到道北简陋肮脏的棚户区。这里聚集着历年从河南逃荒过来的难民,是西安最穷的三不管区域。张寒晖左右看看没人注意,才对他们说道:“火车站今天加强了警备,重点盘查去延安的革命青年,听说咸阳火车站查的更严,所以我们不能坐火车去咸阳了。”
“那咋办呀?”关若云急了。
“我们步行走草滩,从草滩上咸榆公路。”张寒晖说,“大家记住,我们身上现在穿的是税警团的军服,一路上我们要冒充税警团的人,这样也许能少些麻烦。”
“尤露露和张绿萍还没来呢。”关若云忽然说。
刘音说:“尤露露和张绿萍还有李承继他们三个人家里不让去。现在加上老师只有我们八个人了。”
“这就叫非战斗减员。”张寒晖幽默地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延安在全国的影响如日中天,成为了有志青年心目中的革命圣地,成群结队的穿着草鞋,打着绑腿的青年人成为了咸榆公路上的一大景观。仅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两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延安输送的青年就达两万人。然而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国民党省党部给蒋委员长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有这么一句话:……长此以往,青年才俊尽属共党,其势其力日炽,后患无穷。
蒋委员长阅后颇有同感,随即下手令一道:青年乃国之未来,若尽付匪逆,孰为可惜,汝等务必千方百计塞源截流勿使泛滥。
令行禁止,西安通往延安的公路上设置起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同官、中部(今黄陵)、洛川等七道关卡,专门拦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作为配套措施,还在西安的东厅门增设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在咸阳北门外成立了干训四团特训总队,专门收容各地关卡扣押下来的赴延安青年。
张寒晖深知他们这次行动的危险性,一路上他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遇到关卡,他就夜行昼伏,绕道而行,因此,他们的行程格外艰难困苦,走了半个月,才走到洛川境内。他们的布鞋早就穿坏了,他们平均一天买一双草鞋。他们的脚被草鞋磨烂了,他们只好撕下衣服上的布包脚,他们因此变得衣衫褴褛。他们十五天没有洗澡,他们的身上发出难闻的气味。他们的头发乱蓬蓬的,浑身上下甚至眉毛上都粘满了黄土,他们好像一群叫花子。好在他们没有挨饿,唐风和关若云身上的钱保证了他们食宿无忧。他们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然而就在这成功在望之际,张寒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在张寒晖的思想里有一个固定的认识:只有贫苦农民才是他的朋友,有钱人都是靠不住的。因此,快到洛川检查站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最贫穷的村庄里最贫穷的一户农民家借宿。他们准备在这家农民家里度过白天的时间,天黑后再行动。张寒晖慷慨地给了这家农民一块大洋作为借宿费用,又让唐风拿出一块大洋给农民,托他买两只鸡和一些吃的。张寒晖的慷慨引起了那位看起来很老实的农民的怀疑。那个农民舍不得花那一块大洋到外面去买鸡,他把自家养得两只鸡宰了炖了。鸡炖熟了后,他把鸡肉鸡汤倒到一个瓦盆里,用腾出来的锅煮了一锅小米饭。然后他趁他们吃饱喝足横七竖八地挤在土炕上睡觉的时候,跑到检查站举报了他们。那个农民从检查站领到了一块大洋赏钱。那个贫苦农民一天内挣了三块大洋,为此他整整高兴了一年。他曾经跑到肤施(延安的旧称)去给人家扛活,那个以乐善好施闻名的老财给他一年的工钱也不过三块大洋。他的好运气导致那个贫穷小村子的贫苦农民集体患上了红眼病,他们晚上跪在自家的炕头上给老天爷磕头,祈求老天爷保佑自己也能碰上这种自投罗网式的好事,也发上一笔横财。
张寒晖他们实在太累了,如果没有检查站的军警把他们一个个揪起来,他们能一觉睡到天黑。等他们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带到了关卡检查站。面对检查站站长的审问,他们按照张寒晖预先统一的口径一口咬定,他们是中央税警团派往延安执行特殊任务的特工人员。
检查站站长问:“既然是税警团的人,为什么不大大方方地通过关卡,反而鬼鬼祟祟藏到农民家里?”
张寒晖反问道:“你啥时候见过的大大方方的特工?”
“你们的证件呢?”检查站站长脱口而出,说完后自己也觉得说了句蠢话。
张寒晖又一次反问道:“你见过带证件的特工吗?”这一次语调里带着明显的嘲弄。
站长一拍桌子,喊道:“你少给我装腔作势,你们一口的东北腔,可税警团一水的南方人。你说你们是税警团的人?拿我当瓜娃呀?老实交待,省得受皮肉之苦。”
“你也是个军官,咋不知道‘兵者,诡道也,实则虚之,虚者实之’的道理呢?东北人有沦亡之痛,容易获得共产党的同情和信任。换几个浙江人去,你倒是放心了,共产党可就不放心了。”张寒晖的狡辩从容不迫,搞得站长有点摸不着向,想来想去没敢动粗。这时候,他的一个部下给他呈上从关若云身上搜出来的家书,站长看过后,更觉得这些人还真是有些背景的,就越发拿不定主意了,最后决定先把他们关起来审查审查再说。
第一次审讯勉强搪塞过去了,张寒晖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真实身份迟早会暴露,必须尽快从这里逃出去。他们被关在离检查站工作人员的驻地不远一个农家小院里。很快他们就发现检查站名声挺大,检查人员却不多,只有十几个人,听口音,除了站长几个人是关中人之外,大部分都是洛川本地人。距此一里左右的一个小镇上还驻扎着一个排的军队作为紧急情况下的支援力量,彼此没有统属关系。
为了麻痹看守人员,张寒晖让大家尽量和对方搞好关系,他自己也是一口一个自己人的和对方套近乎,唐风主动掏出钱请看守帮他买烟卷抽。看守自然求之不得,买三包,他自己就能落一包。唐风就是这几天学会抽烟的。他们被关押两天了,每到开饭的时候,唐风就抱怨伙食太差,说从来没吃过这么差的饭菜,甚至还掏出钱让检查站伙房买肉给大家改善伙食。站长联想到抓他们那天,他们累成了那个怂样子还不忘买鸡吃肉,更对他们的身份将信将疑,对他们的戒备无形中松弛了许多,看守也从两个人减成了一个人。
到了第三天晚上,陕北高原上刮起了大风,刮得飞沙走石的,走路都睁不开眼睛,气温骤然下降了许多。唐风托看守到镇上去买酒,说是想喝点酒暖和暖和。看守踡缩在自己的小屋里不愿意去,说想喝酒自己买去。唐风说你不怕我跑了?看守说你不会跑,你跑了剩下这七个人就该倒霉了。唐风顶着大风出门几次差点走迷了路,好不容易摸到小镇上,买了几斤羊杂碎,打了一罐散酒回来,叫上看守,几个人就在屋里喝开了。
陕北人见酒如命,爱喝也能喝,一罐子酒看守一个人就喝了一多半。喝得高兴话也就多了,拍着唐风的肩膀直夸他够朋友。张寒晖趁机套看守的话,问他站长对他们不审不问也不放到底安得什么心?看守大着舌头说,站长是个小心眼,没球本事还老想升官发财。不过人还不坏,对弟兄们也还过得去,就是家里人口多,薪水老不够花。过去路过这里投奔延安的人多,抓住的也多,抓住的人多,得到的奖赏就多,站长干的也有劲。现在不行了,去延安的人少多了,好不容易抓住你们,又说是啥税警团的。税警团谁惹得起?那是老蒋的心尖尖肉蛋蛋。调查吧,站长知道自己人微言轻,只在电话里向上级作了汇报。上级也觉得此事棘手,答应尽快派车来把你们押回西安再说。
一罐酒喝完,看守酒醉心里明,还盯着羊杂碎紧吃。张寒晖叹息道:“看来老兄肚里真缺油水,剩下的包起来带回去,留着明天再接着吃。”
看守借酒盖脸说实话:“不瞒老兄,别看我们人前人五人六的,其实也就是人家的一条狗,吆喝咱咬谁咱咬谁,咬着人了给块肉骨头啃啃,咬不着人,扔把谷子吃去吧。可怜哪!”说着他便动手包羊杂碎,酒喝多了手不当家,掉到炕桌上一块,捡起来塞进嘴里嚼着,摇摇晃晃地拉开屋门,摇摇晃晃地回他的小屋去了。
狂风裹挟着黄土高原特有的沙尘冲进屋里,吹得油灯闪烁起来。张寒晖关上屋门,对学生们说:“大家赶紧打好行李背包,等那家伙睡着后,立即出发。今晚的沙尘暴对于我们逃出检查站很有利,但是这里沟壑纵横道路崎岖,没走过的人极易迷路,所以你们必须紧跟着我。万一掉了队,不要惊慌,一直朝北方走,淌过介子河就到家了。”反复叮嘱过后,张寒晖出去在看守屋门上敲了敲,里面毫无反应,便挥手带领大家悄悄地从小院逃了出去。
这时候,豆大的雨滴随风砸了下来。张寒晖心说不好,他在竞存学校工作期间,几次返回延安请示工作,深知陕北气候恶劣,紧接着沙尘暴而来的往往是倾盆大雨。他担心大雨中介子河涨水,把他们阻隔在河南边,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们必须赶在河水暴涨之前淌过河去,然而等他们八个人气喘吁吁地赶到河边时,河水已经齐腰深了。事不宜迟,张寒晖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第一个跳下水,然后招呼大家手拉手鱼贯而行。刘音和关若云两个女生夹在队伍中间,唐风紧跟在她们后边。她们紧紧拉着彼此的手,她们被黑夜、狂风和暴雨吓坏了。河水凶猛地冲撞着她们的身体,她们感到自己轻飘飘的像一片树叶,随时会被河水冲走。
手拉手的队伍挣扎到河心,河水掀起的浪花拍打着她们的脸,她们被呛得喘不过气来。关若云咳嗽着,她觉得背上的行李包越来越沉,带着她直往下坠,她每前进一步都是那样困难,她的头开始晕眩起来。她想抓紧刘音和唐风的手,可是她的手却软绵绵的使不上劲。又一个浪头打过来,她的身子摇晃了一下,她赶忙抬起右脚,想踩稳脚下的石头,那块石头晃动了一下,她的脚从石头上滑了下去。她喊了一声,顿时被呛了一口水,她拉住刘音的手滑脱了,紧接着拉着唐风的手也滑脱了,她感到唐风的手拼命地想抓住她的手,但终于没能抓住。她的身子像块木头似的漂了起来,她在漂下去的时候分明听见唐风声嘶力竭的哭叫声。
关若云顺流而下的时候,心里不但没有糊涂,反而格外清醒。她明白自己处于生死关头,她知道她必须浮出水面喘气才有生的希望。她很快就发现刚才还把她往下坠的行李包现在却带着她往上浮,她赶紧利用浮沉的瞬间像乌龟那样仰起头来喘上一口气,她立刻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捕捉喘气的机会上。她不知道她漂了多久,漂了多远,她突然发现她的身子开始翻滚起来,河底的石头碰撞着她的身子。她不知道她漂到了一个乱石滩上,但她感觉到河水突然变浅了,她心里顿时燃起了生的希望。她赶紧翻过身趴在乱石滩上,她惊喜地发现她的头居然能够轻易地抬离水面了,抬起头后她看到岸边近在咫尺。于是她双手撑着石头想站起来,可她每次刚刚站起来就被只到她膝盖但十分湍急的河水冲倒了。她急中生智,双手交替抓住河床上的石头,一步一步往岸边挪,她终于挪到了岸边,跌跌撞撞地爬上了岸。这时候,她知道她活下来了,她喘息着闭上了眼睛,她想歇一会儿。
五
多年以后,关若云还常常回味无穷地想起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那一刻。她首先苏醒过来的是她的额头,一只绵软温暖的手在她额头上轻轻地抚摸着,这轻柔的抚摸逐渐唤醒了她的意识,让她的身体陷入一种酥软的状态。她喜欢这种感觉,她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这种感觉了,这种感觉让她想起了妈妈的怀抱。她生怕这是一种幻觉,她一睁开眼睛就会消失,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姑娘的幻觉一样。她没有睁开眼睛,她只是动了一下嘴唇,叫了一声妈妈。一个人的身体靠近了她,从那股沁入肺腑的芬芳中她感觉靠近她的是一个女人。
“醒啦,小家伙?”和妈妈一样亲切的声音。她睁开眼睛,一张漂亮女人的脸让关若云怦然心动,让她怦然心动的首先是那双水汪汪的眼睛,那双眼睛向她输送着怜悯和慈爱。
“你是谁?”关若云声若游丝地问。
“我叫吴薇,是上帝专门派来拯救你的天使,你信吗?”漂亮女人侧过脸,用眼角看着她诙谐地说。
“我不信。”关若云斜着眼看了看吴薇身上的军装摇摇头,“你和检查站那些坏人是一伙的。”
“这你可冤枉我了,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而且我也不是坏人。要不是那天我来得早,你的小命恐怕早就没了。”
“那天?哪天?”关若云眨巴着眼睛。
“想不起来了吗?三天前,我刚到检查站,就看见检查站那些人把你往检查站里抬,我问他们抬的是什么人?他们说是逃跑的共党分子。我拨开你的头发,发现你是一个女孩子,我就骂他们混蛋,还不赶快送医院。就这么着你就到了医院,你都昏迷三天了。你说,我是不是上帝派来救你的天使?”
“我昏迷了三天?”关若云不相信地皱起眉头。
“是三天。三天前,他们在介子河边找到你的时候,你发着高烧已经奄奄一息了。”吴薇的话触动了关若云,几天前的事回到了她的心里:铺天盖地的沙尘暴,沟壑中艰难的奔跑,波涛汹涌的河水,浅滩激流中的挣扎,那一切一切就像做梦一样恍惚,又像梦境一般真切地回到了她的心中。
“我小表叔呢,张老师他们呢,刘音呢?他们在哪儿?”关若云一把抓住吴薇的手,“你们把他们弄哪儿去了!”
“检查站的人顺着河水走了十几里,什么也没找到,估计你的同伴都过河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