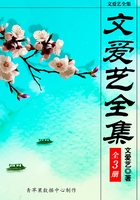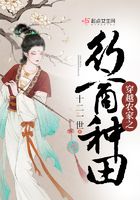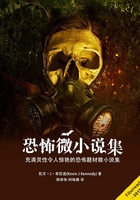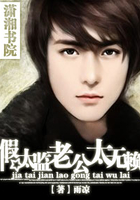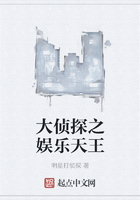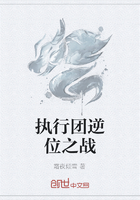从大喇叭和广播,听到外面的好消息;又记起黄浦江畔,记起自己是上海人;公章“砰”的一盖下去,一个家庭解体了;挤在火车上三天四夜,鞋带全都绷断。
到70年代后期,高考全面恢复,全社会思想解放正在萌发,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给许多彷徨中的知青带来强烈冲击。上山下乡运动积重难返,长年远离家乡的知青正在失去耐心,陆续出现倒流回城、上访请愿等等动向。返城风潮正在从边疆、乡村波及到各地的大中小城市。
与早年从内地迁到新疆的老职工相比,上海支边青年虽然也已经在兵团安家,但还是难以完全安心。漫长的岁月与遥远的距离,并未真正削弱思乡之情和内心深处的回城渴望。当60年代末插队的弟妹们已经纷纷返城的时候,他们这些当初知青的先锋,再一次面临着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了。
花二百多亿换来四个不满意
全国知青的所谓“胜利大逃亡”,是从云南西双版纳的景洪触发的,代表人物丁惠民,也是一位来自上海的知青。1978年9月,他冒着极大风险,给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历数广大知青的困惑、烦恼和对生活的无望,希望能在政府的帮助下回到原籍家乡。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下决心解决积压的问题。
据说当时的一个重要背景是,邓小平委托一位分管的副总理组织调查知青的总体情况。最后得出的说法是国家花了两百多个亿,那时的两百多个亿,换来四个不满意:“国家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地方政府和百姓不满意。”
进入1979年以后,这些支边在新疆的上海人也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可能要改变了。因为从亲友的来信里得知,全国都在松动。云南那边是疾风暴雨式的,一下子争取了三个月,就把问题解决了。在新疆的上海支边青年也都收到了家里来信,知道弟弟从黑龙江回来了,或者妹妹从江西回来了,不断地有这种消息。所以他们免不了要着急起来,心想怎么就把我们给忘了?
在他们中间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当年被动员出来支边的时候,没有父母当大官,他们不是普通市民就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但后来上山下乡的知青呢,父母当大官的不少,因为在文革初期给打倒了,或靠边站了,他们的子女也只好走;到后来,爹妈平反,又坐回到位子上,就会为自己的孩子想些办法。而像上海支边青年这些走得早的,没有背景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回去呢?
事情的变化还得从三十多年前说起。1979年,身处南疆阿克苏农一师5团的上海人顾幸运,听到广播里有关知青回城的政策,她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开始要有转机了。
因为各个连队都有广播站,就像全国各地的农村一样,大喇叭挂在树上或房上,最高的房子上肯定有最大的喇叭。连队每天早中晚都用大喇叭广播,转播中央台的节目,播报各级的通知或任务安排,播送政治文件、革命歌曲、样板戏等。大家早晨起来,中午吃饭,或扛着锄头拿着镰刀从田间工地回来,我能听到那个大喇叭在广播,任何角落都能听到。
关于回城的政策,顾幸运第一次就是从广播里听到的,那意思是,如果上海的家里属于特困情况,本人就可以回去。她和旁边的同伴都互相诧异地看看,不用说,一下子意识到有回去的可能了!
人人都相信,只要上面开口子,就表示有希望。从那以后,他们就开始没什么心思干活了,抑制不住地高兴,整天在田头工地、在宿舍里都是跳啊、蹦啊、吵啊、说啊,好像真的就快要回去了。
那天,周敦福和其他人正在连队外面挖排水渠,通信员送信来了,路过他们旁边,就没往连部去,直接掏出信看看说,谁谁谁,你们有信。有个人手最快,他把信拆开刚一看,马上叫起来:“妈的!上海有好消息了,能顶替的可以回去啦!”
各地解决知青回城问题初期,还是沿用50年代起实施的城镇职工顶替政策。而远在新疆已不大年轻的近十万“上海青年”,能够顶替父母工作的毕竟是少数,其中那些幸运儿成了大多数人眼红的对象。当年农二师34团的李良高,率先接到家里给办好的顶替回城手续后,是悄悄离开团场的。他明白,为什么大家眼红?倒不一定是妒忌。问题是,谁一走对大家是个刺激。都不走,几十年一起下来了;而一旦有的能走,有的不能,结果就都坐不住了。
总之,这些已经把塔里木当作家园的人,忽然又记起了黄浦江畔,记起了自己原来是个上海人。在他们的心底,其实从来也没有放下那梦里的石库门和南京路。同时,当十多年的青春抛撒在大漠戈壁,当步入而立之年的“上海青年”大多在地窝子、土坯房里结婚生子,他们早已完成了从城市学生到兵团农工的身份转变。
那些年间,他们已经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他们长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忙着婚姻嫁娶,养儿育女,还忙着添置家什用具。而这个时候,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超出他们想象的急剧变化。
回城呼声淹没在遥远的边陲
中央在解决云南知青问题的时候,就有相关干部提出,应当一并考虑新疆的上海支边青年。但是从上海至新疆的列车上搜集反映上去的信息是,上海青年每次探家都大包小包地往新疆运东西,可见他们已经很安心了,所以暂时可以轮不到给他们解决。但是,实情真的如此吗?
1979年春节前的一天傍晚,南疆阿克苏农一师14团的欧阳琏,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云南发起知青返城并取得成功的消息。
当时是在排长家里,他们六个上海人坐在那儿聊天,收音机开着,听到了中央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和报纸摘要”,里面提到云南的事情。大家听完以后都没有走,谈到很晚,先是发发牢骚,后来忽然就提出来,我们干脆也集体请愿吧,大家一拍即合。于是便写了个海报:“定于正月初五礼拜天上午,在团部商店门外,举行上海支边知识青年聚会,商讨相关事宜。欢迎积极参加。”
这个消息一下子在整个团场传开了。到了那天,骑自行车的,坐毛驴车、牛车的,走路的,农场的上海青年能到的都到了,有的连队简直走空了。聚会的时候就都站在那里,大家议论什么?主要形成的话题,就是讲云南知青、黑龙江知青能回去,我们在新疆的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回去?我们也要自己争取。
这次在14团的自发集会之后,他们议论得不少了,但是怎么能有结果呢,大家推举出几个代表,到乌鲁木齐的农垦局去反映共同的回城要求。因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曾经在1975年取消,团场都划归农垦系统。
接待这些代表的干部说:“你们当年不是自愿报名来的吗,怎么现在又都要求回去呢?”先拿这个话敲打他们。接着又说了:“你们和其他地方的知青不一样,你们是支边青年,就相当于移民了。”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仅仅是支边青年,就不属于知识青年行列。既然不是知青,就没有名分,不在中央文件所指的范围之列,那还来说什么落实知青回城政策?不是胡来嘛。
去反映诉求的代表就这样无果而返,没法给等在家里的大伙儿一个交代。不过他们碰壁之后不但没有放弃,反而当即决定效仿云南知青,直接派代表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1979年2月24日,新疆的上海支边知识青年代表又出发了。在这些代表里面,欧阳琏年龄稍长,阅历较多,又一向热心和有担当,很自然地成了一个牵头的。当时大家讨论后提出来,14团每个连队两百多个上海人中间选派一个代表,然后一人出一块钱,凑了两百多块,这个代表到北京的来回路费和开销都有了。欧阳琏临走的时候,把自己的一辆从上海托运来的“永久”牌自行车卖了六十块钱,放在身上。
经过数天数夜的长途旅程,他们下车以后,出了北京站,首先看到的景象让他们很意外。正值“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期间,各个信访站前面早就人满为患,许多人就席地睡在火车站的广场上。那年月等待平反昭雪的人实在太多,满地都躺着破衣烂衫的男女老少。
他们这些代表,都在连队的大喇叭里听过不知道多少遍,那个时候李双江唱红的《北京颂歌》,“北京啊北京”,多好听,多么伟大壮丽,多么令人向往。可是到了首都北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他们禁不住心里都少了一些乐观。
有关部门派人在站外等上海支边青年的代表们,他们被拉到远郊区一个偏僻的招待所。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此后在北京的那么多天,仅仅关于他们身份的说法就一直难以认定。上面的口径原则上没变,依然还是说,你们去新疆的这些人不属于知青,是屯垦戍边,是“文革”以前的事情,所以和云南、黑龙江的那些情况不一样。你们是支边青年,他们是知识青年。
就为了这个名分一直在那里讨论,甚至断断续续争论了五十二天。事实上,这十万上海青年在60年代是作为知青运动的先例,大规模地集体到新疆。最后,总谈不下去也不行,人家给他们下的结论是:“承认你们是知识青年,但是要跟后来上山下乡的知青有个区别,你们叫做‘支边知识青年’。”这样的叫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搞不太清楚。
当初,杨清良在上海作为基层团组织干部,自己也参与了支边的动员和招收工作,所以他就有条件掌握更多的资料,比较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此行,他也是代表们的带队人之一。在北京的这次对话会上,在最僵持的时候,如同是庭上拿出关键证据,杨清良从包里拿出准备好的一个大信封,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它打开,将里面的文件材料一一排开在面前的桌子上。
所有人自然都伸过头来看,只见里面有1963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上海从市到各区的招生简章、录取通知书、沿途须知手册等等。上面都盖着公章,其字样是:“新疆上海知青招生办公室。”一目了然。当时各个区都是刻的这个公章。
之后,杨清良特意从中把国务院知青办74号文件拿起来出示,对在场的人说:“这份文件的第一条,我来背给各位听一听好不好—‘凡是1961年以来,全国各大城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均享受知识青年政策。’各位领导,这可是国家权威部门的正式文件呀!”
在乌鲁木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档案室里,现在可以查到相关文件,上面标示着“支边知识青年”。另一方面,那一次上海青年的代表还搜集并呈交了大量的证据,比如当初每个人进疆的光荣证上就写的是“知识青年”,印得清晰可见。
那次上海青年们到北京反映情况,虽然谈得艰难,但面对他们迫切的诉求,高层随后派出了工作组,前往戈壁深处的基层团场调查摸底。
调查组有一个刘济民,是农垦部的一位负责人。在团场马上传开了,北京的工作组来了,大家听到消息都很高兴,感觉上面说话算数。领导的车走在路上,连队的人都跟着吉普车在后面跑,路不好,特别颠簸,车走不快,所以人都能跟着吉普车跑。正好遇到前面木桥被水冲垮了,上海青年就纷纷跑来,直接跳到大渠里,人分两边,把吉普车抬了过去,热情高涨。
工作组到了农场以后,腾出一个院子接待,结果,院子四周,甚至附近的树林子里,白天黑夜都站满了等候消息的人。男男女女,都是一起在这里苦干了十多年的人,而且都还讲着同一种口音:上海话。
但是如此热情的阵势,让工作组很不适应,可以说很紧张,甚至后来有一种被围困不得解脱的担心。尽管实际上只是这些上海青年的期望太强烈了。三天之后,虽然没有得到什么承诺,但大家还是礼貌地站在路边目送走了工作组。
希望闪现之后,是漫长的等待。整个过程从1979年初到1980年末,这期间,国家频频发生的大事,似乎把上海支边青年的回城呼声淹没在了遥远的边陲。
从偏远连队汇集到阿克苏
据说,上海支边青年呼吁要求返城的那年,一场黑风暴刮了七天七夜。因为他们长年开荒造田,没有了胡杨林的阻挡,整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仿佛都被卷到了空中,暗红色的悬尘在天地间拉起了巨大幕布,七天七夜看不见太阳和蓝天,分不清白昼与黑夜……
在那个记忆中异常寒冷的初冬,成千上万的男女,这些昔日的上海青年看上去已经不那么年轻,也已经无异于农工了,他们从各个偏远的连队,走向团场,又从团场走出来,顶着刺骨的风沙,沿着塔里木河,沿着他们亲手修筑的公路、林带或者干渠,陆陆续续地,汇集到了阿克苏地委大楼的前面。
原农一师副师长赵国胜,在阿克苏干休所的家中做着手势说:“当时的情况是,忽然各个团场的都纷纷赶来了,一下子在阿克苏集中了上万的上海青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一些当领导的抱着避而不见的态度,把上海青年要求回城的举动,几乎看成了敌我矛盾。当时我是阿克苏农垦局的副局长,这时候呢,农垦局其实没有权力,也没有力量来制止了。”
回家的愿望被迅速催生与放大。此时,上下奔走的欧阳琏,不知不觉中成了上海支边青年返城的一个富有号召力的人物。阿克苏的请愿人群一度进入地委大楼,事情的性质似乎陡然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