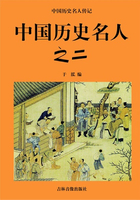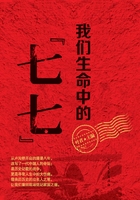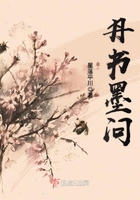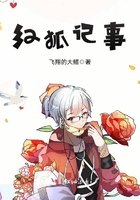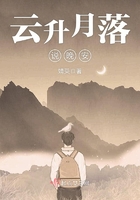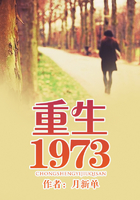在我离开苏州时,因为书没看完,何况画谱这种书非得动笔临摹不能算数,所以我提出带回北京去,特别交代了一句,在北京见面时还。分手时我从他的汽车后备厢里取行李,他别的没说什么,只是又叮嘱了一句,“陆俨少那本书你带走了呵。”我说装好了,放心吧。
论画谱画法类图书收集之全,大概也少有人可以与我相比,只是我偏偏一直遍寻未得这一册。因为这段因缘,乙酉秋后我把这本180页的画谱通临了一遍。如果不是杨先生对此书那么珍视爱惜依依不舍,我倒未必会下这番功夫。此举使我对陆俨少画法又深了一层认识,这便是缘。
纯是巧合,另一次聊天时他问我有无英文版的中国美术史,我的美术专业图书资料既多且杂,其中就有不少英文书,也有牛津版的中国美术史。过了些日子,他特地又再问起,说是在美国都找不到。于是向我借了去,说是一个朋友的女儿在日本写论文急需此书。次日他就还了,说已经复印了一本寄往日本。平生所交师友甚多,可是在学术与艺术上有书的往来却并不多,尤其是画家们的书架上,极少有哪本书是我想借的。我总是认为,愿意借书给人的,才是真心与人相交、能够与人为善、金针度人的。此事虽小,亦可记也。
由于职业关系,我行走江湖也算得上是行万里路了,我有一方闲印是马士达先生刻的“九万里”,后来韩大星先生也为我刻过一方,别人以为是言志,其实只是写实而已。近两年我对乘夜车每以为是苦事,而年过六十的杨先生却穿梭往返习以为常,无乃劳顿过甚乎?我到西安去参加时任西安美术学院院长杨晓阳先生主办的会议,与杨先生两次长谈,还到他的一处住房看了他收藏的高古陶器。
西安美术学院院里到处堆放的都是从西北各地收集到的老旧拴马桩,是杨院长的爱好。
他的院长办公室是阴面,他告诉我,好在全世界的画室都是朝北的。
出于我的疏忽,访谈内容没有交代手下的及时整理出来。
2009年我在云南挂职时,听到消息说杨晓阳已经调任中国国家画院院长,虽然行政级别还是司局级,但是在美术界的地位影响大大不同了。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颇好奇:西安美术学院那一院子石头拴马桩,怎么着了?我知道中国国家画院那个小院子,是根本摆不下几根拴马桩的。
黄格胜酒量大、爱说笑话。这是他两大过人之处。
在南宁我与他多次长谈,后来到了北京,他来过我办公室,我也去过他住的宾馆。我感觉这是位绝顶聪明的人。
我曾在2004年桂林举办全国书市时有意请他参与我主持的《大师谈艺录》首发式活动,后来阳太阳老先生替代了亲自到场,活动很成功,全国四十几家新闻单位报道了。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广西美术界的朋友和我在一起,总是会提起这位广西艺术学院的院长,后来又升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在篆刻家中,李刚田的名字是我很早就记住了,这是因为我感觉他的名字本身与篆刻家的身份非常匹配。我很在意语言文字的品味与境界,有时对字与字的搭配所产生的奇妙效果很着迷。刚田二字,就每令我想到笔耕。
在名气与地位上,李刚田是国内篆刻界公认的一流名家。我曾经在担任《郑州晚报》顾问期间频繁地去郑州,日报晚报重组的项目结束前,报社的领导知道我还有一个专业是美术,便提出他来安排请几位郑州的名家一起坐坐。不出我所料,其中就有李先生。其实此前我们已经认识。记得那天席间谈得很随便,李先生说了一句大实话,那便是刻印的挣的全是外行的钱,内行像在座的各位都是朝我要,不会给钱的。
大家听了都笑。
人与人的交往,知己知彼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尤其是在两代人之间。
能够单向地了解,就足以保持良好关系。我自以为是理解李刚田先生的艺术与人的风格、成就的,反之似乎则并不然。.乙酉之夏偶尔得暇,我对李刚田先生作了一系列访谈。坦率地讲,至今为止,他是我进行类似访谈的名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但是因为正好处在我有空闲档期,却又是我最认真准备的。访谈期间,除了有一次由一位我的研究生陪同参加,其余全是我单刀赴会。虽然多少年来于公于私都不乏鞍前马后跟随的助手,但是我向来不讲什么架子,自认为拿得起来放得下。
连续两周的访谈临了,李刚田先生对我说,你这么忙,访谈其实让学生去做也可以,你把把关就行了。显然,李先生精通书法篆刻,但对访谈与出版这一专业并不了然。如果学生也可以完成同样水平的访谈,那么我当然求之不得。客观地说,我所做的访谈,在专业准备与设计、调控的难度与复杂程度上,与音乐家指挥一场交响曲差不多。也许李先生此言的意思是,反正乐手都是熟悉自己要演奏的内容的,随便找个人当指挥都可以是一样的。
李先生是郑州人,可是却买到了北京的经济适用房康居工程住宅,而且还是两套,合在一处打通了,由此可见李先生是能出世又能入世的高人。
访谈整理完,我给李先生打了个电话,他说寄给我吧。那阵子我忙了起来,没顾上寄,就此也便再无声讯。
姜宝林姜宝林先生是山东人而长年在南方工作,后来又在北京有了兼职,于是北京杭州两地轮流居住,这种南北都有家的画家近来多了起来,我认为与其说是文化现象,不如说是市场驱动。
感觉姜先生总是很忙,中国的画家之忙,也是古今中外所未曾有的现象。其实在我看来,对画家最重要的不是忙,而是闲。
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最早的研究生,姜宝林在美术界是正宗的科班出身,也是中国美术教育的中坚力量。
从衣著风度上看,刘焕章绝对是艺术家,但是他一开口就吓人一跳,他至今乡音未改,如果只听不看,会以为他是一位乡下老汉。
刘先生是雕塑家,住在红庙的宿舍,那次去我本来是找另外一位老先生,不想撞进去的是他的家。老先生对我们很热情,他说刚从美国回来,还让我看了他在美国的照片,上面有他在美国的作品。他的房间里,也摆放着一些他的作品。
他是沈从文先生的女婿,所以我问他是否收藏有沈从文的书法,他一听很有兴致,站在凳子上从立柜顶上取下卷轴来,打开让我们看。是沈老写的诗,神采飞扬。杨明义也有沈从文书法,与我合影中就有一幅。
他说“今天你们太幸运了,大开眼界。”这话本来该我来说的,他替我说了出来,我只好连连称是。我问是否可以在杂志上发表下,他摇了摇头,说看看可以,若是发表,沈从文家里恐怕不同意。我不理解发表出来让沈从文的书法艺术被更多的人所知道、所欣赏有什么不好,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充足的理由,所以也就没勉强。
我在万荷堂再次见到他时,他正倚坐在长廊上休息,我说最近看到他出的一本印纽的集子,老先生很得意,说与别人的不太一样。
在上海去见王元化,他住在一处类似于干休所的宾馆,属于那种长年居住,享受高干待遇。
无独有偶,我被聘请担任上海大学客座教授,每次下榻的上海大学乐乎楼,二楼的一半房间,便是被一位我没见过面的神秘人物住着,知情者告诉我,那是校长钱伟长的居所,九十多岁的老先生一个人住,楼口总是有一位年轻人穿着便装立在那里。
王元化是理论家,主要从事文学批评,他的书出了不少,可是我看的大概也就本把。不知为什么,我对以他为代表的官员理论家的著作,总是读不进去。
我们谈的什么,记不清了,留下印象的是,他表示以他的地位与身份、级别,很难得接受类似的访问,不过他又说,他不需要宣传,无所谓。这可能也就导致了我没有就王元化写过任何文章。
我之拜访王元化,也就是“到此一游”性质。
有一次我出差,在路上接到助手的电话,说来了一位客人找我,他自己说是程大利。助手不是美术圈的,不知他是何方神圣,当成了粉丝贸然求见大腕(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过),便大声大气地告诉来客,我们主编很忙,必须得预约才行。
老天,我听了训诫下属:程先生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无论是年龄、级别还是在美术界的地位、声望,都绝对是很高的。
这就是程大利的风格,平和、低调。此前我没有机会识荆,程先生不知是什么机缘,竟然在日理万机的工作日,未打招呼就上门来见我了。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然而事后我竟然也未回访。我们见面,是在我主持的钓鱼台国宾馆笔会,程先生大笔如椽,让我开了眼。
我离开《中国书画》杂志后,程大利在中国美术馆办个展,他亲自给我打电话,很客气地邀请我前去“指导”,我又一次感到程先生的虚怀若谷。记得他还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尽管到了年龄,但是上级还是让他又兼了法人、书记,三职一身。
我接触的美术界前辈不少,私下心里颇佩服、该学习的是程大利。
黄先生在南京艺术学院从事书法教学与研究,以篆刻名世。这是一位耿介之士,自信而坦诚,我和他初识于2002年扬州的扬州八怪国际研讨会,他在会上做了一个讲演,锋芒毕露,与另一位海外来的学者直接发生冲突,唇枪舌剑,成为会议的一个热点。
在他的房间,我们长聊了一晚上,谈的是1978年他考研,也就是中国美术学院第一届书法研究生,陈振濂、朱关田那四位上了,而他落榜。他说了过程与内幕,随行的录了音。
在会议期间,我到古籍书店买书,扬州的古籍书店,在图书品种与档次上,接近于直辖市,远远高于一般省会。我照例选了一堆有二三十本,因为抱着重,就往收款台上放,被人不满地制止——扭头一看,是黄先生!他买了一册书,翻看我选的,他说某本书不错,是上海出的,回头他可以到上海找他们要。
2003年,他到北京来开会,到我的办公室来作客,同来的有几位全国书协的副主席。我向单位负责人介绍说黄先生几位所分头写的多卷本《中国书法史》是至今国内篇幅最大、最权威的书法史,而负责人没听说过更没有读过,于是黄悖先生说回南京后让江苏教育出版社寄一套吧。
黄永年是目录版本学家,是历史学家,我到西安去他家拜访,而他之所以肯接受,则是因为他有一个业余爱好:篆刻。
当然,见面时我不会与他谈篆刻(尽管此前我创办主编了《中国印》杂志),主要谈的是国学。一位很有修养、很高傲自信的老学者。我读过他两本书,他受过政治打击,有自己的学术主张。他晚年在北京大学兼任职务。
他八十大寿时,所指导过的研究生们集资为他在中华书局出了一本黄永年篆刻集,其中一位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博士生,送了我一本。
何家英的年纪与他的名气不相称,算是年少得志的画家。我在《中国书画》杂志没有创刊时,由当时聘请的兼职人员联系,到北京亮马河大厦见他,匆匆一面。联系人对何先生毕恭毕敬,告诉我,能见到何家英先生很不容易。我笑了,这固然是事实,但是事实的另一面他不知道:能被曹博士拜见也很不容易。
这次谈话我只记住一个细节,何先生对我说,他下学期要教学生临《捣练图》。
我在天津访问书画界的老前辈,尤其是人物画领域的,结果听到了不少对何家英极其尖锐的批评意见。当然,都是针对他的画法与画风。毕竟,他的人物画,已经与传统的工笔人物画完全两码事了。
2004年我在国宾馆组织笔会,请的基本上是一流名家,名单上有何家英先生,那天下雪,何先生驾车从天津赶过来,没迟到。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合了一张影。
在上海的二玄社代理店,我见到了刚到上海的高岛先生。二玄社的复制品,对中国书画的贡献,可谓功德无量。我在办刊时为之做过宣传,还专门与日本东京总部方先生联系过。
高岛先生是中国通,对我很客气,我们聊的是美术报刊,他翻着我办的《中国书画》,说日本没有办得这么好的美术杂志。
2006年二玄社在北京展销,我去选了几张大画,花了两三万元,二玄社从日本来了两位,其中一位正是我当年为发介绍二玄社的文章而通过邮件的方先生,于是,那位日本职员特意又请我选了两幅尺许小品,算是大宗消费的赠品。
张静伯无意间我从书房里找了一册张静伯先生九十年代中期出的香港版画册,说明至少在1997年我就与张先生间接有了联系,大概是当时的员工转送给我的。我与张先生见面,已经是2005年以后,他专程到北京闲闲堂来作客,那时他已经是河北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河北省美术研究所所长。
他生活工作在保定,是我的故乡,而我作为游子,乡情颇重,所以,每次回老家,只要有空闲,就会与张先生见面聊聊。
张先生是唐山人,长年在保定工作,是典型的河北人。以我所见所闻,河北省以保定为界,民风迥异,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唐山、沧州是所谓冀北、冀东,而保定是孙犁等作家反复描写的冀中,石家庄、邢台、邯郸是冀南,无论是方言还是风俗,都与河南更为接近。人们习惯于称河北为燕赵,其实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燕与赵可是大有不同的。所以,保定人强烈地不认同石家庄——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张静伯先生未必这样看。
2007年《文博报》创刊,总署批文下来,我来主持创刊号的稿件,于是写了一篇短评,专题赏析张静伯《柿子红了》,这期报纸出了彩色打样,没有面世便胎死腹中。
后来,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推介画家出画册,张静伯先生便把我这篇小文章移用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