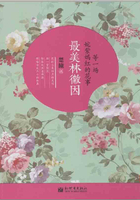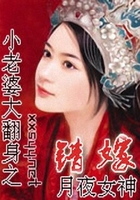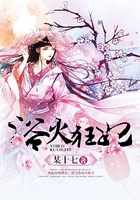1925年10月31日,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九个月的穆尔和十二岁的阿利娅(阿里阿德娜)抵达巴黎。接纳他们下榻的是奥莉加·叶利谢耶夫娜·科尔巴西娜切尔诺娃奥·叶·科尔巴西娜切尔诺娃(1886—1964),俄罗斯文学家,著有《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穆尔的教母。切尔诺娃一家生活拮据,住在维勒特附近,乌尔克运河对岸偏僻的工人住宅区里,但是却从三间房里给他们让出来一间。奥莉加·叶利谢耶夫娜非常喜欢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她的三个女儿——三个少女奥莉娅、纳塔莎和阿加赞赏茨维塔耶娃的诗歌,起初几乎是怀着一种崇拜的心情注视着她,尽她们的所有与客人们分享,并且尽量使他们生活得舒适。但是玛·伊并没有觉得应当对她们表示特别的感激,而且仿佛没有注意到她们的关怀。她在书信里把切尔诺娃一家称为“我们的主人们”(要知道她们是衷心的朋友),抱怨拥挤,街道破旧吵闹,无法专心致志。她看到的是工厂林立的郊区的巴黎,在捷克斯洛伐克平和宁静的乡村住宅住惯了以后,如今周围的环境使她感到非常压抑。
但是她在切尔诺娃家里却完成了她的最长的、大概也是最重要的一部长诗《捕鼠者》——而且甚至还有了一张真正的写字台:是奥莉加·切尔诺娃给她让出来的(奥莉加后来嫁给了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儿子瓦吉姆)。玛·伊是很少遇到这种阔气的东西的——只有她在谁家做客的时候才能遇得到。在许多年当中,她都是把餐桌当作写字台,她带着嘲笑说,“餐桌既是为了我的体力的饮食,也是为了精神的饮食”。要知道,书桌在她的生活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难怪她为了它而写了一部她的最有代表性的长诗,歌颂“比爱情更坚贞——三十年的结缘”:你是松木做的,柞木做的,涂着劣等的清漆,你的鼻孔上挂着圆环,你用途很广——可供就餐,可供花园歇息,但愿不要变成三条腿,但愿!引自组诗《书桌》之一“三十年的结缘……”(1933—1935)。
玛·伊说,她的唯一的财富就是孩子和笔记本。但是后来孩子们离开了她,剩下的只有笔记本了。她在法国自己从来没有写字台,这也是她生活杂乱而贫困的象征。但是她对书桌的歌颂不仅是象征性的,而且也揭示了她的创作的本质。曼德尔施塔姆在街头徘徊,边走边即兴创作,立即使灵感变成了文字,等回家以后再把它们写下来或者口授下来(他的大量的诗稿便是这样创作的),然而茨维塔耶娃却有所不同,她没有笔、没有纸、没有书桌便无法想象。紧接着她的灵感和天启之后,是检查——探索、复查、筛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书桌上创作的过程。
1925年末,玛·伊的丈夫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来到了巴黎。我是1926年1月见到他们俩的,当时我路经勒阿弗尔勒阿弗尔,法国塞纳河口港口城市。,我要在这里换乘航船,去美国各个城市讲学,并且为在俄国被关押的政治犯募捐——当时以高尔基的前妻叶卡捷琳娜·巴甫洛夫娜·彼什科娃为首的政治红十字会还存在。
我觉得玛·伊有些惘然若失。她显然不喜欢巴黎,但是她强打起精神,说在筹备她的公开朗诵会,顺便提到她在写《诗人谈批评》一文。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又在沉浸于他从前的兴趣——他埋头于欧亚大陆运动的事业,筹办《里程碑》《里程碑》系欧亚大陆运动的文学集刊,共出三期。集刊。
我在美国逗留了半年,夏天返回欧洲,在法国南部稍事休息,9月在布拉格重操我往常的文学生涯和社会工作。这期间我收到过玛·伊的几封短简。从这些信里,而更多的是从共同的熟人的叙述中,我得知她二月的晚会很成功,还听说她朗诵时穿的黑色连衣裙是切尔诺娃家的纳塔莎和奥莉娅姐妹俩为她缝制的,她们还在衣服上绣了一只象征性的蝴蝶——普绪刻。玛·伊用晚会的收入同孩子们和奥莉加·叶利谢耶夫娜·切尔诺娃一起在5月里前往旺代旺代,法国西部的一个省会,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皇党叛乱的中心。
旅行。玛·伊认为法国大革命时代这个边远地方的反叛者们是一些浪漫主义的主人公,她喜欢把俄国的白军称为“我们的旺代”;因此才选择了旺代海岸的圣吉尔去休养。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留在了巴黎,忙于《里程碑》集刊。10月举家迁往默登森林附近的默登—贝利维尤,但是并没有住多久。1926年12月31日,我从美国回来以后第一次与玛·伊见面恰恰是在贝利维尤。但是这次会面完全不像她在给捷斯科娃的信里所描述的那样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见的漫画式的,但却完全不可信的反响,在1928年第3期《里程碑》集刊上发表的长诗《新年书简》中有所描写)。我的确是给玛·伊带来了莱纳·马利亚·里尔克逝世的噩耗(他死于12月29日,并非像她写的死于30日)。我非常了解,她对他非常崇拜,因此我在告诉她他的死讯时是非常谨慎的——而不是“顺便”(她的话)。玛·伊非常激动,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今永远也见不到了。”
我在临走之前问玛·伊和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是否愿意到我们的共同的熟人家里,同“自由俄罗斯人”一起迎接新年。当时我个人发生了一件非常悲痛的事,任何节日和饭店我连想都不想想,因此才提到简单的友谊的晚会。如同往常一样,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等着由玛·伊来决定,她回绝了邀请。但是答应了我的请求,请她为《俄罗斯意志》写一篇关于里尔克的文章。过了不久,她往布拉格给我寄来了《你的死》,这篇散文发表在1927年3月号的杂志上。在此之前不久,我在捷俄团结文化慈善协会做过一次关于茨维塔耶娃的创作的报告。显然玛·伊对于根据她的请求由捷斯科娃寄去的关于我的讲演的信息感到不够,因此,当我1927年春天去见她时,她便极想知道关于我的演讲的整个详细情况以及听众对她的反应如何。这时候,玛·伊已经移居到默登村,在贞德大街租了三间套房。
当时她还向我谈起出版诗集的计划,问我喜欢不喜欢《离开俄罗斯以后》这个书名,我对此表示非常赞赏,而然后又同我商量她未来在巴黎举办公开朗诵会,她总觉得主要的难处是选择哪些诗好。她说:“不是为了自己才高声朗诵——而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写诗。”当时我们还商定,在一次晚会上我致开幕词,谈谈她的创作(这件事一直很迟才兑现)。我把《你的死》的校样给她带来了——而且我们说妥,她翻译里尔克的书简(这些书简发表在1929年初《俄罗斯意志》上)。
就在1927这一年里在巴黎与玛·伊会见,对我来说,是值得纪念的。如她开玩笑地指出的那样,“为了办事”她到巴黎来逗留一整天,仿佛强调一下玛丽娜和事情——这两种的结合是荒谬的。她知道了我从现在起打算交替在布拉格住三个月,再在巴黎逗留三个月,便问我是什么原因不在捷克斯洛伐克久居。当然,我只能回答是因为我们准备把刊物移到巴黎来排版印刷,为此购置了一所不大的印刷厂,这一切也可以说成是办事。这是唯一一次玛·伊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问题,而回答——虽然是部分的——毫无疑问她早已明了。我耸了耸肩膀。她连珠炮似的说:“我不想从别人那里,想从您自己的口里听到。”于是我非常简短地向她讲了讲,拉里莎·布奇科夫斯卡娅,我爱上的这位姑娘,去年秋天被捷克斯洛伐克内阁首相的汽车撞死了,警察局企图对新闻界和亲人们掩盖她的死亡的真相。由于我的干预,这件事已被广泛地传播开了,包括国会的问题和向总统马萨里克的报告。在这一切事情过后,我想移居到巴黎来。结束时我也问了玛·伊:“这一切您不是全知道了吗,新年前我去看您时,难道您没有看出我是什么样的情绪?”玛·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因为里尔克的逝世受到很大打击,而您个人的感受我不想当着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的面谈。”就这个话题,我同她再也没有交谈过。
某些苏联批评家很想把茨维塔耶娃的生活与创作划分为三个时期——莫斯科阶段,包括诗人的形成和少年及青年时代的诗歌,这些诗歌对于许多人来讲是最容易理解的,因而也是最容易接受的;1922年出国和侨居期间的沉重的生活,这种生活由于思念祖国而更加沉重;最后,1939年返回苏联,似乎是使她的内心的和诗歌的发展得到了完满的结局。有一点他们却避而不谈,那就是她在苏联受到了如此良好的接待:女儿被发配到劳改营,丈夫被杀害,只发表过她的一首旧作,以至于两年后她自缢而死。总之,整个这一公式是臆造的和虚假的。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远为复杂。
如果能弄清楚,在革命初期的象征主义者、阿克梅主义者、未来主义者以及无产阶级诗人们的圈子里,怎么能够形成像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这样独特的创作个性的,那会是很有意思的,而且这个题目还有待研究。她在1912年到1922年间写的许多抒情诗和长诗,非常之美,但是她逐渐超越了这些诗,而且使她与她的所有的著名的同时代人显著不同的特点,在这些诗里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这些特点构成了她的独创的诗学——即正是那些确定她在20世纪俄罗斯诗歌中的地位和意义的东西。而茨维塔耶娃的天才恰恰是在流亡中,在异国的某种真空中达到了最最充分的发挥。毋庸置疑,我在1922年对她的诗集《离别集》的评论中所指出的转折,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在贫困、孤独和流亡的十七年当中,茨维塔耶娃创作了她的最卓越的作品。尤其是布拉格阶段(1922—1925)标志着创作上的巨大的高涨:被称为“茨维塔耶娃风格”的东西,恰恰是在1922—1926年间,无论是在单独的抒情诗中,还是在《山之诗》、《终结之诗》以及讽刺作品《捕鼠者》(虽然不该给后者,如同给所有具有独特形式的优秀作品一样,贴上文学标签)中,都发挥出了最高的表现力。我认为,茨维塔耶娃的创作鼎盛一直延长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似乎是她在布拉格飞快地起跑以后,一直未停,一往直前地、一个劲儿地继续向前飞奔。“我是在飞跑,”她这样谈到自己。在她少女时代的诗里:“她的大衣的下摆像暴风雨”,或者:我的步伐清楚而又矫健。
我的全部正义恰好在我这步态中得到了体现。引自短诗“他们看到了什么?——大衣……”(1915)。
当然,她的全部诗歌——运动的——都处在语言和韵律的运动和飞行中。但是在1931—1932年间已经觉察到速度在减慢,散文数量在增长。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说这是内心的枯竭。原因在于所谓的巴黎阶段的整个环境。只是仰仗于非凡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在30年代里玛·伊才经受住了命运的一切打击,才没有被摧垮——是后来,在俄罗斯被摧垮的。
很难说,在玛·伊在巴黎近郊最后七年的生活中散文在什么程度上胜过诗歌是有内心根据的,是源于有机的需要以另一种形式来表达自己。当然,许多事情都是由于需要而引起的:散文容易发表,散文容易理解,有读者,稿酬付得多。
如果以玛·伊在法国的全部侨居时间来说,那么可以很容易把它分成几个阶段。1926—1927年间,尽管有许多失败和预示着不祥的征兆,玛·伊还是充满希望的,她相信在法国会找到广大的读者和新的文学创作的可能性。1926年2月晚会的成功肯定了她的这种幻想:这次晚会变成一件盛事,大厅里爆满,玛·伊朗诵她的诗歌,包括《天鹅营》片断,引起了阵阵激烈的掌声,而关于这次演出的总结见于所有俄文的报纸,巴黎的和柏林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态度的转变也使她高兴:不久前他曾说她是“放纵的莫斯科女人”,甚至没有把她的作品收入1924年出版的他编的诗歌总集《俄罗斯抒情诗》,而在《小伙子》问世和私人相识以后,他变成了她的诗歌的崇拜者和忠实的朋友。他于1926年3月为玛·伊安排的英国之行以及她在伦敦两个星期的逗留加深了这种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