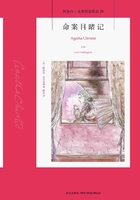发现自己有些反常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明白,这种反常现象万万不该发生在我这个快要退休的男人身上。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里,我是个多少有点名气的画家。我的女儿上高中时因早恋自杀,妻为此生了场大病,治了那么些年,结局是瘫痪在床,并已丧失语言功能。好在妻还能用手写字,当她需要什么时,都会用笔写在纸上告诉我。妻从嫁给我后,就没享过一天福。一个穷画画儿的,日子能好到哪里去?我每天尽心伺候完妻,便静下心来画一些童年时想画的东西。我的心已经麻木了,只有靠回想童年的事情才能有激情作画。除了我的童年,也许这个世界再也不会让我激情澎湃了。可是,就在这时,料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在一次画展中,一位身穿黑衣黑裙的女子微笑着向我走来。坦白地说,她一点也不漂亮,身材矮小且单薄。
她说:“你好。你就是赫老师吧?你的画真好,一个上午我都在看你的画。”
出于礼貌,我答应了她的请求,给了她一张我的名片。她说:“我叫秦媚,也喜欢画画,可以拜你为师吗?”我也记不得当时是对她点头还是摇头。过了好些天,她打来电话,说想把画拿来让我给指导一下。说实话,来找我指导画的男男女女不计其数。等她站在我面前时,我想了半天也没想起她是谁。
她说:“我叫秦媚。”
我忙说:“想起来了。”
其实我在心里早把这个叫秦媚的女子忘得一干二净。她把画的画儿递给我看,我发现她非常喜欢画荷花。尽管画的不是很好,但透着一股灵气。以后秦媚常来让我指导她的画,时间长了,我发现秦媚不光画画儿有灵气,她本人就是一个极有灵气的女子。她的灵气在于她不光能心领神会理解我对她讲过的事,她还能理解好多我不想对人讲的心事。比如,她知道我一直想创作一幅能获大奖的作品,尽管我表面上把作品是否能获奖看得很淡。她还知道我对生活不能自理的妻一直充满感激,因为妻从未抱怨过我带给她的贫穷。妻是一个高干子女,我在妻的面前一直是自卑的,但我从未表现出来。这件事就连温柔的妻也未曾觉察出来,这足以说明我是个很会隐藏内心情感的男人。所以,当我发现自己有些喜欢秦媚时,也一直没表现出来。我想我这一生注定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有一天,秦媚忽然对我说:“我知道,你有一桩最大的心愿未了却,你想开一次个人画展。”
我说:“没影儿的事。我一个快退休的糟老头子,开哪门子画展?”
说实话,我的内心深处,是那样的想在退休前开一次个人画展,可为给妻治病,已花光家中所有积蓄。我所在的单位(画院)是靠国家拔款,能定时发工资就不错了。虽然我知道开不成画展,但我却越来越离不开秦媚了。和秦媚在一起时,创作的欲望是那样的强烈。一连创作了好多作品,妻也为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脸上绽开了久违的笑。当我面对妻的笑脸时,却如同针扎般难受。妻并不知道,我的创作灵感和源泉都缘于另一个女子。妻用笔告诉我她想到郊外住几天,那里,有一间破旧的平房,几年前我为画画儿专门买的。之所以喜欢那里,是因为那间旧平房离村子很远,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非常安静,的确是个画画儿的好地方。房子的价钱更是便宜得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我要陪妻一块去,妻执意不肯。妻要我腾出精力好好搞创作。我只好请一个钟点工陪妻去了郊外。说实话,我真有些舍不下秦媚。我已经深深爱上了秦媚。妻前脚走,秦媚后脚就过来了。秦媚拿来一份开个人画展的协议书让我签字,我感到事情来的太突然,开画展可不是件小事情。
我问秦媚:“你从哪筹来那么多的钱?”
秦媚说:“你到底想不想开画展?”
我说:“想。”
秦媚说:“那你就别再问那么多了,反正这钱不是抢来的,也不是骗来的。”
我看着秦媚,我是那样的爱这个女子。我没有理由拂她的一片好意。那几天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创作中。刚开始,画了几幅都不理想。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的画展了,我总想把最美的作品展示给喜欢我的画的人,也献给秦媚,这个我在心中默默爱恋的女子。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只在火中腾飞的凤凰。醒来后已是下半夜。我再也无法入睡,那只凤凰在我眼前舞过来又舞过去的。我只好走进画室,一连画了七天,才把这只火中的凤凰画出来。在画完最后一笔的时候,我竟累得口吐鲜血,匍然倒地。当我从医院醒来时,这个世界已不是原来的样子。我的妻在我昏倒的那一刻,自己点燃了那间小房子,永远离开了我。据钟点工讲,妻非让她回来拿本书,说书就放在枕头下面。她骑自行车赶回家时却发现枕头下是一封遗书。我颤抖着手接过遗书,看完,我全明白了。原来秦媚的出现,画展的筹款,都是妻早就安排好的。妻的父亲去世时给妻留下了一笔钱,但妻从没告诉我,妻怕我又花在她身上。妻在信上说,不想再拖累我了,她是那样的爱着我,她知道我活得有多苦。她也是这个世上最懂我的人。她要我一定办好画展。要好好的和秦媚过日子。她说已托人了解过,秦媚也是个苦命的女人,也爱画画,会和我有共同语言的。在信的最后,妻说她要走了,要在一片火焰中离我而去。因为这些年她一直瘫痪在床,是我给了她那么多的温暖,她要在温暖的火中到另一个世界里等我。
画展办的非常轰动,特别是那幅名为“火中的凤凰”的画更是吸引了好多商人要出高价收买,都被我婉拒。我们画院的院长劝我把这幅画送到省里参评,同行里的人都说能获大奖已不在话下。
我争求秦媚的意见,秦媚流着泪说:“这幅画的真正主人不是你,也不是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说:“当然明白。怎么会不明白?”
我的画没送到省里参展。
在我家的客厅的墙上,就挂着那幅画,画的旁边是妻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