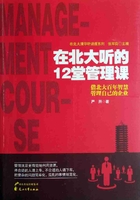这一天程秋云听到桂英诉说她由郑州失败回来的经过,也很觉得心中难受,现在又听到朱氏向她打听消息,料着桂英回家,一定和她母亲有什么为难之处,便在电话里向她道:“桂英若是在家里闷不过,你就可以请她到我这里来玩玩,我总可以劝劝她。”朱氏一想,她们两人,是最要好不过的,让秋云去劝劝她,也许有效,便在电话里重重地拜托了一顿,说是明天一准让桂英再去。
到了次日,朱氏便怂恿着桂英到张家去。桂英在家里,本也就嫌着闷,有母亲一劝,自是更要出去。吃过早饭,第二次又向秋云家来。当她到了秋云家大门口,正要下车的时候,却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白面书生,也是在这里下了车,正在付车钱呢。看他穿了件浅灰色哔叽的长袍,外套着乌亮的缎子马褂,一顶黑呢的帽子,戴着低低地盖了眉头,衬着那脸子白里透红,更是清秀。他付了车钱,正要转身向大门里走,看到一位女郎来了,他就向旁边一候,让她过去。
桂英到郑州去的时候,就把包车夫散了。现在是零碎雇了车子坐,所以到了大门口的时候,她也是站着付车钱。一个当过女伶的人,对于男女之别,是无所谓的。她看见那白面书生站在那里让路,心里却有些过意不去,就向他点了个头,笑道:“不用客气,你请吧。”那书生便取下帽子,点了点头走进去了。
桂英走着进来时,只见他也在秋云卧室外那半内室半客厅的屋子里坐着,张济才夫妇陪着他说话,似乎他在这里也很熟。桂英一进门,大家都站起来,那少年还说了声请坐。桂英笑道:“都是客’别客气呀!”秋云让着座,对他两人看了一下,笑问桂英道:“你们两位,以前认识吗?”桂英道:“你怎么不给我介绍介绍呢?”秋云心里想着,我看你这样子,倒好像熟极了的朋友呢。于是介绍着道:“这是白桂英老板,这是王玉和先生。”桂英点了个头道:“王先生在哪个学校里念书哩?”张济才笑道:“你看着他也像个大学生吗?他可是个小老弟!”桂英欠了欠身子道:“失敬了。”玉和微微一笑道:“这年头,做官还算什么呀,而且是……呵呵,芝麻大的小官。”他说的话,声音并不大,而且又很从容地说,斯斯文文地真像个女孩子一样。
桂英心想,这样一个人,怎么没有一点官僚气,而且还没有一点丈夫气。便笑道:“王先生在哪个机关里?”玉和笑道:“交通部。”桂英道:“嘿!那是个阔衙门。”玉和没有什么可谦逊的,只微微一笑。他和桂英是对坐着的,因为她很爽快地和他说话,他觉得有些受拘束,便偏过脸向左边的张济才谈话,问问这两天铺子里生意怎么样,又问这两天看过了电影没有。张济才道:“今天礼拜六没事,咱们来四圈吧。小一点,五块底。”玉和笑道:“今天我还有个约会。”秋云道:“白老板是难得遇着的。第一次要你打牌,就碰了钉子。”王玉和把脸涨得通红,向桂英一拱手道:“真对不住。”桂英笑道:“这有什么对不住,我又没约王先生打牌。就是约了,您有正事,难道还能为打牌,把正事搁起来吗?”玉和笑道:“不过我这话是不应该说的。大嫂子说的话很对。”秋云道:“你瞧,你还在挺大的机关做官呢!这么一句话,会说得糊糊涂涂,闹不清楚。干脆你就说是‘初次约会,就不能奉陪,很对不住’,这不完了?什么大嫂子说的这话很对。大嫂子说了你什么话不该说呀?”张济才笑道:“人家见了太太小姐们,就够受窘了,你还要在一边儿挑眼,这不是给他难上加难吗?”玉和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笑。张济才道:“你有事,你就请便,明天有工夫,可以真来凑四圈。”玉和在衣架上取下帽子来,两手捧着和秋云、桂英各作两个揖,笑道:“对不住,对不住。”然后走了。
张济才只送到院子里,就不送了。他走进屋来,秋云说:“他这两天来找你找得很勤,有什么事?”张济才道:“他有三百多块钱,放在一家南货店里柜上,老追不起来,托我和掌柜的说,早点腾出来。我已经给他说好了,他想拿回钱去,所以这两天跑得勤一点。”秋云笑道:“他还真能存钱。”张济才道:“他每月拿一百多块钱薪水,一个人,又没有一点耗费,怎么不存钱?”桂英道:“他难道就不养家吗?”张济才道:“他就只有哥哥嫂嫂,在老家守着产业过活。家里本是个小财主,用不着他的钱。他存钱就是想成家。”桂英笑道:
“人家预备钱讨媳妇,你就不该邀人打牌。把人家讨媳妇的钱赢光了,那可损德。”张济才笑道:“他手上,总也有个千儿八百的,打五块底的小牌,能赢他多少钱?你不信,明天他还准来。”桂英道:“那也是你两口子把话说重了,人家不能不来罢?”秋云笑道:“真的,明天你也来打四圈儿玩。他若是不来,我们再找别的角儿。你在郑州搂了一笔来了,应该大家分你一点儿。”桂英笑道:“来就来,还不定谁赢谁的呢。”秋云站起来,挽了她一只手道:“到我屋子里去躺躺吧,我有话跟你说,别瞎聊天了。”于是她二人就走进屋子去了。张济才不便进房,自走开去。
秋云说起朱氏昨日打电话来的话,问她母女有何意见。桂英道:“还有什么好事!我妈要我再唱戏这件事罢了。我实在不愿干。”秋云道:“难道你也想嫁人?”桂英道:“自然,若是林子实没有走,我马上就嫁他。”二人谈了一阵,秋云都觉是满意,桂英都说的是牢骚。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告别,桂英就补了一句道:“明天真约我打牌吗?”张济才夫妇谈的话,不是她重新提起,几乎把这件事忘了。秋云道:“当然是真的。我为什么骗你呢?就算是骗你,你也不过白到我们家来玩上一趟,有什么要紧呢?”桂英听说,这才说了一声“明儿见”,出门去了。
张济才走回屋子来,只见叠的被头,深深地落下两个印,便笑道:“你们两人,一定是搂着抱着,在床上说话的,真是一对孩子。你们说些什么来着,一定提到桂英嫁人那一件事啦?”秋云道:“你管啦,我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张济才道:“不是那样说,我想她要愿嫁人的话,我可以和她做个媒。”秋云道:“你说,和她提个怎么样的人?”张济才笑道:“就是玉和了,不行吗?”秋云脖子一扭道:“你别瞎说了,她什么人也不会看在眼里,玉和在交通部,不过当个科员,她怎样肯嫁他?趁早儿别提。”张济才听了这话,自然也就无可说的。他白天看到桂英一双眼睛,不住地落到玉和身上,正也有些疑心,现在经秋云一说,似乎绝对没有这件事,那也就不必再提了。
这天过去了,到了次日,吃过早饭以后,先是玉和来了。秋云一见,便笑道:“你是来赴牌约的吗?”王玉和笑着点头道:“是的,昨天就对不住,今天我怎能不来呢?”秋云笑道:“我们是跟你闹着玩的,哪个真要你打牌。把你娶媳妇儿的钱赢来了,我们也不忍心。”玉和笑道:“大嫂子这张嘴,我真没有办法,怎么样也说你不赢。”他说着话,取下帽子放在衣钩上,露出他的头发来。他虽然不像时髦少年一样,头发梳得光而又滑,可是既乌亮,又柔软,虽是蓬乱着,也不失其蓬乱的美。秋云心里想着:“这人就是挣钱少一点。照他的人品说,倒是可以做桂英的丈夫。”
她正如此出神,恰好是桂英在院子悄悄地进来。玉和首先看见了她,便是深深地一个点头,这才向秋云笑道:“客来了。”桂英笑道:“我们这算什么客,天天来的人啦。”玉和看了她二人,并不说什么,只站在屋角一边,不住地微笑。秋云笑道:“你姐夫到店里去了,有一阵才能够回来。对不住,要打牌,可得等上一等。”桂英笑道:“我还没有坐定啦,怎么先就谈上打牌起来了?坐着谈一谈吧。”玉和听了这话,脸上倒不免红了一红,似乎坐着谈这句话,桂英是对他说的,却向后退了一步。
桂英坐了下来,只和他的椅子,隔了一张茶几。秋云的老妈子,这时先端上一杯茶来,放在茶几上。因为她放的是很大意的,就靠近了玉和这边,玉和望了她一眼,她很快地转过身子去了,要她移过去,也来不及。他趁着桂英掉过脸去的时候,悄悄地将这杯茶移向桂英的面前来。桂英刚一回头,便闻到一阵茶香,原来人家将茶杯子移将过来了,便笑着道:“别客气,您先喝吧!”玉和将身子微侧了一侧,似乎是个谦让的样子。
桂英身上正披了一条绿色的蒙头纱,溜了下来,慢慢地坠下来,就落到茶几脚边来。桂英正注意茶几上的一杯茶,可就没有注意到脚底下。玉和偏偏是爱管闲事,就俯着身子,将蒙头纱捡了起来。看到桂英带进来的斗篷,搭在一张空的椅子背上,就把斗篷拿起,和那蒙头纱一处,一齐送到挂衣钩上挂着。桂英待要谢谢,他却坐到屋子犄角边去,隔着玻璃窗向外看了看天色。这个小小的动作,把道谢的机会,却已牵扯过去,桂英也就只好不说什么了。
那边茶几上放了一个烟筒子。秋云笑道:“你抽烟吗?”桂英点了点头。玉和靠那张茶几很近,他先把烟筒子送到这边来,接着又在屋子四处张望着,找了一盒火柴,也送到茶几上来。秋云笑道:“你倒成了主人翁了,要你替我招待。”玉和笑道:“我怕招待得不合适。”桂英笑道:“你这样斯文,你们机关里的听差,恐怕也不怕你吧?”玉和不禁笑起来的。他道:“我干我的差事,他当他的听差,我要他怕我做什么?”桂英笑道:“那么……哟,我要说什么啦?说到口里,我又忘了。”秋云道:“准是记起来要打牌了吧?你姐夫就回来的,我们再等一等就行了。你到屋子里来,我有话和你说。”于是挽了她一只手,拉到卧室里。
秋云和桂英同事多年,这两个姑娘,什么秘密交涉都有,两人到了屋子去喁喁密语。一说起来,简直就没有完结。二人连连谈着,恐怕有一小时之久,秋云忽然哟了一声道:“你瞧,我们外面屋子里,还有一个客啦,老把人扔在那里,并不理会,心里可真说不过去。”
说着话,二人同走出来,玉和却笑嘻嘻坐在椅子上站了起来。秋云笑道:
“你一个儿在这里坐着,也不言语一声。”玉和道:“我并没有什么话,言语什么?”桂英道:“坐在这里,不怪闷得很吗?你也该叫人拿一份报来瞧瞧。”玉和道:“我一叫起来,一定把二位的话头打断。知道呢,说是我要报瞧;不知道呢,我这人嚷得主人翁听了,好来陪客。反正二位有事才谈,谈完了,还不出来吗?”秋云听了这话,倒不算什么,桂英留了心听他说话的,觉得这个人,真体贴得有趣,向他微微笑道:“这样说起来,倒是我们没有道理,把你约了来,一个人倒在这里闷待着。”玉和笑道:“那没有关系。这里就像我家里一样,一个人闷待着也好,许多人在一处热闹着说笑也好,没有分别。”秋云心想,“你什么时候约了他?他也奇怪,倒承认你约了他。”便抬了手臂,看了看手表,笑道:“这可了不得,混混就三点多钟了。这个时候济才要到店里去查一査账,牌恐怕是打不成。”玉和道:“没关系,今天礼拜,我又没事。”秋云笑道:“你有了礼拜,好容易休息一天,倒在我们这里干耗着,你有事只管请便吧。”玉和笑道:“也没什么,不过出去玩儿罢了。”秋云笑道:“你还是坐一会吧,要不然,倒好像是我下逐客令了。”玉和笑嘻嘻地拿了帽子在手道:“大嫂子更了不得,现在是出口成章了。”秋云笑道:“我们没念过书的人,什么出口成章,这都是学戏的时候,学来几句歪文。”玉和站了站,笑道:“没事吗?我可告辞了。”秋云道:“昨天是你对不住我,今天是我对不住你。”玉和笑道:“没关系,没关系!”说着,点头拱手地走了。
桂英笑道:“这个人也斯文过分点。”秋云笑道:“你讨厌他吗?”桂英道:“这可是笑话了。一个人太斯文了,倒要讨人家的厌,照你说,应该动手动脚,乱打一顿的,才是好人了。”秋云望了她,微微抿嘴一笑。
桂英在身边一张躺椅上坐下,两手抱了头,瞅了她一眼,笑道:“你笑些什么?”秋云笑道:“我笑我心眼里的事,你就别管了。”桂英伸了个懒腰道:“我也不想打这个牌,身体倦得很,我要回去了。”秋云道:“明天来不来呢?明天晚上,我们来四圈,我两口子,你一个,再把小王找来。”桂英就摇摇头道:“我也没有那样要过牌瘾,昨天打不着,今天来就,今天打不着,明天又来就,难道我们家,就找不出三个打牌的人来吗?”秋云笑道:“不来就罢,我们也不短你这个人啦。”桂英身体实在是疲倦,也不愿和秋云多说,自回家去了。
一进家门,就听到田宝三的嗓音,和朱氏谈话。他道:“大婶,你这话有理,每天进一文,就少亏空一文,若是坐吃山空,凭你手下有多少钱,也是完。”桂英一想,准是田宝三又受了时鹤年之托,前来邀角组班来了。自己实在烦腻唱戏这一件事,有人提到这事,就有些生气。听到田宝三那些话,料着母亲已是和他一条心,便绷紧了脸子,走进堂里去。
田宝三早是站起身来,向她连作了两个揖,笑道:“白老板出门刚回来。”桂英道:“别叫我老板了,我现在又不唱戏,我讨厌这种称呼。”田宝三笑道:“得,不叫白老板,叫白大小姐得了。白小姐,你请坐一会儿,我们有话,和你谈一谈呢。”桂英道:“谈一谈就谈一谈,要什么紧,你让我换件衣服再来谈吧。”说着,很大方地,开着步子走回自己的屋子里去,不多一会,换了一件衣服出来,一面扣纽扣,一面坐着在田宝三对面的椅子上,笑着点了头道:“田三爷有什么话呢?就请你说吧。”
田宝三口衔了烟卷,斜靠了椅子背坐着的。听了这话,立刻将身体坐得端正起来,取下烟卷,用手指头弹了一弹烟灰,先向她笑了一笑。桂英微笑道:“你们说的那些话我也知道,无非是要我上台再唱戏。可是……”田宝三笑着摇了一摇手道:“当然,不能照以前那样干。以前是太痛苦了,白天也唱,晚上也唱,中间还要四面八方去应酬人。”桂英道:“你还少说了两样呢。在馆子里要排戏念戏词,回家又要管家务。”田宝三笑道:“现在不是那么着办了,唱日戏,就不唱夜戏,唱夜戏,就不唱日戏,除非是礼拜六和礼拜这两天,怕要忙一点。再说,我们的本戏也不少了。也许整个月不用得排新戏。我们打算到天津去一趟,去天津的时候,由前台发包银,我也预定了个数目,是一千八百块钱,按日拿钱,准不打厘。”(打厘,即折扣拖欠之谓)桂英道:“真的?谁出那么大的价钱?”田宝三道:“这个你就放心,我不能撒谎。当着大婶儿的面,我田某人,多早撒过谎做事?”朱氏笑道:“田三爷,你干吗说这话?咱们都是吃戏饭的,谁不帮谁的忙呢?反正大家望大家好哇!您要不是为了我们,您今天还不来呢。”
桂英听母亲那话,竟是站在田宝三一条战线上,向自己说话,因微笑道:“我也不是个傻子,有什么不明白的?若是真能拿一千八百块钱包银的话,我倒愿意再干两三个月。开销开销,总也落个一千两千的。”田宝三站起来一拍手道:“白老板,不是,白小姐你这不是想得很通吗?你在没有出阁以前唱一天戏,就可以挣一天钱,为什么不干?有你这一句话,大事全定,咱们这次改到东城吉庆先唱,明天我要去安排。”桂英道:“什么,你不说是上天津去唱吗?怎么又改了在北平唱了?”田宝三笑着用手搔了一搔头发,答道:“我的话,本来还没有和白小姐说清楚。我想,总得先在此地露一露,然而我们整个地往天津一挪,至多在这里也不过唱十天八天罢了。”
桂英鼻子一哼,冷笑道:“我就知道你那些话靠不住。什么上天津,什么包银一千八,我看全是假话。”田宝三站了起来,将眼睛睁得圆圆的,向她道:
“我说句实在话,真不能冤你,若冤你,我是白家的孩子。”朱氏站起来,向他道:“三爷!您别气急,我们姑娘,就是这个脾气,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说着,将茶几上烟卷盒子拿在手上,抽出一根烟卷来,交给他道:“您抽烟,别忙,在我们这儿吃晚饭。”桂英看母亲那个样子,十分的拢络田宝三,似乎不免靠他发财的神气,因笑道:“田三爷,您还和我妈说什么好处来着?我妈真拢络你呀!”朱氏一听这话,不免脸上一红,就道:“你这孩子,说话真有些胡闹,你去唱戏,我能从中要什么好处?俗语说得好,在家不会迎宾客,出外方知少主人。田三爷来了,总是一个客,我能说不招待人家吗?”
田宝三见她娘儿俩抬起杠来,自己很是不好意思,便笑道:“大婶实在客气过分了,我又不是外人。您别张罗,我和白……小姐谈笑。”桂英笑道:“干脆,你还是叫我白老板吧。左一声小姐,右一声小姐,怪不顺口,我看你也叫得怪别扭的。”田宝三见她说话,老是这样开门见真山,也是不好对答,只得笑道:“您知道我不会说话,您包涵一点。”
桂英知道他够受窘的了,也不能再让他为难,便笑道:“这也道不上什么包涵不包涵,不过我为人口直,有话就说出来。咱们废话少说,不管你们在北平唱也好,到天津去唱也好,就是有一层,我要涨戏份,不打厘,有了这两个条件,我就唱着试上一试。还有一层,我不能订什么周年半载的合同,我要干就干两三个月,过了这个日期,我爱唱就唱,不唱呢,谁也不能勉强我。这两件事,你能答应吗?”田宝三手拍了胸道:“这两件事,包在我身上,我就能代表前后台答应你。”桂英笑道:“好!那就得,你回家打赵老四门口过,叫他带胡琴来,明天我先吊一吊嗓子看。这些时候,我什么东西也吃,恐怕是把嗓子糟蹋了。”田宝三道:“行行,这个我准办到。”
朱氏听到她说要吊嗓子,连眉毛都笑着活动起来,连忙站起来插嘴道:“大福在家里,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就让他把老四叫来,要不,就是我自己去跑一趟,也没有什么。”桂英皱了眉道:“我今天又不吊嗓子,忙什么呢?反正是让他明天来,今天晚上去找他,也不算迟。”田宝三插嘴道:“对了,对了,不忙着这一会儿。”朱氏正要姑娘合作的时候,虽是碰了姑娘一个钉子,也不便用话顶她,只好默然坐着。
田宝三心想,好容易把这位姑娘说好了,不要言三语四,说出了漏缝,又把事情闹决裂了,便起身告辞道:“好!咱们还是这样一言为定。我有点事,明天会吧。”说着,向母女拱拱手,走出门去。
朱氏自桂英上郑州去以后,已经知道她十分坚决不肯唱戏了。就是她由郑州回来,几次探听她的口气,她也是口气很紧,没有一点松动。今天她对于田宝三的话,并没有什么为难之处,很痛快地就答应了,这件事很有些奇怪,不过她说只唱两三个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两三个月以后,她还有什么打算吗?这也不必管她,只要她肯唱戏,以后的事,慢慢再说就是了。偷眼看看桂英的颜色,并不大好,也就不敢多说什么了。
到了次晨十点钟,桂英不曾起来多久的时候,就听到院子里有人叫了一声白老板,正是那赵老四的嗓音。桂英笑道:“嘿!你真来了,谁给你带的信?”
赵老四穿了件黑布夹袍子,歪戴一顶呢帽,口里斜衔了一支烟卷,手里提了一只蓝布胡琴袋,一溜歪斜地走到堂屋里来,一边连忙答应桂英道:“这几天,我正在着急,没有了闹儿,正找赵旺呢(土典故,出自旧剧《荷珠配》,即找饭碗之意,剧界人喜言之)。听说您又要露了,我又有希望了,所以一高兴,马上加鞭,就到辕门听点。”说着话在椅子上坐下,将胡琴挂在靠椅上。
桂英一掀帘子走出房门,赵老四立刻站起来弯着腰道:“白老板您好!”桂英笑道:“好什么?好了也不再上台了。”赵老四笑道:“话不能那么说,咱们是干哪行的,总得干哪行。咱们要好,得由唱戏上去找出路。咱们不唱戏,怎么也好不了,反正大银行的经理,不能让给咱们做。”桂英道:“真的吗?老四,你记着我的话。有一天我不唱戏了,你看好得了好不了?”赵老四心想:“你不在唱戏上面找好,你打算怎么着?”可是现在也不敢和她拌嘴,只得闷在心里。由胡琴袋里抽出胡琴来,架起大腿,将胡琴袋盖在膝盖上,胡琴放在大腿上,先调了调弦子,便笑着问桂英道:“今天您打算试试哪一段?”桂英道:“我听到一些消息,有人说我唱功不行了,我倒有点不服,你就跟我拉一段六月雪,看我是行不行?”赵老四心里可就想着,怎么她倒要唱这样的重头戏,一面笑道:“对了,唱功戏,咱们也得预备预备。”
朱氏听了桂英要吊嗓子,早是自己倒了一杯茶,亲自送到桂英的手上来。桂英接了茶杯,向窗户站定,就应着胡琴唱了起来。这六月雪的一大段二黄,音调是非常地凄楚苍凉,而且词句也多。桂英在台上向来以做白取胜,对于这样的唱功戏,向来不肯一试。她今天突然唱起这种戏来,气力可就有些不济,只唱到了一半,便有些吃力,但是她绝对不服这口气。在胡琴过门的时候,喝了一口茶,又接着唱下去。
但是嗓子这样东西,伶家叫做本钱,那是极有道理的,没有本钱,硬拼硬凑,决计是闹不好。所以桂英唱到三分之二时,简直唱不下去,便突然停住,将手向赵老四乱摇道:“得了得了,我不行,明天再唱吧。”赵老四停住了胡琴,笑道:“本来您开口,就试唱这样的重头戏,也不应该,您休息休息,不忙,回头咱们再来试个四句头。”桂英坐下来,那只空手托了拿茶杯的手,许久不做声。
赵老四知道她十分不高兴,放下胡琴不好,拉着胡琴也不好,手扶了琴把,只管望了她发愣。桂英道:“得了,戏饭吃不成了,我得另想我的办法。”朱氏拿了一盒烟卷出来,递给赵老四,他就趁此放下胡琴,接住一根烟卷。朱氏对桂英道:“你不忙,回头……”桂英也不等母亲将这话说完,便起身向屋子里走。朱氏知道她自己嫌唱得不如意,所以生气,这全是小孩子脾气,没有法子和她分证,只得由她去,坐在外面屋子里就和赵老四说闲话。
不相干的话,说了二十分钟之久,不见桂英出来,也听不到她在屋子里什么声音。朱氏口里说着话,耳朵正用力向屋子里听着。忽然啪啪地几声响,非常地紧脆,朱氏吓了一跳,连忙跑进屋子去一看,只见挂着的汪督办的那个大半身像,被她连镜框子一齐打碎,抛在地上。她眼睛红红地,手撑了床栏杆,托住了自己的头。朱氏道:“又犯了你那个倔脾气。”桂英道:“他害得我好苦。我要是不相信他的话,老那样唱着没有什么关系。先是说不唱戏,现在,又唱起来了。若是唱不红的话,我拿什么脸子去见人?”朱氏弯着腰待要将那相片拾起,桂英突然跳了起来,用脚在镜框上一顿乱踏,踏得那镜子上的玻璃,乒乓作响。朱氏向后退了一步,不觉呆了。桂英将镜框连踢了几脚,然后向床上一倒,伏在被上哭了起来。
朱氏对于她这种情形,大是不解,便道:“这是什么意思?你嗓子不好,与他也没有什么关系呀!”不料这几句话,说得桂英更是伤心,索性呜呜然放声大哭。赵老四在外面听了很是纳闷,难道唱六月雪会唱得她伤起心来了?要不然,她是怕嗓子坏了,戏唱不好。可是她根本就不唱这一路戏,嗓子能对付就行了,为什么这样发急呢?朱氏和赵老四,总算是和桂英最接近的人,可是对于桂英的心事,依然是猜不透。而桂英一肚苦水,无人能知,这就更不能止住自己的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