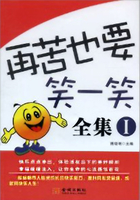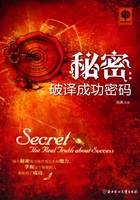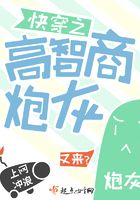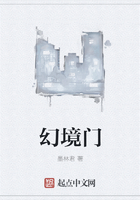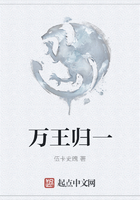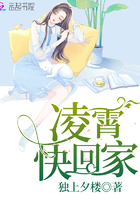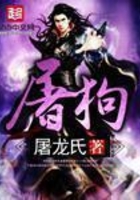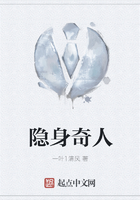世上每一道栏杆
都出于对人的不信任。
你看,你就是不听话。不仅不听话,而且翻开这本书,你在目录里一眼看到这个标题,第一反应绝不是避开这篇文章,而是直奔这里。你想搞清楚,为什么这篇文章禁止阅读,尽管你也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搞清楚。类似的例子还有“千万不要幻想屋子里有一头粉色的大象”。这句话看似禁止,实则是一种提醒。很多容易焦虑的人甚至会被这句简单的话折磨疯掉:你越是不让自己去想一头粉色的大象,那头粉色的大象越是会在你脑海里漂浮不止。
这些年我一直认为,世上每一道栏杆都出于对人的不信任。人能接受这种不信任。但如果栏杆上挂有禁止翻越的提示牌,却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这里一定经常有人翻,进而想:那我也可以翻。几天前,我为了吃一串豆腐跑到市里,路过一条巷子时,看到墙上写了六个大字:此处禁止小便。我一愣,小腹一阵温热,突然有了尿意。看到那六个字前,别说随地小便的想法,我连尿意都没有。看到禁止什么,就会想做什么,是我从小到大始终没能痊愈的顽疾。
我讨厌“禁止”这两个字,它总容易让我产生“假如老子做了,那你又能拿我怎样”的冲动。你对我说人应该不要随地小便,我会表示赞同。但你非要告诉我,人禁止随地小便,我就会想,我尿了会死还是怎样——这简直是在提醒我若此时此地没人,我便可以小便。
禁止会激发我的逆反心。逆反这事,说难听点是犯贱,说好听点是不信邪。但究竟是犯贱还是不信邪,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逆反程度,只取决于世间有些事,到底该不该禁止,到底该何时禁止。
不该禁止的事,禁止即是提醒。像某个世界级工厂,绝不会在自家厂房楼顶写上:禁止跳楼。而禁止无效的事,用简单的一块牌子挂在那里,不过是把错误导向另一个地方。就像一条常被倒垃圾的小巷,在小巷入口挂一个禁止倒垃圾的牌子,最终不过是把垃圾导向另一条小巷。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放一个垃圾桶。
如果我没记错,我小时候闯过最大的祸,是在自家猪栏里纵火。那天爸爸杀完被烧坏的猪,把我揍得半死后,绝望地问:崽,你为什么要用打火机烧猪栏里的柴?我吓坏了,不吭声。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那个下午我之所以用打火机烧猪栏,是因为之前有次我在玩打火机时,爸爸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你点点鞭炮可以,千万不能到猪栏里点柴。这句话当时就把我弄疯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翻来覆去,满脑子都是“不能用打火机去猪栏点柴”。第二天,我就点了。
讲道理的话,这事怪我,因为火确实是我放的。更讲道理一点,这事还是得怪我爸。不是他,我根本不会想到猪栏里有堆柴很好烧,一点就着。事实上,要不是我爸一直显得智商不高,我甚至会怀疑,他是因为每天被我妈勒令去喂猪,于是对猪心生恨意,便以禁止为名义,对我进行刻意提醒。最终完成借刀杀猪的“宏伟计划”。
世间很多事都是如此。以禁止的方式试图阻碍成长,往往会揠苗助长。对人对事都往坏处想,然后为了消除潜在风险和变坏的可能性去提前禁止,有时恰是把人和事往坏处推。而不愿接受质疑的,往往会受到更多质疑。不允许反驳的,往往会勾起人反驳的欲望。被压抑的终会反弹,被掩盖的终会爆发。甚至,很多事,明明是好事,一旦禁止就会显出事情的反面来,好事最后也就成了坏事。实际上,除了法律条文中写定的禁止,社会针对群体的禁止,群体针对个体的禁止,大多数都源于懒惰和想当然。懒惰是,我们以为一块牌子就能使人改变行为;想当然是,我们认为任何事,只要写上禁止,就能让人望而却步。这种拍脑袋的行为,自然会导致更多拍胸脯的冲动。
对于青春期孩子而言,逆反是成长之路的必经阶段,源于建立自我、挑战权威的本能。对于一个社会而言,逆反的背后,必然隐藏不合理的现象和想象。按心理学定义,逆反是人们彼此之间为维护自尊,对对方的要求采取相反的态度和行为。
所以,很多时候,问题不是你明明看到这篇文章禁止阅读却偏要阅读,而是我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不理性甚至是不负责任的标题来吸引你阅读。
在现实生活中,当一个人无视禁止,采取不理性的行为以维护自尊时,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如何使那块禁止的牌子更深入人心、更显而易见,而是要想,那个人的自尊,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受到了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