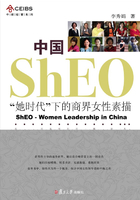1.关于十六步
确认电梯关门的那“咻”一声压缩机声在背后响过之后,我缓缓合上眼睛。我将意识的断片归拢在一起,沿着走廊朝门那边走了十六步。闭眼十六步,不多也不少。威士忌把脑袋搞得昏昏沉沉,犹如磨损了的发条,口中满是香烟的焦油味儿。
尽管如此——即使醉得再厉害——我也能闭着眼睛像用格尺拉线一样径直行走十六步。这是长年坚持这种无谓的自我训练的结果。每次喝醉我都直挺挺地伸直脊背,扬起脸,把早晨的空气和水泥走廊的气味大口吸入肺中,而后闭目合眼,在威士忌迷雾中直行十六步。
在这十六步天地里,我已被授予了“最有礼貌的醉酒者”称号。其实十分简单,只消把醉酒这一事实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即可。
没有“可是”没有“但是”没有“只是”没有“不过是”,什么也没有,醉了就是醉了。
这样,我得以成为最有礼貌的醉酒者,成为起得最早的灰椋鸟,成为最后通过铁桥的有篷货车。
五、六、七……
到第八步站住睁开眼睛,做深呼吸。有点耳鸣,仿佛海风穿过生锈的铁丝网。如此说来,已有好久没看到海了。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六时三十分。看海的理想季节,理想时刻。沙滩尚未给任何人污染,唯有海鸟的爪痕如被风吹落的针叶零星印在水边。
海?
我重新起步。海忘掉好了,那玩意儿早已消失在往昔。
第十六步立定睁眼一看,自己已照例准确地站在球形门拉手跟前。从信箱里取出两天的报纸和两封信,夹在腋下,然后从迷宫般的衣袋里摸出钥匙,拿在手上,把额头贴在凉冰冰的铁门上。片刻,耳后似乎传来“咔嗤”一声响。身体如棉花吸满酒精,只有意识较为地道。
罢了罢了!
门打开三分之一,滑进身体,把门关上。门内寂静无声,过度的寂静。
随后,我发现脚下有一双无带无扣的红色女鞋。鞋很眼熟,夹在满是泥巴的网球鞋和廉价沙滩拖鞋之间,看上去好像过时的圣诞节礼物,上面飘浮着细小尘埃般的沉默。
她趴在厨房餐桌上,额头枕着两只胳膊,齐刷刷的黑发掩住侧脸,头发间露出未遭日晒的白皙的脖颈,没印象的印花连衣裙肩口隐约现出胸罩细细的吊带。
我除去上衣,解下黑领带,摘下手表。这时间里她一动没动。她的背使我想起过去,想起遇见她之前的事。
“喂!”我招呼一声,但听起来全然不像自己的语音,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特意运来似的。不出所料,没有回音。
看情形她既像睡,又像哭,也好像死了。
我坐在桌子对面,指尖按住眼睛。鲜亮的阳光把桌面分开,我在光之中,她在淡淡的阴影里,阴影没有颜色。桌上放着一盆枯萎的天竺葵。窗外有人往路面洒水。柏油路面上响起洒水声,漾出洒水味儿。
“不喝咖啡吗?”
还是没有回音。
确认没有回音之后,我起身进厨房碾够两人喝的咖啡豆,打开晶体管收音机。碾罢豆粒,发现其实是想喝加冰红茶。我总是事后才接二连三想起许多事。
收音机一首接一首播放极为适合清晨的无害流行歌曲。听这样的歌,我觉得十年来世界好像一成未变,无非歌手和歌名不同罢了,我增加十岁罢了。
确认壶水开了,我关掉煤气,等了三十秒钟,把水浇在咖啡末上。粉末吸足热水,缓缓膨胀,温暖的香气开始在房间里荡漾,外面好几只蝉叫了起来。
“昨晚来的?”我手拿水壶问道。
她的头发在桌面上略微上下摇了摇。
“一直在等我?”
她没回答。
水壶的蒸汽和强烈的日光使房间变得闷气了,我关上洗碗槽上面的窗户,打开空调器,把两个咖啡杯摆在桌面上。
“喝呀!”我说。声音一点点变回了自己的语音。
“……”
“喝点好。”
足足隔了三十秒,她才以缓慢而均衡的动作从桌面上扬起脸,怅怅地盯视着枯萎的盆栽,几根细发紧贴在湿脸颊上,微微的湿气如光环一般在她四周游移。
“别介意,”她说,“没打算哭的。”
我递过纸巾盒,她拿来无声地擤把鼻涕,不无厌烦地用手指拨开脸颊上的头发。
“本来想在你回来之前离开来着,不愿意见面。”
“改变主意了?”
“哪里。只是哪儿都懒得去。不过会马上离开的,别担心。”
“反正先喝杯咖啡好了。”
我边听收音机里的交通信息边啜咖啡,用剪刀剪开两封信的封口。一封是家具店的通知,说若在指定期间购买家具可全部减价两成。另一封是一个不愿意想起来的人来的不愿意看的信。我把两封信揉成团扔进脚下的废纸篓,嚼了一块剩下的奶酪饼干。她像在驱寒似的双手拢住咖啡杯,嘴唇轻贴杯边定定地看着我。
“电冰箱里有色拉。”
“色拉?”我抬头看她。
“西红柿和扁豆,只剩这个了。黄瓜变坏扔了。”
“唔。”
我从电冰箱里拿出装有色拉的蓝色深底冲绳玻璃盘,把瓶底仅剩五毫米的色拉调味料全部淋到上面。西红柿和扁豆冻得如阴影似的瑟缩着,索然无味。饼干和咖啡也没有味道,怕是晨光的关系。晨光把所有的东西都分解开来。我不再喝咖啡,从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香烟,擦燃完全陌生的火柴点上。烟的端头“嚓嚓”发出干燥的响声。紫色的烟在晨光中勾勒出几何花纹。
“参加葬礼去了。然后去新宿喝酒,一直一个人喝。”
猫从哪里走来,打个长长的哈欠,然后一跳上了她的膝盖。她搔了几遍猫的耳背。
“不必解释什么,”她说,“那已跟我无关。”
“不是解释,说说而已。”
她略微耸下肩,把胸罩吊带塞进连衣裙。她脸上全然没有称得上表情的东西,使我想起在照片上见到的沉入海底的街市。
“过去一个一般的熟人,你不认得的。”
“是吗?”
猫在她膝头尽情摊开四肢,“呼”地吐出一口气。
我缄口不语,望着烟头的火光。
“怎么死的?”
“交通事故,骨头折了十三根。”
“女孩?”
“嗯。”
七点定时新闻和交通信息结束,收音机开始重新播放轻摇滚乐。她把咖啡杯放回碟子,看着我的脸。
“嗳,我死时你也会那么喝酒?”
“喝酒跟葬礼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只是开头一两杯。”
外面新的一天即将开始,新的炎热的一天。从洗碗槽上面的窗口可以望见高层建筑群,它比平日远为炫目耀眼。
“不喝冷饮吗?”
她摇摇头。
我从电冰箱里拿出一罐冰得很透的可乐,也没往杯里倒,一口气喝光。
“跟谁都睡觉的女孩。”我说。简直像悼词,故人是跟谁都睡觉的女孩。
“为什么对我说这个?”
我也不知为什么。
“总之是跟谁都睡觉的女孩子?”
“的的确确。”
“但跟你是例外喽?”
她的声音里带有某种特殊意味。我从色拉碟子上抬起头,隔着枯萎的盆栽看她的脸。
“这么认为?”
“有点儿。”她低声道,“你嘛,是那种类型。”
“那种类型?”
“你身上有那么一种味道。和沙钟一个样。沙子流光了,必定有人把它倒过来。”
“大概是吧。”
她嘴唇绽开一点点,又马上复原了。
“来取剩下的东西的。冬天用的大衣、帽子,等等。已经整理好装在纸板箱里了,有空儿替我运到运输社那里可好?”
“运到你家去。”
她静静地摇摇头:“算了,不希望你来,明白?”
的确如此。不着边际的话我是说得太多了。
“地址晓得?”
“晓得。”
“这就完事了。打扰这么久,抱歉。”
“文书那样就可以了?”
“唔,都结束了。”
“真够简单的。还认为啰嗦得多呢。”
“不知道的人都那么认为。其实很简单,一旦结束的话。”这么说着,她再次搔了搔猫的脑袋。“两次离婚,差不多成专家了。”
猫闭着眼伸了下腰,脖子轻轻枕在她手腕上。我把咖啡杯和色拉碟放进洗碗槽,拿账单当扫帚把饼干渣扫在一起。太阳光刺得眼球里面一剜一剜地痛。
“小事都写在你桌子的便笺上了——各种文书放的地方啦,收垃圾的日期啦,不外乎这些。不清楚的就打电话。”
“谢谢。”
“想要孩子来着?”
“哪里,”我说,“不想要什么孩子。”
“我相当犹豫。不过既然如此,没有也好。或者说有小孩不至于如此吧?”
“有小孩离婚的也多的是。”
“是啊,”说着,她摆弄了一会我的打火机,“现在也喜欢你的,不过,肯定也不是那种问题。这我自己也非常清楚。”
2.她的消失,照片的消失,长筒裙的消失
她走后,我又喝了一罐可乐,然后冲热水淋浴刮须。香皂也好,洗发液也好,剃须膏也好,什么都开始变少了。
淋浴出来,梳发、抹香水、掏耳朵,接着去厨房热了热剩下的咖啡。餐桌对面再也没有人坐。静静望着谁也没坐的椅子,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小孩子,一个人留在基里柯油画的奇异而陌生的街道上。但我当然不是小孩子。我什么也不想地啜着咖啡,慢慢花时间喝罢,发了一会呆,之后点燃一支烟。
整整二十四小时没睡,却莫名其妙地不困。体内倦倦的、懒懒的,唯独脑袋犹如熟悉环境的水生动物,在纵横交错的意识水路中无目的地往来穿梭。
怔怔地打量无人的椅子的时间里,我想起过去看过的一本美国小说:妻子离家后,丈夫把妻子的筒裙在饭厅对面椅子上挂了好几个月。如此想着,开始觉得这构思不坏。倒不是能解决什么,但总比放早已枯萎的天竺葵盆栽聪明得多。即使拿猫来说,若有她的东西也可能多少安稳些。
逐个拉开她的卧室抽屉,哪个都空空如也。一块虫子咬过的旧围巾,三只衣挂,几包卫生球,别无他物。她把什么都席卷一空。原先逼仄地摆在卫生间里的零零碎碎的化妆品、卷发夹、牙刷、吹风机、莫名其妙的药、月经用品以及长筒靴、凉鞋、拖鞋等所有穿的东西,帽盒、整整一抽屉饰物、手袋、挎包、小提箱、钱夹,总是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内衣、袜子、信——大凡散发她气息的东西尽皆荡然无存,甚至指纹都了无遗痕,我觉得。书箱和唱片架的大约三分之一也不翼而飞。那是她自己买的或我送给她的书和唱片。
打开影集一看,她的照片全取下了,一张没剩。我和她的合影,她那部分齐齐剪下,只有我剩了下来。我的单人照和风景照动物照依然如故。这样,三册影集里收存的便成了被彻底修整的过去。我总是孑然一身,其间点缀着山、河、鹿、猫的照片,简直就像生下来时一个人,迄今为止一个人,以后也一个人似的。我合上影集,吸了两支烟。
我想长筒裙留下一条何尝不好,但这当然是她的问题,由不得我说三道四。她决意什么也不留下,我只有接受而已。或者如她期望的那样,只好当她一开始就不存在。她不存在的地方,她的长筒裙也不存在。
我把烟灰缸浸入水中,关掉空调和收音机,又想了一通她的长筒裙,死心上床。
从我答应离婚、她离开公寓以来,已过去一个月了。这一个月几乎毫无意义。虚无缥缈的、犹如温吞吞的果冻的一个月。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变化发生,实际上也什么都没变。
早上七点起床冲咖啡,烤面包片,出门上班,在外面吃晚饭,喝两三杯酒,回到家在床上看一个小时书,熄灯睡觉。周六周日不工作,一清早就开始转几家电影院打发时间。之后照常一个人吃晚饭,喝酒,看书睡觉。一个月我就是这样度过的,恰如某种人把月历上的数字一个个涂黑。
她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无可奈何的,无非已经发生的事发生了罢了。哪怕我们四年过得再风调雨顺,那也已不再是重要问题,一如被抽去照片的影集。
与此相同,即使她同我的朋友长时间以来定期睡觉而某一天索性搬去同居,也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问题。那种事是完全可能发生并且实际上也屡屡发生的。纵然她果真如此,我也并不觉得发生了什么特殊事件。说到底,那是她本身的问题。
“说到底,那是你本身的问题。”我说。
那是她提出离婚的六月间一个周日午后,我把啤酒罐的易拉环套在手指上玩弄。
“你是说怎么都无所谓?”她问,语调非常缓慢。
“也不是说怎么都无所谓。”我说,“只是说那是你本身的问题。”
“说实话,并不想和你分手。”她稍后说道。
“那,不分不就行了!”
“可是和你一起,哪里也到达不了的呀。”
往下她什么也没说,但我觉得她想说的不难明白。再过几个月我就三十、她就二十六岁了。与此后将要到来的东西的大小相比,我们迄今所筑造的委实太微乎其微了,或者说是零。四年时间简直是在靠存款坐吃山空。
责任基本在我。我大约是不该同任何人结婚的。至少她不该同我结婚。
起初,她认为自己为社会所不容而我为社会所容。我们较为成功地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然而在两人认为可以一直这样干下去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坏掉了。尽管微不足道,但已无可挽回。我们置身于被拉长了的、平静的死胡同中。那是我们的尽头。
对于她,我成了已然失却之人。无论她怎样继续爱我,那都已是另一问题。我们过于习惯相互的角色了。我再也没有能够给予她的了。她本能地明白这一点,我凭经验了然于心。不管怎样都已无救。
这么着,她连同几件筒裙一起从我面前永远地消失了。有的东西被遗忘,有的东西销声匿迹,有的东西死了,而其中几乎不含有悲剧性因素。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二十五分
我确认电子表上这四个数字,然后闭起眼睛,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