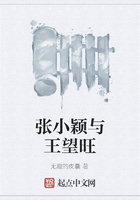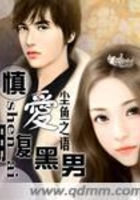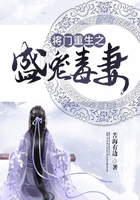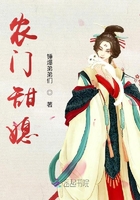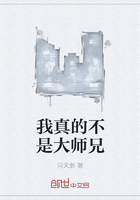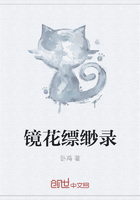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摆脱玄武门之变留下的心理阴影。
我们说过,这样的一种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缔造盛世贞观的潜在动力之一,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也驱使着李世民把权力之手伸向了他本来不应染指的地方。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地方历来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然而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却非进不可。
形象地说,李世民“非法进入”的是“历史殿堂”的“施工现场”。
准确地说,是李世民执意要干预初唐历史的编纂。
进而言之,就是李世民很想看一看——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
为此,当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后,李世民终于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打算调阅起居注的理由是“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听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与他在贞观时代的种种嘉言懿行颇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动机绝非如此单纯!退一步说,就算天子的出发点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轻易放弃史官的原则。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天子的要求,说:“从没听说有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
李世民碰了钉子,可他还是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记吗?”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露骨了,如果换成哪个没有原则的史官,这时候估计就见风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却仍旧硬邦邦地说:“臣的职责就是这个,干吗不记?”而黄门侍郎刘洎则更不客气,他说:“人君要是犯了错误,就算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
这句话的分量够重,以至于李世民一时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次的试探虽然失败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放弃。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观“当代国史”。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这次还是那套说辞,可在听到房玄龄依旧给出那个让他很不愉快的答复后,他就不再用试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龄下了命令:“卿可撰录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就等于是抗旨了。迫于无奈,房玄龄只好就范。结果不出人们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
看完有关玄武门之变的原始版本后,李世民显得很不满意,命房玄龄加以修改,并且对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导性意见”。这段话非常著名,被后世史家在众多著作中广为征引,同时也被普遍视为李世民篡改史书的确凿证据。
当然了,纯粹从字面上看,李世民说的这段话也没什么毛病,甚至还颇能体现他作为一代明君的坦荡襟怀和凛然正气。因为他告诉房玄龄:不必替他遮遮掩掩,反正玄武门事件本来就是像“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那样的义举,目的是为了“安社稷、利万民”,所以史官大可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更不必用“隐语”和“浮词”来替玄武门事件进行粉饰。最后,李世民要求房玄龄及其史官们:在修改的时候不必有什么忌讳,大可“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那么,今天的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段话呢?是把它看成李世民直面历史、忠于事实的一种可贵品质,还是恰好相反,将其视为有损于李世民明君形象的篡改历史的行为?
很遗憾,在绝大多数后世史家的眼中,李世民的上述言行被普遍判定为后者。
人们倾向于认为,李世民所谓的“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安社稷、利万民”等语,其实是为玄武门之变定下了一个政治基调,也是为史官们修改史书提供一个钦定的指导思想。比如牛致功就在《唐高祖传》中说:“李世民要史官们把他利用阴谋手段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正当义举,也就是要把他杀兄夺嫡之罪合理化。房玄龄、许敬宗正是遵照这种要求修改《实录》的。”
既然皇帝已经给定了框架,史官们当然要努力把李世民塑造成“周公”、“季友”这样的人物了,而他的对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贞观史臣的笔下当然也要处处向“管、蔡”、“叔牙”看齐了,若非如此,又怎能衬托出李世民“安社稷、利万民”的光辉形象呢?
时至今日,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贞观史臣在玄武门之变的前前后后确实对李世民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与此同时,李建成和李元吉则遭到贞观史臣不遗余力的口诛笔伐,被描写成了彻头彻尾的昏庸之辈、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兽。对此,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述了《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中的相关描写,今节录于下。
《高祖实录》曰:“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常与博徒游……”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闻于远迩。今上以为耻,尝流涕谏之,建成惭而成憾。”
《太宗实录》曰:“隐太子始则流宕河曲,游逸是好,素无才略,不预经纶,于后统左军,非众所附。既升储两,坐构猜嫌。太宗虽备礼竭诚,以希恩睦,而妒害之心,日以滋甚。又,巢剌王性本凶愎,志识庸下,行同禽兽,兼以弃镇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
正因为两朝实录对建成和元吉极尽歪曲之能事,所以连一向倾向于李世民的司马光也不得不在《通鉴考异》中下了一道按语:“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能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而《剑桥中国隋唐史》也认为:“建成和元吉两个人在正史上都被说得无甚是处。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元吉酷嗜射猎,在战阵上反复无常,又是个好色之徒和一个虐待狂;太子建成则冥顽不灵,桀骜难驯,沉湎酒色。这些贬词至少是传统史料中这一时期的记载对他们故意歪曲的部分结果。”
赵克尧、许道勋在《唐太宗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唐朝官修史书总是把建成与元吉加以丑化,而对世民则尽量粉饰。直至五代,刘昫等编撰《旧唐书》,也持相同的观点。……所谓‘直书其事’,则未必能做到实事求是。”而牛致功更是在《唐高祖传》中强调,从唐朝的《实录》、《国史》到后来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无不受到李世民改史的恶劣影响。他说:“这几部史书,是后来人们研究唐代历史的主要依据。在这几部史书的影响下,高祖缺乏果断处事的能力,李建成庸劣无能,李世民功德卓著,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常识。由此可见,李世民为了文过饰非而歪曲历史、篡改《实录》的影响多么深远。”
综上所述,贞观史臣确实曾经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对玄武门之变前前后后的历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而篡改的主要方向有三个:一、对李世民加以美化和粉饰;二、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加以丑化和歪曲;三、对有关玄武门事件的许多关键性细节加以改动和增删。
也许,正是由于一些重大的历史细节被动过手脚,所以像“杨文干事件”、“毒酒事件”、“昆明池密谋”、“傅奕密奏”、“秦王密奏”等一系列事件才会变得云山雾罩、扑朔迷离,并且引起后世史家和学者的广泛争议,甚至屡屡被指斥为杜撰和造假。
但是,当后世学者在怀疑并指责李世民及其史臣篡改历史的同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却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既然李世民要改史,为什么不改得彻底一点?为什么不把他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行径全部抹掉呢?尤其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亲手射杀兄长李建成的那一幕,为什么仍然白纸黑字地保留在史册当中?假如把建成和元吉改成是死于乱刀之下、或者是身中流矢而亡,岂不是更能减轻他弑兄杀弟的罪名?还有,那十个被残忍屠杀的侄子,李世民同样可以把杀戮责任随便推到某个小人物身上,或者干脆也说死于乱兵之中,可为什么他没有这么做呢?为什么这一切,李世民都没有掩盖?
在此,我们似乎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李世民所说的“周公诛管、蔡”的那段话。也许那不仅是一种冠冕堂皇的道德说辞,也不仅是为史臣改史所定的政治基调,很可能同时也是李世民努力要达成的一种自我说服。
也就是说,李世民需要告诉自己和世人,他诛杀建成、元吉的行为并不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杀戮,而是一种锄奸惩恶、济世安民的义举!进而言之,恰恰是毫不避讳地、大张旗鼓地将这段历史昭示天下,他才能减轻自己内心的负罪感,获得一种内心的安宁,也才能正大光明、堂而皇之地获得一种道德解脱。
如果用宗教的语言来说,这种心态和做法可以称之为“发露忏悔”,也就是主动袒露以往的某些“罪恶”,让其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中,或者说让其在道德与正义的阳光下涣然冰释,从而让自己获得道德与灵魂意义上的新生。
综上所述,在玄武门事件中,李世民真正要掩盖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兄弟和侄子们的死亡真相,而是一种他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的行为。换言之,这种行为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发露”的,宁可背负着它沉重前行,也绝不愿将其公之于世!
那么,这种行为是什么呢?
有关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的那场流血政变,李世民到底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呢?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看了一本古籍中的一篇文章后,内心某个隐秘的角落忽然被触痛,于是潸然泪下、悲泣良久。他动情地对身边的侍臣说:“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父母)也。……朕昨见徐干(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中论·复三年丧》篇,义理甚深,恨不早见此书。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贞观政要》卷六)
李世民说的“所行大疏略”,意思是高祖李渊逝世时,他所行的丧礼过于粗疏简略,未尽到人子之孝,因此深感愧疚和自责,追悔莫及。
也怪不得李世民会感到痛心愧悔,因为对待高祖的身后事,他的许多做法的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埋葬高祖的献陵在规格上就比埋葬长孙皇后(包括逝世后的太宗本人)的昭陵要逊色得多。献陵是“堆土成陵”,规模和气势十分有限;而昭陵则是“因山为陵”,规模浩大、气势宏伟。高祖安葬后,李世民也并未流露出应有的思念之情,而对长孙皇后则是情深意长、无比怀念,曾“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结果立刻遭到魏徵的暗讽和讥刺。
而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突然对父亲流露出的这种忏悔和内疚之情,难道仅仅是因为自己在高祖身后没有尽到孝道吗?在高祖生前,李世民又做得如何呢?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愧悔,是否跟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玄武门之变有关呢?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追问: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清晨,当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一举除掉太子和齐王之后,当守门禁军与东宫齐王卫队激战正酣的时候,太极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真如史书所载,高祖和近臣们正悠然自得地“泛舟海池”,沉浸在一片诗情画意之中,对宫门前正在发生的惨烈厮杀一无所知?是否直到尉迟敬德满身血迹、“擐甲持矛”地前来“宿卫”,高祖和一帮近臣才如梦初醒?
事实上,六月四日高祖李渊“泛舟海池”的这一幕,历来备受后世史家的强烈质疑。
因为它的疑点确实太多了!
首先,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天早晨是李渊召集三兄弟入宫对质的时间,为此一帮宰执重臣也都早早就位了。在此情况下,李渊怎么可能有闲情逸致到海池去泛舟?其次,就算李渊和近臣发现三兄弟全都迟到了,许久等不到他们,百无聊赖之下才跑去泛舟,可是,就在宫廷的北正门,几支军队正杀得鸡飞狗跳、人喊马嘶,而高祖李渊和那帮帝国大佬怎么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就算他们一时间都被海池的美丽景色陶醉了,可宫中有那么多的嫔妃、太监、宫女,难道他们也全都被施了迷魂术和定身术,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察觉、没有一个人赶来通报这骇人听闻的政变消息?最后,退一万步说,就算上面这些都是事实,可当尉迟敬德带着武器擅闯皇宫大内,一直逼到皇帝的面前时,高祖身边的侍卫都哪里去了,为何史书中连一个侍卫的身影都看不到?在天子的人身安全遭遇重大威胁的时候,难不成他们全都约好了,在同一时间集体人间蒸发?
我们只能说——这样的记载太不可理喻了!
如果说李世民和贞观史臣确实是对玄武门事件动了手脚的话,那么我们相信,这个所谓的“泛舟海池”应该就是被重点篡改,以至于改得毫无逻辑、牵强附会、面目全非。
可是,为什么李世民弑兄、杀弟、屠侄的那些真相都可以不改,却偏偏改了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李世民派兵逼宫、控制高祖的真实内情要远比所谓的尉迟敬德“擐甲持矛、入宫宿卫”复杂得多、性质也严重得多,所以只好授意史官进行篡改?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李世民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对父亲所做的一切,已经完全坐实了“不忠不孝、悖逆君父”的罪名,以至于比弑兄杀弟在良心上更难以承担、以礼教伦常的标准来看更不可原谅,因而在面对后辈和世人的时候更难以启齿呢?
也许正因为此,所以贞观史臣最后才不得不虚构了“泛舟海池”的一幕来掩盖真相;也许正因为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当身为君父的李世民在儿子们的夺嫡之争中差一点目睹骨肉相残的悲剧重演时,他才能深刻体会高祖当年的惨痛心境,也才能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有所反省,从而才会借“所行大疏略”为由,深切地表现出对高祖李渊的愧悔之情。
讨论至此,我们似乎已经逼近了李世民向我们隐瞒的那个最后的真相!
关于这个隐藏最深的真相,一部一千年后重现人间的敦煌残卷,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公元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消息震惊中外,可清政府并未对此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于是随后的几年里,一批又一批价值不可估量的古代文献被西方的探险家和文物掠夺者陆续盗运到了欧洲。在斯坦因(匈牙利人,后加入英国籍)盗走的文献中,有一部被冠以编号S.2630的敦煌写本,内容就涉及了唐太宗和玄武门之变。王国维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研究这份文献的学者,将其命名为《唐太宗入冥记》。这份文献虽然只是唐代的民间话本,算不上正规史料,而且作者已不可考,但是里面透露的某些信息却至关重要,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卞孝萱先生在《“玄武门之变”与〈唐太宗入冥记〉》一文中说:“胜利者唐太宗为了维护其仁孝形象,对先发制人、杀兄诛弟、逼父让位的行为加以涂饰。当日唐史臣秉承太宗之意,在两朝实录、国史中,篡改了‘玄武门之变’前后一连串事实的真相。敦煌写本《唐太宗入冥记》编造建成、元吉在阴司告状,阎罗王勾太宗生魂入冥对质的故事,实际是为建成、元吉鸣‘冤’。”
由此可见,这个唐代写本虽然体裁近似小说,内容纯属虚构,但是它所透露出的信息却不可等闲视之。换言之,值得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它的故事情节,而是其中蕴含的寓意。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写本的大致内容。
故事说的是唐太宗入冥之后,在阴司遇见了一个名叫崔子玉的判官,此人在阳世的身份是滏阳县尉。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往来于阳世与阴间的“双重身份者”(在中国古代话本和民间传说中,这种“双重身份者”代不乏人,据传近代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曾入冥充当判官)。由于崔子玉在阳世的身份是李世民的臣子(但是官职卑微),而现在皇帝李世民在阴间反而成了他的审判对象,于是崔子玉就决定利用自己在阴司的职权和太宗做一回交易,借以换取自己在阳世的高官厚禄。他告诉太宗,建成和元吉入阴之后,“称诉冤屈,词状颇切”,亦即暗示这件“官司”颇为棘手,然后让太宗回答一个问题,说如果答得上来就可以回长安,答不上来恐怕就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太宗一听吓坏了,连忙要求崔子玉提个简单一点的问题,并且承诺说:“朕必不负卿!”
然而,崔子玉所提的问题却一点都不简单。
他看着唐太宗,一脸正色地说——“问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在武德九年,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
李世民一听,顿时哑口无言,“闷闷不已,如杵中心”,心里仿佛横亘着一块木头,良久才说,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了。
崔子玉一看太宗的反应,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替太宗想了一个答案,原文是:“大圣灭族□□”。后面脱了两个字,但是大意还是清楚的,无非是太宗“大义灭亲”云云。作为交换,太宗许给了崔子玉“蒲州刺史兼河北二十四州采访使,官至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仍赐蒲州县库钱二万贯”的优厚条件,终于顺利通过这场冥世拷问。
在这个故事中,崔子玉所提的那个问题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一个信息。其中,“杀兄弟于前殿”遍见正史记载,而且李世民本人对此也直言不讳,所以并不稀奇;真正让李世民感到难以启齿、同时也让我们感到非同小可的是后面的六个字——“囚慈父于后宫”。
很显然,这是一个被所有官修正史一律遮蔽掉的信息。
要解开被正史隐瞒的玄武门之变的另一半真相,这六个字就是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
虽然《唐太宗入冥记》的内容出于虚构,但是其题材和寓意在当时肯定是有所本的,不可能毫无依据。据卞孝萱先生分析,该作品很可能成书于武周初期。在唐人张(约生活于武周至玄宗前期)的笔记史《朝野佥载》中,我们也发现了有关“唐太宗入冥”和“冥官问六月四日事”的记载(见《朝野佥载》卷六)。而王国维先生在相关的研究著作中,也曾引述《朝野佥载》、《梁溪漫志》、《崔府君祠录》、《显应观碑记》等多种史料,考订了唐太宗和崔子玉故事的源流,发现崔府君的故事在蒲州一带流传甚广,山西省现存的碑刻中也保存了有关他的一些传说。由此可见,《唐太宗入冥记》中所提到的“囚慈父于后宫”的说法,很可能在唐朝初期已经广泛流传于民间。
然而,就算这样的说法渊源有自,可毕竟属于民间传闻,何况《唐太宗入冥记》也只有这语焉不详的六个字,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看不到。既然如此,那我们又凭什么知道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对李渊都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又凭什么断定“囚慈父于后宫”就是李世民向我们隐瞒的真相呢?
在相关史实已经被官修正史全部篡改或删除的情况下,要破解这个真相确实难度很大,但是并非不可能。
因为我们相信,常识和逻辑的力量始终是强大的;况且,无论贞观史臣如何竭力隐瞒真相,正史中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凭借这些弥足珍贵的线索,再辅以合乎常识的分析以及合乎逻辑的推断,我们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