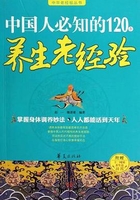我站在小操场尽头,搅扰萨缪尔先生。他住在高高的围栏下面的房子里。萨缪尔先生每星期抱怨一次:男学童把球、苹果和石头扔进他卧室的窗子。在一座四方形的整齐小花园内,他窝在折叠躺椅里,想集中精力读报纸。我离他只有几码远,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假装没注意到我。但我很清楚,他其实知道我无礼却安静地站在那儿。在读报的间歇他时而抬起头,窥视我,看到我静止不动,很严肃,独自一人,瞪着他的眼睛。他一旦生气,我会立即打道回府。我已经赶不上吃饭。我几乎揍了他一拳,报纸在颤动,他呼吸沉重。这会儿,有个陌生的男孩把我推下坡岸,我根本没听见他走近。
我朝他的脸丢石头。他摘下眼镜,放在外衣口袋,脱下外衣,整齐地挂在围栏上,开始攻击我。我们在坡岸顶端扭斗时,我转过身,看到萨缪尔先生在折叠躺椅上收起报纸,正要起身观战。我转身是个错误。陌生男孩接连两次猛击我后颈。我跌倒在围栏旁,萨缪尔先生兴奋得直跳。我被击倒在尘土之中,情绪很激动,刮伤了身体。我咬他,又站起来,手舞足蹈。我冲撞这个男孩的肚子,两人扭成一团,又翻又滚。我一眼睛眯着,看到他鼻子流血不止。我猛击他鼻子,他拉扯我的衣领,抓住我头发让我转圈。
“好啦!好啦!”我听到萨缪尔先生喊道。
我们转过身,朝向他。他正挥舞拳头,在花园里躲来躲去。然后他停下来,咳嗽,整理好睡衣,避开我们的目光,背对我们,慢慢走回折叠躺椅。
我们两人都冲他扔石子。
我和男孩沿着操场奔跑,远离萨缪尔先生的叫嚷,跑到通往山顶的阶梯下,男孩说:“我要对他说‘好啦’!”
我们一起走回家。他流血的鼻子令我惊叹不已。他说,我眼睛像荷包蛋,只不过是黑色的。
“我可没见过那么多血。”我说。
他说,我有威尔士最好的黑眼圈,也许是全欧洲最好的黑眼圈。他打赌,特尼不曾有过那么黑的眼睛。
“你衬衫上全是血。”我说。
“有时候,我的血是整块整块流的。”他说。
在瓦特街,我们从一群高中女孩身旁走过,我把帽子戴斜,希望自己的眼睛像蓝布袋那么大,而他走路时上衣掀开,露出血迹。
吃饭时,我自始至终表现得像不良少年,像个无赖,像来自桑班克斯的小伙子那样坏。其实我应该表现得更规矩些。我像特尼一样默默面对西来布丁。那天正午,我戴着眼罩去上学。如果我再系上一条黑色丝腕带,就会像我妹妹经常读到的那位受伤船长一样。晚上,我也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偷偷读他的故事。
路上,有个不必让父母掏钱的初级学校的男孩,用成年人的刺耳嗓音叫我“独眼龙”。我毫不在意,照样吹着口哨往前走,另一只没受伤的眼睛望着露台街上方的夏日浮云,并未觉得受辱。
数学老师说:“我看到,教室后面的托马斯先生一直在大费眼神,但并不是在瞧他自己的家庭作业,先生们,是吧?”
我身旁的吉尔伯特·黎斯笑得最欢。
“放学后我打断你的腿!”我说。
他大喊大叫,蹒跚走到校长室。学校笼罩在深沉的寂静之中。门房端来一只盘子,上面放着一张字条。
“先生,校长嘉奖,请你马上来。”
“这个小伙子的腿是怎么被你打断的?”
“哦!他妈的,好痛!”吉尔伯特·黎斯惨叫道。
“不过是小小的扭伤,”我说,“我不知道自己的力量那么大,我向你道歉。但没什么好担心的。先生,让我来把这腿处理好。”我抓住他的腿飞快一抖,骨头发出咔哒一声。“先生,托马斯医生为您服务。”
黎斯夫人双膝跪地。“我该怎么谢你?”
“亲爱的女士,这没什么。每天洗洗他耳朵吧。丢掉他的量尺,把红墨水和绿墨水倒进水槽里。”
特罗特先生的美术课上,我们在花瓶素描稿下面歪歪扭扭画着裸体姑娘,并偷偷传阅。有些画作的细部很怪异,其他一些则画有美人鱼似的尾巴。吉尔伯特·黎斯只画花瓶。
“先生,你跟老婆睡觉吗?”
“你说什么?”
“先生,借我一把小刀好吗?”
“如果你有一百万英镑,你会做什么?”
“我要买一辆布加提,一辆劳斯莱斯,一辆宾利,在彭汀沙地上以两百英里的时速飞驰。”
“我要买一群姑娘,把她们养在健身室里。”
“我要买一栋房子,像柯特摩-理查德夫人的房子那样,比它大两倍,还有一个板球场、一个足球场,以及一间有机械装置和电梯的真正车库。”
“来一个梅尔巴凉亭大小的马桶,配有豪华座位、金链以及……”
“我要抽真金烟嘴的香烟,胜过莫利斯的蓝书牌。”
“我要买下所有的火车,只有会员能够乘坐。”
“而且不让吉尔伯特·黎斯乘坐。”
“你最远一次的旅行是去哪儿?”
“去爱丁堡。”
“我父亲大战时去过沙洛尼卡。”
“希利尔,那是个什么地方?”
“希利尔,说说汉诺威街的普希·爱德华兹夫人的事儿吧。”
“嗯,我哥哥说,他什么都敢做。”
我在裸体姑娘腰部下面画了一只大雁,在纸页底部以小写字母写下“普希·爱德华兹”。
“小心,老师来了!”
“把画儿藏起来。”
“我跟你打赌,猎犬跑得比马快。”
“大伙都喜欢美术课,除了特罗特先生。”
晚上,去见新朋友之前,我坐在卧室的炉子旁边,浏览写满诗句的练习簿。练习簿背面是“不能做的危险之事”。卧室的墙壁上,贴着莎士比亚和沃尔特·德·拉·玛雷[1]的画像,它们是从我父亲的《出版人》杂志的圣诞特刊上撕下来的,此外还有罗伯特·勃朗宁、史特希·欧蒙尼尔[2]、鲁佩特·布鲁克[3]以及名为惠提尔的络腮胡男人的画像,另外还有沃特所画的《希望》,外加一张我不想取下来的主日学校证书。我发表在《西方邮件》“威尔士每日专栏”的一首诗,贴在镜子上,好让自己脸红,但这首诗所引发的羞愧感已经消失。在诗的另一边,我用一只偷来的鹅毛笔龙飞凤舞地写道:“荷马打瞌睡。”我总在等待时机,把某个人带进房间。“到我的窝来吧。对不起,很乱;坐吧。不!不是那一张,它坏掉了!”然后,以不经意的方式强迫他去读那首诗。“我贴在那儿,好让自己脸红。”可是,除了我母亲之外,没人进来过。
黄昏降临,我走向这个人的房子,穿过树木成排、僵硬而凄清的规整大街,朗诵我创作的诗歌,听到自己的声音像“公园车道”里一个陌生人的声音,伴随钉鞋的轻盈敲击,在宏大的秋夜轻盈地升上天穹。
我的内心
以交织的方式形成;
隐密的激情
因魔鬼的尘埃而销魂,
从其泉源中涌现的思绪
隐藏着,但充满情欲。
如果我通过一扇窗朝大马路张望,会看到一个戴着深红色帽子的小伙子,穿着大长靴在道路中央阔步前进。我很想知道他是谁。如果我是一个细心观察的年轻姑娘,脸庞像蒙娜丽莎,乌黑的头发盘绕耳际,那么我会在“男装部”的衣服下面看到一个皮肤黝黑、浑身长毛的男性躯体,叫住他,问道:“你要喝茶还是鸡尾酒?”在窗帘厚重、色彩丰富的昏暗会客室里,到处挂着名画的复制品,书本和酒瓶闪闪发光,我会听见他朗诵《草叶赞美诗》:
霜已下降,
在开花的平原中变暗,
脆弱地撒上
片片明亮的月光,
位于我那孤独萎垂、不可爱的红头发周围。
霜已发言,
在沉默的薄片中隐匿、零颤,
有着看不见的蓝唇
把玻璃丢进光滑的星星中,
流着幻想的泪,只对我的耳朵说话。
霜已知道,
从微风所散播的秘会中知道
我根源中的孤独天分
裸露在那儿的一丛果实里,
已种植了碧绿的一年,作为我成长日子的内心发出的赞美。
霜已充满我内心
夜的袖子所流泻的渴望,
满载神圣蒸汽之霜,
未降的雪柱所寻求之霜,
渴望那盘旋于我孤独四周的旷野。
“看啊!那儿有个怪小伙,像王子一样独行。”
“不,不,是像一只狼!看看他跨的大步!”史克提教堂正在为我敲钟。
当我被撒下去
而我所有的灰烬
是一场灾星的恼人哑剧
形成的尘埃……”
我朗诵着。一对青年男女,手挽手,忽然在房子之间的暗巷里出现。我改变朗诵的腔调,哼哼哈哈从他们身边走过。这时,他们一起咯咯直笑,讨人厌的身体紧贴在一起。男人散发着脂粉味,精神恍惚,留长发。我用力吹口哨,做了一个踢屁股的动作,扭头回望。这对男女不见了。那么,踢“榆树”旅馆一下吧。“先生,那些该死的榆树在哪儿?”这是一把沙子,“小牧场”夫人,送给你窗户正合适。总有一天,我要把“屁股”两个字漆在“琪亚欧拉”旅馆的整个大门上。
有个女人站在“琳赫斯特”大楼的台阶上,牵着一条呜呜叫唤的小狗。我把帽子塞进口袋,沿街而下,丹恩的房子“沃姆勒”就在那儿,里面传出响亮的乐声。
他是位作曲家,也是诗人,不到十二岁时就写了七本历史小说,还会弹钢琴、拉小提琴。他母亲制作羊毛画,他哥哥是码头的职员,懂音乐,他姑妈在二楼开了一家预科学校,他父创作管风琴乐曲。他把这一切告诉我时,我们正步行回家,脸上淌着血,昂首阔步,用运动衫朝电车内的男孩挥舞。
我这位新朋友的母亲来应门,手里拿着一团毛线。在楼上休息室的丹恩听到我来,钢琴弹得更欢了。
“我没听到你进来。”见面时他这样说。他弹完大和弦,把所有指头伸开。
房间够乱的,满是毛线、纸张,以及打开的橱柜塞着你永远想不到的东西;所有昂贵的家具都被踢到一旁;一件马甲挂在枝形吊灯上。如果我能永远住在那个房间里该多好,写作,打架,泼墨水,午夜之后跟朋友们在此野餐,捎上“沃勒”商店出售的甜酒奶油,以及“伊农”商店卖的甜点,还有梨汁和廉价葡萄酒。
他向我展示他的藏书以及他写的七本小说。所有小说都关于战争、围城和国王。“都是早期的东西。”他说。
他让我取出他的小提琴,用它拉奏猫叫声。
我们坐在窗下的一张沙发上,交谈的派头仿佛我们相识已久。“天鹅队”会击败“马刺队”吗?姑娘何时能够生小孩?阿诺特去年的打击率比柯雷好吗?
“外头街上那个人是我父亲,”他说,“挥胳膊的那个高个子。”
有两个人在电车轨道上聊天。仁金先生似乎要努力游到艾维斯勒街,他在空气中蛙泳,双脚踏击地面,然后作跛脚状,一肩抬得比另一肩高。
“兴许他在描述一次打架的情景。”我说。
“没准儿是在对莫理斯先生讲一个跛子的故事,”丹恩说,“你会弹钢琴吗?”
“和音可以,但弹调子可不行。”我说。
我们四手联弹,来了一首二重奏。
“这首奏鸣曲是谁写的?”
我们弹了一首波希博士的曲子,他是世界上四手联弹曲最伟大的作曲家,我弹钢琴家保罗·亚美利加的部分,丹恩弹温特·沃克斯的部分。
我为他朗读一本写满诗句的笔记本。他凝神倾听,像个足有一百岁的男孩,头歪向一边,眼镜在肿胀的鼻子上颤动。诗名叫《弯曲》。我念道:
如同因流泪而变红的太阳
玻璃中的五个太阳
在一起,然而却分开,然而却各自呈圆形
也许是红的,但玻璃呈淡色像草一样,
滑动着,无声无息。
结合在一起,五滴泪躺着没睡,虽是太阳,却很咸
头部之中五只无法测度的矛枪
每个都是太阳,但又是一种痛苦,
或许拧成一束,痛苦流淌的血水是憎恨,
把五个拧成一个,五个成为一个,早升的
太阳扭曲成晚升。
现在全都疯狂而又凄清,
用它们五个的布料纺织,疯狂地、
像泡沫一样流动,疯狂而又凄清,
穿射,俯冲。五个之中的一个是太阳。
电车从房子边上驶过,发出咔哒咔哒的噪音,传到海边,或者更远,消失在挖泥船似的海湾里。以前不曾有人听过这样的声音。学校已经消失,在“舒适山”留下一个深洞,透着衣帽间和储藏室老鼠的气味,而“沃姆勒”这间房子在我所不知道的一个城镇的黑暗中闪亮。在我从不陌生的寂静房间内,我们坐在一堆堆肿鼻、单眼的彩色毛线里,感谢我们的天赋。未来展现在窗外的远处,展现在挤满无所事事的情人的辛格勒顿公园上方,涌入铺满诗句的多烟伦敦。
仁金夫人在门外凝望,把灯转亮。“嗯,这样比较像家,”她说,“你们不是猫。”
未来随亮光而消散。我们弹着波希博士创作的一首大曲子。“你听过这么美妙的东西吗?大声点儿,大声点儿,亚美利加!”丹恩说。“留一点儿低音给我。”我说。终于,隔壁屋有人在敲墙。
“那是卡雷一家。卡雷先生是荷恩角人。”丹恩说。
仁金夫人拿着织针和毛线跑上楼之前,我们在为卡雷先生弹奏一个刺耳、重击的乐章。
仁金夫人走后,丹恩说:“什么人总会为自己的母亲感到羞愧?”
“也许老一点儿的时候就不会了。”我说,但我却怀疑这一点。一个星期前,我跟三个男孩放学后走到“高街”,看见我母亲在“卡多玛”外边跟巴崔吉夫人在一起。我知道母亲会当众拦下我,说:“你早点儿回家喝茶。”我非常希望“高街”豁然开裂,把我吸到地底下。我爱母亲,但否认跟她有关系。“我们到街对面去,”我说,“‘格利菲兹’的橱窗里有些水手长靴。”其实,那儿只有一个人体模型套着一件高尔夫球装,以及一匹斜纹软呢。
“还要半小时才吃晚餐。我们干点儿什么?”
“我们来看谁能把那张椅子举得更久。”我说。
“不,我们来编一份报纸:你负责文学部分,我负责音乐部分。”
“那么名称呢?”
他在沙发下面的一个帽盒背面写上“《……报》,D.仁金和D.托马斯编。”就押韵而言,最好是写成“D.托马斯和D.仁金”,但我是在他家的房子里。
“报纸名字叫‘大歌唱家’如何?”
“不,太音乐性了。”我说。
“‘沃姆勒杂志’呢?”
“不,”我说,“我住在‘格兰利德’。”
帽盒盖好后,我们这样写道:
“《大声说话的人》,由D.仁金/托马斯编辑”,用粉笔写在一片厚纸上,钉在墙头。
“你要看看我们的女仆卧房吗?”丹恩问。我们对着上面的阁楼低语。
“她叫什么名字?”
“希尔达。”
“她年轻吗?”
“不年轻,二十岁或三十岁。”
她床铺并不整齐。“我母亲说,你总能闻出一个女仆的气味。”我们嗅嗅床单。“我嗅不到任何气味。”
在她镶铜的盒子里有一个相框,照片是一个穿灯笼裤的年轻人。
“那是她男朋友。”
“我们来给他画点儿胡子。”
有人在楼下走动,一个声音喊道:“吃晚饭啰!”我们匆匆往外走,留下打开的盒子。“哪天晚上我们躲到她床底下去。”我们推开餐厅门时,丹恩说。
仁金先生、仁金夫人、丹恩的姑妈、一位叫贝凡的牧师和贝凡夫人坐在餐桌旁。
贝凡先生念了饭前祷告。他站起来时好像还坐着,他是那么矮。“为我们今晚的膳食祝福。”他说,仿佛完全不喜欢食物。可一旦说完“阿门”,他却像饿狗一样直扑冷肉。
贝凡夫人看来心不在焉。她凝视桌布,拿着刀叉,动作犹疑,似乎不知道要先切什么,是肉还是桌布。
丹恩和我满心愉快地盯着她。丹恩在桌子底下踢我,我把盐弄撒了。混乱中,我设法在他的面包里加了一些醋。
除了贝凡先生外,每个人都注视着贝凡夫人的刀子在盘子四缘缓慢地移动。这时仁金夫人说:“我真希望你喜欢冷羊肉。”
贝凡夫人对她微笑,显得很放心,开始进餐。她头发呈灰白色,脸庞也呈灰白色。或许她全身都呈灰白色。我试图用心眼扒下她的衣服,但一来到她的法兰绒短衫和及膝的深蓝色灯笼裤,就开始害怕了。我甚至不敢解开她长筒靴的扣子,看看她两腿有多灰白。她从盘子上抬起头,向我投来一个邪恶的微笑。
我满脸通红,转身去回答仁金先生问我年纪多大。我对他说了,但多加了一岁。为什么撒谎?我自己也纳闷。如果我帽子丢了,然后在卧室里找到,而母亲问我在哪儿找到的,我会说“在阁楼”或“在帽架下边”。捏造事实令人兴奋,我假装看过的一部电影的故事,用杰克·霍尔特来取代理查德·狄克斯。
“十五岁又九个月,”仁金先生说,“很精准的年龄。看得出来,我们之中有一位数学家。现在看看他能否算对这道题目。”
他吃光食物,把火柴放在盘子上。
“爸爸,那是老题目。”丹恩说。
“哦,我很想知道是什么题目。”我以最悦耳动听的声音说。我很想再拜访这座房子。这儿比家好,而且还有个疯女人。
我无法算对火柴,于是仁金先生告诉我该怎么做。虽然我仍一知半解,但还是谢谢他,要求再做一题。成为伪君子几乎跟撒谎一样好,这让你感到温暖而又羞愧。
“爸爸,你当时在街上跟莫里斯先生说什么?”丹恩问,“我们从楼上看到你们。”
“我正在告诉他斯旺西和‘男音区’如何演出《弥赛亚》!如此而已。你为什么问这个?”
贝凡先生再也吃不下了,他吃饱了。晚餐开始以来,他第一次环顾餐桌。他似乎不喜欢所看到的情况。“丹恩,功课如何?”
“丹恩,听贝凡先生说话,他在问你问题。”
“哦,马马虎虎。”
“马马虎虎?”
“我是说功课很好,谢谢你,贝凡先生。”
“年轻人应该讲真话。”
贝凡夫人咯咯一笑,要求再来一点儿肉。“再来一点儿肉。”她说。
“你呢,年轻人,你有数学方面的天赋吗?”
“先生,没有,”我说,“我喜欢英文。”
“他是一位诗人。”丹恩说,看起来很不自在。
“一位青年诗人。”贝凡先生纠正道,牙齿外露。
“贝凡先生出版过书,”仁金先生说,“《普罗瑟嫔娜》以及……”
“《俄耳甫斯》。”贝凡先生以尖锐的腔调说。
“以及《俄耳甫斯》。你得让贝凡先生读读你的诗作。”
“仁金先生,我没带任何诗作。”
“诗人,”贝凡先生说,“应该把诗放在头脑中。”
“我记得我写的诗。”我说。
“把最新一首朗读给我听。我总是很有兴致。”
“多么不寻常的聚会啊,”仁金夫人说,“诗人、音乐家、牧师,只少了一个画家,不是吗?”
“我不认为你会喜欢最新的一首。”我说。
“也许,”贝凡先生说,微笑着,“我是最好的评委。”
“我的憎恨很是无益,”我开始朗读,真想当场死掉,同时注视着贝凡先生的牙齿。
为残忍的懊悔所伤,
因欲求的力量并未实现,
因最近痛苦的色欲;
现在我能够把她死去的黑暗
身体抬到我自己的身体上,
听到她骨头快活地沙沙作响
在她眼中看见致命的火焰;
现在我能够醒来
在死后面对热情,品尝
她仇恨的狂喜,撕裂身体上
的废物。毁坏她死去的黑暗身体,毁坏。
丹恩屏息凝气,朝我胫骨踢来,然后贝凡先生说:“当然,明显受到某诗人的影响。‘冲击,冲击,冲击啊,在你灰色的冷石上,哦,大海。’”
“贝凡对丁尼生的诗倒背如流,”贝凡夫人说,“倒背如流。”
“我们现在可以上楼了吗?”丹恩问。
“不要搅扰到卡雷先生。”
我们轻轻地关好门,跑上楼,手放在嘴上。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丹恩说,“你看到那牧师的脸相了吗?”
我们在房间各处模仿他,又在地毯上打斗了一会儿。丹恩的鼻子又开始流血。“没什么,一会儿就停。我想让它流它就会流。”
“跟我说说贝凡夫人,她疯了吗?”
“她疯到很可怕的地步,她不知道自己是谁。她曾试图跳出窗外,但贝凡先生完全没注意到,所以她来我们家,把一切告诉母亲。”
贝凡夫人敲门,走进来。“我希望没打搅你们。”
“贝凡夫人,没有,当然没有。”
“我想换一下空气。”她说。她在窗旁沙发上的毛线堆里坐下来。
“晚上怪闷的,是吧?”丹恩说,“您想开窗吗?”
她看了看窗子。
“我可以帮您打开,举手之劳。”丹恩说,冲我眨眨眼。
“贝凡夫人,我来帮您开窗。”我说。
“打开窗子挺好的。”
“这高窗真不错。”
“呼吸一下从海上吹过来的新鲜空气。”
“亲爱的,不用麻烦了,”她说,“我就坐在这儿等我丈夫。”
她玩着毛线球,拿起一根织针,在手掌上轻敲着。
“贝凡先生要很长的时间才会来吧?”
“我就坐在这儿等我丈夫。”她说。
我们跟她聊了一会窗子,但她始终笑而不语,解开毛线,有一次还把长织针的钝头放进耳朵里。不久,我们看她看得厌烦了,丹恩开始弹钢琴。“我的第二十首奏鸣曲,”他说,“这一首是向贝多芬致敬。”九点半的时候,我不得不回家。
我对贝凡夫人道晚安,她挥挥织针鞠躬,坐下来。楼下的贝凡先生伸出冷冷的手要同我握别,仁金先生和夫人要我有空再来,那位安静的姑妈给了我一根火星棒[4]。
“我陪你走一段。”丹恩说。
户外的夜晚很温暖,人行道上,我们仰望亮灯的休息室窗子。这是路上唯一的亮光。
“看!她在那儿!”
贝凡夫人的脸庞压在玻璃上,鹰钩鼻变得扁平,嘴唇紧闭。我们一路上走到艾维斯勒街,唯恐她会跳下来。
在拐角处,丹恩说:“在此作别吧,我今晚必须完成一首弦乐三重奏。”
“我正在写一首长诗,”我说,“关于威尔士王子、男巫以及每一个人。”
回到家,我们全都上床睡觉。
注释:
[1]沃尔特·德·拉·马雷(Walter de la Mare,1873-1956),英国诗人,小说家。
[2]史特希·欧蒙尼尔(Stacy Aumonier,1877-1928),英国作家。
[3]鲁佩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1887-1915)英国诗人。
[4]一种巧克力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