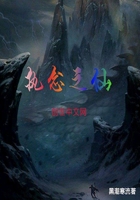野外起了雾,刮着风,冷彻骨髓。天很早就黑了。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空荡荡的火车站上,几盏灯芯捻得很紧的油灯荧荧如豆,发出刺鼻的煤油味,车站的看守盖着件不挂面的羊皮袄,睡着在三等车候车室卖品部的柜台上。我步入上等旅客的候车室——那里墙上挂着的一座自鸣钟,正在昏暗的灯光下慢吞吞地嘀嗒嘀嗒走着。桌上搁着一只长颈玻璃瓶,里边盛的凉开水不知是哪年哪月的,都已经发黄……我由于一路上雨雪交加,泥泞难行,人已疲惫不堪,便朝一张破旧的长毛绒沙发上一躺,立即沉沉睡去。这一觉,我自己觉得睡了很久,可是睁开眼睛,却懊丧地看到自鸣钟的时针才仅仅指着六时半。
我不由得想起俄罗斯一本古书中一句忧伤的话:“那天的白昼就此逝去,换来了阴暗的秋夜。”
周遭仍像我睡前一般寒冷、索寞,窗外也仍像我睡前一般黑暗……
当自鸣钟迟疑地,大有颇费踌躇的样子,敲了八下的时候,不知哪里的一扇门尖利地吱吱响了一阵,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月台上旋即响起凄切苍凉的铃声。我走进三等车候车室,看到一个戴着便帽、穿着厚呢外套的小市民,臂肘支在膝上,双手抱着头,呆定地坐在长凳上。
“火车到站了?”我问。
那小市民全身一震,愕然地望了我一眼,嘟囔了句什么,就满面愁容地往月台门快步走去。
“他老婆难产,快要死了。”看守已经一觉睡醒,正坐在柜台上,一面撕下一片报纸卷着烟,一面告诉我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他心不在焉地补充了一句,突然美滋滋地打了个哈欠,顿时精神抖擞地用一种难以理解的幸灾乐祸的口吻讲道:
“这就是娶有钱老婆的好处!他已经失魂落魄地奔走了两天,求教堂把祭坛的圣幛都打开了——可是一点也不灵验。这会儿要赶进城去请大夫,有什么用?”
“你担心来不及吗?”
“说什么也来不及!”看守回答说,“他要到明天天黑前才能回来,可是到那时,他老婆早已两腿一伸,上西天了。准上西天了,”他很有把握地加补了一句,“他讲,他已经求过三回签,问谁先死,是他还是他老婆,结果求得的签,三回都一模一样。第一回……是怎么说来着?‘你已无须再做过远的打算了。’第二回更糟:‘你应祈祷上帝,禁绝烟酒,出家进修道院。’而昨天,他讲他梦见自己浑身上下的毛发全给人剃得精光,连牙齿也被人统统拔掉了……”
要不是这时恰巧有列货车隆隆驶进车站的话,他还不定要讲多久哩。那扇月台门重又发出尖利、凄厉的响声,打了开来。车长走进候车室,他穿着一件湿淋淋的厚呢制服大衣,大衣后腰的扣带已经断掉,身后跟着个注油工,那人手里拎着一盏光线昏暗的提灯……我走到了月台上。
在这朔风凛冽、潮气很重的黑夜里,我久久地在月台上来回踱步。最后,铁轨终于被震得铮铮发响,从溟蒙的迷雾中射来了客车车头上那只巨大的眼睛发出的红光。我登上了昏暗、暖和,然而臭烘烘的车厢。里边已经睡满了人,直到火车开动后,我才在车门旁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座位,这扇门是通到另外半节车厢去的。在晃动不已的朦胧的灯光下,我四周黑压压地、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有的躺在座位上,有的躺在支起来的靠背上。而地板下面,车轮正在低沉、单调地喀隆喀隆响着,我合上眼睛,始终恍恍惚惚,分辨不清火车在朝哪个方向驶去。这时,一个拿着根拨火钩、浑身黑得像黑人似的司炉走了过去。他没有把我身旁的门带上,于是我听到了谈话的声音,闻到了马合烟的气味……在门那边第四排座椅上躺着个人,那个进城去请大夫的小市民就缩在那个人脚旁的椅子边上抽烟。他脸色阴郁,看起来心事重重。而在门口靠近我的地方,在烟雾腾腾的昏黄的灯光下,好几个庄稼汉正挤在一起,一面抽着烟,一面倾听坐在他们对面的一个人高谈阔论。
“是啊,各位老弟,”透过奔腾前去的列车单调而低沉的隆隆声,传来了那人的声音,“是——啊。那个老头儿神父从叶皮凡市一头栽进了这个倒霉的穷山沟。就是说,把他从城里调到了这个又穷又小的教区。世上再没比这个教区更穷的了,为什么要调动他呢——酒喝得太厉害了……就是说,表面上是调动,骨子里却是处罚。这老头虽说有贪杯的毛病,可为人却再好也没有了。人家问他:‘彼得神父,洗礼或者办个丧事什么的,您老要收多少钱?’‘亲爱的,不是我要收你的钱,而是因为我穷得没办法!你付得起多少就付多少……’没有一回不是这样。他是春上调来的,太太平平地过了一个夏天,可是交秋之后,却害病了。不知是因为他年纪老了呢,还是感冒了——夏天那会儿,他的身子别提有多健朗,可是眼睛一眨,却露出了下世的光景。各位老弟,他自知死期已近,在圣母节那天做完弥撒以后,就走到大伙跟前,同所有的人诀别,说:‘我眼看就要去见上帝了,教徒们——请你们原谅我吧,如果我有什么罪过的话……’他讲了这番话后,朝大伙一躬到底,便走上圣坛去。等他回到家里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只是拿起调羹在汤里搅动了几下,却一口也咽不下去。他站起身来,对兼当他仆人的教堂看守说:‘亲爱的,不知怎的,我直发冷,心头闷得慌——简直没一丝力气。老是想起我那个死去了的女儿,老是感到她在盼我上她那儿去……把饭菜端走吧,我没心思吃。’看守对他说:‘老爷子,您别乱说一气,哪能呢!您才多大年纪呀?’他回答说:‘不,我要死了!只有一件事我死了也不闭嘴眼,那就是到处都苦难深重,这种世道难道就不会变吗?’那天天气比今儿还坏,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够糟的了。这时天已经渐渐黑下来,老头儿走到窗口望了望,挥了一下手,就走进上房去。他把上房圣像前的圣体灯捻捻好以后,躺到床上,本来只想歇个把小时,可不知是睡着了呢,还是想得出了神,反正夜已经深了,他却还一动不动地躺着,躺着……”
“嚄,真是可怜见的!”有个人叹息道,“你是说,这事发生在圣母节[34]?”
“人家不早就讲了,是在圣母节!”一个大高个儿的庄稼汉铁板着脸,瓮声瓮气地打断那人的问话。他就坐在那讲故事人对面一个座位的边沿上,穿着一件破烂的短皮袄,头发火红,两眼凶光毕露。
“是在圣母节,是在圣母节,”讲故事的肯定道,“而且是在黄昏时候。我方才讲到,他走到上房里,躺了下来……是——啊……走到上房里,躺了下来,就好像躺到炉炕上去取暖似的。他面对着圣体灯,可怎么也爬不起来做祈祷,怎么也没法睡着。他说,我躺在床上,望着圣体灯,忽然看到门被轻轻地、轻轻地推了开来,我那个已经死了的女儿朝我走来。我想:‘上帝啊,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可她却径直走到我跟前,把一只手搁在我手上。她浑身穿黑,可脸却是雪白的,雪白而且漂亮!她悄没声儿地对我说:‘爸爸,起来,快上教堂去。’我霍地下了床,可她已经无影无踪。我便坐回床上,但是越坐越感到奇怪,越感到心惊肉跳。临了,我终于跳起身来,抓起教堂的钥匙,披上短皮袄,磕磕绊绊地走到门厅里……屋外风雨大作,门厅里阴风黪黪,黑得吓人,但我转念一想,不,说啥也要去!我急急忙忙爬上山坡,走到教堂门口——只见里边有火光,跟人们在死尸前点的守灵蜡烛的光一模一样。我又害怕起来,但还是画了个十字——走上了教堂的台阶,好不容易把钥匙塞进锁孔。我推开了门——什么死尸也没有,只有在祭坛的圣幛处燃着一支小蜡烛。我心里寻思,是谁点的蜡烛,这是怎么回事?我吓得半死不活地站在那儿——蓦地祭坛圣幛上的帷幔掀了起来,两扇圣幛没有一点声息地打开了,从暗处,也就是说,从圣坛上走出一只大得不得了的红公鸡[35]。它走出来后,站停了脚,扑棱了几下翅膀,喔喔喔地啼了起来,响得整个教堂都给震动了!它一连啼了三次,就不见了。它刚不见,又走出一只白公鸡来,白得就像浪尖上的飞沫,比先前那只鸡更响地啼了起来。也是一连啼了三次……第二天一大早,神父告诉人家说:我当时吓得手脚都发麻了,可我还是站在那儿,想看看下文如何。后来,走出来第三只公鸡,浑身黑得像木炭,只有鸡冠闪闪放光,它的啼声,各位老弟,是那样可怕,那样威严。我连忙跪下来,放开喉咙一字一句地呼救道:‘愿主显灵,把他的仇人一扫而光!’我话音才落,什么公鸡都没有了,在我前面出现了一个满头白发的修士,他细声细气地对我说:‘别害怕,上帝的仆人,把你亲眼看到的传播给百姓们听去,告诉他们这些幽灵启示的是什么。它们启示的可是件了不得的事哩!’”
“怪不得人家管你们这些乡巴佬叫作只会打呼噜的白痴,叫作魔鬼,”小市民睁开眼睛,威吓地蹙紧眉头,气势汹汹地说,“深更半夜,人家心像刀割一样,可他呢,却坐在那里装神弄鬼!你扯这些无稽之谈,究竟安的什么心?”
“我可没安什么坏心。”讲故事的怯生生地嘟囔道。
“你说——你这些胡诌都是打哪儿听来的?”
“什么打哪儿听来的,大伙都说,是神父亲口讲的。”
“那个神父已经死了。”小市民打断他的话。
“这话不假……是死了……没几天就死了……”
“那不就得了,这是借他的名义胡编瞎造,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安到他身上。要知道这是梦幻。蠢货!”
“可我又讲什么来着?谁不知道这是梦。”
“那你就闭嘴,”小市民又打断他的话,“再说早就不该抽烟了,抽得满车厢烟雾腾腾——简直成了烤干禾捆的烘房!”
“你看不入眼,就上头等车去坐。”那个火红头发瓮声瓮气地、恶狠狠地刺了他一句。
“嘿,倒挺能汪汪叫!”
“只有狗和你小舅子才汪汪叫!”
“得了,得了,伙计们,别吵啦!”庄稼汉们不安地大声喝住他俩。
两个骂架的人都不响了。一时间,车厢内鸦雀无声。后来,小市民颓然长叹了一声。
“真是蛮不讲理,畜生,主啊,你饶恕我吧!”他深沉而严肃地讲道,那口吻就好像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
车厢内又静了下来,除了车轮闷声闷气的隆隆声外,只有酣睡着的人们的鼾声。
“干吗要出口伤人?”等骂架双方的火气都已经压下去之后,那个讲故事的问道,“是谁先骂人的?不正是你!我们管自在闲聊,又没……”
“真——见——鬼!”小市民急忙回嘴说,声音痛苦地发着颤,“要知道深更半夜了,人家心像刀割一样,我老婆和孩子搞得不好就要死了。你懂吗?”
“别人也有痛苦,不比你轻。”火红头发回答说。
“不比你轻!”小市民鄙夷地学着他的话说,“现在只要请得到大夫,哪怕要我付给他几千卢布,我也不会舍不得的,可大夫却远在一百俄里之外,而路呢——路又比登天还难!昨晚上,我累得筋疲力尽,连衣服也没脱,一头栽到床上就睡着了,竟梦见有人把我浑身上下的毛发剃个精光,连牙齿都叫人统统拔掉了!你倒设身处地想想——能开心得了吗?”
“哈哈!”火红头发嘲笑说,“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还说什么这就叫作梦——幻嘛!”
“谁到土罗夫卡下车?”车长从车厢的一头走过来,大声问道。
他用提灯照了照谁的一双腿,就随手砰的一声把我身旁那扇通至另外半节车厢的门带上了。
我打座位上站起来,把门打开,站到了门槛上。小市民还坐在老地方,佝偻着腰打瞌睡,而火红头发则皱着眉头,对讲故事的人说:
“快,快,讲下去。”
好几个穿短皮袄的人,紧紧地挤在那个讲故事的人周围。好几双凛然不可侵犯的眼睛,在隆隆奔驶着的车厢内烟雾缭绕的昏黄的光线下,显得目光如炬。那个讲故事的叹了口气,正打算开讲,火红头发却抬起眼睛来睥睨着我,瓮声瓮气地问:
“老爷,您有什么事?”
“也想听听。”我回答。
“我们庄稼人聊天,您老爷不值得听。”
等我刚一走开,那个讲故事的便用原先的声调继续讲下去:“是啊,各位老弟,就是说,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满头白发的修士,细声细气地对他说:‘别害怕,上帝的仆人,你听着,把你亲眼看到的传播给百姓们听去,告诉他们这些幽灵启示着什么。它们启示的可是件了不得的事哩!’……”
那个讲故事的,开始时声音很响,可渐渐地把声音压得越来越低。我虽侧耳倾听,可一句也听不清——他的话声全叫车轮沉闷的响声和酣睡着的人们如雷般的鼾声盖住了。然而透过这响声和鼾声却可以听到远处响起了机车凄凉的鸣笛声,说明快要到站了。一个戴眼镜的士官生,从我身旁的座位上慌慌张张站起来,用惊愕的目光环顾一下四周,随即又坐了下去,用臂肘撑着他那只小手提箱,立刻又睡着了。一个穿深色印花布裙子的、上了年纪的妇人站了起来,难受地紧锁着眉头,蹒跚着向过道走去。横七竖八地躺着的人、背囊、手提箱以及短皮袄,构成了一幅恶浊阴郁的图画,在我的眼前晃动。那个编讲公鸡故事的庄稼汉探出身子,凑近火红头发,轻声地,然而兴奋地讲着。尽管我竖起耳朵想听他在讲些什么,可是打我对面那片烟雾腾腾的昏暗中却什么也听不见,只能看到几双灼灼发光的凛然不可侵犯的凶狠的眼睛。
19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