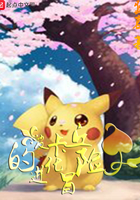啊!每逢这种时刻,他便睁着悲痛的眼睛,回头去看那修院,看那洁白的山峰,那天使们的园地,那高不可攀的美德的冰山!他怀着失望的心情瞻望那令人爱慕的修院,回忆那生满了不足为外人道的花卉,那些被关着的与世隔绝的处女,那所有香气和所有灵魂都能一齐直上天国的处所!此时,他多么想念那个伊甸园哪!当初,他一时迷了心窍,自愿离开了那里,误入歧路,如今,那大门是永不会再为他开放了!他悔恨,悔恨自己当日是那样的克己,那样的糊涂,执意把珂赛特带回尘世!他,为人牺牲的英雄,由于自己的一腔忠忱,作茧自缚,自投苦海,如今成了一个可怜虫!他常常问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
尽管冉阿让的内心如此的不平静,但他尚能控制自己,使自己表面上看上去宁静而温和,对珂赛特甚至比往日还慈爱、还温和,没有任何急躁的表现,也没有半点生气呵斥的举动。这就是他现在的冉阿让,越是不快,越是和颜悦色。
珂赛特则终日郁郁不乐。往日,她看到马吕斯,满心喜悦,如今,她看不到他,满心愁苦。她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当冉阿让改变以往散步习惯的时候,一种女性的直觉却在告诉她:不能显出对散步热心的样子,而应该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样,父亲便会恢复散步。但事实是,冉阿让以一种一声不响的态度,接受了她一声不响的同意。就这样,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她后悔了。当他们重新在卢森堡公园出现时,马吕斯又不去了。把马吕斯丢掉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如何是好?她还有可能和他再次相见吗?她感到自己的心被揪作一团,终日烦糟糟,并且,这种感觉日复一日,一天重似一天。春夏秋冬,晦明阴雨,鸟雀是不是还在歌唱,花开花谢,是大丽还是菊花,卢森堡公园可爱呢,还是杜伊勒里宫讨人喜欢,洗衣妇送回的衣服浆得是不是太厚,杜桑买回来的东西是不是合适,对她来说,这一切统统成了过眼烟云,变得毫无意义。她终日垂头丧气,出神发呆,看眼前,空无所有,回头看,一片漆黑。
不过,除了她那憔悴的面容外,她也不让冉阿让觉察到什么,她对他仍旧是亲亲热热的。
看见她一天天憔悴起来,冉阿让痛心不已。他有时问她:
“你怎么啦?”
她答道:
“没有什么。”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她觉得他也同样闷闷不乐,于是,又来问他:
“您怎么啦?”
“没有什么。”他答道。
多年来,他们彼此亲亲爱爱,相依为命,诚笃感人。现在,却面面相觑,各隐私情,各自苦恼。他们都避而不谈心里的话,但彼此没有抱怨之心,回报的,只是微笑。
八铁链
两人相比,最苦恼的还当是冉阿让。年轻人再不如意,也会有高兴的时候。
有时,冉阿让竟会苦闷到产生一些幼稚想法的地步。这便是痛苦的一种特点。人苦极了,儿时的稚气往往会再次重现。冉阿让感到,珂赛特正试图挣脱出他的怀抱。他要想方设法留住她,其中包括用一些身外的、显眼的东西来鼓励她。这种想法当然是幼稚的,这种糊涂劲儿,犹如小姑娘看到真丝锦缎之后产生种种遐想一样。一次,他见到一位将军,即古达尔伯爵,当时他是巴黎的卫戍司令,全副戎装,骑着高头大马,穿过大街。现在,看那将军金光闪闪的形象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想:“这身服装,是再没有什么可挑了。穿上它,该多么幸福。珂赛特见了,一定会喜形于色,会挽着我的手臂,走过杜伊勒里宫铁栏门前,那时,卫兵都会向我们举枪致敬呢。那样,珂赛特也就心满意足了,不会再去想什么青年男子了。”
突然,一阵意想不到的震颤冲散了这愁惨的遐想。
搬进卜吕梅街住宅之后,他们一直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在这环境中,他们养成了一种习惯,即常去观赏日出。这种活动,可以消遣,使人享受到一种恬淡的乐趣。这种乐趣对一个刚刚进入人生和一个行将离开人生的人来说,都是适宜的。
孤僻之人,大清早起来散步跟夜间散步一样,是很有益的。街上行人很少,空气清新,鸟儿在欢唱。珂赛特本身就是一只百灵鸟,对这种散步方式她感到很合胃口,老早就醒来等待了。这种消遣方式,往往是在前一天便有所准备,而且常常是他建议,她赞同,像是安排一种密谋。每次,天还不亮,他们便出了家门。珂赛特对此特别有兴致。再也不会有什么行动,比这种天真无邪之举更能投年轻人之所好了。
我们知道,冉阿让喜欢去那些人们不常到的地方,那些僻静的山坳地角,那些荒凉处所。当时,在巴黎城外,有一些贫瘠的田野。那里几乎和市区相连。在那里,夏季通常长着一种干瘪的麦子,秋季,麦子收获过后,那里不像是被割光的,而像是被拔光的。那是冉阿让最欣赏的地方,珂赛特也不讨厌。她在这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自由,仿佛自己又回到孩提时代,成为一个小姑娘,可以纵情玩耍。她摘掉自己的帽子,把它放在冉阿让的膝上,去四处采集野花。她望着花上的蝴蝶,但不去捉它们。恻隐之心是和爱情并生的。大凡姑娘们的内心被颤悠悠的、易碎的理想所占据,一定会怜惜起蝴蝶的翅膀来。她把虞美人穿成一个花环,戴在头上。阳光射下来,照着那花环。那花环像火一样红得发紫,在她那绯红光艳的脸上,出现了一顶炽炭冠。
这种晨游的习惯,在他们的心境变得暗淡的日子里,仍然保持着。
1831年秋季,10月间的一个早晨,他们为秋高气爽的天气所吸引,又出了门。很早,他们便到了梅恩便门。那时,太阳还没有出来,东方天刚鱼腹白色。那是一种美妙的时刻。微微发白的苍茫天空里,有几颗星星在闪烁。大地一片漆黑。野草在颤动着,无处不显出一种神秘的薄明。一只云雀,仿佛想去接近那几颗星星,竭力飞向高空,并一路留下了它的歌。寥廓的苍穹,好像也在屏着呼吸,静听这小生灵为无边的宇宙而唱着。在东方,军医学院的巨大轮廓衬托在天边明亮的青钢色里。太白星悬在山冈之巅,发出耀眼的光芒,像是从那座黑色建筑里飞出的一个灵魂。
大路四周静悄悄。偶尔有几个在朦胧晓色中赶着去上工的工人匆匆走过。
冉阿让在大路旁一个工棚门前的屋架上坐下来。他脸朝着大路,背对着曙光,已经忘记了观赏即将升起的太阳。他在深思冥想,视线像是被四堵墙遮住了。可以说,有些冥想与地面是垂直的,它升到顶端以后,要回到地面上来。这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冉阿让的思想眼下正在升空。他在想珂赛特。他在想他们之间的生活,在想他们共同的幸福,想那充塞在他生命之中的光明,在想他的灵魂赖以呼吸的那种光明。他在这样的冥想时是感到快乐的。珂赛特,正站在他的身边,望着东方的云彩染上红色。
突然,珂赛特喊道:“爸,那边好像来了好多人。”
冉阿让抬起了眼睛。
我们知道,通向梅恩便门的那条大路,便是赛伏尔街,它和内马路交成直角。在赛伏尔大路和内马路的相交处,也就是在那分岔的地方,他们听到一种声音。那声音在那种时刻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他们还看到了一群黑压压的模糊形象。那是一种不成为形体的东西。它正从内马路转入大路。
远处的那东西渐渐变得清晰了。它好像在有秩序地向这边移动着。那似乎是一辆车,但看不清车上装的是什么。它好像浑身是刺,微微颤动着。传来了马嘶声、轱辘辗地的隆隆声,以及人的吆喝声,还有鞭子的噼啪声。渐渐地,那东西的轮廓更清晰了。那果然是一辆车,它从内马路转上了大路,朝冉阿让这边驶过来。它不是一辆,跟着第一辆的,还有第二辆、第三辆、第四辆……一共七辆。车上人影攒动。在微明的晨色里,有东西在闪闪发光,那仿佛是些出了鞘的大刀。他们又仿佛听到了铁链相互撞击的声音。那队伍正朝这边开来。人声也渐渐大起来了。真是触目惊心。那好像是些从梦魇里出来的东西。
那队伍越来越近,形体也清晰起来,如鬼影一般。发白的太阳渐渐地把这堆东西照亮了:大大的一堆,似人非人、似鬼非鬼、蠕蠕蠢动。那鬼影上边,与其说是人的面孔,还不如说是死尸的头颅。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大路上有七辆车,一辆跟着一辆往前走。头六辆结构奇特,好像是些运送酒桶的狭长的车子。两个车轮之上架着一道长梯子,梯杆的前端便是车辕。每一辆车,每道长梯,由四匹马拉着。那四匹马前后排成一线。梯上拖着一串串的怪人。阳光微弱,人们看不真切那究竟是不是人。说他们是人,只是一种猜想。每辆车上共有24个,分作两排,每排12个,背靠背,脸冲外,腿脚悬着。他们的背后有什么东西在郎当作响。那是一条链子。他们的脖子上也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那是一面铁枷。枷是人各一面,链子是大家共有。这意味着,这24个人必须动作一致。他们宛若一条大的蜈蚣,脊骨是一条铁链,在曲折中行进。在每辆车的一头和一尾,各立着一个背枪的人,脚踏着那链子的一端。枷全是方方正正的。那第七辆,是一辆栏杆车,但没有顶篷,有四个轮子,六匹马拉着,上面载的是一大堆颠得丁当作响的铁锅、生铁罐、铁炉和铁链。在这些东西里,也夹着几个人,用绳子捆着,直直地躺着,可能是些病人。这辆车四面洞开,栏杆已经破损,足见它在这些囚车里,资格是最老的。
车队在大路中间慢慢地行进着。它的两旁是两行奇形怪状的卫兵。他们头上戴着三角帽,上面满是污渍和破洞,那肮脏劲儿,看上去仿佛是督政府时期的士兵。他们身上穿的是老兵的制服和埋葬工人穿的长裤,半灰半蓝,都破得不像样子。他们戴着红肩章,斜挎着黄背带,拿着短剑、步枪和木棍——一队叫花子兵。这是些由乞丐的丑陋和刽子手的威风组成的刑警队。那看上去像个队长的人,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马鞭。这些细部,在晓色朦胧之时原是模糊不清的,随着阳光的逐渐明亮,它们的轮廓也逐渐变得清晰。一些宪兵骑着马,握着指挥刀,脸色阴沉,在车队左右行进着。
这队伍拉得很长。第一辆车已经到了便门,最后一辆差不多才从内马路转上大路。
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子聚集了很多人,大家挤在大路两旁观看这行进的队伍。巴黎历来都是如此的。不一会儿,附近的大街小巷,响起了互相呼唤的喊叫声、人们跑着看热闹的木鞋声。
那些人堆在车上,一声不响,任凭车子颠簸着。清早的寒气令他们发抖。他们个个脸色青灰,穿的是粗布裤,赤脚套一双木鞋。有的人几乎赤着身子,身上穿了服装的,那服装,恐怕世上没有比它们更破的了。头上是瘪瘪的宽边毡帽,油污的遮阳帽,难看的毛线瓜皮帽。有几个人竟戴着女人的帽子,有的则顶个柳条筐。肘部有洞的黑礼服和短布衫混在一起。人们可以望见毛茸茸的胸脯,从衣服裂缝里还会看到各种文身图案:爱神、爱神庙、冒着火焰的心,等等。有一些则生着脓痂和恶疮。有两三个人在车底的横杆上拴了条破草绳,做成一上马镫那样的东西,脚蹬在上面,以便托住他们的躯体。当时,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在吃东西,吃的是黑石头一样的面包。他们的眼睛是枯涩的、呆滞的,然而又是杀气腾腾的。他们默默忍受着押送人员大声的呵斥和拳棒的责打。有几个张着大嘴打呵欠。衣服破烂得吓死人,脚在空中悬着,肩头在不停地摇摆,脑袋互相在撞击,铁器在丁当作响,眼里在冒着怒火,拳头捏得紧紧的,或者像死人那样,手张着不动。在整个队伍后面,一群孩子在跟着起哄。
不管怎样说,这个队形是阴惨的。或许,明天他们会遇上一场暴雨,把这些衣衫褴褛的人浇个透。如果他们的衣服湿了,便不会再干;如果他们的衣服结了冰,便不会再暖。他们的粗布裤子会被雨水粘在骨头上,水会积满他们的木鞋。鞭子的抽打不会制止住牙床的战抖。脖子上还拴着铁链。他们的脚在空中悬着。血肉之躯竟成了木石瓦块,严寒之下,听凭雨打风吹、狂飙袭击,人们的心肠难道是铁石吗?
要知道,就是那些被绳子捆住、扔在第七辆车子里、像一个个破麻袋似的一动不动的病人,也是免不了挨棍子的。
突然,太阳出来了。东方的巨大光轮在冉冉上升,仿佛把火送给了这些蛮悍的人头。一个个,他们的舌头全都灵活了。顿时,笑谑、咒骂、歌唱,仿佛一阵大火燃烧起来。那片晨光平射过来,把整个队伍截成两截。他们的头和身躯在晨光里,他们的脚和车轮在黑暗中。每个人的脸上都出现了思想活动。这是个骇人的时刻。这些人仿佛恢复了牛鬼蛇神的原形,阳光未能扫去他们那股阴气。有几个兴致来了,嘴里叼着一根翎管,把条条蛆虫向人群吹去,准确无误地落在人群中妇女的身上。这帮人的脸,都被苦难折磨得奇形怪状。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它们个个显得阴森、丑陋。见了这般光景,人们不禁会说:“他们把日光变成了鬼火儿。”第一辆车上的人唱起了当时一首著名的歌——德佐吉埃的《女灶神的贞女》。他们是用一种鄙俗的轻浮态度,怪喊怪叫地唱的。听了这种声调,树木都惨然瑟缩,可路旁的小道上,中产阶级那一张张蠢脸却表现出,他们正对鬼怪们所唱的污声滥调听得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