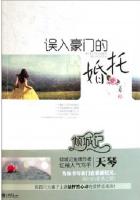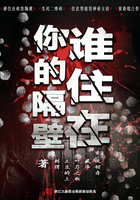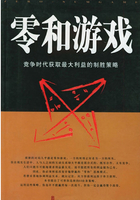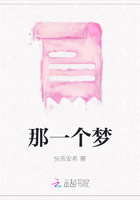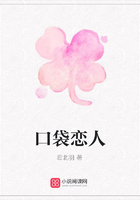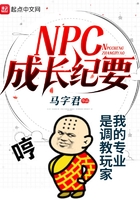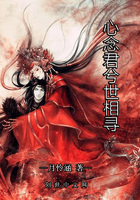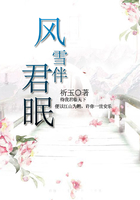刘炜
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 1894-1939)出生于布朗迪(Brody, 今属乌克兰)的一个犹太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里还是奥匈帝国东部边境地区的一座小城,生活着信仰不同宗教的居民,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罗特的父亲是个木材商人,在一次生意失败后因备受打击而精神失常,所以罗特从小是在亲戚的帮助下和母亲一同生活。1913年,他离开故乡前往当时奥匈帝国东部城市雷恩堡(Lemberg)上大学,随后又转入维也纳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的1916年,罗特报名参军。但在奥匈帝国战败并解体后,他又回到维也纳靠给不同报社撰稿为生。与此同时,罗特凭借早期的几部作品,如1923年的《蛛网》,1924年的《反抗》等,步入文坛,并很快为时人所认可。此时年轻的罗特意气风发,世界观明显左倾,在一些报纸文章上甚至署名“红色约瑟夫”。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罗特已是德语国家的明星记者,就职于《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zeitung)。1926年,他受《法兰克福报》委托考察苏联,并发回系列报道。这趟旅行的观感,都作为创作背景出现在了此后出版的一系列小说中,如1927年的《无尽的逃亡》、1929年的《右与左》和《无声的预言》等。同时,这趟旅行也促成了罗特的世界观的转折点。在紧随而来的大萧条时期,作家本人除了亲身经历了动荡时局带来的种种弊端,还不得不面对家园的丧失和理想的破灭。多重打击之下,这位出生于先前奥匈帝国的犹太作家对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他1932年出版的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直到今天都是现代奥地利德语文学中“哈布斯堡神话”的代表性作品。正因如此,曾长期在德国电视台主持《文学四重奏》且有“文学沙皇”之称的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将这部小说列为德国人必读的二十部小说之一。
罗特笔下的奥匈帝国,如同一个面凶心善的老爷子,虽然立下了无数的规矩,却早已无力去维护和执行了。人们偶尔要躲一躲他手中的鞭子,但生活的节奏并未因此而被打乱。在最严酷的现实中,小人物们也都练就了种种偷生的本领。家里虽然破烂,日子虽然贫寒,但没有那泯灭人性的你死我活。人们总能找到一条出路,不会因绝望而走上绝路。这种起码的要求看似简单,但在20世纪大萧条后的那种混乱年代里要想实现,却也非属易事。不过总的来说,虽然环境险恶,人们总还能绝处逢生;前途未卜,人们总能看到严寒中的希望。帝国严峻面孔的背后,也有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豁达,使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放任和宽容,而不是勉强和苛求。在对往昔的回忆当中,流露的更多的是温情。有小过而无大恶,这就是罗特历史观中的评判标准,也是他对过去时代和奥匈帝国总的评价。性情散漫,荒蛮广阔,这其实是宽容的写照。争端纷起的现实生活,所缺少的恰恰是彼此宽容的心态。如此说来,罗特对过去那个宽容时代的缅怀,便有了现实的意义。
在罗特的许多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写实主义(Neue Sachlichkeit)的影子。无论是开头对读者的声明,还是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各种信件、日记、回忆录,都仿佛是在刻意烘托讲述者和故事之间的距离感,好像讲述者是个局外人,在随意讲述着一段与己无关的往事。这种刻意的距离感并非以写实为目的,而是更着意于抒情,营造罗特最为擅长的伤感气氛。“哈布斯堡神话”在这样的讲述中被具体到帝国领地的一隅,并以帝国的没落为界限,通过作品中的亲历者,给读者刻画了充满希望和令人绝望的两个黑白分明的世界。此前的世界祥和安宁,此后的世界充斥着堕落。在罗特的笔下,希望与绝望总是相伴而生,强烈的对比引导着读者的思考。
有意思的是,罗特笔下的“哈布斯堡神话”从来都是以荒蛮落后的奥匈帝国东部边疆区为背景,而非选择现代文明的奥地利城市,如作为文化中心的首都维也纳。现代大城市在他的描述中几乎等同于西方文明的堕落,1930年出版的《约伯记》和1934年出版的《塔拉巴斯》中的纽约就是明显的例子。似乎在罗特这里,荒蛮落后比文明现代更能得到青睐。其实,在帝国东部边疆区表面的荒蛮落后里,彰显出的是传统价值的坚韧。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1935年出版的《皇帝的胸像》中莫施丁伯爵回忆录中所说的对信仰的“真正的虔诚”。具体说来,这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以宗教形式得以确立的善恶标准。掌握住这一点,人就可以在“世界历史的变幻无常”中不至于迷失方向,更不至于失去做人的根本——人性。
罗特笔下的“哈布斯堡神话”中,东部边疆区的标记就是广袤辽阔的大地,人们可以在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呼吸到自由清新的空气。其实这种极具倾向性的描述并非罗特独有,犹太作家德布林在他1924年的《波兰之旅》(Reise in Polen)中,也有过类似描写。他对罗特故乡雷恩堡的描述亦是首先提及东加里西亚地区的广袤无垠。这种广袤无垠象征着自由和宽容,与一战后形成的诸多新国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之所以成为“哈布斯堡神话”,首先因为它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园,代表一种跨越种族、宗教和民族界限的传统文化精神。和谐和统一是帝国的标志。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各个领地各具特色而又整齐划一;讲着各种语言的不同民族就像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一样和谐相处。哪怕是最卑微的贩夫走卒,罗特的理想世界都能为之提供生活的种种机遇。作者由此向国人和世人展示着真正的奥地利民族精神,它能唤起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其次,在罗特笔下的奥匈帝国中,人们看不到彼此的倾轧,看不见意识形态和民族种族斗争的你死我活。统治者的仁爱与宽容造就了理想世界中的祥和。祥和静宜的气氛是美好生活的佐证,也是理想家园给人带来的希望。类似的描述也可以在同时代的另一位犹太作家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中读到:“奥匈帝国,那是由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皇帝统治,由上了年纪的相国们管理着的国家;它没有野心,唯一所希望的就是能在欧洲大地上,抵御所有激进变革的冲击而完好无损。”再者,哈布斯堡王朝是个亘古不变、秩序井然的社会。同样在茨威格的笔下也有更为直接的描述:“那是个让人有安全感的黄金时代。在我们几乎有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帝国,一切看起来都恒久长远,国家本身就是稳固的保证……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拥有什么,能得到什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所有的一切都中规中矩、有条有理。”长幼尊卑各守其位,上行下达令行禁止,维持这种秩序的并非严刑峻法,而是人们心中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传统价值。
在罗特笔下的“哈布斯堡神话”中,与希望对立的是现实中的绝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好的家园变为废墟,帝国分崩离析,百姓流离失所。对一个犹太作家而言,这种绝望首先归咎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皇帝的胸像》里莫施丁伯爵与犹太人萨洛蒙的对话中,民族主义者被说得一文不值,甚至不如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猴子。而正是极端排他的民族主义在一战后甚嚣尘上,这是一种缺乏理智和人文情怀的意识形态,是人与人以及国与国间隔阂敌视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战后在哈布斯堡王朝废墟上形成的许多新民族国家,正如莫施丁伯爵回忆录中的“小格子间”,令人感到局促不安。当时的欧洲,民族主义者以革命为口号,到处制造事端,欧洲充满着血腥暴力和尔虞我诈。从一战后初期的革命,到希特勒夺权当政,直至最后大战爆发,生当此时的人绝望痛苦,而犹太人则还要面临更为可怕的种族灭绝。现实社会中虽然不乏各种信仰和思潮,但却是个传统价值缺失和被否定的时代。在人们放弃了建立于人文精神之上的传统价值后,纳粹主义等极端思潮的传播和泛滥才会成为可能。这正是令作者感到绝望,也希望能警示世人的地方。在罗特眼中,时代的发展并不等同于进步。在他的书中,现代都市所展现于世人眼前的文明,只能够满足人不断膨胀的欲望。而欲壑难填的各种野心造就的是一群对现实不满、渴望出人头地的战后世界的新主人。
果不其然,在混乱的政局中,得势崛起的是法西斯。1933年1月30日,在希特勒被任命为魏玛共和国总理的第二天,罗特便乘早班火车离开了柏林。同此后其他许多左翼和犹太出身的作家一样,罗特开始了寓居他国的流亡生涯,并同他们一起形成了流亡文学中的主要创作群体。在这非常时期中,历史人物和历史题材引起了许多流亡作家的兴趣。在当时这些作家所处的环境和背景中,历史小说有着别的文学体裁所不具备的优势。1936年,德布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历史小说本身并不是一种应急创作。但在有流亡作家的地方,历史小说这一体裁还是很受欢迎的。究其原因,除了因为流亡外国而与国内读者群隔绝外,人们还希望通过寻找历史上相同的例子,明确自己在历史中的定位,并对自己的状况作出判断。同时,通过历史小说的创作,可以激发自己的思考。再者,就是基于自我安慰的需要。”这一观点是当时的人们对历史小说的期望,也符合多年以后人们对流亡文学中历史小说的理解。由于借古可以喻今,历史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在短期内得到了充分发展。很多当时成名的作家都涉猎于此,如茨威格、布莱希特、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等等。在这一背景下,罗特也发表了多部以历史事件为背景的作品,如1934年的《塔拉巴斯》、1936年的《百日》、1938年的《先王冢》等。
在许多作品中,罗特笔下的主角往往会经历一条从“凶徒”到“圣徒”的心路历程。他们往往以冷血暴君的面目出现,但在故事的发展情节中,内心世界却不断受到宗教信仰的冲击,从而经历善恶搏斗,最后善战胜恶,人性得以升华。这种人物形象中善恶间的转变是和罗特对人性善恶的理解密切相关的。在他看来,区别人善恶本质的界限,不在于社会地位或所持信仰,而在于人性中善恶对人所起的作用,在于每个人身上是善的部分还是恶的部分在发挥作用。正是出于这一认识,罗特才会在他的笔下创作出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拿破仑和塔拉巴斯。当人物恶的一面占上风时,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暴君;但当人性中善的一面被宗教信仰唤醒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善人,成为了一个正面形象。于是读者不禁要问,这样靠战争发迹和崛起的人物,居然也能够驻足于教堂的圣殿前,完成人性向善的转化,进而达到一种罗特所向往的完美境界吗?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能促使善的一面在人性中发挥主导作用呢?罗特的答案是宗教信仰,即对天主教的信仰。他本人虽然是犹太人,但在成年后皈依天主教。他认为天主教有两个作用:其一,对上帝的信仰能引导人心向善。在罗特看来,只有传统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才能促使人在其内心世界以人性为前提,形成正确的善恶标准,而这一切都只能建立在宗教,即天主教的价值观念之上。在当时混乱纷争的时代,宗教信仰能够使人具备区分好坏善恶的判断能力。其二,罗特认为人性中恶的一面始终存在,但对上帝的信仰能克服和压制恶念在人心中的膨胀,也就是说,对上帝的信仰是一剂救世良药,它能使人摆脱各种恶念的毒化,净化人的心灵。也正因此,罗特才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一再讴歌天主教对人性改造的重要意义,并尽一切可能加以美化和理想化,甚至夸大宗教对人的正面影响。拿破仑和塔拉巴斯那种类似于大彻大悟的转折,就是作者这种观点的反映。
在流亡时期,罗特对逝去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怀念更是日益强烈。而他对过去时代美化、理想化甚至乌托邦化的创作思路,往往为同时代的左翼作家所诟病,认为这是一种逃避现实、毫无斗志甚至自暴自弃的保守态度。他们认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是黑白分明的两大阵营,非此即彼,绝无中间路线。在当时,凡是不直接批判纳粹政府的作品和作家,常被戴上思想守旧的帽子。其实,罗特对现实有着清楚的认识,不曾抱有任何幻想。他在给许多朋友的信中都对时局作出了准确的分析,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生灵将受涂炭。他不认为纳粹政权会在短期内倒台,因而需全力投入与纳粹的斗争,不作任何形式的妥协。流亡生活虽然艰辛,但罗特从未停下手中的笔。一方面,他写出犀利的文章鞭笞纳粹当局,指出什么是恶;另一方面,又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一个理想世界,告诉人们什么是善。在后一点上,罗特与左翼作家也有根本的分歧。因为他所塑造的“哈布斯堡神话”,在左翼人士眼中恰是封建势力的堡垒。
在对抗纳粹的斗争中,罗特的思路的确与众不同。他认为只有恢复已经崩溃了的奥匈帝国,才能真正从根本上与纳粹抗衡。纳粹政权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是独裁和暴政;而奥匈帝国的传统却恰恰相反,它的基础是多民族共生,具有宽容和包容性,这正好与纳粹的理论针锋相对。此论一出,复辟的帽子随之而来,保守落后的标签更是躲不掉的。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有其合理性。
给过去时代献上一曲挽歌,对本身生活在困苦中的流亡作家而言已显得不合时宜,但罗特并未就此止步,他还想把神话变成现实,试图恢复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早在1933年,罗特就不仅在给茨威格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打算,而且还真的试图通过当时奥地利共和国的总理多尔富斯(Engelbert Dollfuss)恢复帝国,但对方对此并不感兴趣。后来,他还曾潜回维也纳,联系同志,希望重建帝国,恢复哈布斯堡王朝,以此来与纳粹抗衡。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随着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而灰飞烟灭。甚至在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并吞一年后的1939年初,罗特还试图从奥地利流亡者中招募士兵组建军队,希望通过恢复哈布斯堡王朝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后来,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人奥托·哈布斯堡也曾在回忆中赞扬罗特为此投入的精力和做出的努力。
然而,神话在现实里终究难寻容身之地。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政权如日中天。先在萨尔区通过公民投票赞成归属德国,旋即德国宣布重新武装,并单方面取消了《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同时,纳粹政府还与法国、波兰等邻国签订了一系列和平条约。希特勒不但巩固了政权,而且骗取了德国国内大众的好感。今天的读者可以设想,当罗特落笔写下《皇帝的胸像》和《先王冢》时,面对纳粹的所谓“文治武功”该是何等绝望。希望与绝望像对孪生兄弟,在罗特作品中交替出现,而现实中的作家也经历着二者的此起彼伏。但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中,尤其是在失望取代希望时,受伤最深的莫过于诗人自己。在希望中创作,在失望中酗酒,罗特最终毁了自己的健康,于1939年在流亡地法国首都巴黎去世。
罗特笔下的“哈布斯堡神话”与历史上的哈布斯堡王朝出入颇大。前者取材于历史,但又不恪守史实,于是才会有读者眼前政治清明、人民和睦、疆域广大的理想社会。其实,神话与现实在罗特的生活中从来都纠缠不清。就连自己的身世,罗特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人也有着不同的讲述。有时他说自己是波兰贵族与犹太人的私生子,有时又称自己一战时曾当过俄国人的俘虏。时至今日,在有关罗特的生平介绍中,依然可以读到类似的“神话”。
同样,他的文学世界也被世人按照不同需求和取向进行解读。尤其在流亡时期,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都将他视为知己和同志,以至于1939年罗特的葬礼上出现了混乱的一幕。天主教牧师、犹太教经师、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人奥托的代表、左翼人士、复辟分子都出现在了他的葬礼上并致词,歌颂他为各自阵营所作出的贡献。造化弄人,“哈布斯堡神话”中的共存现象居然以这种形式在罗特身上得以印证。
约瑟夫·罗特在国内的译介并不充分,此前有一些作品的中文译本零星出版。本次由漓江出版社组织出版的《罗特小说集》包括了作家不同创作时期的作品,有助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罗特的创作之路和写作特点。当20世纪发生的一切成为历史后,我们重读罗特笔下的故事,则能对那个时代、那场战争灾难有更深刻的认识,也应能更好地理解罗特作品中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所载有的价值和意义。这些作品的翻译之所以能和读者见面,首先要感谢漓江出版社的周向荣编辑和漓江出版社的同事,正是她们的悉心关照,才促成这些作品的出版。此外,各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劳也是这套丛书得以面世的根本保证。而译事的艰难,则非言语所能表达。在此一并致谢。
一本书最需要读者的批评指正,作为丛书主编,期待读者不吝赐教。
刘炜
2017年11月10日于上海仁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