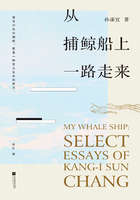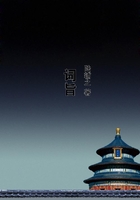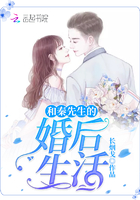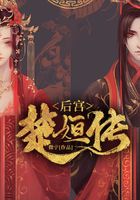他为什么要到“内地”来?不大可解,也没有人问过他。自然,你现在要是问我究竟为什么大老远地跑到昆明过那么几年,我也答不上来。为了抗战?除了下乡演演《放下你的鞭子》,我没有为抗战做过多少事。为了读书?大学都“内迁”了。有那么一点浪漫主义,年纪轻,总希望向远处跑,向往大后方?总而言之,是大势所趋。有那么一股潮流,把我一带,就带过了千山万水。这个人呢?那个潮流似乎不大可能涉及他。我们那里的人都安土重迁,出门十五里就要写家书的。我们小时听老人经常告诫的两件事,一是“万恶的社会”,另一件就是行旅的艰难。行船走马三分险,到处都是扒手、骗子,出了门就是丢了一半性命。他是四十边上的人了,又是站柜台“做店”的。做店的人,在附近三五个县城跑跑,就是了不起的老江湖,对于各地的茶馆、澡堂子、妓院、书场、镇水的铜牛、肉身菩萨、大庙、大蛇、大火灾……就够他向人聊一辈子,见多识广,社会地位高于旁人,他却当真走了几千里,干什么?是在家乡做了什么丢脸的事,或怄了气,一跺脚,要到一个亲戚朋友耳目所不及的地方来创一番事业,将来衣锦荣归,好向家中妻子儿女说一声“我总算对得起你们”?看他不像是个会咬牙发狠的人。他走路说话全表示他是个慢性子,是女人们称之为“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的角色。也许是有个亲戚要到内地来做事,需要一个能写字算账的身边人。机缘凑巧,他就决定跟着来“玩玩”了?不知道。反正,他就是来了。而且做了完全另外一种人。
到我们认识他时,他开了个小馆子,在我们学校附近。
大学生都是消化能力很强的人。初到昆明时,大家的口袋里还带着三个月至半年的用度,有时还能接到一笔汇款,稍有借口,或谁过生日,或失物复得,或接到一封字迹娟秀的信,或什么理由都没有,大家“通过”一下,就可以派一个人做东请客。在某个限度内还可以挑一挑地方。有人说,开了个扬州馆子,那就怎么也得巧立名目去吃他一顿。
学校附近还像从前学校附近一样,开了许多小馆子,开馆子的多是外乡人,山东、河北、江西、湖南的,都有。在昆明,只要不说本地话,任何外乡口音的,都可认作大同乡。一种同在天涯之感把掌柜、伙计和学生连接起来。学生来吃饭,掌柜的、伙计(如果他们闲着),就坐在一边谈天说地;学生也喜欢到锅灶旁站着,一边听新闻故事,一边欣赏炒菜艺术。这位扬州人老板,一看就和别的掌柜的不一样,他穿了一身铁机纺绸褂裤在那儿炒菜,盘花纽扣,纽襻拖出一截银表链。雪白的细麻纱袜,浅口千层底礼服呢布鞋。细细软软的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乱。左手无名指上还套了个韭菜叶式的金戒指。周身上下,斯斯文文。除了他那点流利合拍的翻锅执铲的动作,他无处像一个大师傅,像吃这一行饭的。这个馆子不大,除了他自己,只用了个本地孩子招呼客座,摆筷子倒茶。可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木架上还放了两盆花。就是足球队员、跳高选手来,看看墙上菜单上那一笔成亲王体的字,也不好意思过于嚣张放肆了。
有时,过了热市,吃饭的只有几个人,菜都上了桌,他洗洗手,会捧一把细瓷茶壶出来,客气几句:“菜炒得不好,这里的酱油不行。”“黄芹菜叫孩子切坏了,谁让他切的!——不能横切,要切直丝。”有时也谈谈时事,说点故乡消息,问问这里的名胜特产,声音低缓,慢条斯理。我们已经学会了坐茶馆。有时在茶馆里也可以碰到他,独自看一张报纸或支颐眺望街上行人。他还给我们付过几回茶钱,请我们抽烟。他抽烟也是那么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品尝,仿佛有无穷滋味。有时,他去遛弯,两手反背在后面,一种说不出的悠徐闲散。出门稍远,则穿了灰色熟罗长衫,还带了把湘妃竹折扇。想来从前他一定喜欢养鸟,听王少堂说书,常上富春坐坐的。他说他原在辕门桥一家大绸缎庄做事,看样子极像。然而怎么会到这儿来开一个小饭馆呢?这当中必有一段故事。他自己不谈,我们也不便问。
这饭馆常备的只有几个菜:过油肉、炒假螃蟹、鸡丝雪里蕻,却都精致有特点。有时跟他商量商量,还可请他表演几个道地扬州菜:狮子头、煮干丝、芙蓉鲫鱼……他不惜工本,做得非常到家。这位绸缎庄的“同事”想必在家很讲究吃食,学会了烹调,想不到竟改行做了红案师傅。照常情,这是降低身份了,不过,生意好,进账不错,他倒像不在意,高高兴兴的。
半年以后,店门关了几天,贴出了条子:修理炉灶,停业数天。
重新开张后,饭铺气象一新,一早上就坐满了人,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扬州人听从友人的建议,请了个南京的白案师傅来做包子下面,带卖早晚市了。我一去,学着扬州话,给他道了喜:
“恭喜恭喜!”
“托福托福,闹着玩的!”
扬州人完全明白我向他道喜的双重意义。恭喜他扩充了营业;同时我一眼就看到后面天井里有一个年轻女人坐着拣菜,穿得一身新,发髻上戴着一朵双喜字大红绒花。这扬州人在家乡肯定是有个家的,这女人的岁数也比他小得多,因此他有点不好意思。
不知道是谁给说的媒。这女人我们认得,是这条街上一个鸦片烟鬼的女儿。(这条街有一个富丽堂皇、古色古香的街名,叫作“凤翥街”。)我们常看见她蓬着头出来买咸菜,买壁虱(即臭虫)药,买蚊烟香,脸色黄巴巴的,不怎么好看。可是因为年纪还轻,拢光了头发,搽了脂粉,就像换了一个人,以前看不出的好看处全露出来了。扬州人看样子很疼爱这位新娘子,不时回头看看,走过去在她耳边低低地说几句话;或让她偏了头,为她拈去头发上的一片草屑尘丝。他那个手势就比一首情诗还值得一看。扬州人自己也像年轻了许多。
白案上,那位南京师傅集中精神在做包子。他仿佛想把他的热情变成包子的滋味,全力以赴,揉面,摘面蒂,刮馅子,捏褶子,收嘴子,动作的节奏感很强。他很忙,顾不上想什么。但是今天是新开张,他一定觉得很兴奋。他的脑袋里升腾着希望,就像那蒸笼里冒出来的一阵一阵的热气。听他用力抽打着面团,声音钝钝的,手掌一定很厚,而且手指很短!他的脑袋剃得光光的,后脑勺挤成了三四叠,一用力,脑后的褶纹不停地扭动。他穿着一身老蓝布的衣裤,系着一条洋面口袋改成的围裙。周身上下,无一处不像一个当行的白案师傅,跟扬州人的那种“票友”风度恰成对比。
不知道什么道理,那一顿早点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猪肝面,加了一点菠菜、西红柿,淡而无味。我看了看墙上钉着的一个横幅,写了几个美术字:“绿杨饭店。”(不知是哪位大学生的大作。)心想:三个月以后,这几个字一定会浸透油气,活该!——我对猪肝和美术字一向都没有好感。
半年过去,很多人的家乡在不断“转进”(报纸上讳言败退,创造了一个新奇的名词)的战争中失去了。滇越铁路断了,昆明和“下江”邮汇不通,大学生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学生在外面兼了差,教中学的,在拍卖行、西药铺当会计的,当家庭教师的,各行各业,无所不有。昆明每到中午十二点要放一炮,叫作“午炮”,据说放那一炮的也是我们的一位同学。有的做了生意,而且越做越大。还有一些对书本有兴趣,抱残守缺,除了领“贷金”,在学校吃“八宝饭”(糙米中有砂粒、鼠矢种种东西),靠变卖衣物维持。附近有不少收买旧衣的,背着竹筐,往来吆唤。其中有一个中年妇女,嗓音极其脆亮,我一生很少听到这样好听的叫卖声音:“有——旧衣烂衫找来卖!”
学生的变化,自然要影响到绿杨饭店。
这个饭馆原来不大像一个饭馆,现在可完全像一个饭馆了,太像了,代表这个饭馆的,不再是扬州人,而是南京人了。原来扬州人带来的那点人情味和书卷气荡然无存。
那个南京人,第一天,就从他的后脑勺上看出这是属于那种能够堆砌“成功”的人,一个非常现实的人。他抓紧机会,稳扎稳打,他知道钱是好的,活下来多不容易,举手投足都要代价。他一大早冲寒冒露从大西门赶到小南门去买肉,因为那里的肉要便宜一点;为了搬运两袋面粉,他可以跟挑夫说很多好话,或骂很多难听的话;他一边下面,一边拿眼睛瞟着门外过去的几驮子柴,估着柴的干湿分量(昆明卖柴是不约斤的,木柴都是骡马驮来,论驮卖);他拣去一片发黄的菜叶,丢到地下,拾起来,看一看,又放回案板上。他时常到别的饭铺门前转转,看看人家的包子是什么样子的,回来的路上就决定,他们的包子里还可以掺一点豆芽菜,放一点豆腐干……他的床是睡觉的,他的碗是吃饭的。他不幻想,不喜欢花(那两盆花被他搬到天井角落里,干死了),他不聊闲天,不上茶馆喝茶,而且老打狗。他身边随时搁了一块劈柴,见狗就打,虽然他的肉高高地挂在房梁上,他还是担心狗吃了。他打狗打得很狠,一劈柴就把狗的后腿打折。这狗就拖着一条瘸腿嗥叫着逃走了。昆明的饭铺照例有许多狗,在人的腿边挤来挤去,抢吃骨头,只有绿杨饭店没有。这街上的狗都教他打怕了,见了他的影子就逃。没有多少时候,绿杨饭店就充满了他的“作风”。从作风的改变上,你知道店的主权也变了。不问可知,这个店已经是合股经营。南京人攒了钱,红利、工钱,加了自己的积蓄,入了股,从伙计变成了股东。我可以跟你打赌,从他答应来应活时那一天,就想到了这一步。
绿杨饭店的主顾有些变化,但生意没有发生太大影响。在外兼职的学生在拿到薪水后会来油油肠子。做生意的学生,还保留着学籍,选了课,考试时得来答卷子,平时也偶尔来听听课。他们一来,就要找一些同学“联络感情”,在绿杨饭店摆了一桌子菜,哄饮大嚼。抱残守缺者,有时觉得“口中淡出鸟来”,就翻出几件值一点钱的东西拿到文明新街一卖。最容易卖掉的东西是工具书,《辞源》《牛津字典》……到绿杨饭店来开斋。有一个四川同学家里寄来一件棉袍子,他约了几个人一同上邮局取出来,出了邮局大门,拆开包裹,把一件全新的棉袍搭在手臂上,就高声吆唤:“哪个买这件棉袍!”然后,几个馋人,一顿就把一件新棉袍吃掉了。昆明冬天不冷,没有棉袍也过得去。
绿杨饭店的生意好过一阵,好得足以使这一带所有的饭馆为之侧目。这些饭铺的老板伙计全都对它关心。别以为他们都希望“绿杨”的生意坏。他们知道,“绿杨”的生意要是坏,他们也好不了。他们的命运既相妨,又相共。果然,过了一个高潮,绿杨饭店走了下坡路了,包子里的豆芽菜、豆腐干越掺越多,卖出去的包子越来越少。时间很快过了两年。大学的学生,有的干脆弃学经商,在外地跑买卖,甚至出了国,到仰光,到加尔各答。有的还选了几门课,有的干脆休了学,离开书本,离开学校,也离开了绿杨饭店。在外兼职的,很多想到就要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不再胡乱花钱(有一个同学,有一只小手提箱,里面粘了三十一个小牛皮纸口袋,每一口袋内装一个月中每一天的用度)。那一群抱残守缺的书呆子,可卖的衣物更少了。“有——破衣烂衫找来卖”的吆唤声音不常在学校附近出现了。凤翥街冷落了许多。开饭馆的江西人、湖南人、山东人、河北人全都风流云散,不知所终。绿杨饭店还开着。绿杨饭店犹如一面镜子,照出种种变化。镜子里是变色的猪肝、暗淡的菠菜、半生的或霉烂的西红柿。太阳光如一匹布,在阳光中游尘飞舞。
那个女人的脸又黄下来,头发又蓬乱了。
然而绿杨饭店还是开着。
这当中我因病休了学。病好后在乡下一个朋友主持的中学里教几点钟课,很少进城。绿杨饭店的情形可以说不知道,一年中只去过一次。
一个女同学病了,我们去看她。有人从黑土洼采来了一大把玉簪花(黑土洼是昆明出产鲜花的地方,花价与青菜价钱差不多),她把花插在一个绿陶瓶里,笑了笑说:“如果再有一盘白煮鱼,我这病就生得很像样子了!”她是扬州人。扬州人养病,也像贾府上一样,以“清饿”为主。病好之后,饮食也极清淡。开始动荤腥时,都是吃椒盐白煮鱼。我们为了满足她的雅兴和病中易有的思乡之情,就商量去问问扬州人老板,能不能像从前一样为我们配几个菜。由我和一个同学去办这件事。老板答复得很慢,但当那个同学说“要是费事,那就算了”时,他立刻就决定了,问:“什么时候?”南京人坐在一边,不表示态度。出了绿杨饭店,我半天没有说话。同学问我是怎么啦,我说没有什么,我在想那个饭店。
吃饭的那天,南京人一直一声不响,也不动手,只是摸摸这,掇掇那。女人在灶下烧火。扬州人掌勺。他头发白了几根了。他不再那样潇洒,很像是个炒菜师傅了。不仅他的纺绸裤褂、好鞋袜、戒指、表链都没有了;从他下菜料、施油盐,用铲子抄起将好的菜来尝一尝,菜好了敲敲锅边,用抹布(好脏)擦擦盘子,把刷锅水往泔水缸里一倒,用火钳夹起一片木柴歪着头吸烟,小指头搔搔发痒的眉毛,鼻子吸一吸吐出一口痰……这些等等,让人觉得这扬州人全变了。菜都上了桌,他从桌子底下拉过一张板凳(接过腿的),坐下,第一句话就是:
“什么都贵了,生意真不好做!”
听到这句话,南京人回过头来向我们这边看了看,脸色很不好看。南京人是一点也没有走样。他那个扁扁的大鼻子教我们想起前天应该跟他商量才对。这种平常不做的家乡菜,费工费事,扬州人又讲面子,收的钱很少,虽不赔本,但没有多少赚头。南京人一定很不高兴。他的不高兴分明地写在他的脸上。我觉得这两个人这两天一定吵了一架,不一定是为我们这一顿饭而吵的(希望不是)。而且从他们之间的神气上看,早已不很融洽了,开始吵架已经是颇久的事了。照例大概是南京人嘟嘟囔囔,扬州人一声不响。可能总是那个女人为一点小事和南京人拌嘴,吵着吵着,就牵扯起过去许多不痛快的事,可以接连吵几天。事情很清楚,南京人现在的股本不比扬州人少。扬州人两口子吃穿,南京人是光棍一个,他们之间不会有什么会计制度,收支都是一篇糊涂账。从扬州人的衰萎的体态看起来,我疑心他是不是有时也抽口把鸦片烟。唔,要是当真,那可!
我看看南京人的肥厚的手掌和粗短的指头,忽然很同情他。似乎他的后脑勺没有堆得更高,全是扬州人的责任。
到我复学时,学校各处都还是那样,但又似乎有些变化:都有一种顺天知命,随遇而安的样子。大图书馆还有那么一些人坐着看书。指定参考书不够。然而要多少本才够呢?于是就够了。草顶泥墙的宿舍还没有一间坍塌的。一间宿舍还是住四十人。一间宿舍住四十人太多了。然而多少人住一屋才算合理?一个人每天需要多久时间的孤独?于是这样也挺好。生物系的新生都要抄一个表:人的正常消耗是多少卡路里。他们就想不出办法取得这些卡路里。一个教授研究人们吃的刺梨和“云南橄榄”所含的维他命,这位教授身上的维他命就相当不足。路边的树都长得很高了,在月光中布下黑影。树影月光,如梦如水。学校里平平静静。一年之中,没有人自杀,也没有人发疯,也听不到有人痛哭。绿杨饭店已经搬了家,在学校的门外搭了一个永远像明天就会拆去的草棚子卖包子、卖面。
这个饭店是每下愈况了。南京人的脾气变得很暴躁。背着这爿半死不活的饭店,他简直无计可施,然而扔下它又似乎不行。他有点自暴自弃起来,时常看他弄了一碗市酒,闷闷地喝(他的络腮胡子乌猛猛的),忽然把拳头一擂桌子,大骂起来。他不知骂谁才好。若是扬州人和他一样的强壮,他也许会跳过去对着他的鼻子就是一拳,然而扬州人是一股窝囊样子,折垂了脖子,木然地看着哄在一块骨头上的一堆苍蝇。南京人看着他这副倒霉样子,一股邪火从脚心直升上来!扬州人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背佝偻得很厉害。他的嘴角老是耷拉着,嘴老是半张着。他老是用左手捋着右臂的衣袖,上下推移。又不是搔痒,不知道干什么!他的头发还是向后梳着的,是用水湿了梳的,毫无光泽,令人难过。有人来了,他机械地站起来,机械地走动,用一块黑透了的抹布骗人似的抹抹桌子,抹完了往肩上一搭:
“吃什么?有包子,有面。牛肉面、炸酱面,菠菜猪肝面……”
声音空洞而冷漠。客人的食欲就教他那个神气那个声音压低了一半。你看看那个荒凉污黑的货架,看到西红柿上的黑斑,你想到这一块是煮不烂的;看到一个大而无当的盘子里的两三个鸡蛋,这鸡蛋一定是散黄的;你还会想起扬州人向你解释过的“鸡蛋散黄是蚊子叮的”;你想起孑孓在水里翻跟斗……吃什么呢?你简直没有主意。你就随便说一个,牛肉面吧。扬州人捋着他的袖子:
“嗷——牛肉面一碗……”
“牛肉早就没有了!要说多少次!”
“嗷——牛肉没有了……”
“那么随便吧,猪肝面吧。”
“嗷——猪肝面一碗……”
那个女人呢?分明已经属于南京人了。不用打听,一看就看得出来。仿佛这也没有什么奇怪。连他们晚上还同时睡在那个棚子底下,也都并不奇怪。这关系是怎样转变过来的呢?这当中应当又有一段故事,但是你也顶好别去打听。
我已经知道,扬州人南京人原来是亲戚。南京人是扬州人的小舅子。这!
过了好多好多时候,“炮仗响了”。云南老百姓管抗战胜利战争结束叫“炮仗响”。他们不说“胜利”,不说“战争结束”,而说“炮仗响”。因为胜利那天,大街小巷放了很多炮仗。炮仗响了以后,我没有见过扬州人,已经把他忘记了。
一直到我要离开昆明的前一天,出去买东西,偶然到一家铺子去吃东西,一抬头:哎,那不是扬州人吗?再往里看,果然南京人也在那儿,做包子,一身老蓝布裤褂,面粉口袋围裙,工作得非常紧张,后脑勺的皱褶直扭动,手掌拍得面团啪啪地响。摘面蒂,刮馅子,捏褶子,收嘴子,节奏感很强,仿佛想把他的热情变成包子的滋味。这个扬州人,你为什么要到昆明来呢……
明天我要走了。车票在我的口袋里。我不知道摸了多少次。我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喜欢把口袋里随便什么纸片捏在手里搓揉,搓搓就扔掉了。我丢过修表的单子、洗衣服的收据、照相的凭条、防疫证书、人家写给我的通讯处……我真怕我把车票也丢了。我觉得头晕,想吐。这会饿过了火,实在什么也不想吃。
可是我得说话。我这么失魂落魄地坐着,要惹人奇怪的。已经有人在注意我。他一面咀嚼着白斩鸡,一面咀嚼着我。他已经放肆地从我的身上构拟起故事来了。我振作一下,说:
“猪肝面加菠菜西红柿!”
扬州人放好筷子,坐在一张空桌边的凳子上。他牙齿掉了不少,两颊好像老是在吸气。而脸上又有点浮肿,一种暗淡的痴黄色。肩上一条抹布,湿漉漉的。一件黑滋滋的汗衫(还是麻纱的),一条半长不短的裤子。这条裤子像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穿的。衣裤上到处是跳蚤血的黑点。看他那滑稽相的裤子,你想到裤子里的肚皮一定打了好多道折子!最后,我的眼睛就毫不客气地死盯住他的那双脚。一双自己削成的很大的木履,简直是长方形的。好脏的脚!仿佛污泥已经透入多裂纹的皮肤。十个趾甲都是灰趾甲。左脚的大拇趾极其不通地压在中趾底下,难看无比。对这个扬州人,我没有第二种感情:厌恶!我恨他,虽然没有理由。
一九四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