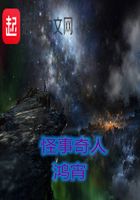你只要夏夜里在山区呆过,你就晓得,山区的夏夜,星星很多。
横过头顶的那条明亮的带子是银河。
银河从远处流来,渐浓渐密。向远处流去,渐淡渐疏。
河周围东一颗西一颗的,是不太听话的星。那些星都是有生命的,一不注意,就会从很近很近的空中,跳到刘家寨每家屋檐下都有的青石水缸中去。
萤火虫最爱和星们凑热闹。听老辈子讲,它们和星星原本是弟兄姐妹,只是天河太挤,房屋不够分配,才自愿贬谪凡尘。它们在狗尾巴草和桤木林子以及灌丛的阴影间神秘地巡逻,悠忽悠忽地,象是在打捞散落于山缝中的久远的故事。
刘光宗和本家侄子刘明兴,在去年底已经完工的盘山公路上走。
他们背着大巴山里特有的运输工具“背架”,背架上各绑着用麻布口袋装着的一百多斤苞谷。今春雨霖,庄稼不结实,该收的小春眼看收不上手,他们是到一百二十里外的山沟那面的杜家坪去借粮的,如今借了粮往回走。
刘光宗的腿边,跑着那条浑身麻黑的母狗,母狗大名“箩篼”,除了看家,箩篼跟着刘光宗秋天进林子里打野鸡,也是一条撵山的好手。
到了一段较陡的路面前,刘光宗把“丁”字型的铁头打杵撑在地下,沉重的背架不下肩地放在上头,开始原地歇气。
箩篼坐在自个儿的后腿上,吐着长舌看住他。
刘光宗怪叫一声:“噢呜——”
气息从饱满的胸膛里猛烈地压出,拖得长长的,声音在重叠的山峦间一跳一跳,翻过左侧的垭口,被一颗流星击到沟里去了。
“呜——”
二十三岁的刘明兴小声应和。他同样背架不下肩地放在打杵上,坐在离刘光宗十步开外的地方。
刘明兴比刘光宗矮一辈,按族谱里“光、明、重、庆”的字牌顺序,他是“明”字辈的。但刘明兴年轻的媳妇都生了一个女儿了,也就是说刘光宗都有侄孙了,而刘光宗呢,将近五十的老婆几个月前才害喜。
嗨!真是南瓜老了才开花。恐怕也要感谢去年他炸掉了神灵不应的贞节牌坊,打那以后,老婆的肚子好比猪尿泡儿装气,眨个眼睛就鼓大了。
“幺娃子!——”刘光宗又喊。
“呜——”刘明兴抑着嗓子应。然后轮到他大声武气地喊:“大爸!——”
刘光宗撮着嘴唇轻声应答:“噢——”
一呼一应,一远一近。歇气间,他们扮着各种口气,呼应了十几个有关的步伯婶娘、侄甥儿媳的名字。如果山里面有剪径的强盗,听到这么多人一起走夜路,断不敢上来抢他们。
山里人聪明,这是祖先传下来的方法。
但有时也不是为了防强盗。
深山老林,原始去处,即或白天走百把里山路也难捡到一根人毛,何况半夜三更。强盗疯了,到空寂无人的大山沟里抢哪个?恐怕别人没抢着,自己的小命就遭野豹子叨走了。
他们是在防山精。
山精爱在夜晚出来巡视自己的林子。
山精是女身变的,不穿衣服,皮肉雪白。在马尾松和麦草捆子上飘,飘得没有声音。刘光宗在少年气盛的青春时期,曾十分渴望见到山精。既然是女的,又不穿衣服,只这一点,就令血管里有着越来越炽烈的岩浆奔涌的山里少年神往。不久,刘光宗的堂弟刘光华摔了岩,是夜里去苞谷地里防野猪,路过并不险要的关刀梁掉下去的。人们把他抬回来,看他脑袋摔得稀烂,胸口早没了热气,但脸上却漾着柔软的笑,喜滋滋不能自己。即使已死了,笑容还把周围的空气染得温馨。
“作孽哟、作作孽哟!那是山精勾、勾了魂去哟……”
刘光宗的老爹一时就明白了其中的奥妙。
也就是自那时,刘光宗脑壳里的山精不那么保险了,不穿衣裤的女鬼也在他的幻想中显露出狰狞赫人的模样。他继承了不知哪一代先祖发明的办法,走夜路时,只要人少,少到一个两个,他就变幻出各种声音,大呼小叫,或唱山歌,显出人多势众的阵势。
结果呢,这办法果然名不虚传,好多年过去了,漂亮迷人的山精不曾光顾他。
歇够了气,大山把自己的力气,通过两个山民的腿脚,输进他们的心脏,他们又默无声言地上路。
他们离开盘山公路,走一条捷近的羊肠道。小道穿过一片墨黑陡峭的松树林。两袋烟的功夫,小道就能穿出林子,又和公路汇合,但那已经跃上了家乡所在的小高原。
汗水顺着刘光宗的络腮胡子淌,顺着敞开的胸脯淌。胸脯上有一片森森的黑毛。一根柔嫩的枝条横刺里探进去,扫了一下,凉浸浸的芽苞儿触到了毛根下温乎乎的皮肤。
刘光宗觉得是他女人带茧巴的、粗糙的手指在温柔地抚摸。自女人怀了细娃儿后,他们的感情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双方活到几十岁后的今天,才第一次尝到了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夫妻甘甜。
桅子花儿的香气从什么地方飘来,找着了刘光宗的鼻孔,自己嗤溜一下钻了进去。刘光宗浑身毛根一乍,心儿化作一泓闪着光斑的春水。
黑夜热情地用手臂圈住两个行路人,伸出潮润的舌头舔他们的脸,他们的四肢。
黑夜象一匹才下了牛犊的黄沙牛,亲热,友好,热恋幼小的生命,抱着他们,安详地蜷伏在大巴山的星空下。
刘光宗脑子里飞出一些断断续续的情歌,那是他父亲在世时爱哼哼的。现在它们在刘光宗的脑子里膨胀,象发了酵的醪糟,气泡儿一股股地涌动,自自然然冲出了刘光宗的喉咙:
“太阳落坡又落岩吔,
一对杨柳长上来,
风不吹柳柳不摆,
郎不招手哟姐儿不来……”
如今这些山歌从刘光宗粗莽的喉咙里涌出,就象屋角落里一个尘封已久的包铁木箱,一朝打开,那些破破烂烂乡里巴叽的小东西,不但不惹人厌烦,反而勾起了浓浓的温馨的乡情。
是哟,他的女人要生细娃了。刘家寨最有经验的民间产婆刘杨氏说,再迟跑不过端午节。
难怪刘光宗要在山路上唱民歌。
他们终于钻出了松树林,翻上了陡坡。
黑黢黢的家乡的小高原就在他们面前。
象熟睡了摊开手脚的老婆,仿佛还吹出了微弱的鼻息,散发出白天染上身的泥味、猪草味和汗水味。哦,家乡!
和他们一样气喘吁吁地挣扎上来的公路,浑身酥软地躺在桤木林子旁边。
就在这一瞬,刘光宗和刘明兴同时把打杵杵在地下,同时靠上背架,同时松了背系,并且脱出了身子。
箩篼的两只耳朵象竹叶似地标挺直立,嗓子里发出了不安的咆哮。
他们听见了,不,在心里感到了什么。
在悠远悠远的天边,在暗不可测的坡下,传来野兽的叫声。不是山豹子,不是麻老虎,不是野熊,更不是野猪,是一种从未听见过的叫声。
毛孔张开了,触觉象尖利的缝衣针一样刺出体外,感受着湿润的夜里的灾变。然后整个身体下意识地往内里看不见的中心点收缩。
该不会是山精?
这才叫人头皮发麻。山精,女鬼!
轰……
声音从下往上,向小高原的顶部盘绕而来。
呵,乖乖,眼睛!六只闪烁的眼睛。一会儿隐在沉默的松林后边,转个弯儿却又跳到了门板样的岩石前。
转瞬不见了。
突然又蹦了出来,更加恶狠狠地向高原上爬,向两个山里人冲锋。
就在此时,刘光宗和刘明兴一同松开了扶着背架的手。两座小山訇然倾倒,象受了致命伤的野熊。他们把打杵抽来握在手里,平端着,对着越来越近、越来越快地扑上小高原的三个庞然大物。
“汪!汪汪!!”箩篼狂蹦乱跳,做出誓死保卫的样子。
“来哇来哇!”刘光宗一步一步向后退着,机械地动着嘴。
而刘明兴早就躲在了他岩石般宽厚的身后,嘴里也含混不清地嘟哝:“你敢来整,老子认你,老子手、手里的打杵不、不认你……”
两人退着,下意识地哼着,把夜色往后挤着。夜色浑身抹了油,从他们握打杵的手臂下溜过去,又站在他们面前,象条湿衣衫包裹着他们。
轰!!——
三只贼亮的眼睛发出强大的光芒,对直刺住他们的眼睛。野物翻身耸上了崖坡,毫不留情地顺他们站身的地方扑来。
箩篼夹着尾巴,转身逃向密密匝匝的桤木林。
只有拼个一死了!
肌肉在刘光宗的小臂上愤怒地凸起,粗大的血管好似山沟里纵横奔流的江河。
他想起了老婆。
怪事!他想起老婆的肚子,肚子里是给他承接香火的晚辈。他还想到老婆的奶子,刘杨氏说他老婆长的是“锲子奶”。简直羞死先人,小得只配做卡锄板的小锲子。刘光守担心她奶不活二天生的细娃儿。
就是这样,人到了危急关头,就要想到这些平时好象不足挂齿的鸡零狗碎。你要不信,你也到危险里去试试。
怪物就要扑到眼前了……只差三步远了……完了!!
只觉得一股狂风刮过周身。
待他们再睁开眼,三个巨大的黑影早已擦身而过,疯狂地向刘家寨方向扑去。
“来哇来哇……”刘光宗嘴里还在机械地念。
一对宿林的鸦雀夫妇凄切地扑上树梢,强烈抗议怪物破坏了它们今晚的好梦。
萤火虫提着幽幽的小灯笼,镇静地在母牛般蜷伏的夜的背上巡逻。
第二天下午,三辆解放牌翻斗车从高原西部的山脉上下来,穿过刘家寨时,被三十多个山民拦住了。
这是刘家寨王国的全部臣民,领头的是刘光宗。
狗在向三个怪物乱叫,一群老鸹绕着激动不安的刘家寨叽呱盘旋。
人们放了三挂响鞭,请司机喝了荷包鸡蛋汤——山里待客的规矩,谓之“整一碗开水”——他们凭直觉猜到,眼面前的三个钢铁怪物就是“汽车”,修的那么长那么长的公路就是为它们跑路用的。
开车的工人老大哥热情地向农民弟兄介绍,说他们是为矿上送器材的,从公路修好到如今,耽误了一年,县上最后还是决定要上马。二天他们就要经常上山来了。只是公路很难走,跑了许多地方,没见过如此艰险的。刘家寨的人民帮忙修起了它,不定费了好多力。不过只要公路通进了山,农民弟兄是能得到无限益处的,这是先进的生产力嘛!
山民们十分感兴趣地听,也做出很感兴趣的憨厚样子。但山里人尽管聪明,毕竟一辈子没到过比七十外的公社小街更远的地方,他们不懂“矿”、“上马”、“生产力”,他们对将到的“无限益处”早就从筑路伊始的张副指挥嘴里听得滚瓜烂熟。他们现时现地感兴趣的是汽车本身。
一个司机掀开领头车的引擎盖,给水箱灌水。立时,山民们轰动了:
“观音娘娘呃,看它好大个嘴巴子!”
“怪不得跑那么快,晓不得一顿要整好多草!”
“妈吔,啷个才整那么一桶水?”
“象你么?整多了水光起夜,弄不好一泡尿就冲到岩底脚……汽车也要起夜,不敢整多了。”
末了,议论转为窃窃私语,转为腼腆的暗示。刘光宗站前一步,向工人老大哥挑明了乡亲们的愿望:
就想坐一下汽车。
那不十分容易吗?
“好,上车!你当代表,他们二天再坐。”
带头的司机爽快地同意。那时的工人是最讲礼貌的,是最顾及本阶级的光辉形象的。
汽车在小高原上飞驰。
刘光宗的心狠狠撞击着胸膛。一排肋骨象是竹篾子编的篱笆,心儿象一只想破笼高飞的小鸟。刘光宗看到近处的桤木林象一群群惊狂硕大的老鹰,向车后颠颇着疾飞。稍远一些的小麦油菜地和更远的一列山的剪影,却恰恰与汽车行进方向相同,慢慢向前移动。整个车窗外的景物围绕着他惊讶的眼睛在或急或缓地转圈。他成了世界的中心,小高原的中心!
刘光宗第一次感到了速度。
如果自己的肩背上象野鸡一样长出闪烁的花翎子,飞快地扑过天宇,翅膀上托着春天多沙的晴空,托着一颗灰白的害病的太阳,那还有什么留恋于世的,即或要他马上死,也死得下去了。
他的脑壳里从此揉进了过去几十年从来不曾有过的一些新鲜而朦胧的想法。
到了高地边缘,汽车调了屁股,要送刘光宗回村。昨天就是在这里,他和刘明兴端着打杵躬着腰,象端着猎枪打野豹子似的,准备打汽车呢。
他请求汽车翻一下背上的“大圈”,先前乡亲们要求坐在大圈里,工人老大哥不同意,和气地说,上级规定,“翻斗上不准载人。”
现在刘光宗提议,既然是空的,总可以翻翻吧。
司机望着他小娃娃般好奇的脸,和蔼地笑笑。他搬动什么机关,汽车象在发哪个的气,原地不动,剧烈地吼着。
刘光宗赶紧下得车来,大圈已高高翘向天空。夕阳扑上去亲它,一颗钢铁的镙栓被夕阳的红唇亲得闪闪发亮。
他和紧跟着下来的司机同时听到了公路边岩坎下发出的哼哼声。探头向下看,一双手死死抓住石缝里长着的一株马桑树,手背上青筋爆得老高,象从野兔肚子里掏出的一网小肠。
他们把他拉上来。是脸色铁青的刘明兴。
好半天才问明白,当汽车发动的一瞬间,刘明兴在乡亲们耽心的欢呼声中攀上了车背上的大圈。刚才汽车调了头,升翻斗时他没注意,一家伙就被倒了出去。若不是年纪轻轻脑壳机灵,恐怕就整下岩脚二天喂野狼坏子了。
刘明兴鸡啄米一样直向司机道歉:
“师傅,我根本晓、晓不得你的车圈坐不得……刚才一坐、坐翻了,晓不得把车圈整、整坏莫得……我整到岩脚脚不打紧,车圈坏了公家遭孽……”
一说,刘光宗也紧张。司机却笑了个半死。
“哈……哎呀我的妈……不是你坐翻的,不怪你同志……倒赫出我一身毛毛汗,把你摔坏了,我至少有几个月走不脱。哈……”
刘光宗两叔侄彻底放了心。
汽车经常都来了,一辆几辆不等,天黑天亮都开。经过刘家寨中间的公路,把轰轰隆隆的响声和山民们觉得特别好闻的汽油烟慷慨奉送。除了不能走路的老人,和资格太嫩的细娃儿,大家都轮流坐了车。有三个妇女当场下车就发了吐,脑壳晕得晚上不敢砍猪草,大家笑她们享不来新社会的福。有个老汉车门没关紧,行车途中差点颠下去,使后来的乘车者相互间很看重叮咛有关“车门栓子”的话题。
他们跟刘光宗一样,最远的路程就是坐到小高原边缘。所不同于刘光宗的地方,是到了这儿他们下车自己走回寨,而车子也就一头翻下了盘山路。
如此过了近两个月。
端午节过后的一天晚上。
太阳在西边山脉的一蓬白蜡树梢上犹豫了好久,才不情愿地松开抓住树枝的手。
黄昏象个小偷,看着太阳刚一落坡,就蹑手蹑脚从高原四周向中间走来。
刘家寨的炊烟袅袅升起。开头是乳白的,被黄昏越来越紧地抱进怀里,挤变了脸色,就变作淡蓝淡蓝的了。
天地格外纯净,群山逶迤向东。
本来啥事没有的。吃了饭,就很晚了。又不习惯点灯,山里人没啥文件要批阅,也莫得城里男女之间规规矩矩的约会,一般是洗了碗就上床。新婚汉子和婆娘还有点欢娱,其他人就一味死睡。轻易不做梦,享用最多的,是婆娘娃儿和自己身上彼此熟悉的体肤味。
可是今天黑了有些不对头。
刘光宗的老婆在宽大厚实的柏木床上翻了二十几袋烟的工夫了。
刘光宗把新榨的菜油倒二两在土碗里,粗糙的大手灵巧地搓了一根黄表纸捻儿,点燃一盏不坏的灯。
产婆子刘杨氏在照顾他老婆。
刘光宗无事。这事本也不让男人插手。他就蹲在堂屋门外的公路边儿上,慢慢裹叶子烟。他抽一口,吐一泡口水。烟头子热辣辣地明灭,象一个有生命的物件在眨眼。
他听见婆娘在惊抓抓地叫唤,仿佛无形中有人在向她抽鞭子,抽她柔软的下腹部,要把她特别圆大的肚皮抽出豁口,把还没开放的花芽芽打掉。
他此时很痛惜婆娘。婆娘的“锲子奶”早就象发了水的糍粑,突然间长得又大又圆,脸上似乎也年轻了。看见丈夫,不但不象过去一样低眉敛眼,有时还发一两声撒娇的笑。她也晓得有了细娃儿,女人的地位可以提高么?
今天白天,他两个一起和大伙薅迟包谷,然后婆娘到犀牛塘去洗衣服,末了带回来一背架青冈材,少说也有一百一。山里的婆娘比男人辛苦,回了家,又忙着推磨烧火,喂猪做饭。然而饭碗一丢,还没来得及洗,婆娘晕倒了。
刘杨氏从堂屋的门坎上一步跨出,屋内摇曳的灯光漏了几片在她脸上,多皱的脸儿明显地伏满了惊恐。
她那老松皮一样的手上滴着暗红的液体。
刘光宗看见了血。
他把烟锅子在公路边儿上捺熄了。
恰巧夜暗中下来一辆汽车。刘光宗托起硕大的脑袋,想了想,蚕豆似嵌在眉骨下的眼睛觑了觑,站进了公路中间雪亮的车灯光柱里。
汽车连夜连晚地赶,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把刘光宗和半死的婆娘送到通江县城。
是“整”的剖腹产,肚皮上划了条一尺长的大口。
生的是龙凤胎,一男一女。
医生先从热嘟嘟的母亲肚腹里取出男的,男的就是哥。
然后取出女的,女的就是妹。
他们在县城呆了十二天。
县城里到处是红军留下的石刻标语,比刘家寨原先那贞节牌坊上的花样儿多得多。刘光宗不识字,在街上观望时,请教了一个小年轻。小年轻领着他到处转,看“革命法庭”遗址,“列宁公园遗址”,“红四方面军总部遗址”。总部遗址在文庙里。刘家寨山上没有文庙,刘光宗只晓得有一座大半人高的土地庙。
终于在一座石砌屋基上发现了两条标语,那字儿的笔画与刘家寨遇难的贞节牌坊上的标语一模一样,刘光宗油然而起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乡情。
刘光宗惊讶地发现街边一座大房子里竟包容有十几个小房间,而山里头的松木吊脚楼最多也就隔出四、五间。国营食堂里竟是男人家在炒菜,山里头的灶边可只是婆娘家在转,而男人们进了屋是横草不拿竖草不拈的。
晚上又吃了一惊,公家的房子是用么子“电”,一拉,玻璃罩儿就亮了,且不冒油烟。
当然了,城里万般稀奇,怎奈抵不住渐浓渐深的乡愁。有个锥子在他和婆娘的脑壳上外钻眼,钻通了,家乡遥远的气息就一涌而入。
刘光宗念他的苞谷油桐,婆娘念她的鸡鸭犬豕。
他们是第十三天傍晚搭顺路的车子回山的。头天晚上,刘光宗一个人逛了电影院。
他问清了规矩去买票,售票口里那位四十来岁的妇女格外热情。刘光宗不晓得看电影要依照小黑板上规定的时间,这个电影早开演了大半个钟头了。
“这样子,我只收你一半票钱。”四十来岁的妇女说。
那个年代的人就是好,刘光宗感激得话都说不清了。
进得场子,眼睛不能习惯骤然袭来的黑暗,加上只顾留心白布单上一个举枪的人,他于是干脆不动,站在最后一排的椅背后。
“喂,”电筒在黑暗中亮了眼睛,话语也仿佛是由它说出来的,“你的位置?”
“么子位置?”
“票呢?”
他给一个肯定是姑娘的人看票。姑娘也很热情,电筒光低头照在他手扶的椅背上。
“老乡,你的位置刚好就在这里,42排42号。”
他走进长条椅,刚落座在边儿上,白布单上那个带枪的人也就放好了炸药包。也是风声、雷声、电火闪闪、一棵大树举着千万条手臂狂吼乱叫。一切都象刘光宗在高原的风雨之夜中干那件事情的光景。
导火索点燃了,火星纷溅着,嘶嘶啦啦向墙根旁边的炸药包燃去。
刘光宗倏地一惊,不晓得白布单上的事情是假的,他拔腿就向外边跑,刚才验票的姑娘对他眯眯笑:
“老乡你找厕所?”
刘光宗弄不懂啥叫“厕所”,只是一味的神情紧张。姑娘起了疑心,还没来得及盘问,就听放映室内一声闷响——
“轰!!”
跟着是房屋倒塌声。
刘光宗大叫一声,立时清醒万分。他为自己丢下众人跑出来而痛感羞涩。山里汉子不是胆小鬼!救人要紧!他一头又扎进屋去。
当然都以笑话告终。
此刻,刘光宗的老婆抱着两个细娃儿坐在驾驶室里,月母子不敢吹风。刘光宗自己一个人站在后面的车箱里,他已不叫它“大圈”了。汽车已离开县城七个小时,包括离开傍河的小镇四个钟头,现在正在爬危险的盘山路。
黑暗包裹着天地,汽车用脑袋挤开它。黑夜如无声的水,在车脑袋前头急速分开,又在车箱后面急速合拢。
一只猫头鹰坐在路边怪模怪样的峭岩上,孤零零地。车灯扫过了它,它才突发一声惨叫,象一个人被突然刺了一刀,弄得刘光宗身上毛骨悚然。
黑的山和黑的天无边无沿地接在一起,连个透亮的缝儿都没有。
公路右边是万丈深渊,张着沉默的大口。
刘光宗想放开喉咙虚张声势地喊叫点什么了,就象几十年来每每人少走夜路时一样。他还是怕山精附体。山精既是妇道人家,又不穿衣服,足见是又不要脸又不要命的了。他咳嗽,打扫喉头,深吸一口气。突然又收了。
他想起昨晚上在电影院闹的笑话。
如果他在汽车上再出点差错,司机不笑话么?
况且汽车声音早就赛过了他刘光宗的喉咙,轰轰隆隆,硬象打雷。就是山精的丈夫和爸爸加在一起,都不敢来整他刘光宗的了。
他终于没唱。
汽车也就回到了刘家寨。
这是上刘家寨的最后一辆车。打从矿上卸了东西返城后,就再也没来了。
刘光宗用一星期时间准备的一篮莹白的鸡蛋和两腿烟熏黄羊肉,想要酬答送他上下县城的司机的,可惜从第二天起,就没见汽车的影子了。
传来一点点风声,说西边峭壁上的汞矿是“冒进”的产物,终于还是决定下马。现在是自然灾害时期,救肚皮要紧,挖什么矿。
又说县衙门换了人,原先的父母官贬为庶民。
这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