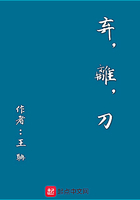柳潇潇既已下了决心,眼下自然要把注意力都放在提高自己武功上了,忽而想到六年前武林众人上华山为夺《玉枕书》一事,又想到陶忘三提过沈逍鹤与薛盼盼,是以问道:“师父,你可知道风月宫的镇宫之宝《玉枕书》?”
陶忘三颔了颔首,道:“这《玉枕书》乃是薛盼盼呕心沥血之作。当年沈逍鹤在西湖见过薛盼盼,便对她一见倾心,又是上她府中弹奏《凤求凰》,又是从东京辽阳府求来岫岩玉做成一方莲花玉枕送于她,暗含同床共枕之意。可惜后来沈逍鹤这臭小子与薛盼盼之父在朝堂上起了争执,被皇上怪罪,从而仕途不畅,不得皇帝重用。他一怒之下,辞官归乡,跑到南雁荡山建了清世宫,当了道士。薛盼盼曾与父亲反目,跑到清世宫找他,想与他重归于好,可沈逍鹤已全心于道,说什么也不肯再与她在一起。薛盼盼心灰意冷,悲痛欲绝,在仙华山上建了风月宫,并自制一套武功心法,将其刻在那一方玉枕之上,因而这武功秘笈便称为《玉枕书》。薛盼盼虽是女流之辈,但武功甚是了得,她曾约沈逍鹤于苏州缥缈峰决一高下,她大败了沈逍鹤,就是运用了《玉枕书》中的武功,自此《玉枕书》的名字传遍江湖,江湖之人都恨不得占为己有,习得这绝世武功。”
难怪就连父亲也鬼迷心窍,要夺得这《玉枕书》呢,试问面对着这样的诱惑,谁又能把持得住呢?话虽如此,但父亲怎狠得下心杀了枕边人呢,想到此,柳潇潇眸中含泪,又是不知所措。
“几年前二狗子和沈三娘回来看我,和我提到薛盼盼,我才知道在那场比试之后不久,薛盼盼就因情伤郁郁而终,她的弟子施无姈继承了她的宫主之位,却并未习得《玉枕书》上的武功,可惜薛盼盼倾尽心血的武功绝学后继无人。”
“薛前辈与沈师兄也是有缘无分了。”柳潇潇叹息一声。
陶忘三却怏怏道:“这都是沈逍鹤那臭小子自作自受的,他与薛父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薛盼盼何干,他竟怪罪到她头上。不过……他对薛盼盼绝情也并非全是坏处,要不是他的薄情,薛盼盼也不会伤心欲绝之下沉迷于武学,作出《玉枕书》了。”
“我在想《玉枕书》既是风月宫的镇宫之宝,必是藏得极隐秘,又怎会被我娘盗走呢?我爹难道从没怀疑过传闻么?”柳潇潇自言自语,却字字句句让陶忘三听去。
“你父亲对你如何?”
莫名其妙的提问让柳潇潇不明所以,但还是实话实说了:“父亲对我一直是很好的,但是……他对我娘……”
“你有没有想过为何你爹对《玉枕书》也感兴趣呢,他真的与其他人一样吗?”
柳潇潇心道:是啊,我虽知道爹爹一心想得到《玉枕书》,却不知道他得到《玉枕书》是为何,难不成此事另有隐情?毕竟爹爹并不是故意杀了娘亲,而是失手错杀。
“我听三娘说过你爹柳十针的事,你爹少时只不过是一个文文弱弱的小医师,从未踏足武林,也不识得武功,但他却与你娘成了亲,成了武林中人,却总受他人欺负。我想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原因罢,或许他的本心是为了保护你们母女,却不料越陷越深,又受人蛊惑,才会与你娘起了争执,一时失手成了千古恨。”
柳潇潇心道:无论他本心为何,他总是不能抵挡住诱惑,连自己的妻子都下得了手,我怎可轻易原谅他呢?
“我知道你一定很恨你父亲罢,毕竟原本一个完整幸福的家毁于一旦,你失去自己的母亲,又发现杀害母亲的凶手竟是自己的父亲,任何人一时之间都会接受不了此事,可时间总会改变事情的……”
柳潇潇静心想了很久,不知如何是好,为何此等匪夷所思的事情会发生在她家人身上呢。
“好了,别想这么多了,吃饭罢,菜都要凉了。”陶忘三登时忘却前事,享用起了美味佳肴来,柳潇潇却是久久才动筷来吃。
窗外繁星点点,于雪中欣赏繁星倒也别有一番风味,柳潇潇心神俱动之下,又忆起夏日夜晚之时与顾缙仰卧船头看星赏月的情景,不由得又尝了相思之苦。
“不知缙哥哥而今在做什么呢?会不会早已佳人在侧,忘了我呢?我真想再见见缙哥哥,这样也可慰聊我的相思之意了。”寒风凛冽,柳潇潇打了一个寒颤,关上窗门,钻进被窝里好好睡上一觉,明日可还要早起习武呢。
此后一月,柳潇潇每日起早贪黑,挑水而返的时间愈来愈短,轻功也因此增进不少。而在沼泽上柳潇潇扎马步是又稳又久,内力也大增,并能自己控制内力。柳潇潇学的快剑从一开始的快慢慢增加了杀伤力,经常在冰上刻字,锋刃过而字留,一气呵成。
冬去春来,万象更新,陶忘三已然教了柳潇潇不少武功招式与心法,柳潇潇天性聪颖,领悟性强,只听得陶忘三教过一次就已烂熟于心,又勤加练习,比之以前武功是突飞猛进,对付天煞帮之人已是易如反掌,可要对付像公孙鸣这样武功高的人还是力不从心,未能成其对手。
这日,陶忘三又教她自创的武功,陶忘三既是隐世逍遥之徒,其武功自然印上了“潇洒”二字,无论剑法、掌法还是拳法都具有飘逸洒脱的特点。柳潇潇便是知了这些,故向陶忘三建议道:“师父,你教了我武功,我到江湖上行走之时难免会使,届时若有人请问我的武功出自何门何派何人,我总不知如何介绍。师父,你的武功既是飘逸洒脱的,你又最喜逍遥,不如就建了一个门派叫做‘逍遥派’罢,你说好不好?”
陶忘三倒对此事无所谓,只是听这“逍遥派”的名字与自己的风格相符,故也默许,随柳潇潇去了。
又过了一月,柳潇潇已学了不少功夫,近日来总听到金国的号角声,内心总是惶惶难安的,故而辗转难眠,和衣披了斗篷到茅舍外透透气,谁知却看到两个黑影从水洞中出来,四处张望,似是鬼鬼祟祟的模样,只见他们轻步踏来,就要进茅舍。
柳潇潇只道是外人闯入了山谷之中,嗔道:“师父在这里潇洒自在地过活,你们就偏要来打扰他,看你们偷偷摸摸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且待我替师父教训你们!”
柳潇潇学了这么久久的功夫终于派上了用场,只见她轻盈飞去,双手抓住他们二人的肩头,将他们往上一提,向两边摔去,此招乃为“大鹏展翅”,那一男一女险些倒在地上摔个狗啃泥,他们倒立时撑地而起,引腰而探,狂呼出五掌,招式甚像“狂栽五柳”,柳潇潇心下纳罕回身一躲,使出一招“飞仙遨游”。
男女也是一惊,快步而踢,招招逼向柳潇潇脚尖,柳潇潇大惊这招式分明就是“飒沓流星”,心下已然有了答案,但又问道:“你们究竟是谁?怎会我逍遥派的武功。”
男女相视一怔,许是惊讶于“逍遥派”的名号,久久才道:“我们便是癫凤狂龙。”
柳潇潇抱拳敬道:“潇潇见过师兄,师姐。”
“啊?师父居然又收了一个弟子啊?”苏旸张目道,只见茅舍的门开了,里面走出了陶忘三。
“你们两个,还记得回来看我啊!”
苏旸与沈珺迎上去挽住陶忘三的手,可是亲昵。沈珺道:“我们可不像大师兄,当然记得回来看你老人家了。”
“老?我哪里就老了,尽瞎说。”陶忘三瞥嘴道,甚似孩童的神态。
“师父是宝刀未老。”
沈珺一把拍向他的后脑勺,道:“你是不是傻啊,宝刀未老不还是说师父老么?”
“师父,你看她,都过了多少年了,她还总是这样欺负我。”
“你还敢恶人先告状啊。”
“我……我……”
“行啦,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都是孩子的爹妈了,还像年少时一般拌嘴,羞不羞人。”
“不羞,我一天不数落他,心里就难受。”
“你,你这婆娘……”
沈珺朝他吐吐舌头,又转过头去不理他,向陶忘三问道:“师父,你是何时收的师妹这个徒弟啊?”
“去年,潇潇她一直想见你们,你们不去和她唠唠。我呢就回去睡觉了,刚刚做了一个好梦被你们两吵醒了,真是……”陶忘三脸上洋溢着幸福与欢欣,连语气中都带了几分得意,沈珺将柳潇潇带进了茅舍,与她聊了起来。柳潇潇这才知道,原来外面金兵已然南侵,皇帝同意割让太原、中山与河间三镇,形势甚为紧张,他们夫妻二人回来找陶忘三是向请他出山,能够帮助宋军,攻打金兵。不过相州城戒备森严,早已成了金人的领地,他们二人好不容易出了城,来到山谷之中,却已是晚上了,他们生怕打扰师父休息,故而轻声缓步蹑进来,这才引起了柳潇潇的误会。
“真是抱歉,是我不问清楚就对师兄师姐动手,实是不该,还望师兄师姐莫要怪罪才是。”
“也是我们没有说明白,让你误会了。不过既是误会一场,师妹你又何必放在心上呢,这几个月来,多得你照顾师父。”沈珺眉开眼笑,望着柳潇潇,心道:我这师妹长得可是水灵,看她古灵精怪的模样,难怪能讨师父欢心,竟让师父建了“逍遥派”。
“照顾师父是我应该做的,不过……今日见到师兄师姐,倒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哦?”
“看你们的样子,这癫凤狂龙……”
苏旸憨笑道:“我是凤,她是龙。”沈珺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脸颊上了红晕,好似彤云一般,低眉一笑,灿若云霞,他们二人之间的感情真是令人艳羡。
“对了,师妹,你可是姓柳?”沈珺抚着自己热热的脸颊,羞涩问道。
“不错。”
“太好了,原来你就是顾兄弟要找的人。”苏旸拍掌喜道,柳潇潇难以抑制激动之心,从凳上起身:“师兄师姐见过缙哥哥?他现在在哪?”
“是啊,前几日我与他还有书信往来,听他说他现在一路北上徐州,想找你呢。”
原来缙哥哥还挂念着我,我定要再见他一面,哪怕是一面也好,我也可安心地投入军营,抵抗金兵了。柳潇潇眸中带着三分笑意,巴不得现在就骑马南下,回徐州找顾缙。
翌日,柳潇潇带上包袱,沈珺苏旸和陶忘三在门前送她,陶忘三与她待了几月,早已习惯她在身边,现下她突然要离开,心里还是有所不舍。
“丫头,你真要南下去徐州了?”
柳潇潇低眉,流露出留恋之情来,道:“师父,我想去找缙哥哥,日后若是得空,我会回来看您的,我不在您身边,您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陶忘三长吁一气,知奈她不何,就像长大了的女儿总要嫁人一样,徒弟总有一天会离自己下山去:“唉……收了那么多个弟子,个个学了本事,就不要师父了……”
“师父,您怎么说这话呢,不是有我们陪在您身边嘛。”沈珺搂搂他的手,安慰道。
陶忘三嗤了一声:“你们不也是要投入宋营么,怎么能陪在我身边呢,你就会安慰我。”
“师父,您跟着我们去宋营,我们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么?”
柳潇潇听到沈珺的建议,欣喜过望,若是陶忘三能投身宋营,宋国便是如虎添翼了:“是啊,师父,您都在这山谷这么多年了,就不想出外看看么,外面的山水钟灵毓秀,若让金兵侵夺去了,您就再也不能看到那般美景了,您就不觉得可惜么?”
“是啊,师父,您武功这般高,世上几人能敌,您若出马抗敌,金兵一定被打得落花流水。到时,我们再带着您老人家去欣赏江南的雨,塞北的雪,带您游山玩水,成为第二个谢灵运,岂不是真真的好?”苏旸亦劝道。
陶忘三倾耳听着,知他们之言不过是想劝自己出山帮助宋朝罢了,他虽蔑视皇帝,但也知“亡,百姓苦”的道理,国若被破,受罪的都是百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尽管知道宋国已是每况愈下,但总可义无反顾,奋力一战,结果如何便由天定罢。
“你们也不用再好言好语相劝了,我就跟着你们出去就是了,不过你们可要记得你们的承诺,若有机会,你们可要带我游遍天下啊。”
“好好好,我们断不敢食言。”陶忘三能出山相助,沈苏柳三人自然是欣欣然,于是柳潇潇辞别而去,领着小白马登上竹筏,划桨逆流而上,待曳出了水洞,柳潇潇便舍船,取道篁竹,往小道一路南下,如今金人已将相州侵占,就连郊外乡下也总能见金兵,百姓皆需经过反复搜查才能出城。
完颜宗望率着大军一路南下,完颜齐应该也跟着他而去了罢。柳潇潇未敢确定,以防万一,还是小心行事为好,于是柳潇潇乔装易容,一路上也没多受阻拦,是以策马奔腾而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