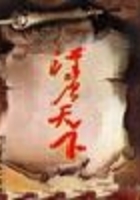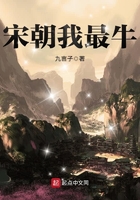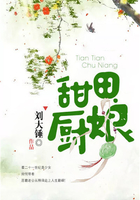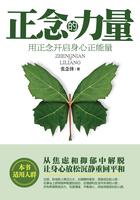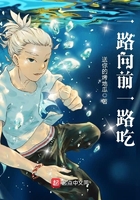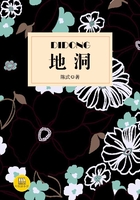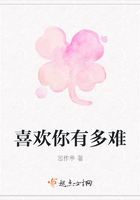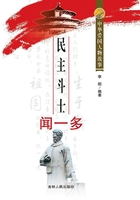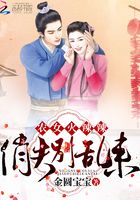第一节 校史杂说
谭文耀:暂驻衡湘 又成离别
1937年秋,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接着整个华北亦为日军侵占,大批高等院校纷纷南迁。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大后方的湖南长沙和陕西城固,设立两所临时大学,以便北平、天津两地的大学生仍然能够在一大批学有专长、蜚声中外的教授和专家的指导下,继续进修,为胜利后建设国家作贡献。为此目的,广大师生不辞艰辛,千里步行,结集到了预先选定的地方。
长沙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组成。北京大学学生学号之前冠以P字,清华大学学生学号之前冠以T字,南开大学学生学号之前冠以N字,以示区别。但在上课时,老师共教,学生互学,亲密无间。临大分设两处:理工学院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文学院在南岳白龙潭圣经学校。
1937年11月,日本飞机空袭长沙火车站。原在北方认为长沙南岳比较安全,如今却像前线一样了,为此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再迁往云南的蒙自县和昆明两个地方。南岳的文学院,迁到蒙自县。长沙临时大学迁来长沙、南岳办学,为时不过半年之久,便分两路离别了湖南。
《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在南岳》
左右:史无前例的“长征”
1937年8月28日,教育部指定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内迁筹委会常务委员。蒋先生不知此一去何日再能见老父,抽空回去看了父亲一转,便赶至长沙参加筹建联合大学。
蒋先生至长沙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已经先到了。9月13日,长沙联合大学筹备委员会在长沙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长沙临时大学的校务由原三校校长共同主持,蒋梦麟兼校务长、梅贻琦兼教务长、张伯苓兼建设长。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而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一面为战局担忧,一面还为战区里或沦陷区里的亲戚朋友担心,身体有些支持不住了,胃病在急和累中复发了。虽然“外忧内患”,他仍然打起精神与梅贻琦校长共同担负起责任,但毕竟是靠许多同仁的共同努力和同舟共济,他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
1937年底,南京沦陷后,日军溯江占领南昌,长沙随之成为日机轰炸目标之一。蒋先生飞到武汉,想探探政府对联合大学继续迁往内地的意见,教育部要他去找蒋介石,他只得去了。蒋介石赞成对联合大学再往西迁,蒋梦麟建议迁往昆明,因为那里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相衔接,从而有利于维护联合大学将来与海外的联系。蒋介石马上表示同意,并提议应先派人到昆明勘察寻找校址。1938年1月,联合大学就在准备搬迁中度过了。
长沙临时联合大学在第一学期结束后,按大多数人的意见于1938年2月底向西南迁往昆明。其时交通困难,除女同学及部分体弱之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外,男同学组织了湘黔徒步旅行团,在闻一多教授的带领下,由长沙步行3000里至昆明。
蒋先生于迁校工作大体完成后,由长沙飞香港,搭法国邮轮到海防,然后乘火车至河内,再乘滇越铁路往昆明。4月2日,湘黔滇徒步旅行团抵达昆明,已先期到达的蒋先生、梅先生及临时大学的其他负责人一起到昆明东城门去迎接他们,几位教授夫人还献了花篮,小孩们还唱:“It's a long way to联合大学,It's a long way to go!”向3000里风尘仆仆的师生表示祝贺。未参加步行者,全程耗时约半月,长短时间各有不同。约350名学生留在长沙,参加各种战时机构。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
黄钰生:增设师范学院
联大师院是当年教育部在全国同时新设的八个师范学院之一。在抗战伊始,战区许多学校仍处辗转流亡之中的时候,一下新设八个师院,除为大量培养师资之外,实有配合国民党所谓“训政”之需要,加强对青年思想控制的目的。这从规定院长须由国民党党员担任;当时其他高校均无训导处,而师院则必须设主任导师负责学生之思想行为训导工作;增设公民训育系以培养各级学校的训育人员等,都可见一斑。而要求联大增设师院,则是因为联大教师力量雄厚,可资利用之故。师院建院时,将原北大教育系、南开哲学心理教育系的教育组及云南大学教育系师生划归联大师院,三系组原有教师人数不过四五人,而1938年师院新招生的五年制本科共设有教育、公民训育、国文、英语、数学、史地、理化等七个学系,此外还先后设置了两年制的文史地、数理化专修科、云南省在职教师晋修班等。因此,多数系主任和教师是由联大其他院系教师兼任,或与联大文、理、法学院系开设的相应课程一同上课的。以后联大每年都新聘一些教师,其中有些是针对师院的需要聘请的专任教师。有些虽由师院名义聘请,实际并未在师院授课。据《联大大事记》所载,曾在联大师院任职的教师先后有91人。其中教授20人,副教授9人,讲师12人,教员14人,助教36人。教师实力之强,在其他师院中是很少见的。
师院的课程除了按教育部颁布的《大学院系必修选修课程表》之外,师院学生还要按西南联大自己规定的大一共同必修课程肄业。师院各系,也有共同的有关教育方面的必修课。除了上述三层必修课之外,师院各系,有由系主任所拟订的必修选修课程表,学生遵循肄业。所以师院五年制本科生(第五年为教学实习)应修的学分总数略多于其他院系。
《回忆联大师范学院及其附校》
刘兆武:五个学院
西南联大有五个学院,文、理、法、工,工学院主要就是清华的,其余三个学院是三个学校都有的,另外还有一个师范学院,是云南教育厅提出合办的,比较特殊。云南教育差一些,希望联大给云南培养些教师,我想联大也不好拒绝,就合办了一个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先调云南中学的教师来上,后来就直接招生了。可在我们看来,师范学院有点像“副牌”,比如我们有历史系,可师范学院只有“史地系”,大概考虑到将来到中学教书,除了教历史还得教地理,所以两门一起学。再如他们有个“理化系”,可是我们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是分开的,课程的内容和他们也不一样。
西南联大五个学院在地址上分三块,其中,工学院在拓东路,在昆明城的东南角,文、法、理学院和校本部在一起,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校本部就是挂“西南联大”牌子的地方,像校长办公室以及学校的主要部门都在那里。我们住在校本部,是新盖的校舍,叫“新校舍”,其实只是泥墙茅草棚的房子。
《回忆西南联大七年》
左右:蒋梦麟去蒙自考察
早在3月初,由于在昆明学校校舍不足,蒋梦麟便到云南第二大城市蒙自去了解情况。3月14日,这位主要负责外事的校务会常委回到昆明,次日下午即在四川旅行社开会,到会者有蒋梦麟、张伯苓、周炳琳、施嘉炀、吴有训、郑天挺等人,会议决定将联大文法学院设在蒙自,理工学院设在昆明,由北大、清华、南开各派一人到蒙自筹备。19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在昆明召开首次会议,鉴于联大在昆明实在不能立即找到合适房子容纳这许多新客,会议决定接受蒋先生等人建议,把文学院和法商学院设在古城蒙自,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办事处”。蒙自原是中国边疆军事重镇,元代时已设县。近代,更是中国与越南通商的一个重要城市,那里设有海关。滇越铁路通车后,蒙自失去了原来的重要性,海关自然迁走。人去楼空,联大文学院就设在海关衙门里,称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分校只办了一个学期,同年9月,文学院与法商学院即迁回昆明。因为当地各中小学已迁往乡间,原校舍可以出租,房舍问题已不如过去那么严重。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
何宇:叙永分校
1940年日军进占越南,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要求联大迁川,校务会议多次讨论,并派专人入川寻找能容纳联大的校址。但大家都知道搬迁一座大学校“谈何容易”,最后采取最简单,也是最容易实现的迁校形式,就是让一年级到叙永报到,在六座不大的破旧庙宇(会馆)中建立起西南联大叙永分校,这时大半个学期已经过去了,八个月后又迁回昆明。
在向北流入长江的永宁河的峡谷中,叙永算是较平坦的地方,但还需把两岸都利用起来,才能建成各只有一条大街的东城和西城,再用上桥和下桥把这两城连结起来,就成为川黔孔道上的重镇。六百多学子每天的学习和生活就是穿越两座桥,通过三条路,进出两座城,往来于永宁河东西两岸的六座古庙之间,上课,吃饭,睡觉,泡茶馆。
《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陈长平:两首校歌
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和两首校歌,时至今日,仍像当年一样给人以激励和启迪。
一首是7月7日抗日战争二周年旧《云南日报》第四版“抗战二周年纪念特刊”登载的冯友兰教授所作“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歌词如下:
“碧鸡苍苍,滇池茫茫。这不是渤海太行;这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底家乡;莫辜负伟大底时代;莫耽误宝贵底景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底景光,要创造伟大底时代;要恢复失掉底家乡。”
冯先生的这首新诗体歌词,道出了联大所在的春城美景,同时也结合抗战两年祖国大半壁河山沦入日寇手中;教育学生不要忘记失掉的家乡,要赶紧学习,赶紧准备;告诫学生要抓紧时间,不要耽误宝贵的景光;要珍惜和利用千百万前线军民浴血奋战换来的宝贵的景光;要担当起抗战建国的重任,要创建伟大的时代,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要恢复失掉的家乡。冯先生这首校歌虽然没有被正式采用,但与采用的罗先生作词的那首校歌比较,两首都具有教育意义、都具有历史价值、都充满爱国主义精神。
另外由罗庸先生作词,由张清常先生根据《满江红》作曲的那首《西南联大校歌》,其歌词如下:“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洒遍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罗先生采用《满江红》词式作的歌词,有些古朴深奥,不能为一般文化水平低的人所能理解。但加以解释后,还是容易知晓的。
总的来说,罗先生的歌词与冯先生的歌词中心思想都是一致的,为教育和鼓舞学生驱逐倭寇,好好学习,为中国人民雪耻报仇、为抗战建国激越壮志和坚定决心。这两首歌词都可以作为向大、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教育的好教材。
《关于西南联大的两首校歌》
申泮文:三校公物迁移北运
为了办理三校复员迁返平津,联大曾两次组织“三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第一次在1945年8月23日,聘请郑天挺、黄钰生、查良钊、施嘉炀、陈岱孙等为委员,郑天挺为该会主席,后黄钰生因公赴渝,郑天挺奉北大之命,赴平接收,均请假三月。10月17日加聘郑华炽等4人为委员,1946年初又加聘李继侗等3人,4月24日再次加聘马大猷等12人为委员。在这个委员会的主持下,6月26日委派以徐璋为主任的5人押运小组负责将首批急运图书仪器物品(共625箱,重69吨)运往平津,于8月底顺利抵达北方。
联大结束后,1946年7月25日,又由三校分别推定代表第二次成立“三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委员有贺麟、孙云铸(北大),霍秉权、沈履(清华),黄钰生、冯文潜(南开),霍秉权为主任委员。又根据三校推荐和协商决定,委派申泮文(南开)为主任押运员、王大纯(北大)和黄胜涛(清华)为副主任押运员,组成七人押运小组负责剩下的300吨公物的北运任务。这些公物分属三校,北大和南开的主要是图书,清华的以工科仪器设备为主,装在一定大小的木箱里。另外有三校教职员托带的少量行李、书籍、物品,形式不一,行李包、书箱等都有。
同首批启运的公物一样,这些东西也在三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的主持下,包给裕和企业公司承运。裕和公司实际是皮包公司性质的私商。经理姓吴,40岁左右,昆明人,原是帮会头子,自己没有什么资本和运输工具。他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后,由银行或殷实商家作保,从学校预支一大部分运费,然后找一些小包商分包出去。从昆明到长沙是公路运输,小包商各拥有卡车数不等,有的三辆,有的五辆,甚至一辆卡车的主人也来分包。这样零零星星,拖延了运输的时间,增加了工作的困难。
联合迁移委员会主任委员霍秉权教授召开过一次押运人员会议,布置任务。首先是给公物编号,书写箱外标志挂标签,承包卡车来到后,登记装车单,监督装车,招呼装好货的卡车驶离昆明,沿途督促检查,以防失误。裕和企业公司也派三人押运,负责管理、转运等工作。运到长沙后用民船由水路运武汉,转江轮到上海,再转海轮到天津。属于北大、清华的公物再由铁路运去北平,分别向两校交割。
《三校公物复员北运回忆》
第二节 校长,西南联大之魂
刘兆武:“你是我的代表”
三个学校合并以后,组织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三个常务委员就是三位校长,主席是梅贻琦。张伯苓在重庆,实际上是做官了,不常来,我在昆明七年只见过他一面。他那次来向学生做了一次讲话,不过张伯苓好像并不是很学术性,言谈话语之间还带有天津老粗的味道,满口的天津腔。他说:“蒋梦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个表,我就给他戴着,我跟他说:‘你是我的代表(戴表)。’”又说:“我听说你们学生烦闷,你有什么可烦闷的?烦闷是你糊涂。”蒋梦麟以前是教育部长,主要搞一些外部事务,对学校里边的事情不怎么管,实际上联大校长一直都是梅贻琦,他还兼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教务长,所以我们写呈文的时候都写“梅兼教务长”。他的工作成绩还是挺不错的,能把三个学校都联合起来,而且一直联合得很好,在抗战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非常不容易,他确实挺有办法。而且梅贻琦风度很好,顶有绅士派头,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甚至于跑紧急警报的时候,他还是很从容的样子,同时不忘疏导学生。在那种紧急的关头还能保持这种风度确实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度过。
《回忆西南联大七年》
左右:“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联大成立之初,以学校的历史与校长资历而论,蒋梦麟应该居于领导的地位,但蒋先生为了三校的团结与整个中华民族的事业,坚定主张沿用长沙临时大学时的体制,不设校长,实行常务委员制,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及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共同主持校务。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推梅贻琦为主席,实际主持学校日常行政事务。原定校长轮流担任常委会主席,实际上常驻昆明掌理校务的仅梅贻琦,并一直任常委会主席,负责学校日常事务。蒋先生主要负责对外。他们三人之间的友谊与团结是西南联大能在艰难困苦时期支持下来的根本因素。据郑天挺在《梅贻琦先生与西南联大》中回忆:“联大初成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蒋梦麟校长说,‘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思想。蒋梦麟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负责,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认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校长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这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
谢本书:多听少说的梅校长
梅贻琦是个沉着冷静,说话不多,甚至沉默寡言的人。然而,在关键时刻却能一言解纷。这在那个纷繁复杂、矛盾丛生的时期,处理问题是很有效的,至少不会激化矛盾。许多人回忆及记载,都异口同声地感觉,梅贻琦是一个“多听少说”的人。然而一到他说的时候,矛盾、工作就差不多到解决的时候了。抗战时曾任经济部次长的张静愚回忆:“凡是曾与梅校长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都不肯轻于发言,甚至与好友或知己相处,亦是慎于发言。但当某种场合,势非有他发言不可,则又能款款而谈,畅达己意,而且言中有物,风趣横溢。”清华同人注意到:“他开会很少说话,但报告或讨论,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争辩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纷。”熟悉他的人则认为,梅“平日不苟言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回味”。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也说:“月涵(梅贻琦字)与元任都有慢吞吞的诙谐习惯。”
西南联大校园内曾经流行一首打油诗,其中有“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可见不见得”两句,形容梅贻琦公开演讲时喜用不确定语气。而有人则将梅贻琦使用不确定语气的习惯,归结为处事严谨的特性。叶公超回忆道:“我认识的人里头,说话最慢最少的人,就是他(梅)和赵太侔两个。陈寅恪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的多听少说,不仅是考虑问题严谨周到,而且也体现了对别人的尊重和礼貌。遇到什么问题,梅总是先问人:“你看怎么样?”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都愿意心平气和地和他讨论。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感到受到了尊重,而不会激化矛盾。
《西南联大掌门人——梅贻琦》
谢本书:值得回味的定胜糕
著名作家兼学者林语堂先生,对西南联大有一个惊世骇俗的评论,这就是“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的确,在相当一个时期,联大在物质上确乎是“不得了”的,教授们的生活相当的困难,即使是常委的梅贻琦也不例外。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就曾说:梅贻琦1939年每月的薪水,可维持三个星期的家用,后来勉强只够半个月。家中常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连青菜也没有,偶尔吃上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开心。1940年3月,全校工友总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而联大亦曾为教职员生活问题开过一次教授会议。1941年底,教授们生活日益难熬,王竹溪、华罗庚、陈省身、吴晗等54位教授联名写信给西南联大常委会,呼吁改善待遇。呼吁书说,教职员生活“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要求增加津贴。为此联大一方面函请教育部解决,一方面召开教授会共商办法。在这次教授会上,“经济学教授供给物价的指数,数学教授计算每月的开销,生物学教授说明营养的不足。”王力感慨地说,“可惜文学教授不曾发言,否则必有一段极为精彩动人的描写。”
在这种“不得了”的特殊困难条件下,教授们及其夫人亦各显神通,多方设法,以维持生计。梅贻琦夫人韩咏华自制蛋糕售卖,以赚钱维持生计就是一例。韩咏华回忆,教授们的月薪,多不能维持全月的生活。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拿出去卖。“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好,只能帮助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售。月涵(梅贻琦)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孩子小,有时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的孩子吃。”还有一次,韩咏华还到大西门旁铺一块油布摆地摊,把孩子们长大后穿不上的小衣服、毛线头编织的东西以及他们自己的衣服等,摆出来卖,一个早晨卖了十元钱。
联大生活的艰苦以及梅贻琦一家生活的艰苦,于此可见一斑。即使如此,梅贻琦也绝不利用职权,不多占一分好处,而且还利用职权,不准家属、孩子们去占任何一点好处。
梅夫人的“定胜糕”,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品牌。这个品牌名字曾经叫响了西南联大和昆明城。张曼菱女士在其著述中呼吁,“我以为冠生园其实应该保存这个名牌,永远让人们看到。现在满昆明都是西式糕点,何不留我‘定胜糕’之品位?”
《西南联大掌门人——梅贻琦》
谢本书:联大人的“梅迷”情结
清华人以至联大人的“梅迷”情结,是与梅贻琦人品风格不可分割的。梅贻琦1938年春到达昆明,1946年9月辞别春城,在昆明生活工作近9年之久。他曾坦言这是其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这一时期抗战形势十分艰难,而联大内部事务繁多,又有诸多矛盾,敌机频繁轰炸,正在上课的师生也要不断跑警报,教学秩序维持与安排颇费周章,物价飞涨、经费奇缺带来生死困窘,“党化教育”、政府操控与守护大学本质的抗衡周旋,知识界上层左右分化及伴之而来的学潮汹涌等等。梅贻琦面对着这些复杂纷繁的局面,呕心沥血,上上下下做了诸多艰苦的工作和调解,对左右纷争,学术异见,皆本着“兼容并包”之精神予以对待,使联大得以顺利维系,确实不易。当联大数次被敌机轰炸,“人心惶惶,形势极为危急”的形势下,“在梅先生的锁定领导下,全校师生照常上课,弦诵之声未尝或辍”。1941年后,“在抗日前线仍能照常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和梅先生艰苦而镇静的领导分不开的。”
“梅迷”“无我的梅校长”之声,是与梅贻琦的人品、作为联系在一起的。
《西南联大掌门人——梅贻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