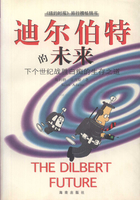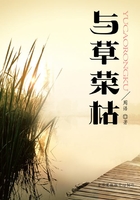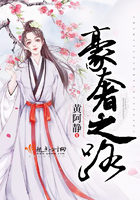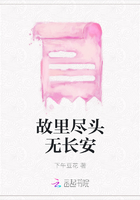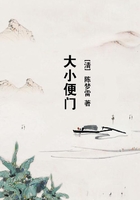丁尼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道理显而易见,他具备的三种品质除了最伟大的诗人外很少有人同时具备:作品众多,风格多样,才能全面。因此,若没有大量阅读他的作品,我们就无法体会其中的妙处。我们有可能不赞赏他的目标:但无论他开始着手做什么,他都会做得很成功,他精湛的技巧使我们产生的信任感是诗歌的主要乐趣之一。他在韵律方面多样化的造诣令人称奇。他熟知拉丁诗律中可以为英国诗人借鉴使用的一切内容,但他不会犯那种用英语写作拉丁式诗行的错误。他说他认为自己知道每一个英语词汇(或许“剪刀”一词除外)的音量,他有自弥尔顿以来英国诗人中最灵敏的耳朵。他是斯温伯恩的老师;斯温伯恩本人是研究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者,但与丁尼生相比,他的诗歌韵律常常显得粗鄙、有时甚至低劣。丁尼生极大地拓展了英语中现行的韵律形式:仅在《莫德》一诗中,韵律的种类就变化多端。但是,衡量韵律上是否创新,不能只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公认的惯例和传统。创新取决于特定的历史境况:在某些时候,一场更为激烈的变革可能比在其他时候更有必要。每一个时期所面临的问题都不尽相同:在有些年代,一场激烈的革命可能既无必要也不可取;在这样的年代,一个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变革就是一个重要诗人所要进行的变革。蒲柏继德莱顿之后所进行的创新可能并不显得多么伟大,但是,一代宗师的标志就是能够进行微小却意义极为重大的变革,就像在另外一个时代,其标志是能够进行激烈的变革,从而使诗歌再次回归传统范式。
有一首只在权威传记中登载过的早期诗歌,已经展现出丁尼生的宗师风范。据记载,丁尼生后来十分遗憾自己将这首诗作从早期作品集中删除;这就是由一些诗歌片断组成的《赫斯珀里得斯》,其中只有《三姊妹之歌》一诗是完整的。这首诗显示了丁尼生的古典学识和对音韵的精通。《三姊妹之歌》的第一节内容如下:
金苹果,金苹果,神圣的果实,
好好守护它,小心守护它,
伫立在神灵佑护的树根旁
快乐地歌唱。
四周一切静悄悄,
犹如山顶的雪原,
犹如山脚的沙田。
咸水湾中的鳄鱼,
沉睡中一动不动,一切静悄悄。
如果你不再歌唱,如果你唱错了节拍,
我们将失去永恒的快乐
活该永远不得安宁。
不要大声笑:请看管好
这西方智慧的宝藏。
智慧在角落里低语。五和三
(不要四处宣扬)是个大秘密:
音乐催生三倍的花朵;
每当新的花蕾绽放,
音乐使树液三倍地流淌,
从树根,
在黑暗中被汲取,
直达果实,
在芳香的树皮下蜿蜒而上,
流动的黄金,彻头彻尾的甜蜜。
目光敏锐的姐妹们,快乐地歌唱,
小心观望
每一个方向,
守护着苹果,不分日夜,
不让东方来的人把它偷走。[1]一个能够这样写作的年轻人没有多少关于音韵的知识需要学习。这个大约在一八二八至一八三〇年间写下这些诗行的年轻人正在尝试某种新的东西,这些诗行中有某种并非来自任何一位前辈的东西。在丁尼生早期的一些诗歌中,济慈的影响显而易见—体现在抒情短诗和无韵诗之中;较不成功的,还有如《朵拉》一诗中所体现的华兹华斯的影响。但是,在我刚刚引用的诗行中,还有《玛丽安娜》诗两首、《海仙女》、《食莲人》、《夏洛特女郎》及其他地方,有一种全新的东西。
这屋子里整日朦朦胧胧,
铰链上的门儿吱吱嘎嘎;
绿头蝇贴着窗玻璃嗡嗡,
朽坏的墙板后耗子叽喳,
有时从裂缝处伸头窥探。[2]
The blue fl y sung in the pane(绿头蝇贴着窗玻璃嗡嗡),一行诗就足以使我们明白某种重要的东西出现了(如果此处用sang取代sung,这行诗就会被毁掉)。
长诗朗诵现今已不大流行,但在丁尼生的时代,这却很容易。因为很多长诗不但被写下来并且还广泛流传;诗歌的水准很高:即使是当时的二流长诗,如《亚洲之光》[3],也比大部分现代长篇小说值得朗读。但是,与其他同时代诗人不同,丁尼生的长诗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长诗。它们在类型上,以他同时代最伟大诗人的最伟大作品为例,有别于《索尔代洛》[4]或者《指环和书》[5]。《莫德》与《悼念》都由一系列短诗组成,而一个诗人有史以来所展现出的最伟大的抒情才华赋予了它们一种形式。《国王田园诗》与《公主》具有相似的优点和缺憾。田园诗就是“描述某个优美场景或事件的短诗”;选择这个名称可能表明丁尼生对自己的局限性有所认识,因为他的诗歌永远是描述性的,而且永远优美生动;它们从来不是真正的叙事诗。《国王田园诗》在类型上与他早期的一些诗歌并无区别,《亚瑟王之死》事实上就是一首早期的诗歌。《公主》依然是一首田园诗,但它是一首过长的田园诗。丁尼生在这首诗中所使用的音韵与其他作品中的一样精湛:这是一首我们必须读的诗,但又是一首我们允许自己不读第二遍的诗。我们一次一次地返回,并且总能被诗中穿插的抒情诗段打动,它们能够跻身所有同类诗歌中最杰出典范之列,但我们却避开这首诗本身,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事实上,并非如我们读诗时可能认为的那样,是诗中对两性关系过时的态度,或是关于婚姻、独身以及女性教育等话题令人恼怒的观点使我们对《公主》一诗退避三舍[6]。如果呈现给我们的是一首激动人心的叙事诗,我们可以容忍最令人反感的信条。但是,丁尼生在叙事上没有一点天分。你只需将他的《尤利西斯》与但丁《地狱篇》第二十六歌中关于同一主人公的凝炼热烈而激动人心的叙述相比较,就可以知晓在表现同一主题时,什么是静态诗,什么又是动态诗。但丁在讲述一个故事,丁尼生只是在表达一种悲伤的情绪。最伟大的诗人呈现给你的是真实的人物在谈话,并且带领你在真实的动态事件中前行。丁尼生根本就不会讲故事。并不是说他在《公主》中试图讲一个故事但失败了,而是这么一回事:一首田园诗拖得如此之长,以致变得难以卒读。因此,《公主》是一首枯燥的诗,那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优美但却枯燥乏味的诗之一。
但在《莫德》和《悼念》中,丁尼生做了每个有自觉意识的艺术家所做的事情,将自己的局限转化为优势。《莫德》由一些非常优美的抒情短诗组成,比如《噢!让这坚实的地面》、《高高庄园许多鸟》以及《欢乐的日子,别离开》,围绕这些短诗,诗人用最精湛的音韵技巧构建了一个戏剧情境的轮廓。整个情境是不真实的:一个濒于疯癫的情人的胡言乱语听起来十分虚妄,而且,就像好斗者的大声咆哮一样,并不能真正使人汗毛倒竖。如果认为丁尼生可能经历过某种与诗中描述相类似的体验,那将是愚蠢的。对于一个有戏剧才能的诗人而言,一种与个体经验迥然不同的情境可能会使他释放出最强烈的情感。我一点也不相信丁尼生是一个情感温和或者说激情不足的人。他的诗中没有迹象表明他体会过对一个女人的激情,但有大量迹象表明他拥有热烈、不羁的情感—但这是一种即使在自己面前也被深深压抑的情感,因此它导向了最深沉的忧郁而非戏剧行动。而且,就我对这些诗的阅读感悟而言,这是一种最终也没有得到彻底净化的情感。我要责备丁尼生的不是他的温和或淡漠,而恰恰是他缺乏平静。
世间难以伫留的爱,
会有怎样的结局?
《莫德》中的情绪强烈但不深切,不过人们在每一个段落都能感受到,诗中的韵律是多么巧妙地随着丁尼生试图表现的情绪而不断变化。我认为,《莫德》作为一部完整的作品所产生的效果之所以表现为软弱无力的激情,源于形式上的一个根本错误。一个诗人无论是采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还是一种抒情化的方式,都同样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但《莫德》既非前者,也不是后者:就如同《公主》既超越了田园诗的范畴,又达不到叙事诗的程度。在《莫德》中,丁尼生既没有将自己设想为情人的角色,也没有让情人的角色等同于自己:结果,丁尼生的真实情感,尽管深厚而热烈,却从未得到表达。
在我看来,丁尼生在《悼念》中找到了最充分的表达方式。仅仅技巧方面的成就已经足以令这部诗集盛名永驻。尽管丁尼生的技巧能力在任何作品中都是精湛和无可指摘的,但《悼念》是他所有诗歌中最无与伦比的杰作。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百三十二个诗歌片断,每一个片断都由几节同样形式的四行诗组成,而内容却从不单调或者重复。这部诗集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理解。我们可能记不住其中的一些片断,我们无法找到一个“适当的样本”;对于一首长度本身即是其根本要素的诗歌而言,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全部。我们也许喜欢记住下面的段落:
昏暗的屋边我再度站立,
站在这不可爱的长街上;
在这门前,往常我的心脏
为等待一只手总跳得急。
可这只手再也无从紧握—
瞧我呀,如今已无法入睡,
却像个可怜东西负着罪,
绝早地悄悄溜到这门口。
他不在这里;但是听远处,
生活的嘈杂声又在响起,
而透过空街上蒙蒙细雨,
茫茫中露出苍白的初曙。[7]
这是伟大的诗歌,语言简练,并且将一种普遍的情感与一个特定的地点联系在一起;它带给我的震动是我在《莫德》中丝毫体会不到的。但是,单独这样一个段落并不是《悼念》:《悼念》是整部诗篇。它是独特的:它是一首由抒情短诗连接而成的长诗,就其完整性和连续性而言,只相当于一部日记,一部由一个男人的自白浓缩而成的日记。这是一部我们一个字都不能错过的日记。
显然,丁尼生的同时代人,一旦接纳了《悼念》,就将其视为希望的讯息和重铸日益衰落的基督教信仰的保证。偶尔,一个诗人由于某种奇特的巧合表达了一代人的情绪,与此同时他也表达了一种离他的时代十分遥远的个人情绪。这并不是缺乏诚挚,而是因为在意识的层面下服从与对抗相互融合。从日常交谈以及他儿子在回忆录中记载的言词话语来判断,丁尼生本人作为一个在记者面前高谈阔论并且经常为摄影师摆姿势照相的公众人物时,在其意识的层面上始终坚持一种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即便他的认识还有些肤浅。他是弗雷德里克·丹尼森·莫里斯[8]的朋友—关于他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比当时的名人之间相互怀有的敬意更加令人称奇。然而,我对《悼念》的印象截然不同于丁尼生的同时代人似乎从中获得的印象,留在我印象中的是一个更加有趣也更为悲伤的丁尼生。畅销传记作家们没有忘记指出,他性情的很多方面有神秘主义者的特点—毫无疑问这根本不是神学家的思维。他极为渴望像一名信徒那样拥有信仰,却不十分清楚他要信仰的是什么:他能够感受某种精神启示,却不能理解它的内涵。《悼念》开篇所吁求的“强大的上帝之子,不朽的爱”与逻各斯或者耶稣基督之间只有一种模糊的联系,那种机械化的宇宙观令丁尼生感到痛心。在哀悼朋友的过程中,他很自然地被永生不死和死后重聚的希望所诱惑。然而,他所渴望的重生似乎至多只是人间友情之乐的延续或者说替代,他对永生的渴望从来就不全是对与神同在的永恒之境的渴望,他所关心的是人的失亡而不是对上帝有所增益。
难道说,人—她最后最美的作品
眼中闪耀着目标的光芒,
建造起徒然祈祷的庙堂,
把颂歌送上冰冷的天庭,
他相信上帝与仁爱一体,
相信爱是造物的最终法则—
而不管自然的爪牙染满了血,
叫喊着反对他的教义—
他曾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
他爱过,也受过无穷苦难,
难道他也将随风沙吹散,
或被封存在铁山底层?[9]
那个陌生而抽象的“自然”在诗中成为一个真正的神或女神,对丁尼生而言,它有时可能比上帝更真实(“上帝和自然是否有冲突?”)。对永生的希望与对这个世界渐进而稳固的进步的希望混为一体(这在那个时代十分常见),关于丁尼生对当时科学发展的关注,以及他对达尔文的印象已经有过很多论述。无论如何,《悼念》比《物种起源》早发表许多年,而对社会民主进步的信念则出现得更早;在我看来,即便达尔文的发现推迟五十年,丁尼生所处的时代对人类进步的信念也会同样坚定。毕竟,两者之间在逻辑上没有必然关联:进步的信念当时已经十分流行,达尔文的发现是被套在这个观念上的。
不再与野兽近乎同宗,
因为我们所想,所爱,所做,
所希望,和所承受的一切,都是
蕴含花朵和果实的种子;
而那个人,那个曾和我一起
在这个星球上行走的人,是一个高贵的类型
在时代尚未成熟前出现,
我那位朋友与上帝同在,
那个永在的、永爱的上帝,
一个上帝,一个律法,一个自然,
一个遥远的神圣事件,
整个造物都向此而行。
这些诗行表现出一种有趣的妥协,在宗教态度和与之截然不同的对人类日臻完美的信念之间的折衷。但是,两者之间的反差对丁尼生的同时代人来说并非那么显而易见。他们可能被蒙蔽了,但我认为丁尼生本人并没有,事实上:他的感情比他的思想更诚实。在其他一些地方—甚至在一首早期诗歌,如《洛克斯利堂》中,也有证据表明:丁尼生绝没有沾沾自喜地看待工业主义的进步以及商业、制造业和银行阶层崛起过程中在他周围发生的那些变化;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英国未来的思考可能带有越来越多的悲观色彩。在性情上,他与自己受到外界影响而接受并颂扬的信条是对立的。
丁尼生的感情,如我所说,是诚实的,但它们通常深藏在表层下面。《悼念》,我认为,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作宗教诗歌,但并不是由于那些令它在诗人的同时代人眼中显得十分虔诚的特质,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它的虔诚并非源于其所表现出来的信仰品质,而是来自怀疑的品质;它的信仰是一个可怜的东西,但它的怀疑却是一种强烈的体验。《悼念》是一首绝望的诗,但这是一种宗教性质的绝望。用形容词“宗教的”对诗中的绝望情绪加以界定,就将它提升到一个大多数模仿者无法比肩的高度。因为,《暗夜之城》[10]和《什罗普少年》[11]以及托马斯·哈代的诗歌与《悼念》相比,都显得无足轻重:它比它们更伟大并且涵盖了它们。[12]
在本文的结尾部分,我们必须回到起点并且记住,如果没有技巧上的成就,《悼念》不会是一部伟大的诗作,丁尼生也不会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丁尼生是音韵大师,同时也是表现忧郁的大师;我认为,任何一位英语诗人都不曾拥有如他一般对元音极为灵敏的耳朵,以及对某些痛苦情绪精细入微的感受:
亲昵得有如死后仍难忘怀的吻。
甜蜜得像无望中假想的吻—印在
留待他人的嘴唇上;深沉得像爱,
深沉得像初恋,绵绵的悔恨难耐。[13]
丁尼生技巧方面的天分绝非微不足道的小技。丁尼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已经具有强烈时间意识的时代:许多事情似乎正在发生,铁路正在兴建,新发现层出不穷,世界的面目正在改变。那是一个忙于与时俱进的时代。多数时候,它无法把握永恒的事物,无法把握有关人、上帝、生命以及死亡的永恒真理。外在的丁尼生随着他的时代一同悸动;除了对语音独特而准确的感觉,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牢牢抓住。但在这方面他有任何人都不曾有的东西。外在的丁尼生,他在技巧上的成就,与他的内里紧密相连:在丁尼生身上,我们最先看到的是那些游弋于表层与内里之间的东西,无足轻重的东西。只有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待表层的东西,我们才最有可能进入到内里深处,进入到深渊般的悲伤之中。丁尼生不只是一个二流的维吉尔,他与但丁眼中的维吉尔同在,一个身处幽灵之间的维吉尔,他是英国诗人中最为悲怆的一位,跻身于地狱之边的伟人之列,一个最本能的社会叛逆者,尽管这个社会的一切习俗他都奉行不悖。
随着《悼念》的完成,丁尼生的精神发展似乎到达了终点;随之而来的既非和解,也非决断。
现在不会再有木杖开花的奇迹,
也没有合唱团的颂歌照亮
一个在衣香鬓影的甜蜜夜晚备感厌倦的灵魂[14]
更准确地说,是暮霭时分,因为丁尼生在晚年面对的既非黑暗也非光明。他的天才和技巧能力延续到最后,但他的精神却已屈服。一个比波德莱尔更加悲哀的结局:丁尼生没有singulier avertissement[15]。他从暗夜之旅抽身而去,变成一个为自己的时代歌功颂德的肤浅恭维者,为此,后来的时代报之以轻蔑,一个与他的时代一样浅薄无知的时代。
金冰 译
注释
[1]本段诗歌中“活该永远不得安宁”一句采用北塔的译文。
[2]以上黄杲忻译。
[3]The Light of Asia,英国诗人阿诺德(Edwin Arnold,1832—1904)的叙事诗,叙述了释迦牟尼的生平和学说。
[4]Sordello,英国诗人勃朗宁的叙事诗,叙述了十三世纪意大利游吟诗人索尔代洛的生平。
[5]The Ring and the Book,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长篇叙事诗,讲述了1698年罗马的一起谋杀案的审判。
[6]关于维多利亚时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以及丁尼生可能认同的观点,参见准男爵爱德华·斯特雷奇(Edward Strachey,1858—1936)为自己所编辑的马洛礼(Sir Thomas Malory)著《亚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删节版所作的序言,这个版本现在依然十分流行。爱德华爵士十分推崇《国王田园诗》(Idylls of the King)。—原注
[7]以上黄杲忻译。
[8]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1805—1872),英国神学家。
[9]以上飞白译。
[10]The City of Dreadful Night,苏格兰诗人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1834—1882)的代表作。
[11]A Shropshire Lad,英国诗人豪斯曼(A.E.Housman,1859—1936)的诗集。
[12]还有其他类型的绝望情绪。戴维森(John Davidson,1857—1909)的伟大诗歌《三十先令一星期》(Thirty Bob a Week)并没有效仿丁尼生。但另一方面,除了《阿塔兰忒在卡吕冬》(Atalanta in Calydon),还有其他作品受到丁尼生的影响。比较一下威廉·莫里斯的诗歌与《梅尔顿之旅》(The Voyage of Maeldune),还有《兵营谣曲》(Barrack Room Ballads)与丁尼生晚期的几首诗歌。—原注
[13]以上黄杲忻译。
[14]这几段诗行来自斯温伯恩为悼念波德莱尔而创作的挽歌《颂赞与告别》(Ave Atque Vale)。
[15]法文,怪诞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