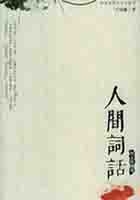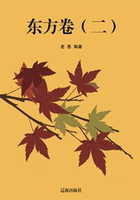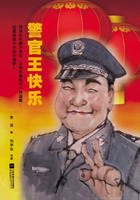《歌经标式》、《文镜秘府论》与歌论的产生——纪贯之、公任与心·词·姿的提出——俊成、定家与“有心论”的歌学思想——歌学体系化与观念形态的文学思潮的完成
日本歌论产生的源头,是《万叶集》的批评意识和文学意识。文学思潮又与歌论相伴而生。所以探讨日本古代文学思潮,不能不从日本歌论的产生开始。
如上章所述,古代前期,即奈良时代,《古事记》序已触及“词不逮心”这样一个心与词的关系问题,同时又提出“夷曲”、“返歌”、“情歌”,或“思乡而作”、“好泣作歌”或“本岐歌”(酒乐歌)、“宇岐歌”(斟酒歌)、“天语歌”(颂歌)等等类别。《怀风藻》序对诗的编纂精神以及山上忆良的《类聚歌林》等也含分类整理的意识,但未明确提出分类法。至《万叶集》的编纂显示出明确的歌的分类法,产生了批评意识和文学意识,但它的论述是零星的、一言半语的,都未能作为歌论立言,不能说是成型的歌论。但它却催促着歌论的诞生。《歌经标式》就是在它们对歌的零星议论的基础上发展为准歌论而走向最初的成型。
《歌经标式》成书于《怀风藻》、《万叶集》之后,是藤原浜成奉敕而作的。所谓“歌经”即歌之经典,所谓“标式”即歌的规范。它是主要讲作和歌的规范,可以说,这是日本最古的歌学书。现存真本与抄本两种。抄本是平安时代后期根据真本抄出的。抄本省繁从简。
《歌经标式》引进中国诗学,并结合和歌存在的问题,提出歌病七种。其所引用的歌例,不少是出自万叶歌,尤其是山部赤人、柿本若子、高市黑人等的歌。但是,它不像中国诗论那样以歌病论为主要内容,而着重论述歌体,提出求韵体(论歌格)、查体(查有缺陷的歌体)、杂体(议有优点的歌体),三体中偏重“杂体有十”,即“雅体别有十种”,主要从美的内容出发,有意识地将歌划分品等,探讨个体的相互关系。这说明和歌开始含有价值的因素,并在其价值框架内规范其歌的优劣,即规定歌品的基础。具体地说,《歌经标式》正文论述声韵、形态和表现三方面的歌学技术性问题。其中以声韵作为中心课题,尤以短歌的音韵论为重点,强调韵是歌的核心部分。但是,日本的歌不像中国诗那样关心脚韵,相反是重视头韵,所以中国诗的脚韵论对日本的歌实际影响不大。在形态论方面,它提出短歌“以五句为一绝。第三终字为一韵,第五句终字为终韵”,这对于和歌的定型化起着理论上的指导作用。在表现论方面,涉及表现内容和表现技巧问题。比如提出雅丽、妙佳二体为最高级的体,并由此派生出比喻与实体等涉及和歌思想和方向的问题。
《歌经标式》的序跋集中论述歌的意义、起源、功能及当时歌的状况等带理论性的问题,归纳如下几点:
(一)提倡歌的社会功能及意义的重要性,指出“原夫和歌者,所以感鬼神之幽情,慰天人之恋心者也”。且“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和歌”。它强调了歌可以起到“动”、“感”、“慰”的教化作用,这是具有道德伦理价值的。
(二)赋予歌以艺术的意义,提出要达到“动”、“感”、“慰”的教化作用,还在于“乐”,说:“韵者,所以异于风俗之言语,长于游乐之精神者也。”“功成作乐,非歌不宜。理定制礼,非歌不惑”,这样给歌以艺术的定位,较之于上代仅仅将文学作为政教伦理的工具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同时它强调“制礼”,以此作为其论歌作用的基础,触及乐与礼的问题,即感情表现与伦理道德的“善”(制礼)的问题,发展了上代歌的单纯感情表现的认识,而指向某一目的的追求。也就是说,开始涉及艺术所表现的感情与道德的感情关系问题,就是美善的问题。
(三)阐述音韵的特殊性,说:“尽雅妙,音韵之始也”,指出当时“歌人虽表歌句,未知音韵,令他悦怿,犹无知病,准之上古,既无春花之仪,仿之来叶,不见秋实之味。何能感谢天人之际者乎”。也就是说,歌的音韵在达到歌的美与善统一方面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如果不知音韵,就犹如春花之不美,秋实之无味,为此主张“建新例”,“抄韵曲”。
(四)说明歌的艺术本质是心与志、心与词的关系问题,“夫和歌者,故在心为志,发言为歌”。它一方面述说“歌含志”的命题,一方面又注意通过“心”来摇荡“志”,将志与心联系起来,歌是心中情感的表现,比上代对歌的艺术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五)主张歌“专以意为宗,以不能以文为本”。所谓“意”者,情意也、事物之内容也。所谓“文”者,文辞、文句也。意与文的关系,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强调了歌应以“意”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美作为前提条件,同时不能以虚伪的文饰,否则“其病未能免”。也就是说,注意到意与文对立的一面,初步概括了文学论的一般的艺术要求。
但是,还有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留待后起的歌论深入探讨,比如,如何把握歌的道德伦理价值,如果过分强调,有可能束缚和歌艺术的感情表现,妨碍刚刚萌芽的个体意识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对艺术所要表现的心的内容,以及心与志的对立与统一的关系没有进一步作出具体的解释;对“意”与“文”相统一的一面没有进一步探讨,更没有解决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这个讨论只有随着歌论的完成,在歌学体系化的过程中展开。
从总体来说,《歌经标式》朴素地接受了中国《毛诗序》有关志情统一的讨论和诗感化作用的“六义”的潜移影响,以及以中国《诗品》的美学思想“文情理通”、“文能达意”为鉴,但又突破《毛诗序》以诗直接作为宣传政教伦理的狭隘的诗学思想,以自己的思想表达方法强调了“心”在歌的中心地位。这说明它在心与志、情与文上吸收中国诗学思想,又不受其束缚,对于内在的——日本古代文学一贯追求的心的“真实”即“真心”,表现出异常的关心。应该说,显示出其重精神甚于咏物的倾向。它对于古代歌学以主情思潮为主体起到了前瞻性的作用。
继《歌经标式》之后,喜撰的《倭歌作式》(亦称喜撰式)、孙姬的《和歌式》(亦称孙姬式)、《石见女式》等都沿着《歌经标式》的基本轨迹运作。但平安时代初期,日本盛行汉诗文,撰定《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不仅出现汉诗文一边倒的倾向,而且宣扬了“文章者经国之大业”的观点,强调诗文是政教的工具。在此前后留唐僧空海回国,应当时的歌坛要求,将《唐朝新定诗格》、《诗格》、《诗髓脑》、《诗议》等诗学书,排比编纂了《文镜秘府论》。作者以该书“披咏梢难记”为由,将其缩写为《文笔眼心抄》,以达“文约义广,功省蕴深”之效。
《文镜秘府论》重点地讲述声病对偶、辞藻典故等技巧性问题,其诗学思想内容则主要放在“论文意”、“论体”上。
首先,阐述诗的社会价值,详尽地引用《毛诗序》的“动”、“感”作用之后,强调“经理邦国,烛畅幽遐,达于鬼神之情,交于上下之际,功成作乐,非文不宜,理定制礼,非文不载”。即要求诗具有道德感及其审美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艺术在伦理道德上的作用。具体地说,以乐为中心来发展诗的情感表现。
其次,提出心、词的关系问题,说:“诗本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因此,“夫文章兴作,先动气,气生乎心,心发乎言”,“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攒天海于方寸。诗人用心,当于此也”。这一方面吸取儒教“诗言志”的思想,一方面又倡导歌的言情作用,将情、志、心、气结合,发展了上代的歌论。
再次,论述“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辩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构建了意+声=格律的歌学方程式。
《文镜秘府论》实际上是专论中国六朝的诗学,内中加以扬弃取舍,集中强调了两点:一是“诗可以兴,可以观”;二是“体韵心传,音律口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在“帝德录”中强调诗之功能乃“叙功业”、“叙礼乐法”、“叙政化思德”、“叙天下安平”、“叙远方归向”、“叙瑞物感致”,它几乎将中国六朝诗学原原本本地搬到歌学论上来,并宣扬了儒佛文学思想。这一时期,即奈良时代末期、平安时代初期,汉诗文压倒一切,和歌衰微,《歌经标式》的影响缩小,许多歌论都模仿《文镜秘府论》。可以说,它是在这个汉诗文一边倒的形势下的产物。正如加藤周一指出的:“空海的哲学思想,在拒绝佛教‘日本化’、彻底贯彻其彼岸性、克服土著世界观方面,是划时代的。”[8]
在儒佛思潮的冲击下,日本诗界致力于诗文的“日本化”,以期对汉诗文一边倒的反拨。这时(公元894年)也正好废止遣唐使。菅原道真的《菅家文草》(900)等就是于汉诗文加入平安时代的审美意识而使之具有日本特色的一种努力的尝试。他在《新撰万叶集》(913)序中提出花实对称的问题,说:“以今比古,新作花也。”他在《菅家遗诫》中将这种努力精当地总结为“和魂汉才”,将日本本土的精神与中国诗学融合,也就是说,强调了以日本本土精神来活用从中国引进的学问的重要性,使外来文化“日本化”的重要性。永田广智从哲学思想的角度论述这段历史时指出:“这些思潮由于与日本原有的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就不能不发生调和变形。表现在各种形态和方法上的神佛调和、神儒调和,以及神儒佛老调和就是典型,而且是最大的变形。”[9]我们从平安时代中期之始的《古今和歌集》及其汉文序和假名序的异同中就不难发现这一思潮的发展趋向。
《古今和歌集》是抓住和歌中兴的机遇而撰定的,其序成为歌论成立以及渐次将歌论“日本化”过程的重要一环,在和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古今和歌集》的假名序作者是纪贯之,汉文序的作者有二说,一说是纪贯之作,纪淑望汉译,一说是纪淑望作。两序都涉及和歌的本质、功能、风格、内容与形式等歌论的基本问题,以及和歌发展史、和歌编纂等问题。在此之前,以《万叶集》为代表的和歌(当时称作倭诗,至《古今和歌集》始称“和歌”)大多以“心”为主导的文学精神,主要是个人感情的朴素表现,如山上忆良之强调“写五脏之郁结”,大伴家持之强调“以散郁结之绪耳”等,都是以歌作为抒发感情的手段,以获得一种慰藉。所以万叶歌只有少数属于道德教化的咏物歌。但受汉诗的刺激,《古今和歌集》的汉文序就逐渐看重歌的政教作用,强调了“词”,序中写道:
感生于志,咏形于言。是以逸者其词乐,怨者其吟悲。可以述怀,可以发愤。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和夫妇,莫宜于和歌。
皆是以动天地,感鬼神,厚人伦,成存敬,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虽诚假文于绮靡之下,然复取义于教诫之中也。
汉文序这种以“述志为本”,即以教诫作为和歌的思想机能,无疑是借用中国诗论的传统思考方法,根据中国诗学儒教道德和政治思想来判断和歌的优劣。以务虚为主。但是,假名序“以心为本”,并无如此着重强调歌的社会意义和道德感化作用,而且有意识淡化儒教的文学思想,尽量以日本固有的文学思想加以制约,或以日本固有美学用语加以解释,且多务实。
首先,以两序开篇明义之句的异同来比较。
汉文序:
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发其花于词者也。人之在世,不能无为。思虑易迁,哀乐相变。
假名序:
夫和歌者,以人心为种,以千万词为表现。世人遭逢种种事件,做出种种行为,其心必有所思,辄发为语言表现者也。
汉文序一般地提及歌是根于心而发于词,心是通过词来表现的。假名序则将“心”与事件、行为有机联系,将“心”所思与所见所闻有机结合,即将“心”的“真实”作为歌论的重要命题,在以“心”的表现作为歌的第一义的前提下,主张“心”与“词”的合成关系。在纪贯之看来,“心”的本质就是“真实”。在这个意义上说,假名序的思想基础是“真实”的文学思想,即是原初的朴素的写实思想。这是日本古代“真实”和“有心”的文学思潮的发端。
其次,以两序对六歌仙的批评之异同来比较。
汉文序:
僧正遍照 然其词甚花而少实。
在原业平 其情有余,其词不足。
文屋康秀 文巧咏物,然其体近俗也。
喜撰法师 其词华丽,然首尾阻滞。
小野小町 然艳而无气力。
大伴黑主 颇有逸兴,然体甚鄙。
假名序:
僧正遍照 然得歌体,其真实少。
在原业平 其心有余,其词不足。
文屋康秀 其词巧妙,其体近俗。
喜撰法师 其词隐约,然首尾确实。
小野小町 然哀而不刚强。
大伴黑主 其体甚卑。
两序都重视歌的心与词的要素,对六歌仙的批评,或以心为中心,或以词为中心,或以心词调和为中心作为歌的批评基准。然而在解释上,两者存在微妙的差异。汉文序用“实少”并非认为是致命弱点,而其重点是放在开头的心词关系上。这里的“实”,没有用日本固有用语“真实”,明显地受中国《文心雕龙》的华实论的影响。假名序用“真实”,不仅包含“实”所指的歌内容的政教机能,而且指相对于词的“心”而言,指“心”的“真实”。即重点强调歌以“真心”的表现为主。比如,假名序批评在原业平时用“心”有余,而汉文序用“情”有余,日文的“心”与“情”基本相通,汉文却存在某些差异。所以两序中的“情”限于指感情,而心则是知性、感情、意志的总体,不仅含感情的内容,而且具观念的内容,即精神的作用。再比如,假名序批评小野小町时用“哀而不刚强”,汉文序则用“艳而无气力”,一“哀”一“艳”,反映了不同的审美范畴。假名序用“真实”、“哀”、“心”作为批评的基准,无疑是根植于本土的文学精神和审美价值取向的。
再次,以两序对六义的表达方法之异同来比较。
汉文序:
和歌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假名序:
和歌有六体,即讽歌体、数歌体、准歌体、譬歌体、真言体、祝歌体。
汉文序关于和歌六义无疑是直接照搬中国《毛诗序》的六义,前三者是概括不同的内容分类,后三者是说明不同的表现方法,但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说。中国的《毛诗序》提出的六义,着重讲其感化作用。比如,日本学者解释时特别强调“风”指“风俗歌”,乃“教”也。“雅”指宫廷歌,并含伦理性、政教性的解释。假名序相当于“风”义的是“讽歌体”,是指讽喻,间接表现的歌体;相当于“雅”义的是“真言体”,即是从“真实”的“心”出发,强调“真心”的风雅之幽玄性,直接表现的歌体。汉文序与假名序对六义、六体的表述,不仅是文字上的不同,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差别。后者所作出的自己的解释,给予和歌以本质的意义,为以幽玄为中心的风雅文学论的生成播下了种子,至中世确立了“雅”的表现世界,酿成以幽玄为主的文学思潮。
尽管两序都接受中国六朝诗学的影响,但假名序存在某种对中国诗学的抗拒意识,很少盲目借用中国诗学的思考方法,或单纯剪裁中国儒教的文学思想,而且更多的是有意识淡化中国诗学的影响,强烈地表现日本意识,出现企图酿造独立的和歌思想的倾向。可以说,两序发表了对文学思想的有机的折中性的见解,这种见解具备歌论的形态,各自从抽象论和具体论的不同角度,开始建立和歌的理论体系。其后的歌论继承这一传统,它们成为日本歌论、歌学的基础理论。
平安时代中期,壬生忠岑的《和歌体十种》(945)提出和歌的最高样式是“高情体”,其他九体也有高情的素质。他特别说明:
此体词虽凡流,义入幽玄,诸歌之为上种也,莫不任高情。仍神妙、余情、器量皆以出是流。而只以心匠之至妙,难强分其境。待指南于来哲而已。
他强调了“高情体”的特征是“义入幽玄”,与余情混其流而进入高情之境,才能成为上品之体。重“幽玄”与“余情”的情趣性与情调性,开始触及和歌的根本文学思想。
作为占当时文学思想指导地位的藤原公任,在前人树立“心词”合成概念的基础上导入“姿”的概念。他提出“心姿相具”的论点,成为歌论史上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歌学思想的原型之一,对于深化歌论、歌学的理论起到很大的作用。他的《新撰髓脑》(年代未详)和《和歌九品》(约1009)就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歌论、歌学的水平和文艺思想。日本古代这一时期,文学思潮已经确立了以“物哀”文学思潮为主潮,这点将在下章论述。这里只着重论述藤原公任发展了纪贯之的“心·词”的观点,调和心词,追求余心,但作为整体是以“物哀”的美感为中心。他的“余心”,产生了新的文学思潮。
在《新撰髓脑》中,他写道:
反歌者心深姿清,应以心有奇处为优。……心姿相具难,则应先取心。心终不深,则应安姿。
他从秀逸之歌必须“心姿相具”来说明两者的辩证关系,强调如果两者兼备有困难,则以心为先,但心不深,不如安姿。在作者看来,心是感情的主体,是构成和歌之美的主要条件,词是和歌的物质素材,词被组合成和歌的形就是“姿”。如果只寻求心或仅作为语言的素材的词都是不够的,所以必须导入由词构成的形——姿。这样具备心深的条件,以及表现上的姿清的具体形态,才能创作出秀歌来。所以他将歌的“姿”作为心与词不可分割的整体形象。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使用“心”的词最多,“姿”的词次之,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公任在《新撰髓脑》中还强调了心、词、姿的复合,达到“余心”的境地,“余心”是以“物哀”的“余情”的美理念作为中心内容的。他的和歌品等就是以“余情”作为基准的。《和歌九品》将和歌划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为三级,合称九品。九品的要点是:
上品上 词妙而有余心也。
上品中 端丽而有余心也。
上品下 虽心深不足然有趣也。
中品上 心词畅达而有趣也。
中品中 平庸而知风体也。
中品下 少有所思也。
下品上 仅有一趣向也。
下品中 不知词之心鄙也。
下品下 词滞而无趣也。
从上述品等分类可以看出,藤原公任的歌论的基点是以心与词调和为中心,将词表现看作是一种手段,而表现的源泉就是心。特别是重视“余情”的“心”,成为“物哀”的依托。
从纪贯之的“心、词合成”到藤原公任的“心、词、姿复合”的“余心”,对于始自平安初期产生的“赛歌判词”的逐渐完备影响是极大的,其判词的基准就放在“心”上。平安时代中后期,歌论出现革新与保守的倾向,也是围绕对“心”的认识表现出来。比如,藤原义忠遵循贯之、公任的歌论,偏重歌的艺术意义,其判词以“心”为重点,可以举出其见解有:“不知歌旨之心”、“具备歌旨之心”、“深心”、“心态”、“心高”、“心有余”等等,而藤原资业等则继承纪淑望的教诫意识,强调“世治者此兴起,时质者此思切。故感动神明。交和人伦,莫近于斯矣”。在歌论中,藤原亲经的《新古今和歌集》序(1205)也将和歌作为“理世抚民”,“治世和民之道”,其后他在《闲吟集》序(1518)中更明确歌者乃“伸数奇好事,喻三纲五常”。可以说,当时虽然尊重“心”、“余心”的艺术表现论占据着和歌美学的空间中心位置,但并非无相反的论点,即并非无偏重从儒教的政教立场来对待和歌的。这两种歌学思潮在互相交织又互相抗衡中向前潜流。前者成为主流,对歌论和赛歌判词的基准起到了固定传统的作用。可以说,平安时代后期开始,歌学思潮渐渐转变方向,更明显地从儒学思想摆脱出来,并扩大了佛学思想的机制,以后经过13世纪至16世纪镰仓、南北朝、室町诸时代,佛学思想占主导地位达四个多世纪之久。这一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歌论从重“心”、“余心”发展到“有心”,演化为“幽玄”的象征的表现,最后树立“幽玄”文学思想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藤原俊成、定家父子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藤原俊成在《赛歌六百首》(1193)等二十多种“赛歌判词”中更加突出“余心”,提出“应以心为本,进行词的选择”,同时“心词深,愚意难得”,“不饰文化,偏全义实”(这里的“实”也是指“心”的“真实”)。而且他强调作为赛歌的歌,应以心词综合的姿为重,主张“幽玄”之境在于姿。比如,在《圣真子·九首》的赛歌判词中写道:“心词幽玄之风体也”,“姿、心均宜为胜”。他的赛歌判词反复地使用了“幽玄”这个词。尽管这个词是藤原基俊在品定和歌优劣时开始使用了,但藤原俊成第一次以“余情幽玄美”作为和歌的最高的美的基准,含有一种朦胧和悲哀的美感。
他在《古来风体抄》序(1197)中分析了“余情幽玄”之思想缘于佛教文学思想:
世人只知歌易诵,根本想不到歌竟如此之深奥。……随时代嬗变,姿、词也有新的变化,应从细枝末节来论述历代撰集之所能看到的。如此,难以说明歌的心、姿,特别是佛道微弱,依靠佛经陈述,为我之事就太粗杂矣。
根据佛道修行与歌的深刻意义,悟到佛经之无尽,同极乐往生结缘,入普贤之愿海,以换此咏歌之词,赞奉佛,听佛法,参拜普度十方之佛土,首先应引导俗世众生。
藤原俊成所处的平安时代,贵族社会开始盛极而衰,作为古代文学的主力——贵族阶级深感人生无常,在无常中寻求永恒的人生观占据主导。因此,佛教文学思想对于歌论、歌学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从上述的见解可见,他关于歌的心、词、姿所追求的目的,与佛教文学思想紧密相连,成为正式将“幽玄”作为和歌一体的依据。可以说,以“幽玄”作为美的基本理念,这是与当时的佛教文艺思潮息息相通的。
与藤原俊成提出“幽玄美”的同时,鸭长明在《无名抄》(1216)中也强调了幽玄美,而且做出“幽玄美”是含蓄之美的解释,说:
总之,幽玄体不外是意在言外,情溢形表,只要“心”、“词”极艳,则其体自得。
镰仓时代初期,藤原定家在这一文艺思潮的引导下,尝试进一步对歌论、歌学进行理论的思考和概括。他的《近代秀歌》(1209)、《咏歌大概》(1213-1218)、《每月抄》(1219)等促进了歌学体系化,并且形成歌学传统而流传下来。
《近代秀歌》详细叙述了纪贯之、藤原公任、藤原俊成以来的心、词、姿、体的特色之后,提出了“词慕古,心求新”的主张,《咏歌之大概》提出:“情以新为先,求人未咏之心咏之,词以旧可用,词不可出三代集[10],先达之所用新古今古人歌,同可用之。风体可效,堪能先达之秀歌,不论古今远近,见宜歌可效其体,近代之人所咏出之心词,虽为一句,谨可以除弃之。”两文都强调“词”可以慕古,可以旧用,因为词经过历史的洗练,与古典有其连续性,而“心”是指歌的素材、内容、风情乃至余情,因此需要具有新的意义,即赋予“心”以新的存在意义。所以歌人必须“深通和歌之心”。
藤原定家在《每月抄》中对上述问题作了更为深入和系统的论述,提出“有心体”作为艺术美的最高价值。
(一)强调“有心体”的重要性,和歌“以心为本”,最高的美的境界在于“有心”。他分析从《万叶集》到各种敕撰集的风姿变迁时,批评许多不应入歌的“词”与“姿”过于近俗,而提出和歌十体,应“以幽玄体、会心体、丽体、有心体为主”,这四体为基本歌体,但尤应以“有心体”为核心,其他九体也必须“有心”,而“有心”是指余情的心,是情调性的、含蓄的表现,具有内涵丰富的意象,从而创造一个神秘的、超现实的象征世界,文章写道:
和歌十体之中,再没有比有心体更能代表和歌的基本精神,而且非常难以领会贯通。只是马马虎虎地胡乱吟咏几首,是不可能咏出这样的歌。因此,所谓秀逸之歌,是整首都有“深心”之谓。……我认为应当尽可能采用有心体,因为不用此体,则绝对咏不出好歌来。同时,这个有心体又可以概括其余的九体,因为幽玄体中亦需要有心,长高体中亦需要“有心”,其余诸体,也是如此。因为任何体假如“无心”,则只能是拙劣的歌。现在,我在十体之中所以特别提出有心体,是因为其余各体不以“有心”为它的特点,而用心体则专以“有心”为主进行咏歌的缘故。其实,对各种歌体,都应当认为是“有心”的。
(二)主张歌的重要的一点,是解决“心”与“词”的关系,应当充分认识“词”的性质。但他又强调“心”、“有心”,并非全然无视“词”,“心词相兼”最好,否则宁可“词”稍差些而不可缺少“心”。文章写道:
所谓以“心”为先,也就等于说可以将“词”看成是次要的;如果认为应该专注意“词”,那也就等于说“无心”也可(这种说法都是不完全的)。总之,能够“心”与“词”兼而有之,那应该说是最好的歌。应该将“心”与“词”看成是如鸟之双翼,如能“心”、“词”兼顾,自然再好不过,否则,与其缺少“心”,毋宁在“词”上稍差一些。
(三)提出和歌继承“幽玄美”的同时,触及“物哀”的文学美理念。文章写道:
我们要了解和歌是日本独特的表现形式,在先哲的许多著作中都提到和歌应当咏得优美而富于物哀。不管什么样可怖的东西,一咏进和歌里来,听起来便感到优美动人。
作者虽然没有就“物哀”的本质进一步阐述,但他在赛歌判词中也常用“哀”的评语,足见“哀”、“物哀”已在他的歌学理论中开始占有了位置,以及他所追求的和歌的艺术美的完成。尤其是从代表他的上述主张的《新古今和歌集》的歌风来看,他的以“有心”之余情为根底的“幽玄”与“物哀”,是具二元性的,即带有象征的情趣性和浪漫的情调性(感伤性)的二元性的。
鸭长明在《无名抄》里划出了日本古代歌论和古代文学思潮这样的完成轨迹:
至万叶时代,只陈述心志,未必不选择词、姿。至古今时代,如入花、实,其体各异。后撰时代有宜歌,始着手搞古今,之后不久,难以为歌,就不选择姿,而首先表现心。拾遗时代开始,其体接近物,明确知性的表现,以姿、实为宜。
可以说,“《无名抄》显示了长明的观察力,他注意到心与词的关系,从以心为先的《万叶集》到以心词调和为旨的《古今和歌集》、《后撰和歌集》(951年开始)打破这种调和,再到心本位,《拾遗和歌集》(1005-1007)又再次回到心与词的调和,来说明以心为主和心词调和交替发展,划出了歌论的发展轨迹。所以尽管这里只论述《古今和歌集》以后的变迁,但可以认为依从长明的看法是贤明之策”[11]。
从日本古代文学意识的萌芽到文学思潮完成的过程,实际上是日本古代文学以心为主体,心词调和交替发展的过程,也是按照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走向,从中国诗学“言志”的功利意识摆脱出来,向以审美为主的转化,它们在歌学体系化的全过程中,培育着古代文学生命体的以“心”、“有心”为基本内容的“真实”、“物哀”、“幽玄”等文学思想基因,催促着古典的写实、浪漫、象征三大文学思潮以观念形态的形式诞生,并独具日本性格的特征。日本古代文学思潮从而走上完成、发展和成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