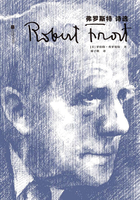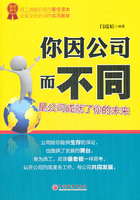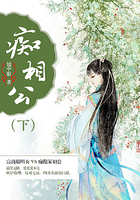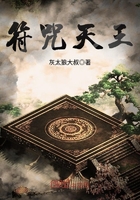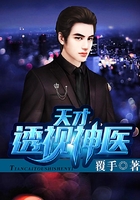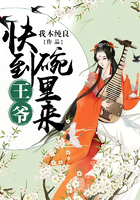古代篇
历史、风土与古代政治经济形态和文化宗教形态——民族的基本性格特征——民族性格与古代文学意识的特质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由于受到不同的历史、风土、社会的条件和文化宗教形态的影响,形成各自不同的国民性格以及相应的文学意识和美意识。即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基本性格和特殊的文学精神及审美情趣。同样道理,同一民族由于生活在同一历史、风土和社会条件及文化宗教形态的影响下,这些相同的诸因素的综合作用,渗透到民族的文化心理,铸造出其共同的基本性格和心理素质,育成其传统文学思想和审美意识的共同属性。在未分化为阶级之前,同一民族具有相同的性格特征,又成为其共同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意识形成之源。而且它们具有相当长远的延续性、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基本性格及其共同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意识的形成,是经过悠久的历史、风土和复杂的环境,包括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铸造,与文化宗教形态的构成和发展同时构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考察日本文学思想、思潮及其源流美意识,离不开民族性格及其形成的历史、风土的基本要素。
远古以前,日本民族在远东一隅的列岛繁衍生息。关于它的历史,有许多古老的神话和历史传说,这些神话和历史传说大多是与日本的国土、皇族和民族的由来联系起来,如《古事记》所记述的神代之初,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男女两神奉天神敕令,从天上下凡,生产日本诸岛和山川草木,再生下支配这些岛屿与天地万物的天照大神、八百万神。历史传说的日本民族以太阳为始祖,是太阳民族。所以古代日本人认为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是天孙的民族,日本皇帝是天皇。而且在他们编造的神话中,天照大神统治下的八百万神都是忠义之神,他们没有对天孙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也没有夺取其国土的欲求,都是归顺天孙,忠于天孙的事业。八百万神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争夺,更没有发生什么战争。缘此日本文化很少英雄神话,也很少英雄神。如果有英雄神的话,也是悲剧英雄的挽歌。日本神话中的天照大神是非常温和的,八百万神也是非常温顺的,没有像外国神话那样将太阳神作为勇者,专治各种妖魔鬼怪,或者各种妖魔鬼怪囚禁或杀害太阳神。总之,日本神话很少出现激烈的行动,一般都是平和的。自古伊始,日本人的原始感情非常崇拜为他们开天辟地的太阳神,进而崇拜太阳神的御子孙,即作为先祖的天皇。在日本人眼里,天皇是“カミ”,即是神,是至上的,意指天皇在一切之上,高于一切,且认为天皇比佛还善,所谓“佛九善而皇十善”,天皇是十全十美的,后来被完全神化了。这些神话和传说,以及其后的文学艺术,反复地渲染这一主题,充分地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原始心理特征,而且对后世日本人的影响是深远的。
事实上,日本的国土和民族,同其他的国土和民族一样,无疑是按照自然界和人类发展历史的自然规律诞生的。但在社会环境尚未确立其政治经济形态之前,日本人的原始性格的铸造和原始的文学意识、美意识的形成,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的生活在其中的历史和风土,包括地理位置、季节时令和其他自然条件,而且这些因素基本上固定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是在亿万年缓慢地进行,这是自不待言的。
日本位于亚洲最东部,回环着浩瀚无际的大海,处在孤立之境。土地面积70%是山地,30%是平原。没有荒漠,更没有大荒漠。在日本列岛上,山岭绵延不绝,但山脉都很年轻,最高的富士山海拔也只有3776米。河流纵横交错,但河床都很短浅。冲积平原散落沿海地带,面积大都很狭窄,稍宽阔些的关东平原也只不过二百公里左右。所以日本的自然景观小巧纤丽,平稳而沉静,再加上日本的地形南北走向狭长,南端与北端虽然存在着寒带和热带的气候风土的差异,但主要的大和地方则处在温带。尽管也有突发性的台风、大地震,但从整体来说,日本列岛气候温和,四季变化缓慢而有规律,基本上没有受到经常性的大自然的严酷压抑。同时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全国1/3的土地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展开一派悠悠的绿韵,在清爽的空气中带上几分湿润与甘美,并且经常闭锁在雾霭中,容易造成朦胧而变幻莫测的景象。整个日本列岛都溶进柔和的大自然之中。日本民族正是充分吸收这种自然环境和气候风土中的养分,形成其基本的性格。可以说,日本这种具有代表性的风土、这种具有特殊性的大自然,无疑成为孕育日本文化的基础之一,直接影响着日本国民的基本性格和原始生活意识和文学意识。
在民族形态上,古代日本社会已经形成日本人种的单一化。日本民族的形成,与其他所有民族一样,是经过历史上无记载的长期的各种血统混合的过程。但是,日本在远东的终极,四面环海,在远古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地理上处于孤立的位置。从外边流入的人种如蒙古种、马来种等,甚少可能向外回流,就全部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又与后来者融合、生活在这岛国封闭的坩埚里。其中最早的原住民阿伊努人,一度占据着整个或大部分的日本列岛。当地人与外来者长期混同,渐次同化了阿伊努人。也就是说,日本各人种渐次混同并融合其原始信仰,调整了民族的对立,最后成为一统的大和民族。他们的结合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是比较和平地进行的。《古事记》的神话里,明晰地记载着大和族一统的历史,也平等地叙述了出云族的神话,它与大和族合并是通过谈判折中完成的。不管怎么说,日本在历史上很早就完成人种和民族的统一,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种族、民族的冲突。
在政治形态上,国家成立之后,日本国家几乎是由单一民族构成,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普遍存在着民族大迁徙和异族间的残酷斗争。就是发生同族的内部纷争,也往往以“国让”[1]的妥协办法来解决。在日本神话中早就传说大国主神奉天照大神的敕令,将国土和平地让给皇孙的故事。即使在中世武家时代,也没有像中世纪欧洲和中国战国时代那种严重混乱的无中心状态。他们始终以皇室为最高中心,没有极端地破坏过社会的统一。所以日本在历史上维持着相对统一的平和的政治形态。也就是说,日本最初的政治形态,完全排除了种族的对立,以民族统一作为其政治统一的中心,其中贯穿日本皇室的权力,以天皇作为国家与民族统一的象征。而不是以武力作为民族统一和政治统一的中心。这种以皇室为中心的单一的民族统一形态和政治统一形态,对于日本民族的心理和性格形成的影响是极大的。而这一古老民族诞生的性格,延续成日本民族的国民性格和日本文化的性格。这种日本历史的特质成为直接生育日本文学及文学意识的根底。
在经济形态上,从距今七八千年的绳文时代,日本民族的狩猎文化就与大自然紧密相连。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大陆传入水稻,日本民族很快就脱离狩猎和渔猎,开始以农耕为主,日本神话大多以农业活动为中心也缘于此。《古事记》、《日本书纪》描述的许多神都是与农业有关的太阳神、月神、风神、水神、稻谷神和“天穗同命”等神,以及将日本称为“丰苇原水穗国”,并描述了农耕的事和与农业有关的祭祀。这说明日本从悠远的神代开始就掌握原始农业技术,社会上占优势的是农耕文化的主宰者而不是宗教。尤其是在上述得天独厚的自然和风土的条件下所形成的人与农业、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非常融合,加上农业集约性的影响,使作为原始农耕的经济形态自然地是以中和为中心的。
在这种以“中和”为中心的自然历史环境和政治经济形态下育成的日本文化存在构成复合型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日本复合型的文化形态表现在各个方面,我们以作为文学和文学意识始源之一的宗教信仰为例,日本民族的原始信仰是崇拜自然神和先祖神的神道,它是原始农耕社会的宗教实体,但其宗教共同的观念和礼仪以祭祀为核心,没有特定的教义,缺乏系统的宗教意识,神道的教权没有绝对化。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古代以后大陆儒、佛、道传至日本,没有遭到神道的激烈抗拒,而且包容了儒、佛、道,多元并存。神道在和外来的儒、佛、道的融合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宗教意识,由于融合自身有所发展,在本质上改变神道的性格,因而它仍然保持着民族信仰的基本性格。我们透过《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风土记》(713)、《万叶集》、《古语拾遗》(807)和以《延喜式》(927)为中心的“祝词”等古籍中所载的神话、祭祀、巫术、习俗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这个国家在统一以前的原始神道精神,也可以了解到原始神道精神对日本民族性格、日本文学和原始文学意识的本质性的渗润。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限于宗教,而且日本文化史的结构也是以调和的形式展开的。
在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的,佛教禅宗在12-13世纪传入日本以后,受到武家政权幕府的支持和保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深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对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人生态度,而且对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文艺创作思想都带来深刻的精神影响,比如不重形式重精神、不重人工重自然、不重现实重想象、不重理性重悟性、不重繁杂重简素、不重热烈重闲寂等等,形成日本文化的中核。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性格与禅的自然性格并存融合为一体。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性格就是禅。
上述日本历史、风土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形态,成为产生独特的日本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那么哪些来自传统文化的国民性格直接影响和决定日本古代文学意识和审美意识,以继续维护着日本文学精神和审美传统的特色呢?
第一,调和与统一的性格。
日本民族的国民性及其精神结构特质,具体表现在追求调和中庸性上。日本学者称这种国民性为“中正”的性格,即不偏为中,不曲为正。他们判断事物一般都采取相对主义、调和折衷的态度,这是以“和”作为基础的,含亲和、平和、中和之意。大和族、大和国、大和魂之称谓,大概也缘于此。正如上述,日本民族史平和的发展,形成日本国民的“和意识”。可以称得上是圣德太子一篇“出色散文的”《十七条宪法》(604)以“和为贵”开首,以“夫不可独断,必与众宜论”结束,说明作者的主体性的思考,是强调确立共同体的和,将调和与统一作为当时最高价值之一。直至近代明治维新以后,仍然强调其社会的基本精神是“以和求存于全体之中,以保持一体的大和”,即保持民族整体的大和。
日本的所谓“和”,表现在对事物观察上的一如性,即任何事物,比如生活与艺术、宗教与艺术都不看作是对立和分裂,而看作是一如的、结合融化为一的。就是把相异的东西综合为一。日本文化上的“和”是对伦理道德、宗教意识的高度感受的结果,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和宗教意识的效果。这不仅是日本精神文化一个重要的范畴,而且是日本精神的力量所在。
日本民族以亲和的感情去注视自然,认为自然是生命的母体,是生命的根源,对自然的爱,带来人生与自然的融合。人生与自然密不可分。可以说与自然的亲和及一体化,与自然共生,成为日本民族最初的美意识的特征之一。这种美意识则不是来自宗教式的伦理道德和哲学,而是来自人与自然共生,人与自然密不可分的民俗式的思考,所以日本民族对自然的感受方法与思维模式与西方民族是迥异的,他们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融进自然之中,主体的人与客体的自然没有明显的区别,而且把自然看作是与人相互依赖依存,可以亲和地共生于同一大宇宙中,人与自然是和谐的。
“和”的精神实际上是日本民族最初表露出来的精神结构特质。这种“和”的精神,经过千余年在广泛的社会心理的深层积淀,最后形成日本意识,即日本民族的思维模式,贯穿和影响着政治、文化、思想、心理乃至社会生活,至今仍然作为人们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的重要准则。在日本,调和与统一被认为是最美的,乃至在文学上、美学上作为一种理想的追求,将“和”之美作为真善美的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
总之,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和”,到心理上、精神上的“和”,正是日本民族美意识所追求的最高的“和”,也是最高的美。调和是日本国民性格基本的、主导的一面,也是日本文明赖以统一的精神基础。
第二,纤细与淳朴的性格。
日本民族生息的世界非常狭小,几乎没有宏大、严峻的自然景观,人们只接触到小规模的景物,并处在温和的自然环境的包围中,养成了纤细的感觉和淳朴的感情,对事物表现了特别的敏感和淳朴,乐于追求小巧和清纯的东西。比如他们喜欢低矮但显出美的小山、浅而清的小河,尤其是涓涓细流的小溪。喜好纤小的花木,国人以细细的樱花作为国花,皇室以小菊作为皇家家徽,国会也以小菊图案作为国会的象征。树木则喜爱北山纤弱的杉。从建筑艺术到日常生活用品也如此,崇尚纤细和淳朴,一切都讲究轻、薄、短、小。所以一些西方学者称日本文化的特征是“岛国文化”、“矮小文化”。
表现在对四季的感受性上,显得特别敏锐和纤细,并且含有丰富的艺术性。比如他们在对季节微妙变化的感受中育成优艳的爱,而这种爱又渗透到自然与人的内在的灵性中,从而激发人们咏物抒情的兴致;他们在四季轮回,渐次交替的过程中,纤细地感受到自然生死的轮回、自然生命的律动,这种对四季的敏感,逐渐产生季物和季题意识,影响到其后的整个日本文学的命运。
日本民族对其原始文化基础的感受文化尤其是色的感觉文化,是非常敏锐和淳朴的。我们从古代文化神话和考古挖掘中就可以发现古代日本人的色彩感觉是很朴素的,在他们的色彩概念中只有白与黑、青与赤对称表现的色彩体系,尤其以白的色相作为其美的理想,以白表示洁白的善,表示平和与神圣,带上一定伦理道德的意味。其原始神道将白作为神仪的象征,白作为人与神联系的色,而且完全依赖自然现象来表达纯白的色。比如古代神社建筑是木造结构,不涂任何色彩,保持原木的白色。用玉串象征神风(风无色,即白)来拂除凡界的尘土,用神水(水透明,即白)来净垢、纯化等等。我们从上述日本民族的自然观和色彩感受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性格的纤细而淳朴的表现,同时这种淳朴的特质与上述的和也是相通的。
第三,简素与淡泊的性格。
日本清幽的自然环境和淡泊的简约精神,对原初民族的简素淡泊性格的形成影响极大。比如日本文艺以柔和简约作为其外表,内里蕴涵着深刻的精神性的东西,这表现在文学思想和美意识中的“真实”、“物哀”、“幽玄”、“风雅”之洗练的美的感觉以及形式之短小上。日本绘画之重线条的柔和性和色彩的淡泊性,整体结构表现出来的情趣之潇洒和韵味之恬淡。尤其是水墨画追求一种恬淡的美,画面留下的余白,不是作为简单的“虚”,而是作为一种充实的“无”,即让“无心的心”去填补和充实。所以水墨画将“心”所捕捉的对象的真髓,用单纯的线条和淡泊的墨色表现出来,表面简素,缺乏色彩,内面却充满多样的线和色,以及多样的变化。日本音乐的旋律单调,却蕴藏着无穷的妙味,回荡着悠长的余韵。日本舞蹈的动作柔和、单调和缓慢,却显露出一种内在的强力。日本语言一个母音只配一个子音,非常单纯,很少拗音和强音。
这种简约的时尚,具体化地运用在数字上是尊崇奇数,以奇数代表吉祥。由此延伸,在文学上也表现出对奇数运用的偏执。从和歌、俳句的格律到歌舞伎的剧名都避开偶数而采用奇数。尤其是文学表现上喜欢使用简约的数字,夸小不夸大,比如“色鱼长一寸”、“苇间一鹤鸣”等,都是以最低的奇数来表示。
表现在衣食住等日常生活方面也如此,和服不仅色素,而且样式单一,无多样多褶皱,从衣领到下摆是一直线的,非常简洁。传统“日本料理”讲究清淡,生食,以保留原味。日本烟酒不浓烈,肥皂牙膏也是淡香。住宅建筑多原木结构、非对称性、不均齐的直线型,连家具也多是原木色和白色。
与日本民族生活密切相连的茶道,更具体地体现日本民族这种简素淡泊的性格特征。他们赋予茶道“空寂”的性格,追求形式与内容的简素的情趣。茶室多是草庵式,空间甚小,整体结构质素,室内布置简洁,壁龛只挂一幅简洁的字画,花瓶里只插一朵小花,造成茶室沉浸在静寂低徊的氛围,让茶人按严格的茶道规范动作,在情绪上进入枯淡之境,并且在观念上不断升华而生起一种美的意义上的余情与幽玄,充分体现“禅心”的“无即是有,一即是多”的性格。
第四,含蓄与暧昧的性格。
日本民族性格不重理性而重实际,缺乏思辨哲学,对事物观察常常直接诉诸感觉和感情。日本文化形态的一切方面,都是从感性出发,但又以“感觉制约”作为原则,单纯表现主观的内在感情,具有很大的含蓄性和暧昧性,直接影响着日本民族的思维模式的定势。
从最能反映民族性格和文学性格的语言来说,日本民族语言的最大特色是具有极大的暧昧性,文章结构往往省略主语、宾语、述语,多代名词,读者(听者)主要依靠语气、语感、遣词用语、敬语乃至上下行文来体会对话的人物关系。在人际交往和思想交流中的用语,也是表现得非常朦胧和含糊,很少使用明确的肯定词或否定词,净讲模棱两可的话。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其语言的文学性往往在艺术上和审美上受到其民族语言特性的制约。语言含蓄,而且一词多义,含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和复杂的内容。比如“无赖”一词,在汉语中只有相近的二义:(1)刁钻泼辣,不讲道理;(2)游手好闲,品行不端。在日语中就含有四种完全不同的释义:(1)流氓、放荡;(2)不可靠、不可信赖;(3)爱的极致;(4)苦恼、痛苦等。所以在日本文学批评上严格界定“文学上的无赖性是不能用流氓、放荡来置换的”。尤其是美学用语更是抽象而抽象,玄虚而玄虚,比如作为日本美形态的用语“わび”(空寂)、“さび”(闲寂)二词,朦胧含糊得令人捉摸不定,不易掌握其真义,甚至连日本人也往往分不开两者意义区别之所在,但通过日本美学语言这种用语的多义性和暧昧性,却让人从中可以感受到其民族的性格,可以感受到其美的感动中带有的民族特性。
含蓄的性格具体化地表现在文艺上,是不重形式而重意境,更重朦胧的格调。以日本美术为例,它甚少明晰清透,重隐约和模棱,尤其是文人画更具“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在淡墨中显其异彩。我国已故著名作家郁达夫就日本文艺美的特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日本文艺“能在清淡中出奇趣,简易里寓深意”,“专以情韵取长”,“而余韵余情,却似空中的柳浪,池上的微波,不知其所始,也不知其所终,飘飘忽忽,袅袅婷婷,短短一句,你若细嚼反刍起来,会经年累月的使你如吃橄榄,越吃越有味”。
民族性格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具有双重性,有其美好的一面,也有其丑陋的一面,有时美好与丑陋并存。我们在这里不是全面论述日本民族性格,而是简述其来自固有文化的,以及决定日本文学思想和美意识,以及继续维护着这种文学思想和审美传统特色的有关基本性格的几个特征,从中考察历史、风土、民族性格与日本文学思潮特质的关系。如上所述,日本的历史、风土影响着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同时这些历史、风土、民族性格又制约着日本民族对美的思考和日本文学的内在气质。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本民族性格与日本文学及思潮混成一体,构成统一的日本性格与日本文学及思潮的联系是多层次的,涉及文学的形态、表现、美理念和思潮诸方面。
(一)从文学形态上的特质来说,日本文学形态是短小型的。日本民族简素和纤细的性格最集中凝结在日本民族诗歌——和歌的短小形态上。从和歌形成过程的动机可以看出,它是根据两个原则构成的。一是从偶数形式到奇数形式,一是从长形式到短形式,最后确立短歌31音节,句调是五七五七七。日文是一词数音节,这样和歌的文字相当简洁。《万叶集》的4516首和歌中,短歌占4256首,长歌只占260首,其中最长的柿本人麻吕的“高市皇子挽歌”也不过149句。而且,长歌兴起不久很快就衰落,分解为小形态。其后的俳句就更短小,只有17音节,句调是五七五,这恐怕是世界诗歌形态中最短小的非对句性形式吧。从短歌到俳句的形式越来越小,且音数和句数都有严格的限制,但却可以准确地捕捉到眼前的景色和瞬间的现象,由于简练、含蓄、暗示和凝缩而使人联想到绚丽的变化和无限的境界,更具无穷的趣味和深邃的意义。小泉八云说它“正如寺钟一击,使缕缕的幽玄的余韵,在听者的心中永续地波动”。这种短小形式而意味幽玄,很符合日本民族精微细致的性格,所以俳句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日本物语文学作为最初的小说形式多为短篇,即使形式上的长篇,也很少汇集整体的构想,实际上仍由短篇合成。比如《源氏物语》既是一部统一完整的长篇,也是可成相对独立的故事,全书以几个大事件作为故事发展的关键和转折,有条不紊地通过各种小事件,使故事的发展与高潮的涌现,彼此融会。《伊势物语》(928)是由125段和206首和歌(有的版本为209首)构成,没有完整的、统一的情节。每段互相联系不大,且非常节约,多者两三千字,少者二三十字。《八犬传》(1842)9辑98卷180回(外一回),虽是洋洋800万言的巨作,写了8个武士的一个个曲折离奇的故事,但从实质上说,也是一个个小故事汇合而成,如果省略某卷回,并不影响整体结构。净琉璃、歌舞伎等古典戏曲也是分段式的小构想,很少统一的整体构思,但情调却是统一的。
(二)从文学表现上的特质来说,日本文学表现之细腻丰富,与纤细、简约的民族性格不无关系。这种纤细、简约性格所形成的对美的追求,不仅表现在文学形式的短小上,而且表现在思想感情的纤细上。《万叶集》的短歌本质在尚未形成时,就已经开始出现从种种形态渐次过渡到短歌形态的现象,它的短歌所抒发的纤细感觉和纤细感情,成为日本诗歌乃至日本文学的统一精神,这是日本民族独有的文学表现。
日本民族性格的含蓄性直接诱导出余情余韵的文学风采。日本文学作品,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曲,都尽量节约,压缩其内容,表现文学素材的主要部分,省略其他部分,而着力把握其神髓、神韵,并且通过含蓄性、暗示性、象征性来表现。最能体现这一文学精神的是作为象征剧的能乐,以幽玄作为其表现的第一原则。它充分发挥日本语言的含蓄和妙用双关语,且每场很短,篇幅不大,道白简洁,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表演更是含蓄而颇具艺术深度,歌舞伎、净琉璃等戏曲也不乏这种含蓄、暗示、象征的文学表现。
日本民族性格反映在文学表现的特质上还有重视文学主观的抒情,如果分解这种抒情的主观性质,不难发现其纤细性和感伤性是非常强烈的。《万叶集》自然观照的歌表现出非常纤细的感情,尤其恋爱的思慕和别离之情所流露的哀愁之纤细、自然和纯粹,恐怕是其他民族不多见的。另外,对自然和人的理解,多是运用直观直觉的机能,感情因素多于理智因素,感觉因素多于理性因素,其文学表现的情调性、情趣性是很明显的。
文学表现的特质不仅反映在感伤性和情调性的感情上,而且也显现在理性制约上。从《万叶集》的和歌历程来看,不全然是主观抒情,也有许多用客观反省与思考的形态表现的,如浦岛歌一类是最早的客观叙事的歌,后期的真间手名儿的歌,题词部分是客观叙述,歌部分是主观抒情。这种表现渐次向歌物语发展,它便成为第一部歌物语《伊势物语》的原型,出现了纤细的反省的理性倾向。从《万叶集》发展到《古今和歌集》,则以自然素材来表现,而且加上简约的理智解释。日本固有文学思潮“物哀”思想,从“哀”到“物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这种感情、理智的简约回环的以情绪为中心的表现而促进的。
(三)从文学美理念上的特质来说,日本原初文学意识形成的一个重要契机,首先是对自然的感觉和对神的感动而引发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以苇芽的萌生象征神的出现,又意味着春之到来,提示季节感的涌动。可以说,在佛教传入之前,日本神话传说,首先是日本民族对自然和神本能性的反应,是崇拜自然与崇拜祖先神相结合,将自然神化,以及自然与神一体化,它是经过自然神话进入人文神话的。正如日本民族尊重自然和神(作为真的存在)的心情非常强烈一样,日本古代文学对自然和神的观察力也是极其敏锐的,常常是本能地将自然与神联系起来观察自然美。这种文学美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将自然与人相连来审视自然美之后,开始与季节美感发生更直接的更自觉的联系。自然在日本文学不仅是一种素材,而且是一种美感。和歌艺术美的思想源泉就是摄取自然景物及其在四季中的变化。一些和歌集完全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来划分歌类,许多和歌纯粹是季节歌。俳句更是“无季不成句”,将季物、季题规范化。在季节美感中,春之优艳、夏之壮大、秋之静寂、冬之枯淡,形成日本文学美意识的特型,尤以秋的咏题最多。因为秋的景物最适合日本民族的情绪性、感伤性的抒发,以它寄托自己的寂寥之情,容易令人涌上悲哀的情绪。这是日本文学对自然的一种感伤的见解,是民族思想感情与自然季物契合的原质。
其他文学种类也如此,描写人物的思想感情多与季节的推移相照应,对季节和季物是亲和与敏感,一般都带有浓厚的人情味,使自然人情化。自古以来,日本文学家以自然为友,以四时为伴,与自然接触很了解自然的心,即自然的灵性,人心与自然心相连,人的生命搏动与自然生命的搏动也是息息相通的。他们从一草一木,空中悬月,也可以敏感地掌握四季时令变化的微妙之处,抚摸到自然生命的律动,乃至从一片叶的萌芽和凋落,都可以看到四季的不停流转,万物的生生不息,甚至可以联系到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命运。所以日本文学描写自然美,是用来表现人情美的。
季节美感产生日本原初文学美的特质,进而成为日本文学思想的底流。从美理念来说,它酿成了文学的悲哀、幽玄、风雅的气质,孕育与之相应的日本特有的美理念:物哀、空寂、闲寂,三者在上古真实(まこと)美意识的基础上形成日本民族的审美主体,而流贯于日本文学各领域,也成为日本文学思潮的源头。
就日本古代文学思潮的特质来说,原初的文学意识,既是对自然的真实感动,也是由对人神的民族式的感动而产生的。这表现在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神的崇拜的一致性上,它是与日本民族原初的生活意识和美意识相契合,也是与日本民族的调和性格相照应的。
缘此,古代原初文学思想的基调是主情,即以情为中心,情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但又并非单纯由情而是由情与理的结合展开的,达到了情与理的一致境地。我们从儒佛道文学思想与神道文学思想合流就可以发现这一点。神道将儒家的“志”、佛家的“空”、道家的“无”调和,在对立、并存、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系统的文学思想,并有所发展,强调了“明、净、直、诚”,其基础是诚(まこと,又曰“真”)。这种调和型的文学思想,流贯于古代各个时期,由于它是多成分、多元素构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具有新的特质。如古代前期以情——物哀文学思想为中心,中期以法(佛法)——幽玄文学思想为中心,后期以义理——劝善惩恶思想为中心展开,对于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起着主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