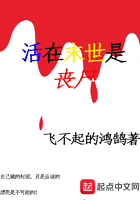来源:《凉山文学》2014年第03期
栏目:小说
滔滔的嘉陵江水,日夜奔流在川北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它沉静的时候,仿佛一位温柔的处子,缓缓踏过平坦舒缓的旷野;它暴怒的时候,一路狂奔乱驰,巨大的嘶吼声终日回荡在巅崖峻谷,仿佛一头咆哮的雄狮。嘉陵江水滋润两岸碧绿青苍的毛竹林,滋润青松翠柏,滋润两岸年年开不败的杏花,也滋养出一方水土一方朴实的山里人。
在嘉陵江的上游地方有座山,名字叫凤凰山。凤凰山不高,面积也不大,但因为山上有座张献忠墓而闻名遐迩。我小的时候,凤凰山还没作为旅游胜地开发,默守一方水土。那时的大人们大多文盲不论官职不管聪明呆傻农民不种田不种地都搞政治去了,留下小孩子没人管。我和伙伴们光屁股坐在牛背上,手里挥舞着墓前随手可拾的生锈断箭头,驱赶牛群颇有雄风。牛群“哞哞”叫着,迈着悠闲的步子踏过这位明末大将的墓地,啃食坟上青草,踩碎芬芳野花,抻倒几棵塔松;然后直到日影西斜,这才在高高的墓碑下乱扔几顶绿草帽样的粪堆,仍是“哞哞”叫着,沐着一地残阳,向山下村里走去。
山下,就是杏花村。田畔地角,沟里沟外,村前村后全是杏花树。这个时节,杏花早开败了,杏子青青的,才只有指头样大,毛绒绒的小个头藏在圆圆的叶下,没红脸,却一副害羞的样子。杏花村,其实窝居在凤凰山的山脚下,村外有条从山崖开凿出的羊肠小道,蜿蜓迤逦穿过重山,通往县城。山崖下,就是汹涌澎湃的嘉陵江了。
杏花村差不多超过百十户人家五六百人口,具说以前全部姓黄,外面人常管这里叫黄家杏花村,足见我们家族人丁兴旺人情发达了。但后来何年何月搬来几多佃农,便有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杂七杂八的怪姓,久而久之,我们黄姓反而日渐没落;加之解放后政治运动连连,今天走一家,明天逃一家,今天抓一个明天毙一个,黄姓几经颠簸气数已尽,只余得五个爷辈贫农老祖分下来不到二十户了。这黄大爷二爷三爷四爷五爷五个爷辈传下的后人又不争气,不知道团结一心挤兑外姓,自家人却常为些田畔地角瓜秧豆苗绿豆样的小事争吵谩骂打架斗殴弄得杏花村是鸡飞狗跳日夜不宁。凡此种种,就连时常在此常驻蹲点的公社领导都大为光火却又无从施为。公社书记张国豪以前提到杏花村时总是眉眼笑成一团:“黄家杏花村那个杏花啊……”,现在呢,虽然还是提,提起却是一脸青黑,“刁民!刁民!穷乡出刁民,姓黄的——”
那时杏花村的生产队长早不姓黄,姓钱,叫个钱官长,是长久有钱长久当官的意思。这钱官长时常在大会小会上给他们眼中的最高领导指鼻子戳眼睛,溅得满脸的唾沫星子,自认在同级的小官中那是抬不起头来啦。春种的时候,杏花村的秧苗迟迟下不了田;秋收的时候,杏花村的粮食两成肥田三成归仓,余下五成呢,自然早在收前已成了“刁民”口中粮腹中餐。杏花村的田地本来就少,每每收成的时节,钱官长只得如同猎狗样满坡满岭地瞎奔乱窜,可守得东守不了西,守得了南守不了北;白天守住了,晚上却是“贼”的天下,他又没得二郎神三只眼。先是黄姓的偷,接着是全队的人偷,后来竟发展到生产队保管员计分员组长都偷。这钱官长才四十来岁的人,几个春种秋收下来,鬓边就现白头发了。他一气之下终于病倒,这一病却更助长了“贼”势,眼看着这年的庄稼,除去抛撒,怕是连两成也收不回来了。
钱官长这一病,足足病了半个多月;他这一病,使得杏花村我们黄姓家族这一年,真正发生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半个月后,他装病起来了,时间已到了农历的七八月间。他先到村里各家各户门前周游了一圈。各家门前早堆起了草垛,房顶炊烟袅袅,门都大开着,该吃苞谷糊时灶房却散发着米饭的香味。他脸上带着诡异莫测的微笑又来到田坝里,队里还没组织秋收打谷,可田里却如同蝗虫飞过一样地干净,光亮的水田里甚至连稻草都没剩下。他手抠着给太阳光烤得焦亮的额头,忽然就想通一件事:他手下的臣民,他朝夕共处的乡邻,确实是一群贼,一群十足的家贼,家贼难防啊!他一个人在田坝里影子样飘荡,无意间就看见好象还有两个人从水田里鬼一样冒出来了!当时太阳光很强,刺得眼睛几乎睁不开。他连忙以手遮额,看是看清楚了,两个人眨眼间却变成了一个,只见那人差不多和自己一般年纪,脸上戴着副宽边眼镜子,穿着半胶鞋,两腿泥泞,手上提着一网袋田螺,腰上驮着个大箩筐,箩筐里装着的,竟是满满的才割下的谷穗。
这是杏花村剩下的最后一块两亩试验种谷田。杏花村人胆大妄为,这点分寸却是识得的,一村人满田满野一寸一寸搜刮,唯独这块田却没人敢动。没有种谷,来年吃什么?种谷,那是种田人的命根啊!
钱官长正找不着痒擦,顿时一个恶毒的念头从心头升起,望着眼前这个人,公社领导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刁民,刁民,穷乡出刁民,黄姓的——”他要杀鸡给猴看,如果不适时使出煞手锏,这个村会乱,这个世界会乱,而他这个生产队长,尽管是个小小的生产队长,怕也是没几天的指望了。
这个人,就是我二叔黄天华。
五个爷辈老祖混到这份上,全都位登极乐。单说大爷传下的的这一支共四弟兄,天字辈,老大是我爹黄天荣,老二便是二叔天华,下面依次是天富,天贵,四弟兄取荣华富贵之意。下面的子女,则是勇字辈。
四个弟兄中,应该说二叔最是能干的。膝下只有个独生女儿,十七岁,比我大五岁,因在黄姓同辈排行第九,都叫她九姑,我排行十一,杏花村人喜欢管男娃娃叫毛娃,九姑叫我十一毛。
那个时候,二叔已经在村小学当了十多年的民办教师,在学校里教语文算术,还能作诗作画拉二胡奏风琴,算得上村里最有文化的知识人。按理说,知识人就不应该做这样的傻事,更何况二叔每个月还拿着令全村人都眼红心热的五块多钱的津贴,又不下劳力,每天却另还有十个全劳力工分。可在这节骨眼上,他却偏偏做了,背上驮着“贼赃”,正大模大样向着生产队长走来呢。
如果说这事退后个几年,生产队长姓黄,或许眼高手低,事情就过去了,反正一村的贼又不怕再多出一个。可遗憾的是,现在的队长不姓黄却偏偏姓钱。钱官长在那一刻也是倍感困惑,“人民教师也做贼?”但很快,他便自以为是地大彻大悟了。在杏花村,钱姓和黄姓都是大姓,两族历来形同水火,这事明摆着,黄姓四兄弟是在挤兑他姓钱的,给姓钱的添乱造事,给他这个队长示威来着!好,很好,你做得出初一,我便做十五,不就个教师么?混了十多年,还不就是个可有可无的民办教师么?教师年年凭先进选模范也不见拿回来一个!看谁牛逼,你黄姓的算老几,你再大个,能大得过公社领导么?
这天正好是星期日。二婶在家熬好稀饭镇在水缸里,急咐咐九姑出门去找爹。那时,我们四家人同住在一个四合院内。二叔住东头,我家住西头,门口正好相对。天气太热,九姑赖在院子不出去,趴在棵杏树下直喊:“十一毛,砍脑磕的十一毛——”
爹此时正在屋里光着上身一身油汉编篾货,听到喊声一脚将我摞出门去:“小鬼头,是九姑叫你啦!”
天气热,谁都愿守在家里,九姑历来都拿我当枪使,自然不会有什么好事。九姑看见我,做个鬼脸,好看的凤眼闪着狡黠的光亮,忽然低声说:“我爹在田坝里捉鱼,你去不去?”小孩子哪听得这话,我连忙点头:“去,去,你呢?”九姑掏出张花手帕直擦额头上的汉,却道:“我不去,你去!快点,晚些鱼就捉完了,你顺便叫我爹回来吃饭喔!”果然是拿我当枪使,我不情愿地噘噘嘴。九姑立刻虎起好看的瓜子脸扬起拳头道:“敢不去!”一摇身边的杏树,“下次给我捉住,有你好看的!”
九姑是独女,在这院子像个公主,谁也不敢惹。我慌忙一溜烟向学校方向跑去,身后听到九姑得意的“格格格”的笑声。
我刚跑到田坝的时候,正好看见二叔给钱官长打倒在水田里触目惊心的一幕。二叔一身泥泞,浑身涂得象头水牛,鼻孔里鲜血直冒,眼镜斜吊在耳朵上,牙齿也打掉了几颗,口里“唔唔”连吐血水,却分不清说什么。在那一刻,我潜意识反应就是回家去喊人。可当我爹和三叔四叔也跟着跑到田坝的时候,钱姓家族的人却全行动了,百十号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将我们分隔开来。
在人潮涌动中,几个人高抬着从二叔身上取下的箩筐,钱官长则将二叔又从水田里拖了上来,拧了头发,横拉竖扯,直拖到生产队的晒场上。二叔的眼镜没了,鞋子不知掉到哪里了,身上的衣服也给撕成条状,在人丛中只见脚手乱蹬乱舞,“唔唔唔”的呻唤令人心悸。二叔先是四肢趴在地上,嘴边又流下一大滩鲜血,大睁着一张恐惧迷乱的眼睛,在人丛中寻找黄家的人。后来不知怎么地,他便一骨碌蹿了起来,反身又向田坝里逃去。钱官长牛高马大手脚麻利,从晒场上捡起根锄头把子自后追赶,两人跑过一条田径又是一条田径,穿过一片水田又是一片水田。两人都是壮年,可毕竟二叔眼睛高度近视不好使,身体又单又瘦,很快便给追到一棵杏花树下,在一村人的惊呼声中,隐隐听到“邦”地一声,二叔头顶鲜血直冒,手先扶着杏花树,跟着又一头栽倒在水田里……
这就是我说的杏花村那年黄姓家族发生的大事。这件事的发生,使得我们黄姓彻底在杏花村失去了做人的根基。这主要反应在几个方面。首先,黄家最有能耐的老二在几兄弟的眼皮下却被外姓打成脑震荡要死不活,就势力而言高下已分;其次,作为堂堂的人民教师光天化日之下作贼偷队里的种谷,黄姓自然颜面无存;再者,人是当着黄家人打的,可几个亲兄弟却谁也不敢相助,这也成了杏花村人耻笑谩骂的话柄。
特别是最后这一点犹为可愤。黄家几兄弟毕竟皆是血性男儿,又如何能输这口气。当晚,二叔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爹天荣已磨好了三把贼亮贼亮的大菜刀。舞一把的时候舞得浑圆,“嚓”地声便削断了院子内一棵腕粗的杏花树;舞两把的时候有些难受,但看起来还可以,可跟着就有一把脱手,险些伤到自家人了。他咬牙切齿手提两把菜刀,当要向腰上别第三把菜刀的时候,却给我娘一下子抢了回去。我娘一手拉着我,一手紧紧缠住爹的腿,大哭着:“爹啊,先人啊,床上都躺了一个,还想躺二个么?我们斗不过人家,你是猪脑还是人脑?”我爹听了这话,顿时一脸惨然,鼻子汲溜着,忽然大叫一声:“二弟啦——”干嚎着钻进屋去了。
三叔天富为人胆小,自始至终守在二叔的床边哀声叹气。九姑哭,二婶哭,他也跟着哭。四叔天贵最年青,最近才从城里回来,是杏花村人公认的“天棒”(恶人),他白天亲眼目睹了二叔被打的场景,嘴唇都咬出血来了。这个时候,他正藏在村外的竹林里,两手握着根两米多长的钢钎。这根长钢钎,尖子磨得透亮,足以将两头牛刺得对穿对过,可想戳在人的肚子上,会是怎样的光景。四叔那时快三十的人了,但还没结婚,因此天不怕地不怕。他孤孤单单缩头缩脑地在竹林里过了一夜,但并没钱姓的人主动送上门,不仅钱姓,就连其他杂姓的也不见个鬼影子。第二天,当二叔好歹活过来的时候,四叔的影子已彻底在杏花村消失,多少年后,也没人知道他人到底去了哪里。
但这天晚上,钱姓的人却着实战战兢兢过了一夜。可到天亮的时候,却连屁事也没发生。钱官长事情做得太绝,良心上毕竟欠安,整夜都没合过眼。他原打算等第二天,再把我二叔弄到公社好好去游一场街,借此向领导表功,并狠狠打击黄姓的嚣张气焰以儆效尤。可黄家并没来寻凶报复,他也便改变了主意。第二天,第三天,依然没有事,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杏花村还是风平浪静,仿佛根本就没事发生过一样。
早上的时候,天空阴沉着,仿佛是要下雨。上个星期很是热闹了一回的大晒场突然间又起波澜。先是公社派下来十多个民兵肩上斜背着枪管生锈枪口塞着棉花团的大盖步枪立在晒场四周,接着从民兵中走出个高高壮壮二十一二岁的年青小伙子,手里举着个铁皮传话筒高声喊:“各家各户听着……”
这个年青小伙子姓周,名叫来福,是山后凤凰村的人。来福脚上穿着双黄胶鞋,头上扣着顶崭新的黄军帽,上身穿着的确良衬衣,下身穿着蓝色吊裆裤,这在七十年代岁头岁尾,那都是很时髦的啦。
不多会,在来福的传话声中,各家各户的门前很快便有响动了。先是钱姓的几个本家兄弟废力地扛着麻袋步履跚跚地行到晒场中央,将麻袋往地上一倾,接着腋下一夹,不吭声不出气地走了。钱官长坐在晒场角上,脚边还放着二叔用过的箩筐,含笑点头,以示允可。在他的身后,赫然坐着的还有公社书记张国豪。
晒场上的人很快多起来,都做着同一样的动作,同一样的表情。围着大晒场绕一圈,有的人甚至眼里流着泪,都躬身向里面添点什么,如同举行一场简单却又无比沉重哀伤的葬礼。
我爹和我三叔也相继扛着麻袋来到晒场。三叔吓得连头都不敢抬,两腿直打颤,往堆上添的时候,脚下一软,就要栽倒下去。来福长长的手臂一伸便将他扶住了。
不到半个上午,晒场的中央便堆起了几座小山。不仅是新收的稻谷,还有黄澄澄的苞谷棒子,最胆小的,甚至连门前的谷草捆也背了来。大人们没脸,看热闹的全是小孩子,我那时候还很不懂事,自然也夹杂其间。小伙伴们最感兴趣的是民兵肩上背的步枪,可当时场面气氛严紧,谁也不敢出声,唯一能听到的声音,便是大人往堆上添东西的沙沙声和时断时续的哭哭泣泣。
最后,九姑来了。十七岁的九姑已出落成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九姑垂着两条长长的麻花辫,穿着件粉白粉白的衫衣,脚上是一双半新旧的塑料凉鞋,这使她看上去,真婷婷如一株美丽的杏花树。九姑刚走到晒场的时候,人群便有了不小的骚动。钱官长见九姑两手空空,自己身后又坐着张书记,不知她来要干什么,心里一紧,倏地从椅上站了起来。
九姑先立在晒场中央,冷冷的目光逐一从民兵脸上扫过。年青的小伙子们还从未见过这样一张冷漠绝艳的脸,不由自主的垂下头。只有来福,目光一直追随着九姑,看着她大踏步竟向晒场角上走去,脸上莫名地闪过几丝不安的神色。这个时候,我爹天荣和三叔天贵在晒场上还没离去。对于爹来说,当着公社领导的面交出偷来的稻谷,那真是脸面丢尽了,但他也有心安理得的理由:人人都瞧着的,不是钱姓的本家兄弟先交么?先交就是先示弱,就做人而言,如果说黄家的人活得窝囊,那么钱姓的岂不更窝囊么?更何况,粮食他最多也只交了一半,然后还藏了一半,这和那些连谷草把都背来的人比,其胆量高下之分,还用谁来说么?
我爹正自我安慰的时候,不想九姑却不识好歹,跑到晒场来了。爹下意识地想过去把九姑拉回来,这个傻丫头,你个女娃娃,青天白日地又逞什么能出什么风头?你爹做贼不知羞,难道你还敢去找领导的岔子不成?爹刚向前走了两步,但不知为何脚下便一软,如同拖着重铅一般再也挪不开步子了,眼睁睁地看着九姑径直走到张书记面前。
张书记第一次看见钱官长把杏花村人整治得服服帖帖,正兴致勃勃。蓦见一道影子站在面前遮挡住了视线,先是一怔,跟着瞧清是个漂亮女娃娃,向钱官长一望道:“她是——”
钱官长心里七上八下,正要介绍。不想九姑却先道:“您是公社张书记么?”
张书记含笑点点头。
九姑道:“我叫黄九姑,我爹叫黄天华!”
钱官长鼻子一嗤道:“你看你个女娃子,真是不懂事!你还有脸,你还有脸?”
九姑道:“这里有张书记在,我有不有脸,还不用你来说!”
钱官长一挥手道:“还不滚回家去!”
张书记不高兴道:“小钱,咋这样说话,让九姑说。”
九姑冷冷的目光望着钱官长道:“姓钱的,你把我爹打得好惨,这种亏心事,你自问良心,晚上睡得安稳么?”
张书记道:“九姑,其它事就别说了,你心里有委屈,我们领导的心里也能体量,不过你爹也真是的,一个堂堂的人民教师,不能作人民的表率,但也不能做坏事嘛,你说对不对?再者——”
九姑忽然打断话道:“我爹没做坏事!”
钱官长用脚一踢箩筐怒声喊:“那这是什么?”尽管过了整整七天,那箩筐仍还保持原貌,上面涂满稀泥,里面除了稻谷穗之外,还有一网袋田螺。
九姑也怒声道:“这箩筐不是我家的!”
钱官长回转身向张书记双手一摊,做了个无可耐何之状:“这箩筐一直锁在保管室里,今儿天才拿出来——”跟着又向里面一抄,“谷子都发霉了!张书记,您老来凭凭理,我和这小娃娃那是说不伸(清)!”
张书记用手捋着下巴问九姑:“你说这箩筐不是你家的,那你说是谁家的?这箩筐难道不是从你爹身上取下来的么?”凛利的目光望着了钱官长。
钱官长嚎声道:“一村的人都看见的,难道还有假?我说黄九姑,你别不识好歹,没把你爹弄去游一场,杏花村的人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九姑哽声道:“我承认这箩筐是从我爹身上取下来的!”眼睛一眨,泪水蓦地涌出,“这……这……沿上还有……有……我爹的血……”
钱官长双手又一摊:“那还有啥说的,这不结了?”
九姑强抑住哭声,正色道:“箩筐虽然是从我爹身上取下来,但并不能证明粮食是我爹偷的啊。比如现在箩筐在你这,难道能说是你偷的么?”
钱队长气得七窍生烟,差点没背过气,道:“你别做得可怜兮兮的,你……你……我不跟你讲,我跟你讲不伸!”
九姑慢声道:“讲是讲得清的,就看是谁来讲了。我了解我爹,他是决计不会做这样的事。我家没这样的箩筐,这就说明箩筐是别人家的呀。姓钱的,现在你可以挨家问村里的人,看是谁借给我爹的?”
钱官长疑惑道:“那又怎样?”
九姑道:“只要你找出借箩筐的人,这才能证明我爹确实做了坏事。万一是别人偷的,他刚巧遇上,然后顺路捡回来呢?如果找不出,那我爹的事,你就得负全部的责任!”
这个时候,很多围观的人也聚了上来。我爹大着胆子夹在人丛中,听了这席话,心里依然迷迷糊糊,暗道:“这又是个什么理?小丫头和他爹一个德性,只怕又要撞祸哟!”
听钱官长说道:“你会捡,你再去捡个来看?我找不出,难道你又找得出?”
九姑冷声道:“如果我找出来了呢?”
钱官长道:“那你就找啊!只要你找得出,我钱官长就在这给你黄九姑磕九九八十一个响头!”
九姑道:“我不要你磕头,我消受不起,我只要你还我爹一个清白!”
张书记听得不耐烦,问道:“黄九姑,你说箩筐是谁家的?”
九姑缓缓俯下身,将箩筐一倾,把里面的稻谷全倒了出来,然后双手高举,一一让众人看。
人人都脸现疑惑,有声没气道:“没什么呀!”
九姑回头向人丛中喊:“十一毛——”
我“嗨”一声从人丛中钻了出来。
九姑道:“你去打盆水来。”我又“嗨”了一声,拿过早准备好的脸盆,跑到晒场下边的水田里舀了盆清水上来。上来时,爹拦住我,汹汹道:“你个小杂种,你想给老子惹祸么?”伸过蒲扇样的大手使劲拧我耳朵。我“哎哟”一叫,水倒了半盆。九姑过来,将半盆水接了过去,然后往箩筐的里面一倒,跟着又半扣着,水流滴答地又让大家看。
九姑道:“这事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凤凰山就只两个村,一个杏花村,一个凤凰村。每年交公粮时,箩筐混杂,为了便于清认,所以在箩筐的底部都作了记号。大家再仔细看看,这到底是不是杏花村的箩筐?”九姑说完话,将箩筐放到了张书记脚边。
张书记寻眼望去,只见箩筐底部果然写着个字。是用油漆写的,虽然字的轮廓很多都给磨脱了,但依然认得清楚,是个大大的“凤”字。杏花村的箩筐写的是“杏”字,事实不容置疑,箩筐是凤凰村的。
为了稳妥起见,张书记问钱队长:“这里有不有凤凰村的人?”
钱官长此时已觉事情有些不妙,额头汉水涔涔,但仍然说:“有,有的!周来福——”
来福提着话筒大踏步过来道:“张……张书记,是您叫……叫我?”
张书记指指箩筐道:“你认认,这箩筐是不是你们凤凰村的?”
来福点头道:“是……是我们凤凰村的!”
张书记说道:“既然箩筐是你们凤凰村的,咋又跑到杏花村的田坝里来了?我仔细想了想,九姑的话确实也有些道理。难道真是凤凰村的人先偷了种谷,然后这个……这个……”
钱官长急道:“张书记,这人能偷种谷,难道就不能偷箩筐?这事大伙儿都是亲眼瞧见的!”
九姑问道:“你有没有亲眼看见我爹在田里偷稻谷?”
钱队长抠抠脑门:“这……这……倒没……”
九姑道:“钱队长,我爸上午一直在学校给学生补课,十一点半钟出的校门,这事他的学生都可以作证,可十二点钟就出事了。你是做庄稼的老把式,凭你的能耐,你能在半个小时内摘下这一大箩筐谷穗么?”
钱官长急声说道:“这是用镰刀割的!”
九姑质问道:“那镰刀呢?”
钱队长脸涨成猪肝色,一时出不得声。
张书记也觉其中疑点甚多,他对九姑印象很好,却摆摆手道:“我看你们就别争了。今天主要是来搜粮食,这事下来慢慢查!”
有黄姓家族的人终于大着胆子提议:要查明其实简单,你们去两个人看看黄老二如何,再当面问问不就清楚了!”
就在这时,忽听有人大声道:“不用喊了,黄天华自己来了!”
张书记不好护短了,坐在椅上招手:“黄老——”他想喊黄老师,蓦地又改了口,“黄天华——”
钱官长伸袖口直揩额头上的汉水,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是啊,要是真给问出偷东西的另有其人,黄家老二受了冤枉,那这事可就真不好收场了。
九姑快步跑过去,哭着直喊:“爹——,张书记叫你啦!爹——”
九姑连喊好几声,二叔却总是不应。来福也跟着跑过去,哽声喊:“黄老师,黄老师——”他以前是二叔的学生。
来福直扯二叔的衣袖。二叔头上缠着给血浸得紫红的纱布,身子歪了歪,缓缓转过头,空洞散乱的目光望着晒场中央,向着众人忽然傻傻一笑。
来福蓦地惊呆了,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道:“黄老师,您……您是……怎么了?”寻问的目光望着了九姑。
张书记也惊呆了,怔怔道:“黄九姑,你爹——”
九姑满脸泪水,却不回答。半晌,才一把挽住二叔的手,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说道:“爹,你受的冤屈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也知道。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把那个人找出来,一定找出来。这里风大,爹,我们回家,我们回家吧——”
在众人各种复杂的目光中,来福跟着又跑了回去。他立在二叔面前,两眼含泪,怔怔地望着一脸痴呆的老师。后来,他又做了个令在场所有人都大惑不解的大胆动作:一把抓下头上的军帽,轻轻地戴在二叔的头上,掩住浸血的伤口。
晒场上确实起风了,跟着有细细的雨丝自空中飘落下来。炎热了数月之久的川北山区终于迎来了一个久违的凉爽天气。可这凉爽的清风,它能吹散凝在人们心头的乌云么?这细细的雨丝,它是滋润人们干涸心田的甘露,还是预示着新的寒冬已然不远呢?
没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