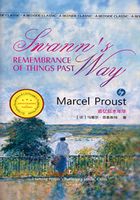“进来,进来。”一个男性粗犷的声音。
“天呀,终于找到了。”听出那是次旺的声音,疲惫的我都有些激动了。
次旺穿着一件休闲抓绒夹克,略带自来卷的头发有些凌乱。即使光线不好,他脸上那两片高原红还是可以看得出来。那对像新疆人一样的眼睛一直天真地眨巴着,他又重新抱起吉他,一边热情地让座,一边坐回床边开始弹一些简单的和弦。
藏北,冬季,没电,这间夏天暖融融的屋子现在冰冷昏暗。狂风肆虐着草原,把窗户也拍打得咣咣乱响。原来空着的客厅现在已经满满当当,墙角一个藏式炉子正半死不活地烧着,中间放着台破旧的木制办公桌,两张铁架床对着木制办公桌进行了半包围,靠墙另一张简易的桌子上摆放着电视机和DVD机。办公桌上点着三四支蜡烛,乱糟糟地放着简易小音箱,很多碟片,一把近尺长的银鞘藏刀,几个凝着污渍的杯子,还有从一进门,他们就谦让我吃的一大块黑黄黑黄模样像蛋糕的东西。后来听说,那是藏北人的至爱——奶渣酥油糕,是次旺的两个苯教出家喇嘛舅舅带来的。
“我听我们局长说你来了,然后去招待所找,他们说没有新来的人登记。”他调了调弦说道。
“县里没电,我没打算住旅馆。桑珠呢?我出来之前打了几次电话,可都是关机。他说,在找到下乡车之前我可以住在中学。”我觉得很意外,因为桑珠并不在宿舍里。
“他前天回乡了,好像有事找他。他说过要在这里等你,都住了一个多月了。”次旺点了支烟,“我没钱交话费,停机了。”
“噢,我因为生病,所以迟了。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再上来?你能帮我找下乡的车吗?”我有些不知所措。
“刚才拿着行李不方便,又不知道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县里没电,我觉得一个人出去住不太安全。桑珠也没告诉我,他回乡了。”我继续说着,觉得自己这次实在太大意,怎么满脑子就只想着吃,而忘记,如果桑珠回乡,我自己是很难解决下乡交通的。
我恳求次旺帮忙打电话给桑珠。他只好又借别人的电话,但乡里的卫星电话一直占线。“估计是风大,电话打不通。明天再打,应该没问题。下乡的车,我明天帮你在县里问,”他满口藏普,温和干脆,“那你去不去招待所,还是就住我们这里?哦,这里有些脏呀,你别笑话。”他依旧抱着吉他,当说到脏的时候自己先笑了,脸上的两朵红雀跃着,可听不出有什么羞愧。
我知道自己绝不能一个人在黑洞洞的县招待所住。我当然马上告诉次旺,最好能够在学校宿舍,希望可以有地方住。他还是没有放下吉他,笑着说,可以,他和老吉睡一张床——刚才开门的人就是老吉,今年刚分配下来的老师。望着他憨实的笑容,我觉得踏实很多,事情好像都没有问题了。尽管屋里很冻,但也许后天,最多大后天,我就能到文部乡了。
“为什么炉子不能烧得旺些?你们不觉得冷吗?”我把手放在脸颊上,希望可以暖和些。
“这房子的烟道设计有问题,炉子就只能这样。今天还没倒烟呢。”虽然是这样说,可次旺还是立刻起身走到门口卫生间的地方,几下折腾的声音过后,他拿了些牛粪出来扔到小小的藏式炉子里。转身坐回床上,又抱起吉他,弹的还是那两下。
“你该多穿些,看,看我们。”其实他根本没穿太多衣服,一件橘黄色的套头抓绒衣罩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毛衣,外套是件蓝不蓝黑不黑的厚夹克衫。而我当时穿着两件抓绒,一件冲锋衣,外面还有一件棉警察大衣。老吉穿得也不是很多。旁边那两个一直默不作声的喇嘛舅舅身上就更只有一件棉藏袍而已。到底是那曲本地藏族,没得比。
次旺终于放下了那把怎么也不舍得放下的吉他,开始介绍他的喇嘛舅舅们。两位苯教喇嘛舅舅是和我一趟车从那曲上来的,难怪瞅着有些眼熟。他们早上在车里不停地念经,我记得后面嘟嘟囔囔的声音。次旺告诉我,他的舅舅们说我不停地在车上拍东西。我告诉他,因为总是听到后面有念经声,就用DV拍了下来。次旺又说,舅舅们是到当惹雍措、穷宗神山和达果尔雪山转山绕湖的,因为那是苯教的神山圣湖。通常这样的话题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决定第二天要好好向苯教喇嘛打听一下转山绕湖的行程,琢磨是不是也跟着走两天。
那夜,大家休息得比较晚。凌晨我觉得身体有些缺氧反应——虽然还不至于头疼,但明显呼吸开始急促,一定要半坐起身才会缓和。我用的是自己的睡袋,但次旺说夜里寒冷异常,又给我加盖了一个休假回家老师的被子。那味道可真不怎么样,而且极其厚重,感觉压得不能呼吸。但为了不冻着自己,忍了。因为房间里用的藏式炉子使用牛羊粪做燃料,所以不能长时间保持火种,入睡后炉火就会熄灭。室内温度可想而知,这里的清冷比起那曲和班戈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三个人分别睡在客厅的两张床上,不到一米的距离就是开放式的法式玻璃窗。白天有太阳的时候温暖明亮,入夜,飓风刮得窗户咣当作响,天地苍穹倍显诡异凄凉。
一宿半梦半醒,干燥和稀薄空气在冬季的尼玛县很容易感觉到。天一点点地放亮,县中学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半上班。宿舍楼距离教学楼不到三百米,所以,一般老师们都九点起床。也许是因为我住的宿舍里都是藏族男老师,也许是因为用水比较困难,总而言之,我迷迷糊糊地感觉,他们早上几乎都没洗漱就去上课了。
老师们上班之后,我觉得自己也该赶快离开那个有味道的被窝儿立刻起床。虽然他们不洗漱,我可是不想省这点儿水。打开面对山坡的大玻璃窗,可以刷牙,洗脸,废水都是泼到后墙根那边——这就是变通的尼玛式给排水。一切收拾妥当后下楼,准备去教学楼找次旺老师——看看上课的学生们,也希望能够尽快联系到下乡的车。白天的尼玛县,阳光永远是热烈充沛,一点都不糟蹋“尼玛”的称号!
刚出宿舍楼门,就碰到昨天晚上一起吃饭的那位眼镜老师。他好像有些疲惫的神态,我笑着打了招呼。也许是因为尼玛县物质匮乏,这里的人经常看上去带些菜色,不过他的样子显得有些格外孤单不合群。后来和次旺老师很熟悉以后才听说了一点关于他的事情。那时刚过完元旦,从文部乡到县城置办点东西。学校早已放假,但次旺“不幸地”被轮到要教为期一个月的成年人扫盲班。天寒地冻,我们待在怎么也生不起旺火的宿舍,聊起了在县城里工作的青年们谈恋爱的事儿。尼玛县恋爱速度之快比比皆是,无尽的荒原,那些整日被太阳厚爱的人们实在不喜欢独自面对清冷孤寂的夜晚。
当时我问到学校里汉族老师的情况,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解决成家问题的。次旺说,基本上在县里工作的汉族家属都是外面的汉族,外族很难在这里找到对象。接着又似笑非笑地说,学校里曾经有个老师包养过“三陪女”。当时这句话听得我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首先,我怀疑这一条街的县城是否有三陪女;再有,也不太相信一个老师能够和三陪女搞到一起。我笑他说话太夸张,又问他怎么知道的。有谁愿意自己包养三陪女的事情被别人知道呢,何况还是个人民教师。
“你不信呀,切,全县人都知道。他还背着那个女人去医院看病,据说当时满医院跑着找大夫。而且,因为这件事在学校挨了处分。还有别人说的更多呢,不过我没那么八卦。”可我还是感觉出他语气神态中的鄙夷。次旺的确不八卦,但我却忍不住问是哪个老师。他简单地回答说,戴眼镜,好像经常和小耿一起。
对于这样的事情,我当时听说后,也实在没能对那位老师产生什么同情。后来,为了赶回拉萨过藏历年而在县城等班车滞留时,意外地碰到了这位教师。那天晚上,和小耿、小土一起正在吃饭,看着他进来我很吃惊。那时中学已经放假快两个月了,除了看门大叔和我,并没有看到其他人在学校。而且,当时县里又是停电,有两三天吧,关闭的学校很难找到燃料,也没有水。我奇怪,他依旧留在县城。当然,再次遇到也勾起对其之前传闻的好奇。
“你怎么放假没回家?现在住在哪里?是学校吗?”
“是呀,想有个清净的地方写书,就申请寒假在学校值班。我也住在学校,你从乡下回学校的那个晚上我看见了。”他微笑着,神态平和。
“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住在那里呢。”的确有些意外,“那你写什么书呢?是小说还是论文什么的?”我知道这东西一定对他很重要。不然,一个年轻的汉族小伙子,经过了一年的工作,春节还不肯回家休息,主动申请留在这个好像天尽头一样的地方,必然是需要意志和一些想干什么事情的原动力驱使的。
“是一部关于藏北教育状况的报告。”他说到报告时神情凝重。可当时旁边的小耿和小土都在窃窃地笑。
“看来你对自己从事的教育工作很负责任呀。”我心里有些怀疑,眼前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次旺说的那个老师?
“我在这里工作两年多,对现行的藏北教育有很多看法。现在年轻,想多做些事情,也能够多学些东西。”依旧是比较凝重的态度,烛光映得他的面孔发红。
“靠,你丫不就是想借着给教育局提意见引起重视嘛,说得那么高尚干嘛。写好了,交上去,如果有反应,能很快调走就可以了。”
“尼玛这里的学生,有几个能真的认真学习呀,国家花钱买个心安而已。”小耿和小土一边夹着炸烤出来的羊肉,一边前后地说着。他们的态度多少有些像当前城市里的小青年,对什么都认真不起来。
“我可不计较他们说的。”估计是眼镜老师看出我听到他们的话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解释起来,“我们在一起都是这样的,有什么说什么,无所谓。也不真较真儿。”
小耿和小土在一旁笑着,不再说什么。
“其实这就是藏北的好,说什么,做什么都坦诚。大家都没心思藏着掖着。”我很想赶快把话岔到关于包养的事情上。“听说这里有个老师,连三陪女都敢包养,也算是至情至性了。”因为有些犹豫是否传闻中的人就是眼前人,我采取了迂回。但一看到小土满脸戏谑的笑,我知道,没错,应该就是这个眼镜老师了。
“你笑什么,就是我。不过,我得声明一下,那不是包养,我也没那么多钱包养别人。”眼镜老师全然没有羞愧就承认了,他的口气很坦荡,好像那不过是一件最正常的事情一样。
“啊,实在对不起,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没搞清楚就是你。真不好意思。”他的坦然使我有些羞愧自己耍的花花儿肠。
“没什么需要对不起。不过,这中间的确没有包养。我家是农村的,全都是农民。我的工资省吃俭用后都是要寄回去的,你也知道尼玛县的物价,哪里还拿得出闲钱去包养女人。倒是她,还经常照顾我一些,晚饭什么的,都是她弄。不就是送她去趟医院嘛,有什么。”他对于是否被别人认为包养女人很在意,但并不介意别人议论那曾经轰动全县的行为。
“爱情有时很奇怪,你为它做什么都心甘情愿。我相信你们不是金钱关系。而且,我觉得你能够背着她去医院,到处找医生,不计较别人怎么说,可见你们还是有真感情的。”说这话的时候,我眼前突然浮现出夏天在县里见到的那个和康巴男人有感情纠缠的四川女人——她那被暴打后结在人中处的痂在脑海中一下变得特别清晰。我得承认,在这地方,就这个荒漠中凸竖出来的小镇子,什么奇怪的感情好像都有可能发生。
“那还真是这样。外面来的人就是不一样。一下就可以理解。她是我们老家来的,但之前我们并不认识。只是在这里碰到了,一聊知道是一个地方的。老乡嘛,她后来经常叫我去吃饭,说话聊天什么的。我知道她是干什么的,但她从来没有找我要过钱。慢慢地,我开始在那里过夜。靠,经常夜里从县城走回学校也挺累的。”他好像因为我的话来了精神,点了支烟后继续说道,“我平时不怎么抽烟,那花费太大。”
“你丫就见到我们抽。”小耿笑着也点了一支。他是全县人都知道的经济富户,尽管平时话不多,可也算是个豪爽的人,并不真的和别人计较那些和钱有关的小事。
“可我没想过和她真怎么样。也就是说,我没想过娶她。她也知道,而且从来没提过。说白了,就是两个人都觉得彼此对对方不错,在这样的地方,搭帮凑合取个暖,解个闷罢了。真要说以后的事儿,谁想那么远呀。”他深深地吸着烟,吐烟圈儿的时候神态有些迷茫,我搞不清楚是眼镜反光,还是他有些开始怀念那时的生活。
“那后来呢?听别人说去医院不是普通的病,她后来怎么样了?”我有些在引导,虽然这也许算不得什么清白感人、伟大热烈的爱情故事,可你很容易想象出两个孤寂又年轻的男女相依在一起的画面,那至少代表了温暖,很实在。
“本来日子也没什么,都是那样过的。有一天她突然说肚子疼,而且一下就疼得连路都走不了,一直出汗。我害怕有什么事儿,哪里还顾得许多,背起她就到医院了。当时是晚上,还要找大夫,是有几个人看到,可那是人命攸关,如果我怕别人说,要是人真的出什么事,那怎么办!”他开始有些激动,“何况,我们在一起,她对我那么好,你说,哪个女人愿意干那事儿呀!她这么远从家乡跑出来挣钱,又没有读过什么书,咳,就这样呀,反正是赚点男人钱吧。”他又点了一支烟。
回民小饭馆里好像弄了个发电机,刚才的蜡烛已经被一盏二十瓦左右的日光灯取代,它散发的青色光芒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有些变形。而老师的眼镜看上去更像是两片白玻璃。
“那到底是什么病?而且,你们住在一起……”我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问出了口,“如果有人找她,你怎么办?”
“其实很少人找上门,即使有什么她也会直接告诉我。尼玛县就这么大,想通了也没什么。那次去医院是胆囊炎。我知道你听别人说什么,不就是流产嘛。上嘴皮碰下嘴皮,说什么都成。”他对流言很是不屑。
“其实我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这样说过,大家都很隐讳。不过,我知道胆囊炎有时也很危险。她对你好,你这样也算回报了。”
“那次几乎算是救了她一命,没做手术,稳定了之后她就离开了,再没回来。”没想到结局如此简单,就像事情的发生。也许就是因为太简单了,才会有人猜测。连绵的山丘静静地接着广阔的天空,大家也真是闷坏了。
“你们后来还有联系吗?据说你因为这事儿受了处分?不过,学校是以什么理由处分你?”
“没有联系。她应该根本就不知道我受处分的事儿。还要什么理由呀,我是人民教师。也就是‘发配’到乡里教书半年呗。不过我从来没后悔过。汉族人在这里生活不容易,你看这里的汉族,干脆说,除了分配来的藏族,如果不是在学校有女朋友,想在这里找对象,那就不可能。我承认,这事儿放在教师身上是有些不太合适,但这样的事情,又不是事先安排的,有就有,彼此对得起就够了,其他还能计较什么呀。”他一直狠狠地吸着烟,聊天这会儿工夫好像抽了四五支。
那天,后来因为我想去小耿家上网,所以他一个人默默地回了学校。我不知道自己的刨根问底会不会使他陷入某种伤感之中。但我觉得,自己明白了最初见他时那种无奈落寞的神情因何而起。
想起自己还经常和女朋友们讨论什么是爱情,找什么样的人最合适——爱我的人还是我爱的人。这些问题在尼玛好像都显得有些可笑。出了县城那条唯一的街道,离开尼玛镇,方圆几十公里都难得见到人烟,爱情在大片大片的衰草中无迹可寻。可感情又真实得如同空气,随时贯穿于所有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后来又从米玛那里知道,与康巴男人有情感纠葛的四川女人最终死掉了。这些压迫着我的习惯思维,原始的感觉像牙膏一样慢慢地被挤了出来——从来就没有什么伟大的爱情。生活在这里的人,无论藏族,汉族,还是其他什么民族的人——在这个离太阳最近,却又异常荒凉的地方,男人、女人,有血有肉,真挚热烈地惺惺相惜着。他们的日子甚至比我们任何一个在繁华都市里的人都更让人激动。
县中学的教学楼、老师宿舍楼、学生宿舍楼都是国家投资。高大敞亮的水泥楼房矗立在羌塘草原的旷野上,甚是瞩目。目前除了中海石油援建的县政府办公楼和尼玛宾馆可以媲美外,还没有什么建筑能胜过这些楼房。漂亮的教学楼里很安静,只有若即若离的讲课声音在回荡着。楼道并不是非常清洁,大风带来的沙尘,一些随手扔弃的纸张,有些像假期中。
楼道很宽,上到二楼,隐约听见一阵语速很快,语气类似责骂的藏语。当时我正拿着DV,循声而去,看到一间空荡的办公室里站了三个学生,他们低着头,明显地在偷偷嬉笑。学生对面坐着一个黑脸身穿黄色羽绒夹克的男老师,手提一根一米半长的木棍,边说边不停地敲打着地面。面相粗犷好似武僧一样的老师看见我举着DV站在办公室门口,并不问我是干什么,先用藏普说了一句“不要拍”,然后赶紧把棍子往身后藏。可坐着的他无法完全挡住,棍子的小半截露在外面,而那几个学生也从窃窃之态转成明目张胆的大笑。阳光从后面洒过来,老师的脸显得更黑,有些滑稽。
“我是来找次旺老师的,您知道他在哪里吗?次仁旺堆老师。”我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连忙收起DV。
“在前边的办公室,不过他好像不在,是不是去县里了?”男老师还是一脸尴尬。
我谢过他,笑着离开直奔旁边的办公室。而他却紧随着过来,“刚才你是不是录了什么?给我看看可以吗?我可没有打他们,你看到的。”他丢下那些学生紧随上来,并积极地解释着。
“我又不是记者,不过是拍着玩的。可那几个学生怎么了?如果不是要打他们,你为什么拿那么大一根棒子呀?”我不想他紧张,何况本来也就是拍着玩而已。
“你是次旺老师的朋友,那几个学生不好好上课,捣乱。我是班主任,正在教育他们。棍子不过是吓唬吓唬他们。”他那样子真跟做了什么错事被当场抓住的孩子。
“那棍子看着好暴力呀,小孩子会吓着的,”我不太能够接受老师体罚学生。不过,想到那几个学生被骂时还调皮的嬉笑,又觉得自己说的话也挺可笑,“嗯,还好,他们也没给吓倒,是挺调皮的。”
“就是就是,你都看到了,这样还笑呢。”他终于有些如释重负。
次旺老师的办公室是空的。办公室里其他的老师说次旺老师应该是去县里了,也许一会就回来。我猜,可能是去帮我找下乡的车吧,真希望能够尽快离开这没电没水没火的县城。
武僧老师还是一直解释着刚才的事情,那些学生是因为私跑到县城玩而受到责罚。老师一直嘟囔着说,很多学生,尤其是男学生们,就算你真的打了他们,他们也还是那副无所谓的样子。也许知识的重要还没有能够根植于他们的意识当中。而我在琢磨,为什么这些从来都不需要花钱就能读书的孩子们就是不珍惜机会呢?在内地听到无数次关于中小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不得不辍学的事情,也看到很多辍学孩子的照片,那无奈忧伤却又饱含期待的眼神,显示了他们对学校的渴望。但在西藏,从路过昌都地区的然乌镇,第一次看到两个镇长亲自出马挨家挨户通知放虫草假的学生回校上课开始,就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惑着。为什么那些被国家“三包”的藏族学生们,大多不喜欢学校的学习生活。
外面已经开始喧嚣,是课间休息的时候了。次旺老师刚好也回到办公室,他告诉我,去县教育局办事的时候顺便问了下乡的车,没有。而且,桑珠的电话依旧打不通,可能还是大风的缘故,那些卫星电话没有信号。
我很失望,又问他知道不知道县里什么时候可以来电。他说,如果他会维修,那马上就给我电。这话让我更加郁闷,开始有些怀疑自己——没事找事,如果去尼泊尔过冬一定没有这么倒霉。可一想起当惹雍措的湛蓝,想起小丫头曾经甜甜地媚笑,我知道,我只能在尼玛,在文部,在当惹雍措。于是,自己的心好像也因为惦念的一切而平静下来。
一时不能离开县城,我决定先去探望一下米玛。她的家是一间简易的土坯房,集合了厨房、卧室一起,艰苦却温馨。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了饭。她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依旧浑圆结实,脸上挂着温和且憨直,又略带羞涩的笑容——非常典型的日喀则人。她很快就能够调离尼玛县回到拉萨和家人团聚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也觉得很开心。
“真搞不懂你们这些人,我们都想往外走,你却要在大冬天跑过来。很冷的,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第二个菜没炒出来,第一个菜就都凝上了!”我当然理解她认为的不可思议。我记得夏天曾经用水井里的水洗衣服,八月份,还把手冻得紫红紫红的。当时曾经问过米玛,她是怎样在冬天洗衣服的。她说,戴着棉手套。那时,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可现在,我马上也要面对这样的问题了。
饭后我们一起随便走了走,她的家离县液化气站比较近,那里已经是县城的边缘,公路从那个地方是往申扎方向去的。“还记得我曾经和你提过的那个和康巴男人搞在一起的四川女人吗?她死了,就埋在这液化气站旁边。”米玛突然冒出了一句。
“啊?就是那个被康巴人老婆把上唇打裂的女人?”她的话使我震惊了,一个正直青壮的人,说死就死了?
那个女人是我在夏天来的时候就听说过的。还在县城唯一的街道上见过她一次。当时,她上唇的伤痕还没有完全好,黑红的结痂在白皙的脸上十分醒目。据说,她和老公一起从四川到西藏谋生,开了个小卖铺,落户在这个羌塘草原上的小镇。后来认识了一个阿坝的康巴藏族,那康巴男人也是在尼玛县找营生的,有个泼辣彪悍的康巴老婆。据说康巴女人通常在家里的地位并不高,很多甚至都不能上桌喝茶吃饭,但对于老公是否有外遇可看得很紧,不乏大打出手的事件发生。不知是什么原因,反正听说是白皙柔弱的四川女人和高大粗犷的康巴男人相好了。也许是康巴男人看腻了英姿飒飒的康巴女人,也许是四川女人在这个天边小镇尤显娇弱,反正街上那场身体和心里的羞辱也没能够把他们的关系结束。
“他们后来还是有来往,可那女人几乎在街上看不到了,估计不怎么出门吧。入冬没多久就死了。据说是因为怀孕,自己找了药吃,结果大出血。她丈夫送她去了医院,已经不行了。我们这里的医院你也知道,看不了什么病的。当夜就包了一辆车准备上那曲,出去几十公里就回来了,人已经死了。她丈夫一直陪着。现在就埋在这儿了。”米玛对着液化气站努了努嘴。
“那康巴男人呢?他知道吗?她的丈夫居然就一点话都没说?他老婆死了!”我一直半张着嘴,因为这实在令人诧异。尽管我知道,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不过是件女人红杏出墙,男人偷情风流的丑事,但还是觉得有些心酸。不知是四川女人付出的代价太大,还是因为米玛的叙述太平淡,竟然没一点要感叹悲情的劲儿使我有些失望。这事情莫名其妙地使我联想到草原上的野兽,几天,游荡在方圆几十公里,偶尔碰到同种的异性,相互蹭蹭舔舔毛,慰藉一下彼此的孤寂与寒冷。
“很少见那康巴男人,四川女人的丈夫后来很快就把店转让给别人,离开尼玛县了。听说他们在四川老家还有孩子。”米玛还是那种平静的口气。仿佛一个人的死亡在这样的地方不足为奇。我们开始往回走,一路也没怎么说话,也许都觉得刚才无意中说起的事件太让人伤感了。
当我回到中学宿舍的时候已经十点了,宿舍楼的一些窗户映出摇曳的烛光,恍如隔世。半喘着上了三楼,次旺弹着吉他,老吉无所事事地坐在旁边听着。这间宿舍有三个男老师居住,其中一位已经有了女朋友。老吉和次旺一样,也挂单呢。所以,这样黑灯瞎火的夜晚,通常只有次旺和老吉在,而索朗——那位女朋友是小学老师的人一般就去约会了。进了屋,我自然也加入了次旺这半发呆半萎靡的音乐之中。
次旺是西藏大学艺术系毕业的,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够成为一位像Kurt Cobain一样的乐手。当然,他可从来没想过去自杀。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和本系同学组成了一个摇滚乐队——羚羊角,据说是为了表明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的决心。他们也曾经为此专门写了首歌,我在桑珠那里听到过,是藏语的,尽管听不懂,但曲调不错。毕业后,因为是那曲考上去的学生,所以,在没有找任何关系的情况下,他理所当然地被分配回了那曲。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工作的地点在那曲西边最偏远的县——尼玛。
乐队有四个人,次旺是贝司手,另外三个人分别在墨竹工卡、日喀则和察隅。无论气候、交通,还是物质丰富程度,尼玛县都无法和其他三个地方相比较。据说他刚分配到尼玛县时,觉得自己将很快离开,因为他从来不觉得自己能够离开心爱的音乐,离开乐队的朋友。可一年很快过去,之后又很快地过了这个学期,可他离开尼玛县的事儿不要说八字没一撇。
夏天在文部的时候,我喜欢坐在乡政府的后墙根看当穷措。中午过后,我和桑珠经常都会傻呆呆地坐在那里懒散地晒太阳。对着美丽的湖水,他时常谈起次旺。那时我还没有见过他,但已经知道他是如何在西藏大学读书,如何喜欢摇滚乐,如何组建了乐队,如何“倒霉”地分配到那曲尼玛县中学工作,还经常被叫去为接待各种上来检查工作的工作组唱歌。还有他喜欢的乐队,Nirvana,Slash,Metallica,Beyond,黑豹什么的。他高大剽悍的康巴人体形,他对音乐的执著。桑珠总是略带崇拜的口气讲述这些,尤其说到次旺从来没有过老师教如何弹贝司,靠着一点点看书,看碟片自己苦练出来时,一向自负的桑珠总结说,“反正我是干不了,他真能下工夫。”桑珠还告诉我,次旺的乐队那时刚刚在拉萨录制了第一张专辑,也经常去酒吧演出,反应都很不错。
忽明忽暗的烛光把次旺脸上的两朵高原红映得一会发红一会发黑。“我弹得不怎么样,以前就没学过,只是弹贝司的一点基础。”也许因为我们那时还不很熟悉,他看到我微露的浅笑,以为是因为他弹吉他不熟练。“我觉得还不错,起码能把和弦弹得八九不离十。”看着他的认真劲儿,本来没怎么笑的我反而大笑出来,“那你能不能找个能听的歌弹弹?不然老吉都要睡着了。”旁边的老吉听到我说的话,连忙换了个姿势,以表示他也很认真。
“好吧,那就《光辉岁月》,这里有谱子,可我从来没弹下来过。”次旺依旧还有些羞怯,烛光映出他脸上高原红中的一些血丝,也许因为紧张,感觉有些血丝似乎要爆出来。就是那些舞着的烛光,窗外吼叫的狂风,几张破旧的摇滚乐队海报,和我们一起听着次旺半生不熟地唱起了《光辉岁月》。
对于学校学生及老师用水这件事,得当成一个工程来看待。首先,县城里的大多数人吃水、用水基本还是需要到水井里打。而学校距离县城一公里,曾经打过两口井,可惜,都不出水。所以,老师、学生们的用水都是从县城里买回来的。移民到尼玛县的那些善于开动脑筋的回族人做了这门生意。据说,开始是因为回族人要满足自己的宗教信仰的需要,必须开设淋浴室。后来,逐渐对外营业,因此需要大量的水,于是有了自己的拉水车。县中学二〇〇四年在县城外建好后,他们也就顺带着做起了送水的生意。
送水车是时风牌小蹦蹦改装的,车后斗上固定了一个一吨装的油罐桶,用来装水。桶的底部还有个胶皮的简易出水开关。一般每天中午前后过来送一次水,水车会开到学校宿舍楼门口。需要水的老师大多会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就把家里的水桶放在楼门口儿,到水车来的点儿,老师们就回来打水再拎回家。一般从教学楼上就可以看到蹦蹦跳跳进来的水车。一桶好像是两块钱。
中午,次旺上课的时候水车来了,他派了学生到宿舍帮我提水。本来最高愿望只是洗个脚的我,到了中午突然想去洗澡。全尼玛县有两个可以洗澡的地方,都是回族人开的,就在县城和尼玛镇的岔口。夏天曾经去过两次,条件很简陋,但这样的地方还能够淋浴真是不错了。我依旧去了夏天那家。老板娘是个非常和蔼的回族妇女,她永远都用黑色的头巾把头发连带发迹围得严严实实。白净缺油的脸和当地藏族呈鲜明对比,但永远带着有些怯怯的笑容。她一见到我就问是不是夏天来过,我点头,她的样子好像很开心。因为有夏天用井水洗衣服的经验,这次我出来就决定,和老板娘商量多给些钱,在洗澡时把衣服也洗了——为了几件衣服,冻出冻疮来可不值得。在尼玛县洗澡绝对是件体力活儿,再加上洗衣服,折腾了快两个小时。当听到次旺在外面喊我名字的时候,我已经累得连穿衣服都费劲了。刚一出来,他马上说道,“秃子明天要到县城了。”
“秃子?”我不确认自己在尼玛县还认识个秃子。“桑珠呀。”次旺的样子很开心,“‘十一’从拉萨回来就是秃子了,你不知道吗?他说是在拉萨剃的。”
是了,桑珠在拉萨碰到了以前的女朋友。他以剃掉齐肩的头发来表示沮丧。我当时甚至以为他会出家做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