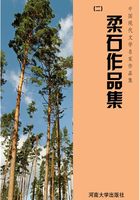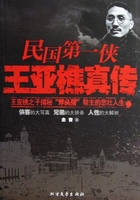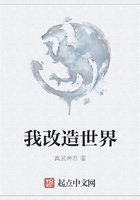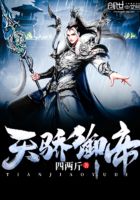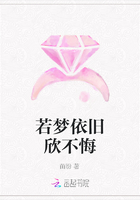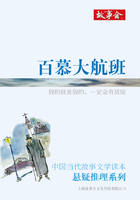19.导向何方
“文华奖”奖杯近年来,有关部门搞的艺术比赛颇多,什么大奖赛、邀请赛、观摩赛等等,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不能说是坏事情,对提高演出团体的艺术水平也确实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赛事的副作用亦越来越明显。一些剧团为了在评奖比赛中夺得好名次,在创作排演剧目时,不是把眼睛盯在演出市场上,盯在观众身上,而是趋时赶潮,为评奖而评奖,创作排演新剧目,都是为争奖而去的。评奖组织者亦不把参评剧目是否有观众,是否经过演出市场检验作为参评条件,而是来者不拒。这样做的结果是,得奖剧目一大堆,老百姓还是嚷没好戏看;有些获奖剧目缺乏生活、缺乏观众基础,首演之日即封箱之时,演一场赔一场,演得越多赔得越多。因此,现在一些赛事奖项要把演艺团体导向何方,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
应当指出,在向市场经济发展中,评奖机制对演艺团体和演出市场确实起着重要的导向和调节作用。方法措施得当,就有利于各级演出团体走出旧体制的阴影,面向观众面向演出市场,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步子。否则,就会使一些演出团体误入迷途,继续在旧体制的阴影下兜圈子。欣闻,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五个一工程”奖和“文华”奖都要求参评剧目要演够一定场次,这对我们改进评奖方法和机制很有启发,也是值得评奖组织者学习效仿的。
20.向这位不相识的校长致敬
这篇短文我几次提笔又放下,因为我怀疑向六百多里外的一位素不相识的校长表示敬意是不是值得。几经踌躇终于下笔——我找回了自信。
事情发生在1994年严寒的冬季。12月3日,北京音乐厅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听众——北京四中全体师生。该校停课专门欣赏精彩的“伏尔加之声”音乐会。
稍微对教育界情况有所了解的人就不会不知道12月是什么时期。这正是学校期末考试总复习的关键阶段。在一般学校,学生早被校方赶入题海之中了,哪有余暇旁顾。北京四中乃闻名全国的重点学校,期末考试成绩的好坏对她的声誉会有颇大的影响。而在此时此刻竟让全校师生停课跑到音乐厅听音乐,校长何等大胆!
我曾设想这其中或许有过非议:学生家长会不会埋怨学校浪费时间耽误孩子前程呢?学校教师会不会对此不理解,批评校长赶时髦呢?学生会不会怕挤占复习时间而影响考试成绩呢?而在此关键之时,站出来拍板的一定是四中的一校之长。他(她)的学识和素养在此时此地得到充分显示,也让我们这些局外人深怀敬意。
我们喊出加强学校艺术审美教育已非一日,然而时至今天,不少学校的学生还挣扎在作业和题海之中,连一场电影都不敢去看。在此情况下,北京四中的做法实在值得学习和效仿。让孩子们离开闭塞的课堂,到艺术殿堂听听美好的音乐之声,应该是校长的责任。
据称,北京四中因成功地组织包场“伏尔加之声”音乐会,而获得最佳听众组织者奖。我想北京四中和他们的校长是当之无愧的。
21.儿时的电影
电影在庆祝自己的百年华诞。百年,若为人,或垂垂老矣,或早已羽化成仙了。电影则不,依旧生机勃勃,充满朝气。
回想20世纪,就艺术来说,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是电影的世纪——虽然近年来电视开始走红走俏,而就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受的影响最大、熏陶最深的艺术形式当属电影。电影与我们是很亲的。如今我们长大了,但偶而静下心来就常想起儿时反着看电影的情景。
应当是三十年前。那时机关大院每个周末都要在篮球场放电影。片子都很精彩:《刘三姐》、《地雷战》、《三进山城》、《满意不满意》、《冰山上的来客》,等等,所以星期六下午的课总上不好。放了学就急着从家拎个小板凳去占地方。若去晚了没好地方,放映机后边又站着一片黑压压的人,个子小看不到,就只好到银幕的反面去看。反面虽也有看客,但毕竟疏朗得多,而银幕上的人物故事是一样的,只是影像模糊一些而已——张嘎照样堵胖墩家的烟囱,“飞刀华”照样刀无虚发,“得月楼”的杨友生照样用他挤出来的笑容吓跑许多食客,女警官石云照样追回了秘密图纸……总之坐在银幕的反面,确实看了不少的电影,《秘密图纸》、《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兵临城下》等大概至少也看了三四遍,虽然如此,依旧如痴如醉。
现时已经很难找到反着看电影的机会,电影也包装得愈来愈华美,看客更被抬举到须享用包厢待遇了。但不知为什么我依旧怀想儿时反着看的那些电影。那时的电影真迷人!
22.读书可以养气
十几年前刚到机关工作时,正赶上整党。一位领导同志做报告,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读书可以养气。这位老同志在“文革”中被批斗挨整时,躲在斗室内读完了《资本论》等一批书籍,受益匪浅,读书可以养气则由此而引发。
应当说此言在我脑海中也留下了印象。然而真正感悟和理解,则是几年后通读了司马迁的《史记》之后的事了。《史记》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奇书,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记载了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勾勒出帝王将相、官吏、学者、商贾、游侠、农民起义领袖等社会各阶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它的最大特点是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大文学家苏辙曾言道:“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濛,颇有奇气。”读这样的书自然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使人恍若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孟子像其实,读书养气是古人历来倡导的。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那本很有名的《文史通义》里也说:“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吾养吾浩然之气。”在读书过程中,精神得到滋养,思想得到升华,胸腔自然激荡着一股凛然正气。所以欲锤炼品性,陶冶情操,认真读书,“涵养吾气而后可”。
当然,并不是读什么书都可以达到养浩然之气的目的。若每日钻研《厚黑学》之类的书,大约只能长诡诈之气;若沉溺于《金瓶梅》、《香艳丛书》一类的书,则只能生绮靡之思,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23.“原型”热该降温了
这几年,在报刊、广播和电视等传媒上,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文学作品“原型”热的日渐升温。我们常常在某个早晨就被告知一个爆炸性消息:某文学名著(或小说或电影或电视剧)中的主人公原型找到了。如《小兵张嘎》中张嘎的原型,《沙家浜》中阿庆嫂的原型,《英雄儿女》中王芳的原型,等等,似乎一个早晨就从地平线下冒出来。最新奇的是笔者手头的一篇文章,称长篇小说《红旗谱》中朱老忠就是以宋某某为原型创作的,并宣布住“在保定市城南”,“一个幽静小院”里的“朱老忠”之子欲续《红旗谱》。看了真让人如堕五里雾中。由于工作关系,笔者接触过一些梁斌谈创作的文章,从未见到他把自己精心创作的人物形象硬贴在某位原型身上,不知该文作者的“创作灵感”从何而来。
稍有点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作家对生活中的诸多人物进行广泛艺术加工概括后创作出来的。鲁迅先生六十多年前在谈自己创作经验时就说过:“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事实上,如果按照某些人找寻“原型”的逻辑“创作”下去是相当可笑的:《红旗谱》中冯兰池的原型是谁?他的孙子是不是也有“幽静的小院”可居呢?《围城》中方鸿渐的原型是谁?《废都》里庄之蝶的原型是作家吗?照此推下去,我们这个世界可够热闹的。
现实生活中,我们许多英雄模范的事迹已非常感人,完全没有必要硬往一些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上贴。我猜想,“创作”原型的热情大半来自一些摇笔杆的先生。他们于寂寞中总试图制造些“轰动”,于平淡里常试图搅起波澜。殊不知这样干,不仅误导了观众读者,也损伤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所以我们当给他们泼点冷水,使他们发热的头脑降降温。
24.说不尽的《红楼梦》
有人说《红楼梦》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我是颇赞成的。《红楼梦》自诞生以来让许多人为之洒下一掬泪水,有多少文人的笔墨官司是围绕她而展开的,就可知其魅力有多大了。正因为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所以她的语言、思想、结构、情节都是彻头彻尾中国化的。外国人可以读懂《三国》,可以弄通《水浒》,唯独对《红楼梦》,大约只能莫名惊诧:一大家子人天天在一起吃吃喝喝,有什么看头?
曹雪芹先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谜。谁能说清作者的身世,谁能说清红楼梦中的人物关系,谁能说准大观园的方位……就在不久前,一家电视台播放一部关于曹雪芹祖籍的电视片后,立刻引来一场论争。正因为她有数不清的谜,才让文人墨客“为伊消得人憔悴”。王蒙从文化部长的位子上下来,有人问他首先想干的事是什么?他说首先想了却多年的心愿,写本关于《红楼梦》的书。著名作家刘心武正当创作盛年,撇下现实题材,硬钻入红楼之中,写出了“秦可卿之死”的小说。可见,哪个文人梦中无红楼呢?
不独文人,政治家亦如此。毛泽东自称至少读了五遍《红楼梦》。并说他“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不仅自己读,毛泽东还劝别人读。他对表孙女说: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劝爱将许世友读一读《红楼梦》。据说,从此许将军就一直把《红楼梦》摆在自己的床头。
二百多年了,国人魂牵梦绕的竟还是这薄薄的一本《红楼梦》,文学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25.输个明白
中央电视台到底是一派大家风度——虽然一百个城市的有线电视台已播完了《武则天》,但“任凭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依旧不慌不忙每天一集地播着这部女皇片,让人急不得恼不得。
此期间或捧或骂,一些报刊上也是一片喧嚣之声,如今曲终人散,似乎也该有个说法。说法也难,不过硬要让说,我倒觉得《武则天》剧组是个大赢家,中央电视台则是大输家。
《武则天》剧组的制片人无论如何是个极具眼光的“商人”。《武则天》从筹拍开始就瞄着市场而来,先是千呼万唤地请出了刘晓庆,继而戏还没拍就造得国人皆知,翘首以盼了。片子完成后,先卖给有线台,再卖给中央台,播出过程中又闹哄哄出了个作者署名权的纠纷,总之是在热热闹闹中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或曰创造了电视剧生产的良性循环。
相形之下中央电视台的角色就显得颇为尴尬。先是声称买断《武则天》播出权,话音未落,全国数百个有线电视台先期播出。继而又声称不影响总体收视率,而实际的收视率呢,实在是不敢说乐观。
其实,以巨资买断版权,在近年来中央电视台可能不是第一次了。上次潇洒之举好像是买断《爱你没商量》,其结局读者心里都明白:“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引来一片责怨之声。作为全国覆盖率最大,资金最雄厚的国家电视台以巨资买来这类让观众摇头的电视剧放到黄金时段播出,算不算一种失误呢?
输并不怕,但总得输个明白吧!
26.“纪念”随想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河北文坛曾有过一个辉煌时期,在那个隆起的文学山峰上,站立着一批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梁斌《红旗谱》、《播火记》,孙犁《风云初记》,徐光耀《平原烈火》、《小兵张嘎》,冯志《敌后武工队》,刘流《烈火金钢》,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短短十几年间,有这样多的一流作家涌现,有这样多的优秀作品问世,我们在振奋之余似乎应该寻找一下他们的根。
孙犁李英儒徐光耀当我们沿着这批优秀作家的成长道路探寻时,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他们都经历过抗战烽火的洗礼和考验,他们的作品也大都反映的是抗战时期河北人民的斗争生活。记得一位名人说过,革命就是一座熔炉。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也是如此。它不仅锤炼出一批身经百战的将领,也陶冶出一批英姿勃发的作家。抗战之初,孙犁是个经济拮据的农村小学教师,李英儒是个普通中学生,徐光耀还是乡村少年……是抗日战争使他们觉醒,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这就正如孙犁先生文在80年代初回忆往事时所言:抗战给一切要求生路的人们指明了一条生路。
今天,抗日战争的硝烟已散去五十年,我们在向那些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文艺战士致敬时,更应该深入思考向他们学习些什么?从他们成功的道路、成长的足迹,我们应该借鉴些什么?
27.级别读书
刚分到机关时,我去机关图书室借书,偶然发现了一套匣装百图本的《金瓶梅》。我是学中文的,从未读过足本《金瓶梅》,自然爱不释手。但好心的图书管理员大姐告诉我:这套书只借给厅局级干部,身为小兵的我,只能与此书失之交臂了。
当然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不过我国图书出版和阅读有级别限制确实是由来已久的。许多不错的书籍都在版权页上注明“内部图书,请勿外传”。把图书管理与保密局的机要文件纳入同一轨道,这也许是我们的一项发明吧。记得“文革”前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套相当不错的西方哲学思想读物,版权页上就赫然有“内部读物”的字样,大约是怕普通读者中了毒。还有那本几个日本留苏学生搞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虽发行量极大,却也被纳入“内部读物”的圈子。可能内部读物在当时是一种身价、一个光环吧!
毛主席晚年身体虚弱且患眼疾,但依然手不释卷,视读书为生命。为了满足毛泽东的读书欲望,曾将他晚年喜欢读的一些文章辑印了一册书,仅印了几十册大字本,供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阅读,这大约是级别最高范围最小的一本书了。
大概是前年吧,碰到一家出版社的熟人。他向我推销《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说这就是当年仅印了几十册的那本书,被他们独具慧眼的总编抓过来推向社会了。我笑着说:咱恐怕不够级别吧?朋友正色道:你瞧你,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说这话!
是啊,这都什么年代了!
28.精装书的“老底”
已经不止一位朋友与我说起目前出版的精装书太多。的确,到书店走走,傲然屹立的多是那些“西装革履”的精装书,一副得意洋洋、睥睨一切的贵族派头。
作为读书族的我们,不妨去揭揭精装书的“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