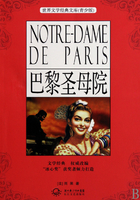一语成谶。那是又一个薄雾升腾的早晨,一夜几乎没合眼的唐英刚刚睡去。顺喜和虎子在院子里玩耍,商量着去东头的李子树地里挖土梨吃。虎子妈活着的时候,常去唐英家串门,有一次碰上唐英的婆婆刘高氏炒熟了土梨,就给虎子装了一口袋。那细长的土梨长得像小蚯蚓,又像小得不能再小的葫芦,和黄土同时盛在铁锅里,用柴火慢慢小炒,炒成和黄土一样的金色,香味就出来了,摊开凉凉,吃起来咯嘣脆响,年少的虎子便充满了向往和回味。前几天,看见前坪东山头上下来一个老头,担一担笸篮,在那棵大杏树下挖出了土梨。虎子就记住了土梨生长的地方,带了比自己小的顺喜去挖。
李家下地是要经过杏树下的,弟兄三个依次从院门出来,就看见了顺喜和虎子在地里玩成了泥猴。自从唐英不再让李生看梳头起,两人就结了暗恨。无缘独享盛宴的李生绝了一厢情愿的念想,睡懒觉对他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听得院里五乱十翻,他也就跟着早起,和李福李憨一起去下地。都晓得老二懒,却不知他自藏了一段心思。
李福孩子多,日月过得苦,带了大儿子得财,爹种地,娃跟着做力所能及的营生。看见比得财还大的顺喜和虎子贪玩,气就不打一处来。老大李福说:“妈的,死性不改,不知道下地光知道享福,这大的男孩,就知道个玩玩玩!”
老二李生养活这个外姓儿子,想着老大夜里的快活和唐英别转着自己的眉眼,一股邪火冒出来,无处发泄,就把邪火转移在虎子屁股上。一脚飞来,虎子没防备,仰面八叉栽倒在泥地里。刚要哭来,看婶子不在跟前,把鼻涕和眼泪抹在袖口,像被打怕的小狗,跟在爹屁股后头,也去地里拾柴。
李憨本不打算叫顺喜的,那唐英洗衣做饭,缝新补烂,把个穷日月过出了几分生机。女人什么都好,就是不让虐待顺喜和碰她一下。李憨最没胆,一来就被这个女人给镇住了的;二是妈临死时有交代,说等于案板上供个神神哩。但两个哥哥回头看他,憨憨就觉得很没面子,壮了声气说,顺喜你也下地里去。顺喜没了玩伴,像个小布袋子,也吊在憨憨屁股后头。
憨憨家的地在泥沟里,是弟兄三个中最不好伺弄的。当初分地,先尽着长子儿,比较而言,李福的地算好的;其次是老二挑,李生挑了一块远些的地块,虽说远,却是最齐整的,一亩半分的地,不和任何人搅和,独自连成一块,好种好收;剩下憨憨,已经没了挑选的余地。憨憨的地,是他爹李栓出过蛮力开出来的,红胶泥直立的山崖上,星星点点嵌满了红燎泡,那是一种坚硬的顽石。山崖下,开出二三分大的条形地块,晴天一块铜,雨天一包脓,难种。起先,憨憨在地里种玉米,唐英过来,听说了这块地,就让改种成南瓜和红薯。娘家也有这么一块地,专门用来种红薯。秋天了,从泥地里刨出来的红薯晾干了水分,拣着个小细长的,放在柴火堆里焐,焐着焐着那香味就焐不住,自己跑出来了,红薯里吃出的香甜经久不散。憨憨依了唐英,果真,红地里种出来的南瓜和红薯吃着就是香甜,就年年种这个。
很久没下雨了,地里干巴巴的,走到红石泡上,千层底鞋都抵挡不住,烙得脚疼。憨憨朝手心吐一口吐沫,呵呵手,将镢头举过头顶,用力下去,干硬的土地立马被劈出一个白印子。顺喜在别家地里挽去年没收完的玉米秸,没镰刀帮忙,小嫩手挽出了红印子也没能挽倒一棵。“算了算了,明早起带个镰刀来,挽下一棵是一棵,你还是过这边来弄点蒿也成。”
顺喜走到条形地边的时候,就看见了几颗红燎泡往下滚落。“呀呀家!”顺喜直立的眼睛瓷了,不会说话。憨憨顺着顺喜的目光抬头,那一瞬间,纷落的顽石便像陨石一样萧萧而下。李憨胸腔里酝酿的一声“啊”溜到嘴边,他扑过去抱住了顺喜。不长眼睛的顽石砸在了顺喜和憨憨的头上,红土地上凝固着同样红色的血,使人辨不清颜色。
唐英的五脏六腑一下被掏干了,像风中飘着的纸人人,所有的血肉骨骼散了架,飘浮在了空中。按照当地的风俗,孩子是不可睡棺入土的,小顺喜被扔在野狼出没的后沟里。晚上,李福李生进了唐英的窑,一唱一和和唐英商量憨憨的后事。弟兄两个看上了唐英带过来的柏木棺材,想让这个至死也没能闻上女人味的弟弟死后能舒展一点。
那棺材是秉廉的爹在世时给秉廉妈刘高氏置办下的。土改一来,秉廉吃了鸦片寻了死,工作队说他畏罪自杀,怎么也不让睡这口材入土,秉廉是光着身子埋进老坟的。人们听了秉秀放出来的风,说谁要了这口棺谁家要遭殃。柏木棺材好,但谁也不想早睡进去,棺木才没被分掉而随了刘家。婆婆刘高氏投奔远路里的女儿时,握住了唐英的手:“妈没福分,活得太久了,赶不上睡这口棺。孩子,这是刘家最后的东西了,给你留着,百年后你用吧!”
“那是秉廉家的东西,李憨睡了不合适吧?”唐英的声气像从地窖里发出来的,丝丝带着寒气。
李福说:
“怎么不合适?憨憨春种秋收地养活你们娘儿俩,挣不下睡你这口棺?”
唐英抬起一张失去血色的泪脸:
“我不白吃他的,洗衣做饭,纺花织布,我都做过。李憨的衣裳全是我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李生说:“你是憨憨的老婆哩,你不伺候他还要伺候谁!”
“他种地,我操持家,我们俩平着,他没理由睡秉廉的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