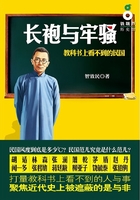现在云府的庭院里,已经站满了打手,云府的十八罗汉,已经全都整装完毕,他们都在庭下,听着江二公子的训话。江二公子表面上看起来悲愤异常,可是他的心里,却是偷着乐的。他是云府三公子中的老二,在云家三公子中,论资格,他不及老大云羽,论实力,他又不及老三云彩,他想出头,可是他没有的机会。更何况,老大的娘,是父亲的原配夫人,老三的娘,也是父亲最为宠爱的妾,而自己的娘,在承受雨露以前,只是一个婢女而己,在生下自己以后,她被他的大娘,也就是云铜的原配夫人,找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给塞到井里去了。
这些年以来,如是不是他发愤图强,处处小心谨慎,逆来顺受的话,他活不过五岁。
现在好了,老三被人杀了,老大也被人打了一个重伤,虽经府中郎中的救治,也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那张脸,却已经毁了。听郎中对他的大娘讲,云羽以后就是一个疤面汉子了,而且他还有很多的东西不能吃,不能有过份的情绪反应,不能流汗,不能流泪,各种各样的不能,让云夫人听得气不打一处来,狠狠的几巴掌下去,才终止了那个郎中的这个不能那个不能的絮絮叨叨。
现在整个云府,就是自己的天下了。他心底时暗喜,可是他在表面上不能显现出来,而是一付悲愤的样子,他现在就命令云府的十八罗汉,去德丰楼,将那个外地汉子,抓拿归案。
现在还只是未末申初时分,太阳还老高,凉州城的四个城门就已紧闭,现在整个凉州城里,都处在一片恐怖之下,很多人都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绝大多数人家,都已经关门闭户,有一些人更是在敬神,他们在祈祷,这个外来的汉子,能够走得痛快。他们在心底里感激这个外来的汉子,可是他们也深深为这个汉子而感到悲哀。
几乎所有的人,他们都认定,这个外来汉子死定了,虽然他的身手一流,可是云府的十八罗汉也不是好惹的,更何况,那个云铜的手下,还有数十万的雄兵在城外布扎。
就是州牧吴良也是这样认为的。他接到他的侄子的消息,他的那个侄子,就是与云羽他们在一起的三个公子哥儿之一,也是一个好事的主,他倚仗着吴良的势力,也经常骑在百姓的头上拉屎拉尿,用百姓们的话说,也是一个恶少。
吴良对侄子的话,不太相信,自己的侄子是一个什么品行,他心里还是有几分谱的,如果只是侄子一个人被人打了,他也不想再去追究人家了,自己无数次告诫过侄子,要积德行善,要学文练武,可是这个侄子从来都是将他的话当耳边风,不当作一回事。偏偏自己又无后,哥嫂也早死,于是他将这个唯一的侄子视为己出。
云羽被打了,这个性质就严重了,他可以忍受当着众人的面被人打一个耳光,也不能默许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让云家的人吃半点亏,虽然他不齿云家的所作所为,但自己的身家性命,财富仕途,都在别人的一个意念之间,就是有再大的悲愤也只能换作是笑脸。
他也点了二十个捕快,亲自带着队,赶到了德丰楼。
他刚到,云家的人就到了,云二公子见到吴州牧,对他只是略略的抱了抱拳,就算见过礼了,径直从他的身边走过,不再回头看他一眼。吴良的脸色变了变,马上肃容,跟在云二公子云空的身后。
他们看到了肖尘,云空问一个浑身是血的仆人道:“打伤公子的,是他吗?”
那个恶奴,用手捂住半边脸,闻言才将那只手松开,他的右边脸,高高肿起,就像一个猪头相似,他看了看,点了点头,含糊不清地道:“不错,就是他,就是他!”
吴良也看着他的侄儿,侄儿也点了点头,经他们两个人的双重确定,云空与吴良对视了一眼,都点了点头。
他们走到肖尘身边三丈之处站定,吴良开口问道:“你是谁?你可知罪?”
肖尘慢慢地睁开了眼,他从桌子上取过最后半个馒头,慢慢地撕下一块,放到嘴里,再端过那碗水,浅浅地喝了一口,才正眼着吴良,道:“这是大堂吗?”
“什么意思?”吴良身后的捕头叱道:“这是州牧大人,你连一点礼节都不懂吗?州牧大人问你话,不要说是跪着回话了,你最起码也得站起来,作揖才回答吧?难道你父母没有教过你这一些吗?”
这个捕头一定是一个狐假虎威的角色,在想主子面前好好表现,以便日后有更好的前程。这几句话说得还理直气壮,一点缝隙也没有。肖尘笑了笑,道:“礼?是相互的吧!我们两个狭路相逢,我问你是谁,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没有?有的话给我坦白交代!你听了以后,你会怎么想?”肖尘的口才也是一级棒,他的反驳也不无道理。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站在最前面的,就是胖掌柜他们。他们一个个都紧张得很,额头上的汗珠直掉,现在已是初秋了,在北国的秋天,风中已带有冬的味道了,没有理由会有这么大的汗水。
吴良抬了抬手,打断了那个捕头的话,他问道:“现在我接到报案,说你在德丰楼前,行凶打人,现在我来调查情况,小伙子,你跟我走吧,我们堂前说话。”吴良也是一个老狐狸,他没有几把刷子,也不能做到二品大员,牧守一方。
肖尘还是没有站起来,他道:“你就是州牧大人吧,请问我们已经过堂,我已经承认按了手印吗?”
吴良愣了愣,道:“你的意思是?”
肖尘冷笑道:“如果我没有过堂,也没有按手印,也没有什么人证物证等等什么的话,你凭什么说我是行凶?而不是正当防当?或者是为民除害呢?你是凭什么判定我是行凶的呢?你审都没有审,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决定吗?你是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凉州一方的百姓?”一连串的问话,问得吴良没有办法回答。
人围中也不知道是谁在鼓掌,吴良回过头来,冷冷地看了一眼,那鼓声马上就停了下来。
“吴大人,对待这样的凶人,你没有必要这样婆婆妈妈!将他抓起来就是了,如果他反抗,就是抗捕,在中汉律上,有一条写得很是明白,抗捕就是死罪,格杀勿论!”云空冷冷地道。
肖尘站了起来,看了看云空,问吴良道:“原来,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师爷或者捕快头头呀,真正的州牧这么年轻,看来我看走眼了。”他走到吴良的面前,摇了摇头,道:“不对呀,你的这个打扮,就是州牧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吴良气得脸都白了,他回过头来,对捕快们道:“去,将他抓拿归案!”
肖尘回到了桌子旁边,他一条腿喘在椅子上,道:“要抓我也是可以,但是,我必须要声明一句,要抓的话,要一起抓!两个人打架,凭什么只抓一个,而对另一个不闻不问?州牧大人,你能告诉我,这一条出自于中汉律哪一条哪一款就行了。如果你不能说出来,告诉你,一切的后果,你们必须负责!”
吴良瞪着他手下的捕快,骂道:“还不动手,是不是要我请你们呀?”
那个捕头将刀一抽,举了起来,大声地道:“兄弟们,上呀,将他绑了!如果他反抗,将他砍了!”众捕快们都涌了过来。肖尘动了,他的脚不知道是怎么的,一下子就将那张椅子带到了,他一个旋腿,那张椅子,呼啸着向众捕快们飞旋而去,众人都集中在一起,根本就没有办法躲闪,一片椅影过付出,二十个捕快,倒了十二个,一个子就倒了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