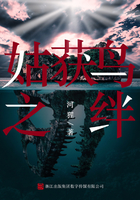“侍卫长!这是一家酒楼。“才刚刚冲进房里一行人只是扫了几眼,便从这房间里的布局推断出这里是一间酒楼。
其实不用他说,侍卫长也已经知道了,酒楼门口本来正有许多人无脑的往外冲,不过被他们这帮人撞了进来,七扭八歪的躺了一地,几乎把脑浆都给撞成浆糊。
这些本来慌不择路,无脑想往外冲的人,被这狠狠一撞,顿时清醒了不少,再一看到外面血肉模糊的大街,哪里还敢出去,不顾气质疯狂往桌子底、楼梯底下钻。
从登天楼掉落的木头残渣不断砸在这栋三层酒楼的头顶,灰尘、青砖与碎裂的各种东西如下雨帮,“唰唰”的直往下掉。
能见度降到了最低,所有人的心都高悬于空中,不断有东西从空中砸落到他们的身边,“啪”的一声,便几乎要将一个人活生生的吓死,胆战心惊的他们只能不停跟着侍卫长往前跑,不然呆立在原地的下一秒,便可能被从空中掉落的杂物,拍碎脑袋。
侍卫长自己的心也是吊着的,而且他的心里还暗骂不止,但作为家主交给他的责任,他只能一边在这混沌的空间中摸索,一边保护着小公子,快速朝酒楼内部移动。
“后厨在哪?后厨在哪?带我们去后厨!”虽然侍卫长奋力前进,但他对这里并不熟悉,所以他也找不到一个牢固支撑的地方。但随着掉落杂物的变多,他的心越来越急切,不管不顾的将一个缩在桌子底下的人拖出来,大声问道。
“那躲在桌子底下被拖出来的人心里也是焦急,虽然对他们一行人十分怨恨,但看现在情况这么焦急,也不敢表现出来,连忙朝一个方向指去。
侍卫长还未来得及说什么,那人便如泥鳅一般从他手里溜走,同受惊躲回洞穴的小兽,缩回桌子底。
“李叔,快走!”
不用小公子开口,侍卫长自己也知道,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既然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就没必要打扰别人了。
“快跑!”
侍卫长的话永远没有他的动作快,他的话才说道一半,但人已经提起了小公子,朝那个人所指的地方冲去。
“咚!”才跑了没两步的侍卫长只感觉到了一声重物撞击声,两脚脚掌突然失去平衡,止不住的向前扑倒。
顿时,整个人就像喝多了酒一样,站都无法站稳,胸口还有一种沉闷的要爆炸的感觉。
在地上滑了几步的侍卫长连忙向后看去,但只是一眼,他却能感觉到根根寒毛竖起,浑身冷汗直流。
只见一张缺了两只腿的登天楼特有的厚重桌子,不偏不倚的正好砸在刚刚那个人藏身的薄板桌子上,只看到处崩落的血浆就知道,这人的情况看起来不是很好。
不过不幸之中的万幸是,他们一行人只是被震倒,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
但越是这样,侍卫长的内心也就越激动,登天楼快倒了,他根本没有其他选择带着小公子从厨房离开这条街道,况且想要完全离开登天楼倒塌的范围,要跨越的可不仅仅是一条街道,而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公子。只能藏在这里了!”侍卫长大叫,带着小公子和刚刚从地上爬起来的众人冲进厨房。
此时厨房里早已空无一人,灶上大锅里烧着的菜,因为无人翻炒,整个房间中充满油烟与焦糊味。
几乎要另人窒息,已经让人呼吸不畅通的浓密油烟中,侍卫长看着眼前的大锅,心中突然涌现出一个特别的想法。
“找水来!”
他对着其他家奴吼道,然后一马当先的冲向其中一个还烧着菜,灶底还燃着熊熊火焰的灶台。
将袖子遮住手掌,他便直接抓住那口大黑锅,将它给整个掀了起来。
厚实的铸铁黑锅重重的砸在灶台上,里面糊了的菜肴则撒在一边。
“水呢?”
他现在似乎正在和死神赛跑,恨不得将每一分每一秒都掰开成为两半用。
”来了,来了。“一名身躯壮硕的的家仆抱着一桶刚刚从缸里舀来的清水冲了过来。
侍卫长接过清水,倒了一点在翻过来的黑锅上,瞬间黑锅的温度便降了下来。但侍卫长却没有停下,反而大吼道“都闪开!”
话还未说完,众人才走出几步,那桶水便被侍卫长全部倒进了炉灶中,熊熊燃烧的火焰顿时熄灭,但一股炽热的水蒸气,却冲天而上。
小心避过冲上来的水蒸气,侍卫长蹲下试了试炉壁的温度,除了湿漉漉的以外,温度已经彻底降了下来。
“公子,得罪了!”
侍卫长突然说道,然后将小公子给提了起来,准备塞进炉灶中。
“李叔,你?”
“公子,你的命天生便要比别人尊贵,况且,紫禁城还等着你二十年君临呢!“
侍卫长不由分说,便将秦政整个塞入炉灶中,并将刚才的大黑锅反过来扣在灶上。
“你们都学过战阵之数吧,我要你们以锅做盾,保护好公子的安全!
是的,侍卫长并没有将那些小公子未来的班底也塞入灶孔中,反而让他们拿起一口大锅,以锅为盾,牢牢保护住秦真的安全。
可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把别人也埋入灶孔中,那等下能活着人的数量,会大大增加,但小公子就有可能受伤。
所以,他宁愿选择让他们这些纨绔去送死,也要力求让小公子毫发无伤。
所以这些只是经过不长时间训练的纨绔们,便要像一个个白痴一样,顶着一口大锅迎接接下里可能要掉落的一切。
虽然他们心里都不舒服,但他们也知道,如果让秦政受伤,那不管结果怎样,他那对他不是一般溺爱的父亲都不会让他们好过的。
但对他们来言庆幸的是,灶台上站不了多少人,所以他们都能靠着一口锅,龟缩在灶台附近。
而防范从空中掉落杂物的任务,则由侍卫长和那些身强体壮的家奴们承担。
那个人仍然站在塔尖,砸在已经弯曲朝下跌落登天塔塔尖,他的脸上仍然是那般平静,没有为任何东西,产生任何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