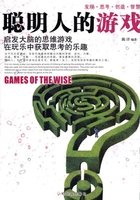立秋了,天空湛蓝而透明,几朵白云闲散地漂浮着,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不真实的迷幻感。窗外,江风扑面而来,带着一丝宜人的凉意。楼下是宽阔的黄浦江,江面波光粼粼,大小船只往来航行,构成一幅略带惆怅的写意画。
这里一九四〇年的上海外滩。
江畔,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大楼八楼的临窗办公室里,刘牧楚从大堆文件中抬起头,浅浅地品了一小口咖啡,趁着闲暇欣赏一下窗外的风景。一个多月前,他已经与杜伊霖在扬子江饭店结了婚。
师部禁闭室出了那起事故后,祁连长被调离仙江。雷师长晋升为军长,王团长升了混成旅旅长,由隋连长接任城防团。杨哲带着刘牧楚和伪钞设备飞了一趟重庆,拿回军统局批准的由杜伊霖起草的对日金融反击计划。刘牧楚变卖刘家产业,只留哑叔守着老宅,将汉信银行总部设到了上海。一年多的时间过去,凭借重庆政府的资金支持,汉信迅速从众多私营银行中脱颖而出。在银行里,夫妻俩的身份依然是董事长和总经理,而刘牧楚只是挂个名,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民政府财政部特派专员。为配合“以伪制伪”的“青蚨计划”第二阶段工作,他毅然肩负重任,组织上海私营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与日伪展开殊死搏杀。
一记敲门声响起,刘牧楚回过神。
司机王师傅前去开门,将一位客人请了进来。此人身穿毛呢西服、头戴小礼帽,皮肤黝黑、腮帮宽大,不像商人,倒像一个南洋土豪。
“老杨!”刘牧楚掉头一看,忽然孩子一般奋地叫出声来。
杨哲调任负责军统上海站的领导工作,一方面暗中配合刘牧楚夫妇的工作。
“好了,先让杨先生坐下吧。”杜伊霖闻讯从隔壁办公室走过来,为杨哲倒了一杯红茶。
“哎呀呀,真是气派,我这土包子可算开了眼啊!”杨哲慢慢坐下来,让王师傅将一只木盒呈上,笑眯眯地说:“牧楚啊,结婚也不告诉我一声,好歹讨杯喜酒啊?”
“我倒是想请,可你比田队还神出鬼没,到哪儿找啊?”刘牧楚打开木盒,惊喜地叫道:“反动式汽轮机,英国人帕森斯的杰作,谢谢啊老杨!”
“别谢我,这也是田峰的遗愿啊。”杨哲黯然答道。
刘牧楚脸色忽然沉下来,默默地将木盒关上,回头望了望陈列柜里的那台德国发动机模型,伤感地说:“哎,我现在更没有精力鼓捣机械了。转眼一年多过去,回首故乡恍然如梦,也不知仙江现在怎么样了?”
“想田峰了吧。”杨哲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道:“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玉莲妹妹在延安那边生活得很好,已经从护理培训班结业,正在野战医院实习呢。”
“好啊,这丫头总算有了盼头。”杜伊霖边说边削着苹果。
“我倒是想问一句,据说延安那边一派自由民主新气象,你怎么不和玉莲一起回去呢?”刘牧楚小心地看了看门外,压低声音问道。
“工作需要嘛。”杨哲已经向刘牧楚夫妇透露了共产党员身份,还在极力争取刘牧楚入党。他啃了一口杜伊霖递上的苹果,毫不避讳地说道:“按照关方炽留下的名单,我从仙江一路追踪到上海,直到上个礼拜,才把潜伏在这里的焦主任除掉。经过同志们的努力,日本军部苦心经营的杉机关已经岌岌可危。”
“这刀尖舔血的日子我可受不了。”刘牧楚摇摇头道。
“你们也轻松不到哪里去呀。”杨哲从杜伊霖手中接过苹果啃了一口,摇摇头道:“据说法币汇率直线下降,重庆方面大为光火,我都时时为你们捏一把汗啊。”
“与仙江相比确实困难多了,日本方面不断收集法币冲击外汇市场,投机商趁机推波助澜,‘华兴券’刚刚压下去,‘中储券’又开始兴妖作怪,搞得我们实在焦头烂额。”杜伊霖理了理一头漂亮的卷发,忧心忡忡地说。
“上午我才去了钱业公会,同仁们都表示要抵制‘华兴券’和‘中储券’,但如果没有战场上的胜利,要从根本上稳定我们的金融市场无异于缘木求鱼。”刘牧楚正了正眼镜忧郁地感叹。
“你们切不可灰心丧气。日军咄咄逼人,汪伪政权甚嚣尘上,目前看来我们仍然处于劣势,但日伪势力已经在走下坡路。就在前几天,八路军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抗日大战役,已经出动了一百多个团……,国共只要真诚合作,没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杨哲目光灼灼地盯着刘牧楚,又看了看杜伊霖,耐心地说:“记得我给你们的那本《论持久战》吧,现在我们必须再咬咬牙,抗战最后的胜利就快到了!”
说完,他笑了笑,故意谦虚地问道:“牧楚啊,那个叫雪什么的怎么说的来着?”
“雪莱。”刘牧楚盯着对方乐观自信的笑脸,缓缓答道: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