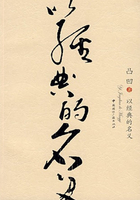军旅作家李存葆一篇《飘逝的绝唱》,洋洋洒洒三万言,仰古俯今,纵横捭阖,把流传久远的《西厢记》和一时之盛的普救寺汇入一炉,以春秋笔法,以大家气度,或发思古幽情,或作深沉叹息,挥洒得淋漓尽致。作品由《运城日报》首发,本地读者争相传阅,复印。《散文海外版》选载后,永济新华书店一次竟购进5000册。永济市政府召开了一次作品研讨会,北京、天津、太原、西安的作家、评论家冒着酷暑,乘兴而来。可以说形成了一个近年来并不多见的起码可以说是区域性的文学轰动效应。
拜读之后,除了与众多读者一样欣赏、激动和感悟之外,山西籍、晋南籍、永济籍的作家们该作何感想呢?普救寺我们不知已去过多少次了,张生莺莺的爱情故事我们也改编成故事片、戏曲片、舞台剧了,《西厢记》的艺术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作为作家也不会一无所知,但是,我们没有人注意到这一题材资源。李存葆来永济转悠一圈,竟弄出这么一场文学轰动,不应该引起我们一些思索么?
比起李存葆来,我们缺少些什么呢?
缺少的是对生活的深入思考,缺少的是对人生和社会沉重的责任感。这是衡量是否是优秀作家的重要尺度。
王实甫写作《西厢记》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他面对的生活现实是罪恶的封建礼教扼杀着一代代青年男女的爱情理想和婚姻自由。他看到一个个青春生命由于缺乏爱情的滋润而枯萎了,他看到一对对青年男女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中煎熬挣扎。作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王实甫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终于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大胆呼喊和深刻思想。他把自己的艺术目光,转向已经流传了五六百年的崔张故事。那时候的崔张故事,是张生被崔莺莺的容貌吸引之后的迅速厌倦,是封建士子始乱终弃的道德完善。只有经过王实甫对现实生活深入的理性思考和强烈的道义责任的驱使,才使崔张故事通过他的艺术描写发生了质的飞跃:崔张两位青年男女摒弃门第观念,争取婚姻自由,冲破封建藩篱,叛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大胆私下结合,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使崔张故事成为经久不衰的爱情经典。
而李存葆关注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呢?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负面,物质力量的强大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弱化导致了一定范围的精神迷茫和道德迷失。在强大的物质利益和金钱诱惑面前,原有的道德原则已经开始失落而且得苍白起来。于是,本来是男女之间心灵碰撞和相互欣赏的爱情,在不少地方和人群中已经退化到男女之间的简单吸引甚或是金钱交易下的异性服务。有识之士对这类现象虽然不无忧虑但很少进一步深入思考,许多作家虽然已经把笔触伸入到这一领域但却缺乏深入剖析。时代需要优秀的作家对此进行王实甫式的思考和抒写。
真该庆幸,我们毕竟拥有李存葆这样的优秀作家。面对现实中大量充斥着的桑拿按摩、歌厅包间、“三陪女”、“包二奶”、粉领阶层、猎艳大款等等醉生梦死现象,面对男女之间的欣赏倾慕还原成简单吸引,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蜕变为感官刺激和金钱交易现象,李存葆投进了他锐利的历史的目光,投进了他责任的良知的目光。经过深刻地理性思考,作家终于提出了一个新时代的生命追问:
“何处才是人性解放的最后底线?”
如果说王实甫面对的是感情园地的贫瘠,那么李存葆面对的则是感情园地的杂草丛生。这是同样可怕的精神疾患,李存葆能不发出这样的追问么?
和王实甫“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一样,这一声生命的追问,同样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
现实社会太需要这样的追问了。思考已经成熟,追问已经提出,作家自然会将他看到的情感还原和爱情蜕变现象,联想到一个具有对比意义的参照——经典爱情的参照。
这个参照在永济。
也在河东,在山西。
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西厢记》,这就是我们经常流连的普救寺。
这就是我们和李存葆的差距。
这就是普通作家和优秀作家的差距。
这也是我,一个普通作家的自问和自知。
《运城日报》200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