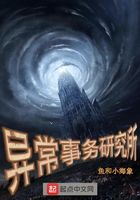“怀上甚啦?”“娃啊。”“不会,俺这不是已经有娃了啊。”“我是说,你自己的娃。”“志强就是俺自己的娃。”“我说你是不是无知啊?你不觉得你的腰比先前粗了吗?”“是粗了不少,裤腰肥了有二寸多。俺也奇怪,原先三四十天就要尿几天血,尿的时候一拧一拧的小肚子疼,这有好些日子没尿了,小肚子也不疼了,可能是吃小葱吃好了。”“你怎么不敢承认呢?上回回来,你家虎子没上过你的炕?”“上是上啦,没睡着,急哩忙慌就走了,你可不敢跟外人说虎子回来过。岳家门里的后人要陷害他呢。”“什么感觉?”“感觉?甚叫感觉?”“舒服不舒服?虎子上你的炕舒服不舒服?”“不舒服。”“他没上你的身?”“压得俺喘不上气来,生疼生疼的,害得俺早早尿了血。噢,对了,就是从那回尿血以后,就再也没尿过。”“你娘就没给你讲过,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做甚?”“没有,俺娘在俺三岁过生日那天好好的就死了,俺爹说是俺妨的。”“你那是第一次做爱,处女膜破了。”
“甚是处女膜?”“跟你说不清。第一次做爱都会出血都要疼,以后就不疼了,夫妻在一起是非常舒服、非常快活的。”“你说他那么个大块头压着你舒服?哄鬼哩,俺连气也喘不过来。你家五槐是不是也压过你?”“废话,他不上我的身,我咋能有了娃?”“噢,原来娃就是男人压出来的?怪不得你婆婆说,男人不在就有不了娃。”“你啊,真傻,女人就是让男人当下种的庄稼地使换的,一个萝卜一个坑,男人是萝卜女人是坑。他舒服,你才能舒服。”“俺没觉得舒服,疼,就是疼,生疼生疼的,疼得很。”“愚昧。我和五槐天天在一起,一晚上好几回呢。”
“那不要了你的命?俺可不想受那罪。”“你呀,有福不会享。”“甚的个福,俺不稀罕。”
又到了间苗的季节,那活儿真是个苦营生,偷不得懒,蹲在地上,一步一步往前挪。她突然觉着肚子里的肠子在动,站起来,扶起衣襟看,好像肚皮在颤抖;她用手按了一会儿,反而动得更厉害了。她急急跑进五槐家:“五槐媳妇,你快给俺看看,这是咋啦?俺肚子里是不是蹿进蛇啦?一个劲儿地动。”“这叫胎动,我给你算算,除了他们送志强回来那一次,你记着虎子再没回来过?”
“没,没回来过,就那一回。你可不敢说,让邻居知道了,还不把他打死。”
“哎哟,我的姐姐啊,你不说虎子回来过,肚子里的孩子哪来的?谁给你做造下的?不敢再瞒了,对你的名声不好。”“不是俺要瞒,俺真的不知道这娃是咋怀上的?俺嫂子进门的时候就怀着娃,不到半年就生下了,你这不也是早早怀上了娃,俺还以为俺像了俺家大姑姑,不会生娃呢,俺大姑姑一辈子就没有娃。”“女人就是怀娃娃的。”“那你跟俺说说,这娃娃是从哪出来啊?屙出来的还是尿出来的?还是从胳肢窝挤出来的?”“你白活这么大,连生娃娃也不懂。”“俺又没见过生娃娃,是不是和鸡下蛋一样?”
在改灯眼里,五槐媳妇眉棱骨上的那颗美人痣,就是智慧囊,懂得好多好多事,还会写毛笔字。那天,她们几个年轻媳妇坐在街门道听五槐媳妇讲戏文,略懂点风水的八爷爷说,五槐媳妇是女人精,甚也知道,是如来佛的书童转世,旺夫的命,你看五槐,人家没几天就当上了农会主席,在这个村说一不二。
五槐说,她说的那些故事,书本本上都有,她认识字,所以她比你们知道得多。他向大家述说了志强的来历,公开了虎子的身份,改灯怀孕,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人在背后再指指点点了,再也没人说改灯是什么精啊怪啊的了。
改灯和五槐媳妇都快做妈妈了,五槐娘帮着改灯准备生孩子所需要的一切,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抽空俩孕妇就凑在一起,谈感受谈未来。改灯心灵手巧,在五槐娘指点下做了许多小衣服小被子;五槐媳妇就给她讲故事,改灯对五槐媳妇敬佩得是五体投地。
村里人都知道虎子是在给共产党做事情,当然是照顾对象,地里的活儿有帮耕队给包了。改灯领着志强牵着羊,经常去地里看看。今年的谷子长势不好,不知道是帮耕队的人不尽心,还是像五槐媳妇说的,地得轮番种,换个品种,连着几年种一种作物,收成当然就不理想了,她问她为什么,她说跟你讲不明白。
五槐媳妇知道的事情真多,懂的东西也多,能掐会算,告诉她甚时候才会生娃娃,还有多少天,改灯客气地谦让着,你的肚子比俺大,你先生,俺侍候你。
五槐媳妇哭笑不得,这是谦让的事情吗。
因为你的肚子比俺的大,就该着你先生嘛,俺不跟你抢。改灯既认真又固执。
五槐媳妇看看自己的肚子,确实比改灯的大,就安顿改灯,多吃点有营养的食物,开水就窝窝头不行,影响孩子骨骼、智力的发育,还影响奶水……改灯听得目瞪口呆,神了,五槐媳妇简直像她讲过的那个会借东风的诸葛亮。
身子越来越笨了,老天爷真是照顾她,不闹口不瞌睡,精神头一天到晚足足的,不知道甚是个累,放下镰刀拿簸箕,从来不舍得让自己歇一歇。
志强睡着了,她看着自己微微颤抖的肚皮,这个娃会从哪儿出来啊?她记着她问过五槐媳妇,五槐媳妇笑着说,你家虎子的肉萝卜从哪儿进去,娃就从哪儿出来。管他呢,到时候有五槐娘帮着,娃肯定会出来。她摸摸胳肢窝,她想不出这个娃娃有多大,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期盼。虎子,你快回来吧,俺也给你生个肉小小。
苦日子难熬,有期盼的日子过得更慢,每天清早一担水,那是必须的。她挑水的样子很好看,走起来轻飘飘的,胳膊一甩一甩的,小志强拽着后桶边边跟着跑,成了村里的一景。
五槐媳妇给五槐下了命令,以后虎子家起圈、垒墙、担水等体力活,统统由你负责,五槐当然义不容辞,面面俱到。在他去县里开会走以前,给改灯挑满了水缸,用个两三天足够了。会议通知上只写着一天半的内容安排,今儿已经四天了,五槐还没有回来,瓮里没水了。她不好意思找别人帮忙,心想,不就一担水嘛,不能总麻烦别人。她挑着空桶,领着志强来到河边,好长时间没来挑水了,看着清清的河水,心里那个惬意没得说,忘了自己是个有身孕的人。她潇洒地像往常一样,把桶甩向河里,水很快就满了,她使劲一提,没想到连人带桶滑倒在地,志强吓得“嗷嗷”大哭。
改灯觉着肚子一阵儿紧似一阵儿地疼,怎么也爬不起来,她以为自己不行了,要死了:“快,快去喊三爷爷。”
拾粪老汉正在自家地里忙活着,志强跑过去拽住老汉的衣襟,指着河边。
老汉忙招呼着人们把改灯抬回家,孩子已经在裤裆里了。
接生婆婆赶到的时候,改灯还没醒过来。娃娃只有鞋拔子大,是个妮子。
改灯第二天就下炕了,好像没事人一样,还有点尿血,尿就尿吧,又不是没尿过,生娃娃原来就这么简单,她觉着很轻松。
五槐娘不让五槐媳妇去看改灯,说是有身子的人不能见血。五槐媳妇就坐在当街石条上,砸核桃、嗑瓜子吃,说是这两样东西对孩子大脑发育有好处。志强像个跟屁虫,天天围绕在五槐媳妇的身边,蹭点好吃的。五槐更是不顾一切地去满足老婆的害口,跑了三十里山路,剪回了一篮子醋柳柳,什么连金儿、山梨儿、松子儿,想起一出是一出,找人要、托人买、求人借,想尽了法子给媳妇解馋,娘家人也没闲着,今天给送来了麦子面,明天送来软糯米,村里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白米,都来看稀罕。五槐媳妇就指点着五槐娘做好了,给左右邻居都尝尝,当然也忘不了给改灯送一碗。
人们都眼红五槐娘养了个好儿子,娶了个好媳妇,跌进了运气洞里。见面就恭维她,你家祖坟上冒烟了,长树了,儿子成气候了。看看媳妇命多好,娘家底子厚,这还没到日子,就牵来一只羊,五只下蛋鸡,给她备月子。
五槐媳妇更是得意,逢人就说,俺找医生把过脉,保证是个长萝卜的肉小小。五槐娘高兴得屁颠屁颠的,美滋滋得合不上嘴,更舍不得让媳妇动弹,每天就像供菩萨一样供着。五槐媳妇的肚子,就像正在往里打气的皮球,越来越大。
妮子没人稀罕,该给娃取个甚名字呢?不外乎猫啊狗啊,花啊草啊的。改灯不喜欢,她找五槐媳妇帮忙,人家有学问。五槐说,给娃娃起名字是大事,是有讲究的,咱这地方,男人当家、男人做主,特别是给娃起名、给老人过寿,都是男人说了算,等虎子回来再起吧。
五槐媳妇一听火了,凭什么要男人当家?不等他,现在就起,他这个爹倒是当的容易,进门就上炕,提起裤子就开拔。你在鬼门关上转悠的时候,他在哪儿?凭什么让他做主?我看,就叫玉,玉峰吧,玉代表女性秀丽、珍贵,但不能像你一样太温顺了,得有点锋芒,让她锋芒四射,咱们这里都是山,就叫玉峰,玉峰。
五槐娘说,名字可不能随便起,那得查查,按祖上的说道排,看石家这一辈占哪个字,不敢乱了辈分。
五槐媳妇:“甚的辈分不辈分,要不就叫她虎妮,专门跟她爹争辈分,让他不顾家、让他不负责任,等他回来,俺出面,俺就替你跟玉峰她老子论个高低。”
五槐说:“算了算了,暂时就这么叫吧,玉峰?实在有点硬邦邦的不好听。不过,妮子无所谓,叫甚也行。”
五槐媳妇不高兴了:“咋?不待见妮子?如果我生下闺女,你还要窝尿盆里捂死啊?”
五槐说:“哪能呢?闺女小子俺都待见,暂且就叫她玉峰吧,等虎子回来再改。都是男人说了算的事情,咱是外姓人,不能给人家做主。”
五槐媳妇霸气地说:“玉峰娘,从今天开始,这妮子就叫玉峰。他男人是人,咱们女人也是人,虎子他对这个家不负责任,管种不管收啊?他把志强送回来,这就没事啦?没影啦?甚东西,等我见了他,我替你收拾他,替你出气。我早就看不惯了,新婚之夜说走就走,回来什么都不问,就知道上炕放他的劲,别人的死活他连问也没问。噢,你舒服了你快活了,提起裤子就走人,连个信儿也不捎,哪有这美的事情!要是我,哼。”
改灯为了缓缓气氛:“不说他了,你生下了,肯定会起个好名字。”
五槐媳妇随口就来:“闺女叫喀秋莎,小子叫手榴弹。”
五槐认真了:“啊?这叫甚的名字。”“你不是到现在也忘不了做地雷、手榴弹嘛,我就希望闺女俊俏、儿子结实,就像铁疙瘩一样,我儿子,我怀的肯定是儿子,就叫铁蛋。”
日子过得飞快,小玉峰会翻身了。每当晚上,收拾停当,看着一双儿女熟睡的样子,改灯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她拿出针线笸篮,继续给虎子做鞋,心里想着,虎子,你快回来啊,你看看咱娃多喜人,生娃娃原来就这么简单,你回来,俺给你生一炕的娃娃,男欢女叫的,多热闹,不愁吃不愁穿的,这日子多滋润啊。每当想到这,她就拿过镜子,呆呆地看着自己,脸上是不是又添了皱纹、鬓角是不是有了白发?她翻找了半天,没有,她还是那么年轻。
她认为自己不丑,好像脸色比做闺女的时候还红润,要是虎子现在就像那天一样,突然回来,她就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她为自己的想法羞红了脸。
五槐隔着墙,用打枣棍子轻轻地敲着窗户:“虎子家的,虎子家的,睡了吗?快起来,你快过来看看,她肚子疼得可炕滚。”“那你过来帮俺照护这俩娃,别掉地上。”五槐跳墙过来:“知道知道,你快过去看看,是不是要生啦?你生过娃,知道火候。”“俺去叫接生婆。”“老太太已经过来半天啦,使不上劲儿,哭天喊地的,折腾好一阵子了,俺心里慌慌的,你去帮帮,俺给你照看俩娃娃。”
五槐媳妇满头是汗,哎哟哎哟叫个不停,惊动了左右邻居,听到信儿的妇女都来了,看看能帮什么忙。
接生婆说:“来这么多人做甚?你们又插不上手,多一个人就多一个时辰,等着吧,早着呢。”
五槐娘婉转地劝走邻居。
五槐媳妇龇牙咧嘴,疼得脸都变形了,生娃娃原来这么怕人啊,就像被小鬼捏住了筋,一会儿站起、一会儿爬下,身不由己,炕上地下地来回蹦,无济于事,骨盆就是不开。
五槐媳妇就这样折腾了三天三夜,早已经筋疲力尽,还是没有生出来,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叫喊了,大家急得团团转。丈母娘请来了镇上的大夫,是个男人,五槐娘已经顾不了这些了,跪在地上:“救命菩萨,快帮帮俺媳妇,只要母子平安,俺给你磕头……”
大夫摸了摸五槐媳妇的肚子:“不能再等了,臀位,脑袋太大,靠她自己的力量是生不出来的,拿剪子来。”
五槐媳妇紧紧握着改灯的手,她阵痛的时候,就咬改灯的指头,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她的痛。改灯默默忍受着,她总想给她些力气。
五槐媳妇早就没力气了,不喊不叫了,泪也不流了,闭着眼睛,头发像被水洗过一样湿漉漉的。五槐娘和接生婆一人压着一条腿,大夫双手交叉使劲往下压,只听见剪子“咔嚓”一声,随即就是五槐媳妇声嘶力竭的喊了一声:“娘……”
大夫毫不迟疑地伸进手去,生拉硬拽把孩子掏出来,提住双脚,一下一下拍打着,孩子的脸青紫,半天才哭出来。
改灯觉着五槐媳妇的手突然松开了:“好了,是个小子,俺看见娃的小鸡鸡啦。”
五槐媳妇脸色苍白,闭着眼。
丈母娘摸着闺女的脸:“妮儿,醒醒,俺知道你太累了,哎哟,大夫,你快看,咋这么多的血。”
“不好,大出血,快,堵住、堵住。”接生婆没堵住血,反而弄了自己一脸一身,像个妖怪,改灯吓得快要哭出来。
血像漏桶里的水,小溪般的潺潺流出,越来越多,接了一盆又一盆。
五槐媳妇的嘴唇渐渐变白,跟她的脸色差不多,像被烟熏过的墙皮。
五槐媳妇死了,她没有看自己儿子一眼,耗尽了最后一滴血。
改灯吓坏了,好几天没有缓过劲儿来,奶水明显少了许多,玉峰饿得哇哇直哭,可她顾不了自家妮子,她得留这一点点的奶水喂铁蛋,没娘的孩子更让人疼。
五槐娘经不起这样的打击,病倒了。
五槐一下瘦了十多斤,顾了老的顾不了小的,孩子扔在虎子家,不闻不问。改灯一边玉峰一边铁蛋,同时奶着两个娃。五槐忘记了工作,忘记了儿子,每天蹲在老娘身边,唉声叹气。他根本不知道,给娃娃刮屎、洗尿布这回事,给改灯挑水的任务也忘记了。改灯只得领着志强自己去挑水,断不断的还得过来看看老太太。老太太心里也憋着一股子怨气,不是这个愣小子,俺的媳妇咋能要了命?
死了谁苦了谁,活着的人总得活,改灯强挣强扒地带着三个娃度日子。
五槐娘渐渐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看着孙子会笑了,会和玉峰抢奶吃了,老太太干脆就住进了虎子家,她想帮着玉峰娘,把三个孩子养大。
五槐心灰意冷,整天窝在家里睡大觉,心情不好,母子俩还短不了要戗戗几句,去了村公所也是见了谁都没好气,生活一下子陷入了低谷。
五槐娘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指着五槐的鼻子骂,俺二十多岁守寡,还不照样把你拉扯大,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还不如个女人家,你看看人家玉峰娘,该下你啦?还是欠下你啦?凭甚让人家给你奶娃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