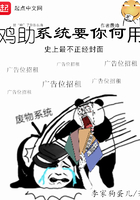故事发生在荒唐年代的1967年。
田国军和肖娆是一对恩爱的年轻夫妇。国军由于天生的长短脚残疾,高中毕业以后没被高校录取。他靠自学具备了英语、法语的书面翻译能力,靠长期为书局翻译书籍谋生,属于自由职业者。而肖娆则是美术学院的人体模特。
他们原先工作、生活在一个省会城市,“文革”的熊熊烈火燃烧起来以后,他们眼看到举凡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都受到冲击,担心有朝一日烧到自己身上,于是逃离都市,逃到叔叔所在的一个小县城。由于叔叔家6口人蜗居在10多平方的小屋里,他们只好另租居所。
他们原以为这里可以是避世的桃花源。没想到,住下不到两个月,一天晚上深夜,住房的木板门突然被粗暴地踹开,一群臂戴红袖箍的人闯了进来,说是接到举报执行搜查。
原来是几户“革命警惕性”很高的邻居举报了他们。
举报的最大疑点是,这一对夫妻从来不吵架。他们深居简出,有时外出购物办事,回来后就“砰”的一声关上房门,从不与他人交往。邻居们认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不可能留有阶级斗争的真空地带,这一对来历不明的“外来人”十分可疑。于是到“工纠”(工人纠察队的简称)举报。
工纠队长一想,在白色恐怖年代,就有一些革命者,假扮夫妻,潜伏在敌占区,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如今是“红色恐怖”年代,莫非这一对男女反其意而用之?
那时候,“专政工具”被滥用,无需搜查令即可抄家。“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嘛。
工纠这么一搜查,果然搜出了大批“罪证”。
一是许多“洋文书”和写满洋文的稿纸,这分明是“里通外国”罪。二是许多裸体书画,足以证明这是“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方式”。
于是连夜对田国军和肖娆执行“逮捕”。
连夜突审。
田国军的名字成了第一条罪状——他取名“国军”,就是准备迎接“国军”反攻大陆。
田国军连连喊冤。他说,他们那里的田氏族人讲究辈分,轮到他这一代,男性是“国”字辈,只第三个字有所选择。
国军生于1940年代初。当初,爷爷给他起名“国君”,意为希望他长大后做君子不做小人。新中国成立后,毕竟他家成分颇高,感到名字还是小心点好,于是改名“国军”,意为欢迎解放军进城。这些工纠队员哪里肯信,认为他是砌词狡辩,于是一顿毒打。
至此,里通外国即间谍罪、梦想变天罪和“传播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方式”罪已成铁证,无可“翻供”。
问题是,替哪国当间谍?都犯了哪些罪行?需要一一落实。
开始时,田国军据理力争,即使被打得皮开肉绽也不招供。
工纠队采用“疲劳轰炸”手段折磨他。工纠队每天2小时换一批人,不分白天黑夜持续拷问。
人可以忍受饥饿和皮肉之苦,但无法承受几天几夜被剥夺睡眠的折磨。科学实验证明,人在太长时间得不到睡眠,就会出现幻觉,甚至暴亡。
在三天三夜持续不断轰炸之后,田国军精神崩溃,胡乱认罪,虚构了接受某国派遣,潜伏搜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革”情报的“罪状”,并且签字按下指模。
为此,田国军被判无期徒刑。肖娆以“协同间谍罪”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直至1978年复查案件时,国军和肖娆才双双改判无罪释放。但这时他们已含冤被关押11年了。
30多岁时,他们才诞下一个独生女儿田蕊。
女儿长大了,读的法律系。大四那年,老师布置了一个社会调查的课题。田蕊选择的课题是《从“文革”个案看法制的缺失》。之所以选这样的选题,是因为她在日常生活中偶尔听父母讲起,“文革”年代无法无天。田蕊选择了父亲作为社会调查的对象。
于是,父亲就带着沉重的心情,向女儿讲述了夫妇俩在“文革”初期的离奇遭遇。讲到动情处,父亲几度哽咽,潸然泪下。
没想到,田蕊不但不悲伤,反而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她说,老爸老妈你们是书读多了,成了书呆子,是太过迂腐惹的祸。你们不懂得顺应时势。所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要是你们也像其他人一样,三天两头砸锅打瓢,喊打喊杀,寻死觅活的,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