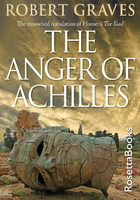从紫禁城出来,穿着铁靴的刘统勋叫上戴着枷板的纪衡业,两人踏着晨曦,叮叮当当地慢慢地走到京城一家有名的汤池。
早晨汤池没有人,两人脱掉枷板和铁靴,温暖的汤池水,熨帖了紧张的皮肤和神经。
刘统勋道:“好好泡一泡身子,若是我没说错,这是你纪衡业此生最后一次泡澡了。闭上眼,把脑袋浸在池子里,出出汗,活活经络,好戴上枷板去刑部大狱。”
纪衡业在雾气里仰着脸:“刘大人,我想请求上朝奏述诸城空仓案时,让我亲自把那袋沙子扛到殿上去。案子是我犯下的,我得将罪证扛着。再说,我若能上殿,就能对百官们说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刘统勋一抬手:“这句话留到上殿的时候再说吧。”纪衡业道:“刘大人愿成全我?”
刘统勋把一块布巾递上:“好好洗净身子,等会儿再让剃头匠给剃个头,将满脸胡子也刮了。还是那句老话:剃剃头、刮刮脸,有点晦气也不显。若是有来生,再干干净净做官吧。”纪衡业泪流满面。为了不让刘统勋看见,他把脑袋泡进了热水中。
洗净一身的尘土之后,纪衡业穿好衣服,又重新戴上枷板,跟在刘统勋身后走出澡堂子,从袖里取出一张纸片,双手递给刘统勋:“这是罪官在来京的路上写下的名单,我所知道的那些在户部清吏司的贪官污吏,全都在纸片上了!”
刘统勋接过纸看了看,收入袖中:“这张纸,或许能换你不死。你放心,我会提请三法司慎重审理此案!”纪衡业苦笑着摇头:“我这是在赎罪,谁也不必为我脱罪。”
次日清晨,大雨后的紫禁城皇城浮着一层水雾。乾清宫内,凛冽的寒风中传来“啪啪啪”的上朝鸣鞭声。阳光似乎是被鞭子抽打出来的,在云缝间渐渐射下一道道淡黄色的金线。
众臣进殿,列班,乾清宫正殿一片异样的沉默。乾隆扫视一会儿众臣,目光落在刘统勋身上:“刘统勋,你这一路走来的时候,朕老远就听到你的铁蹄子底下传来了金戈铁马之声!朕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响声了!”
刘统勋道:“皇上这是在告诫微臣,沙场之马该如何效力!”乾隆笑了笑:“说得好!”讷亲的眉头暗暗拧了一下。
殿前太监在大门外鸣鞭,众臣下跪。
刘统勋扶着残腿,痛苦地跪下。
乾隆道:“朕不是恩准你免跪么,你怎么也跪下了?”刘统勋的腿痛得直冒冷汗:“微臣若是哪天挺不过了,再恳求皇上免跪吧。”众臣对着端坐在须弥座上的乾隆山呼:“臣等恭叩皇上金安!皇上万岁!万万岁!”乾隆道:“都平身吧。”
众臣从地上爬起。刘统勋硬撑了几次,没把残腿给撑起来。讷亲嘴角露出一丝嘲笑。跪在一旁的梁诗正急忙将刘统勋扶起。
梁诗正低声道:“刘大人能回来,大清国有望了!”唐思训眼睛放着光,把手伸向刘统勋:“刘大人可回来了!”刘统勋与唐思训握了握手,用力摇了摇。唐思训低声道:“尽在不言中!”刘统勋也低声:“昨日回来,还没来得及拜望二位大臣,今晚上咱们聚聚。”
乾隆朗声:“昨日,天公打下了大雷,而且还打了好一阵子,乾清门的殿瓦落下了一大堆,听说太和殿的日晷也震裂了。朕心里很不踏实,找来了天象书看了看,看到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冬日雷,遍地贼。’这意思就是,朕的大清国并不太平,朕的身边到处有贼人。细想之下,这话也对,把爪子伸进军机处的裕善是贼人么?一把金剪子剪出的十大臣是贼人么?都是大清国的贼人。朕在书上还看到了另一句话,那就是:‘雷打冬,十个牛栏九个空。’也就是说,这冬天的大雷在提醒朕,在朕的面前有一个‘空’字!”
众臣脸色紧张,都屏住了呼吸。
刘统勋的脸色却格外的平静。
乾隆道:“裕善和十大臣这帮子贼人,如今都已下了狱,‘遍地是贼’这句话,今日就暂且不议。贼人之外,那就是‘牛栏之空’了。好吧,朕和各位臣工一块儿来议议,这个‘空’字到底是怎么回事?有谁愿意来回答朕?”
一直在瞅着机会说话的张廷玉见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出列:“老臣以为,出了裕善和十大臣巨案后,又陆续将涉案的犯官揪出了一大批,皇上身边的可用之臣已是空了不少,这个‘空’字,正是应了此意。”
不少大臣点头附声:“对,对!”
讷亲听出乾隆是要为刘统勋的出场打开场锣鼓,也抢着表态:“在皇上身边,虽然可用之臣‘空’了,可刘统勋大人回来了,足以以一当十,填补这个‘空’缺!”
刘统勋声色不动,静静地听着。
张廷玉急忙开口:“对!空缺一补,那就实了!”
乾隆道:“你们说的都没错,刘统勋回朝,填补了这个‘空’字。可你们或许不会想到,刘统勋昨夜在见朕的时候,也给朕带来了一个‘空’字!这个字,逼着朕一夜未眠,眼睛一直睁到天明!这会儿,朕要是告诉你们,这个‘空’字就是一出戏,一出名叫《空城计》的戏,你们都会信么?”
殿上鸦雀无声。
乾隆道:“这出《空城计》是怎么唱的,刘统勋,你来告诉各位!”刘统勋出列,铁靴声在殿上“咚”的一声大响。众臣一惊,回脸看着刘统勋。刘统勋道:“我想借一把算盘用用,谁有?”
众臣不明其意,怔然。
刘统勋看向梁诗正:“梁大人,你在户部有‘铁算盘’之称,那我就借你一用吧。你说,入库的运粮马车,每辆车能装多少粮食?”
梁诗正道:“粮食入仓,每袋一石,每辆马车能装粮食二十袋,也就是说,一车粮合计为二十石。”刘统勋道:“好!一辆马车能运二十石,那么二千五百石粮食得装几辆马车?”梁诗正道:“得用一百二十五辆马车来装。”
刘统勋道:“大家都听明白了,要将二千五百石粮食从仓廒里抬出来,搁上马车,等验粮官验过以后再运回仓去,至少就得装一百二十五回马车。我这么算,对不对?”众大臣道:“对!”
铁弓南低声问张廷玉:“他怎么当真像是上了沙场?”
张六德站在乾隆身边,对着殿上重喝一声:“安静!”
殿上安静下来。
刘统勋道:“有一座官仓,存粮二千五百石,朝廷派官员下去验仓,那些仓官们便开始劳师动众,将仓廒里的这二千五百石粮食全抬了出来,搁马车上,赶着车来到验粮官的面前重验一遍,这合情合理么?当然合情合理。可是,要是我告诉各位,本该用一百二十五辆马车才能装下的粮食,只用五辆马车就装下了,你们信么?”
大臣们议论起来。
刘统勋道:“你们当然会信,一辆马车要是装二十五回,那么,五辆马车装上一百二十五回,二千五百石粮食就运全了。梁大人,我这么算账,有错么?”梁诗正道:“没错。”
“可是,要是我再告诉你们,这五辆马车只是装了二十袋粮,在整个验粮之时再也没有装过车和卸过车,就把二千五百石粮食都运了一遍,你们信么?”刘统勋道。
大臣们又议论起来,纷纷摇头:“不信,不信!”
“若按刘大人的说法,这五辆马车上,只有一百石粮食!”梁诗正道。
刘统勋道:“对,只有一百石。我纳闷的是,一百石粮食能变成二千五百石粮食吗?如果我说能变,恐怕这儿的每位大臣谁都会笑话我;如果我说不能变,这儿也有一个人会笑话我。这个人是谁呢,是铁弓南大人。”
就像一瓢冷水泼进了油锅,大殿上顿时炸了起来,臣工们纷纷议论,都把脸转向铁弓南。讷亲眯缝着眼睛,默默地观察着各个大臣的表情。
铁弓南怔愣了一会儿,忽然哈哈大笑:“我还能笑出来,是因为我记起了乾隆元年那会儿的一件事!那天,刘延清就站在这块地砖上,抬进了一座粮仓,给咱们这些大臣们演了一出河南的‘空仓计’。那时的情景,想必各位都还历历在目!实在说,我对刘大人肃贪正纲的勇气佩服之至,不仅如此,还时常提醒户部的司官们,粮仓就是生死场,谁不想活了,谁就上粮仓造假去!七八年下来,据我所知,户部没一个司官敢在粮仓上再做手脚的!不单如此,连各省州县的粮道官员也噤若寒蝉,都将这个生死牌举在头顶,从不敢轻慢!甚至连户部尚书裕善这么一个贪得无厌的大蛀虫,他敢染指的也只是帑银,只是田产,而不是粮仓!刘大人,我说这么一番话,你不会不懂我的意思吧?”
刘统勋道:“这么说,铁大人是不会笑话我不能将一百石粮食变成二千五百石粮食喽?”铁弓南道:“刘大人,在皇上跟前,有你这么开玩笑的么?”
两人对视,都“嘿嘿嘿”地笑起来。讷亲摸着下巴,也笑出了声。刘统勋道:“开玩笑,我不敢;开杀戒,我敢!一百石粮食要是变不出二千五百石粮食,那就是某些人的万幸;如果一百石粮食变得出二千五百石粮食,那就是某些人的万劫,这个杀戒谁也逃不了!”
铁弓南脸色顿变:“刘大人,你一回朝堂就吃上了我,是么?”
刘统勋道:“不是吃,是吐!你得和我一样,一吐为快!当然,我知道你铁大人不会蠢到教别人如何去变把戏,也更知道你压根就没想到诸城官仓的二千五百石粮食在别人的手指上玩得滴溜溜地打转。我只是在告诉你,如果不是你的失误,就不会发生这种骇人听闻的事!”
“听明白了,你说的就是山东诸城那二千五百石贡粮?”铁弓南道。刘统勋道:“看来,你还是记起来了!当着皇上和众臣的面,请你把这二千五百石粮食为何没有运到京城来的事讲个明白!”
铁弓南道:“京通二地的仓廒年久失修,这两年,正在一座一座地修缮,各省每年的贡粮若是全都运到,只能搁在露天。为不损耗山东的这批好粮,我拜托山东巡抚萨哈谅,将诸城的二千五百石粮食暂存在官仓中,待来年京通二地仓廒修成之后,再一并解到。好了,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信不信由你!”
刘统勋道:“铁大人所说当然句句是实,可我还是要问你,你把这大宗的粮食存放在诸城,可曾派人去看过?”
铁弓南语塞。
刘统勋道:“你哪怕是派一位司官去过那里,就不会再冒出一百石变二千五百石的天下奇事了!铁大人,你想过这‘借仓’二字的背后,会有什么交易么?你想过有人会借你的手如何瞒天过海、暗度陈仓么?你想过这二千五百石粮食如今在何处飘荡么?”
铁弓南的脸色苍白如纸,突然将头顶的帽子摘下,往地上重重一摔,气得白胡子翘了起来。铁弓南道:“我铁弓南活到五十岁,今日才知道什么叫血口喷人!”他咬破舌头,将一口血向刘统勋喷了过去。
众臣喧哗。一直在默默听着的乾隆抬了下手,制住了众臣的哗然。讷亲掏出帕子,递给刘统勋。
刘统勋说了声“谢谢”,不慌不忙地用帕子抹去脸上的血迹:“血口喷人不怕,就怕有人不知道是谁在张着血盆大口!铁大人,您别捺不住性子,静静心,听我跟您细细道来!把戏人人会变,只是手法不同而已!当年河南的空仓案,是在粮仓的进仓口横了一块木板,一石粮食倒在搁板上,就算是仓满了,于是乎,明明是只装了一石粮食的仓廒,就成了百石粮的仓廒。这手法,十年前就被破了。可是,只隔了短短十年,空仓的把戏又换了一种新的手法!这手法更隐蔽、更高明,也更可笑!这手法是什么呢?那就是让粮食动起来,绕着粮仓转!”
众臣们吃惊,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刘统勋脸上浮着冷笑。刘统勋继续往下说:“话说诸城官仓这二千五百石贡粮,本该在去年秋收之后由运漕的船队送往京通二地的仓廒,可是铁大人竟然下了一道口谕,告知京通二地的仓廒正在修葺,无法腾出来,吩咐山东巡抚萨哈谅,将这批粮食存放在诸城官仓之内,于是乎,这批粮食就这么堂而皇之地成了户部的账面之数,而粮食呢,却根本就没有一粒进过诸城的官仓之中!”
众大臣震惊。
铁弓南脸色发青,对着乾隆跪下:“皇上明鉴!微臣铁弓南虽向萨哈谅借仓储粮,却未曾有任何造假之念!”
乾隆道:“站起来,听刘延清往下说!”
大殿上一片静寂,静得连喘气声都清晰可闻。
唐思训对梁诗正暗声道:“来劲!真来劲!”
刘统勋道:“‘金殿验鸟’之后,皇上派出户部官员在全国各省普查粮仓,山东诸城官仓自然也在其列。刚才说了,仓中根本就没有一粒粮食,面对查粮的司官,那些知道内情的人能不急么?当然会急!于是乎,户部山东清吏司郎中纪衡业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官仓大门口设了一座验粮台,弄来五辆马车,在车上各装粮二十石,从大门而进,再从后门而出——请听清了,是从大门而进,再从后门而出——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在验粮台前绕起了圈!这五辆马车上的一百石粮食,在验粮官的眼皮子底下,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变成了二千五百石粮食!”
殿堂里又“轰”的一声炸开了锅。
铁弓南脸色越来越青:“刘大人,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刘统勋道:“正殿之上,我刘统勋说过一句假话么?”铁弓南道:“据我所知,此次山东诸城验粮官是户部主事侯祖本,莫非他的眼睛瞎了?”
刘统勋道:“带证人!”
两个都察院司官带着侯祖本进殿,侯祖本手里提着那个装着银锭的包袱。
侯祖本下跪:“户部主事侯祖本,奉命前往山东诸城验仓。户部山东清吏司郎中纪衡业为瞒天过海,行贿于我!下官为避免打草惊蛇,假意收下贿银,与他虚与委蛇。验仓之时,当场看出破绽,立马回京,连家中都未回就赶往都察院,揭露诸城造假之眼见!这包银锭,就是纪衡业的行贿之物,铁证如山!”
满殿又炸开了锅。都察院司官将侯祖本带下。看着侯祖本的背影,刘统勋冷笑了一声。
一列大内卫士执着兵器,沿殿廊小跑着过来,在殿门两侧肃然站定。远远传来“叮叮当当”的铁镣声,有重犯正被押来。
刘统勋道:“现在该回到那五车粮食上来了。为了开验的时候能够交代过去,这五辆马车上的粮袋,只有一袋装有稻谷,而剩下的全都是假的!如若不信,各位大人可以见一个人,他会告诉各位,麻袋里到底装了什么!”
乾隆重声道:“打开殿门!”
御前侍卫将殿门轰轰隆隆地打开,挂着缠腰铁镣的纪衡业肩上扛着一口沉甸甸的大麻袋,艰难地跨进了殿门。殿内又陷入了一片死寂。
纪衡业一步一步地走到大殿正中,将肩上的麻袋放下,理了理铁镣,对着乾隆跪了下去:“罪臣纪衡业,叩见皇上!”乾隆垂下了眼睑,痛楚而又愤恨地扭过脸去。
铁弓南拨开身边的几位大臣,走近纪衡业身旁:“纪衡业,抬起头来好好看看,知道我是谁么?”纪衡业道:“您是铁大人!”铁弓南重声:“我问的是,你还认得这个‘铁’字么?”
纪衡业道:“认得。”
铁弓南顿时暴怒:“你不认得!我对你说过多少遍,身为户部的粮官,不得侵贪一粒粮食,那是铁律!如果你还认得这个‘铁’字,那你就不会戴上铁镣了!”
纪衡业道:“我有负铁大人的厚望!”铁弓南道:“我问你,诸城官仓中真的没有一粒粮食么?”纪衡业道:“真的没有!”
铁弓南道:“那你告诉我,二千五百石粮食都被谁给侵贪了?”纪衡业道:“这二千五百石粮食,从来就没有进过仓!”
如同巨石滚过,满殿俱震,继而寂静,旋即又大哗。
刘统勋抬手道:“安静!让纪衡业往下说!”
纪衡业挣扎着从地上爬起:“山东缺粮,已经整整五年,每年都在寅吃卯粮,每年都是挖了东墙补西墙,连每年解往京城的漕粮,有一半以上都是向江浙、两广甚至台湾购买的。”
满殿顿时炸开,臣工们大声议论,群情激奋。
乾隆一拍御案,猛地站来:“纪衡业,继续说!”
纪衡业道:“山东之所以粮食短缺,之所以要外粮代漕,只缘于一个字,那就是:田!也就是说,山东的粮田早已名不副实,早已是个虚数,早已养不活万千黎民,早已供不起百万漕粮!正因为如此,不光山东诸城的官仓是空的,全省州县的官仓十有六七也都是空的!”
臣工们因为震惊而变得哑口无声。乾隆的心像被锥子狠狠地扎了一下,痛得闭上了眼睛。
刘统勋道:“看来,纪衡业的话惊着各位了。我刘统勋刚从山东来,我可作证,纪衡业在这儿说的每句话都是真话!”
纪衡业泪水涌出。
殿门打开,刘统勋让侍卫扛一个麻袋进来,道:“这口麻袋是我从山东临清舅家的仓房取来的,我想让各位看一看,袋里装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侍卫,将它打开!”
侍卫将麻袋解开。刘统勋拎起麻袋一倒,倒出的是扎成捆的烟叶!众臣吃惊地看着。
刘统勋拾起一捆烟叶,举着:“山东的粮田不产粮么?不!它不是不产粮,而是因为种上了黄烟才不能产粮!”
殿内一片沉默。乾隆痛心地扭过脸。良久,乾隆回过脸来,望向纪衡业:“纪衡业,你扛来的袋子也当着众臣的面打开吧!”
纪衡业抚了抚“粮袋”,痛悔地摇了摇头,又有泪水涌出:“我纪衡业还有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只有四个字:谎言误国!这四个字,就是我纪衡业留给大清国的遗言!”话音刚落,纪衡业捞起长长的缠腰铁镣,在自己的脖子上猛地绕了一圈,两只手抓住铁镣往左右狠狠一勒,“咔嚓”一声,颈骨被勒断,重重地倒地死去。
刘统勋震惊。满殿臣工大吃一惊,看向须弥座。乾隆垂着眼皮,沉默。许久,乾隆低声:“谁来打开那口粮袋?”乾隆猛地抬脸,重声道:“铁弓南,你来打开它!”铁弓南咬紧牙关,弯下腰,将粮袋的扎绳抽去,双手往袋里一抄。手突然定住,好久才抽了出来。
众臣们瞪大了眼睛。铁弓南的手掌缓缓松开,落下的是瀑布似的黑沙子!
朝堂上的乾隆痛彻心扉,下朝之后,又让讷亲、张廷玉、刘统勋来到暖阁中,暖阁中却只有一片揪心的沉默。最后只让刘统勋将今日在朝堂上未能骂出口的话,明日早朝全都当着大臣们的面说出来、骂出来!
第二日的乾清宫正殿殿中依然是一片异样的沉寂。满殿大臣恭立着,乾隆坐在龙椅上脸色肃穆。每个人都在看着出班的刘统勋。一夜没睡,刘统勋的脸色难看。
刘统勋道:“皇上昨日要让微臣把肚里的话倒出来,微臣那就索性一吐为快!当今朝野忌惮真言,无不都在粉饰太平;臣工奏闻圣上的折子,无外乎盛世景象,却不知背后掩藏着一个个弥天谎言!其根源之一,他们是将圣上的宽仁当成了宽免,将仁政当成了虚政,将体恤当成了赈恤,将信任当成了放任!继而将国家当成了自家,将天下当成了私下!再如此下去,大清国的前程,必是岌岌可危!究其根源之二,在皇上的身边,竟然有这么一群大臣视《大清律例》为无物,以为天下乃为官者之天下,却不知天下乃万民之天下,更不知天下乃法度之天下!心中无法,必然目中无国;目中无国,必然心中无君;心中无君,必然目中无民!心目之中既然无君无民,那么,定然会祸国殃民!三桩巨案虽为大恶,却也在警告咱们这儿的每位忠君之臣,倘若仍不整饬吏治之松弛、仍不高扬法度之威严,那么,大清国就离亡国不远了!”
刘统勋说罢,扳着铁靴子,艰难地跪下,双手伏地:“皇上!微臣是带棺复任,早已不惧一死,若是说出的话有违圣意,请严惩!”
孙嘉淦、梁诗正、唐思训等一干大臣面露惊色,却频频点头。铁弓南、邹之旺等一干大臣咬紧牙关,目露不屑之色。张廷玉的脑袋伏得更低。
讷亲高高抬起脸庞,让周围的人都能看见他的脸色中充满了对刘统勋的敬意。不用说,乾隆也注意到了讷亲的表情。
乾隆站起,急踱数步,突然站在丹墀前重声:“本朝家法,至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落。但朕只长了两只眼睛,也只长了两条手臂,二眼纵然能看透春秋,双臂却难打天下!刘延清,你放心,朕不会做亡国之君!今日当着满朝大臣的面,朕给你说一句话:你敢放言,朕就敢放权!”
刘统勋抬起身,一脸正肃:“皇上敢放权,微臣就敢放胆!”
乾隆道:“说得好!你能放胆,朕就能放心!”
张廷玉闭紧了眼睛。讷亲出列,在乾隆面前跪下,一脸感动道:“皇上!刘延清重回朝堂,大清国正本清源就有能臣了!微臣替皇上高兴!”
大臣们急忙齐道:“臣等替皇上高兴!”
乾隆道:“刘统勋接旨!”刘统勋伏首:“臣恭聆圣谕!”乾隆道:“着刘统勋为户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替朕恪慎办差!钦此!”
刘统勋重伏下头去:“臣刘统勋不负圣望!”
乾隆道:“各位议政大臣,还有话要说么?”众大臣齐道:“皇上圣明!”乾隆道:“着令军机处会同吏部,将此旨即刻明发六部三院及各省督抚!”张廷玉道:“遵命!”
讷亲埋着脑袋久久没有抬起。张廷玉道:“讷大人,你怎么了?”讷亲渐渐直起腰,眼里闪着泪光:“我是替刘延清高兴!”
刘统勋动容,将一只手递给讷亲。讷亲伸出一只手,与刘统勋紧紧相握,还用力摇晃了三下。
刘统勋和讷亲走出议政大殿的时候,讷亲突然道:“对了,裕善案和十大臣案都已经定谳,皇上批下了斩立决。按以往的规矩,刑部大狱就能将斩刑办了,可这一次不一样,皇上下旨要将声势造得大大的、足足的,让每个在京四品以上官员都能到刑场上去观斩,以儆效尤。”
刘统勋道:“这事我已知道。回京那天路过刑场,见到里头正在搭台,斩墩也都换上了巨木。”讷亲道:“延清,如今你已升任都察院左都御使,犯官的审案与正法,都归你管。行刑那日,就看你的了。”刘统勋道:“好吧,这一二日我上都察院熟悉一下案情,到时该说些什么肚里就有底了。”
讷亲道:“二案经三法司定谳,那就成了铁案,你若是不得闲,我让人将案子的要点摘抄下来,让你过目。”
“不必了,还是我自个儿细细看一遍吧。金殿验鸟是我提的,而我上户部顶替的又是裕善的位子,说到底这二案都与我有关,案情细末我都得了如指掌才行。”刘统勋道。
刘统勋一瘸一瘸地走出大宫门。梁诗正站在门前等着他。
梁诗正兴奋道:“刘大人,朝中好些位大臣们见到你重回朝堂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刘统勋道:“承蒙各位还看得起我刘统勋!对了养仲,你说户部出了裕善案后,院门里人心如何?”梁诗正苦笑:“当然是人心浮动喽。”刘统勋道:“这么说,收拾人心是头件要务?”
梁诗正道:“正是如此!新官上任三把火,大家都在看你怎么烧!”
刘统勋摇了摇头:“三把火能烧出什么东西来?能烧熟一只鸭子还是烤熟一只鹅?我看什么也烧熟不了。三把火之说,无非是来个上马威,来个虚张声势。这一套,别指望我会做。得明白,放火我刘统勋不会,可杀人那就难说了!”
梁诗正笑了:“刘大人在江湖上走了一遭,说话更带点匪气了!”刘统勋道:“江湖之匪可远不如朝中之盗,或许我的这丁点儿匪气,根本就压不住盗胆。”
两人大笑。刘统勋拍拍梁诗正:“好伙计,你没变,还是那味!”
下朝之后,刘统勋又分别去孙嘉淦、铁弓男和唐思训府上拜会。孙嘉淦正在府中养伤,但是在刘统勋拿出纪衡业写的名单纸片时,立即决定当日就回刑部,会同刘统勋的都察院,派一批干员到各省去查实这些人的犯案事实,要替朝廷挖出毒根。而拜会铁弓男时却遇到了老臣的眼泪。
铁弓南一看刘统勋来府上,气得胡子都颤起来,指着刘统勋道:“朝堂上这么一折腾,我……我铁弓南在皇上眼里,就不再是个忠臣了!我铁弓南在你刘大人眼里,就更不是个忠臣!”说罢连连摇头,眼角挂上了两颗浊泪。刘统勋道:“苦耘,为臣忠不忠,谁说了都不算,得靠天下百姓来说。我刘延清要是不把你当朝廷的忠臣,我会登门来拜见你么?”
二人促膝长谈了半天,刘统勋将朝堂之上的种种一一列给铁弓南,铁弓南虽心中委屈,也决意支持刘统勋清查朝中蛀虫。
刘统勋从铁弓南府上出来时,恰巧遇上载着唐思训回浙江的马车驶过。两人在城门外,停下马车,迎着夕阳,交谈许久,得知唐思训要回浙江,刘统勋目光沉重:“唐大人,回浙江后,多去省内的粮田看看,到底有没有全都种上粮食!”
“哦?莫非刘大人对浙江粮田有所耳闻?”唐思训道。
刘统勋道:“山东粮田普种烟草的事,你在大殿上都看到了。你想想,山东这么一个产粮大省,如今竟然成了一个缺粮大省,于国何堪?于民何堪?我是担心浙江的粮田也有类似情况出现,将大好的种粮之田移作了他用,毁了浙江这座偌大的天下粮仓。”
唐思训抱拳:“唐某知道分量!”
刘统勋道:“对了,我在诸城遇上了你女儿小放生。实在说来,诸城空仓案,她也立了一功。你回去带上句话,我刘统勋谢谢她。”唐思训惊奇道:“还有这等事?真没想到,我这个野丫头,竟然跑到山东去玩耍了!”
刘统勋道:“请唐大人上车吧,延清就不远送了,路上多保重!”唐思训道:“刘大人也保重!咱们一块儿替朝廷建功!”
两人抱拳作别。刘统勋站在路边,看着唐思训的马车远去,久久没有收回目光。这边刘统勋京城风起云涌,那边杜霄在千里之外的江西也同样天翻地覆。
满脸胡子的杜霄背着行李出现在江西青铜县杜家庄村头时,县衙把总正站在台阶上,手里执着火铳,大声道:“杜家庄的刁民们都听着!青铜县令在庄子里陪你们玩了三天,他不想再玩了!今日是最后限期,尔等要是再提那笔银子的事,那就是说,在逼着我把总大开杀戒!”
被火铳包围的村民们攥紧拳头,怒目而视,默不作声。
把总又环视一眼:“很好,看来你们都想把脑袋给留着!本大人成全你们!谁要是再敢暗中作祟,蓄意起事,那就只能说声对不起,本大人取你首级,连眼睛都不会眨一眨!”
把总将手一掸,兵勇们猛地架起刀枪,排出一道长长的“刀枪走廊”。把总也一下拔出了剑,高高举着。把总厉声道:“想活命的都从这刀枪底下退场吧!不想走的,那就留在这儿,看本大人如何血溅祠堂!”
乡民们又骚动起来,默默地从刀枪底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场子。几个年轻后生用目光相互暗示了一下,也默默地退出场去。很快,场子里已空无一人。杜霄冷冷地看了一会儿,拾起一根被人丢弃的萝卜,慢慢吃着,嚅动着胡子拉碴的下巴,反身离去。走到庄子里一座小院门前,放下行李,起身推开屋子的边窗,跳进屋去。阔别八年的家,如今已被翻箱倒柜,一片狼藉。供案上,父母的牌位也翻倒着,香炉倾翻在地。杜霄站在屋子里,默默地环视着。
好一会儿,杜霄走近供案,将牌位扶正,往香炉里重新插上两炷香,将香点着,对着牌位跪了下去,重重地磕了三个头,爬起身,推开了内屋的小门。陈年落尘纷纷,陈年回忆纷纷。当年二十岁的杜霄身着一袭青衫,神情桀骜,将刚刚绘成的《六雀图》挂到墙上,如今这轴落款是“六雀堂主”的画蒙满蛛网和积尘。
记忆里狂放的大笑声、杂乱的说话声、哗哗的铁镣声、捕人的吆喝声、囚车的隆隆声在画下响着,重重地敲击着杜霄的心。
杜霄深深吸了口气,走到一张硬桌前,往桌洞深处摸索了一会儿,摸出了一个记事簿,拍去灰土,借着窗外的阳光看了一会儿,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痛楚。
好一会儿,他回身将一口柜子打开。柜里,一套白色的麻布孝衣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他取出孝衣,抖开。又把挂在墙上的一条桐油雨披扯下,用牙咬着,扯下一大块,又找出针线,将针上的铁锈在靴底下磨去,摊平记事簿,用桐油布包裹住,严严实实缝住,然后贴孝衣的后背下方再缝了上去。
他做完这事,将孝衣贴肉穿上,重又穿回上衣。他感到极累,仰身重重倒在床榻上。
八年的尘灰在他身下澎起。
次日清晨,杜霄在庄里的小食摊前打听哥哥杜云的下落,没想到哥哥却成了庄里人讳莫如深的话题。最后一个小伙计追上杜霄,悄悄告诉了杜霄事情的经过。
原来,朝廷在杜家庄修筑官马大路,征用粮田一百八十七亩,按律须全数复垦还田,并拨下银两,由当地乡民做复垦之需。而杜家庄乡民未曾取到半文拨银,与青铜县衙交涉无果。更可恶的是,青铜知县与把总率数十兵勇,以“开杀戒”恫吓乡人。杜云等八人写了状纸,要去巡抚衙门告状,不想被把总发现,就发生了杜霄刚进庄子时见到的那一幕。被青铜县令和把总追杀的杜云现在正藏身庄头废弃的粮仓里,杜霄马不停蹄地赶到粮仓,告状的八人正在商议如何将状纸送到巡抚衙门,杜云一见身着孝衣的杜霄,两兄弟抱头痛哭,杜云也给杜霄讲了告状被追杀的始末。众人聚头小声说着话,对外头的动静却丝毫没有察觉。
青铜县令与把总也得知了他们的藏身之所,正领着一二十个抱着柴草的士兵,猫着腰向粮仓摸来,在黑暗中指挥着士兵们将柴火堆放在墙边,单等着把总下令放火,要烧他们个尸骨不留。
杜云将状纸塞进一节竹筒,扭紧木塞,双手捧到杜霄面前。众后生在杜霄面前跪下。杜霄道:“这是……”
杜云道:“粮田被征用走了,可又无法复垦,往后的日子就只有死路一条!哥哥我领着大伙向官府讨银子,其实就是在讨命!这事儿,不光是为了一个杜家庄,更为了因修官道而失田的万户百姓!弟弟此时回来,定是天意!就由兄弟你去送这张状子!大哥代杜家庄乡亲跪谢于你!”杜霄庄重地接过竹筒,双手托起,沉声道:“杜霄不负众望!”
突然,门窗外一片通红,浓烟夹着火焰扑卷进来。
一个后生大声道:“坏了!被官兵发现了,他们在放火!”七八个人跳起,向后窗退去。
火势借着大风,顷刻将屋子烧着。
杜云大声道:“大家都别乱!只要杜霄活着就有指望!弟,快走!”
众人不容杜霄分说,猛地打开高高的后窗,一起托起杜霄,将他狠狠地推了出去!
被推出高窗的杜霄重重地朝着屋后的运河落去,轰隆一声沉下了水。杜霄在黑暗中下沉着,头顶水面上,晃动着一片通红的火光。拱在水面上的杜霄震惊地看见,粮仓已经大火冲天,官兵们举着一杆杆长柄火铳,对着后窗方向猛射着。
火焰中,杜云出现在窗口,火铳声成排地响起。杜云中弹,趴倒在窗户上,顿时被火吞没。杜霄狂喊:“大哥——!!”士兵掉转火铳,对着河里放铳。
铁弹在水中四溅。杜霄怒目圆睁,长吸一口气,潜下水去。粮仓在大火中轰然倒塌!
杜霄将竹筒往衣服里面塞了塞,暗下决心,官场如此,要告就直接告到京城去。
杜霄破衣烂衫地到了京城工部都水司,在外面跪了三天三夜,喊着工部郎中讷图的名字,说有冤情上告,打扮架势着实像个进京告御状的灾民。
可是这讷图是个只关心吃喝玩乐的官场草包,只仗着是中堂讷亲的侄子,在工部也混得风生水起。到了第三天,讷图约请铁箭飞和侯祖本,酒正酣时,杜霄又开始在门外喊冤,讷图便让手下绑了杜霄带进公房来。
公房桌上摆满了菜肴,三人喝着酒。讷图抹着鼻子,打了个响亮喷嚏:“阿嚏!朝廷在江西征用粮田修筑官马大路,按章程,征用多少粮田,就得补回多少粮田,工部按每亩六两银子拨给地方衙门,再交到乡民手中,让他们把新田给开出来。就为这么点陈猫古老鼠的事,此人就上工部来练上了!”
侯祖本道:“朝廷给下六两银子开一亩新田,给的不少了,人不能太贪心嘛!”铁箭飞道:“恐怕还另有隐情吧,要不,他傻呀?”
讷图笑起来:“铁公子是明白人!谁都知道,地方衙门的那些官员,手掌上都是长锉牙的,就是铁弹子让他们过过手,也得给锉一层皮去!这姓杜的真他娘傻,逮住蛤蟆攥出尿来,这好玩么?不好玩!”
门猛地推开。
杜霄进来,见到酒桌上的讷图,讷图皱眉:“你怎么还来?本官问你,带什么来了?”杜霄道:“空手而来!”讷图道:“要带什么走?”杜霄道:“拨银实数!”讷图道:“既然空手而来,那就得空手而归!你说,这公平么?”杜霄道:“讷大人!您听我说……”
讷图站了起来,怒容满面:“放肆!簸箕大的天你见过几个?还真玩上瘾了!告诉你,本官是谁?是讷中堂的亲侄子!也是个吃了扁担、横了肠子的爷!”
铁箭飞默默地打量着杜霄。
杜霄道:“讷大人,青铜县杜家庄修官道征田一百八十七亩,却没有拿到一文复垦还田的拨银!您是掌管工程拨银的郎中,我来找您,只是请您给一句话,那笔银子到底有没有拨到青铜?就这么一句简简单单的话,您为何就不能说呢?”
讷图抓起酒碗,往地上重重一掷:“你想堵着鸡窝要蛋,本大人就是不给!来人啊,把这个疯子拖出去!”
四个赶到的衙卒冲进来,按住了杜霄。
杜霄重声道:“等一等,让我再说一句话!”铁箭飞道:“松开他,让他说。”讷图一怔:“公子……”铁箭飞道:“让他把话说完。”
讷图对着衙卒使了个眼色,衙卒松开杜霄。
杜霄从地上爬起,将破棉袍的大襻口一个一个解开,脱下扔在地上,露出的是一身麻布白衣。
杜霄眼里噙起泪水:“讷大人!我听人说,您是个孝子,您父亲过世的那天,您抱棺不放,哭昏了三回。既是孝子,那您一定认得出我这身麻布白衣是什么了。”
讷图道:“滚!快滚!本官是不是孝子,关你屁事!”
杜霄道:“讷大人不愿说,那我就代您说吧。这是一身孝衣。十年前,我爹娘死的时候,我刚当上钱塘县令,第一回穿上孝衣,此后不久,我去了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获释回来后,重又穿上了它。我之所以将孝衣贴肉穿着,是因为我不敢将这个‘孝’字给放下。我为何会这样?是因为我父亲告诫于我:为儿孙者,对父母须得‘孝’字当先;为官者,对百姓、对朝廷须得‘孝’字当先!这个‘孝’字,就是我杜霄做人的本分。正是凭着这个字,我才千里迢迢赶到京城,赶到都水司,赶到您讷大人面前,跪着讨您的一句话!讷大人,看在你我都是孝子的分上,咱们一块儿替青铜县失田的百姓尽一回孝心吧!”
铁箭飞轻轻鼓起了掌:“说得好!这番话,想必在朝堂之上是听不到的。讷大人,愿听我一句话么?”讷图道:“请铁公子赐教。”铁箭飞道:“你在京城混了不少年,见过几个人是戴孝为官的?怕是没有吧?像杜先生这样的真孝子,如今已不多,好生待他吧。”
讷图脸色尴尬:“好吧,看在铁公子的面子上,杜霄你先找个客栈住下,待本官一有空,就让人去找你。送客!”
衙卒拖起杜霄:“走吧!”铁箭飞道:“慢。”铁箭飞离桌,从地上拾起棉袍,给杜霄披上。铁箭飞道,“外头寒冷,别冻着了。”
杜霄感动道:“敢问这位公子尊姓大名?”铁箭飞道:“在下姓铁,草字箭飞。”杜霄抱拳:“多谢铁公子相助!”
铁箭飞抱拳还礼:“戴孝为官者,你是当朝第一人。如果不是我眼拙的话,杜先生前程无量!”
都水司大门口,讷图送铁箭飞、侯祖本出来:“铁公子,侯兄,过些日子我再做东,咱们接着玩。”
铁箭飞道:“你们二位记住我的一句话,想成大事的人,可以看不起高士,看不起清士,不能看不起死士。告辞!”
护卫牵上马来,铁箭飞骑上马背,疾驰离去。讷图咀嚼着铁箭飞的话,一脸困惑。讷图道:“莫非铁公子看出杜霄是个死士?”
侯祖本一笑:“铁公子是什么眼力?您不知道,可您叔叔知道,要不能收他当干儿么?”讷图道:“这么说,你也知道?”侯祖本又一笑:“我敢说,在铁公子眼里,您还不如这个青铜来的不速之客。”
讷图脸一沉:“你……”
侯祖本道:“咱们都是铁公子的朋友,要是见外,那就是跟您叔叔见外了!”
送走了两人的讷图阴着脸走进大门。笔贴式疾步迎上。
讷图仍在嘟哝:“他侯祖本刚换了身官袍,就一脸小人得志!”
笔贴式道:“讷大人,您回哪个家?”讷图道:“先换身行头,去情天楼。”笔贴式道:“好嘞,我这就去备轿。”讷图道:“等一等。”
讷图嘿嘿阴笑了起来,在笔贴式耳边咕哝了一阵。
笔贴式脸色一紧:“这罪名……安得上么?”讷图狠道:“怎么安不上?给人安功名难,给人安罪名还难?如今空仓案余党一个接一个逮出来,也算上他一个!一屎盆子扣死他!”
杜霄从工部都水司出来,坐在路边小酒摊的板凳上,面前是一坛子烈酒,桌上撒着一把茴香豆。他在端着碗喝酒。四个捕兵骑着马驰来,一眼看到杜霄,翻身下马,拔出刀,围上。
杜霄站起:“你们是谁?”捕兵道:“还废话!你逃不了了!”杜霄道:“逃?我干吗要逃?”捕兵道:“有人告你是裕善的余党,合伙侵贪帑银,犯的是死罪!”杜霄愤怒:“这是血口喷人!”
捕兵拎起铁索子,道:“说错了,爷这是血口咬人!”杜霄道:“等等!”他端起酒坛,仰脸大口喝尽,重重将酒坛往地上一掷。杜霄一抹嘴,大声道,“下索子吧!我就不信偌大的京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
捕兵大笑道:“又是个大傻子!”
铁索子将杜霄锁住。捕兵骑上马。长长的铁索拖着杜霄,一路狂奔。杜霄跌倒,在地上被拖行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