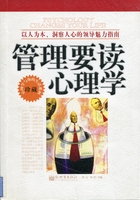伤筋动骨一百天!第五实在捱不了那么久,为了尽早出院,他天天超标锻炼,年轻人恢复快,腿上的瘸态一天比一天轻微了,爸爸一来看他,他更是忍着疼走的豪迈健康。
腊月二十七,他执意出院了。
医院他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再呆下去,腿好了,人疯了!
二十七出院,二十八早上迫不及待出家门,打车来到学校附近的天桥。
走上桥端他再不敢向前走了,心下忡忡的,从柳豆洗盘子的饭店回学校,这座天桥是必经之路。
这段时间他让武大楚时不时的盯着豆,知道她在饭店!
腊月滴水成冰的天气!他爱俏,穿的单薄,站在桥上顶着风半个小时,脸冻麻了,人却心事重重没觉得冷。
他心扑扑跳着,不时望向天桥另一端,
近段时间他让武大楚把吃吃喝喝源源不断的给豆送过去,但是不送钱。
他是一直算计好腊月出院的,可腊月学校就放假了,他怕豆有了钱放弃打工回家去,她若回了家他不好找她,而他必须一出院就见到豆。
他的一颗心早就急到要跳出来了。
他们之间有许多事情等着他去做呢!再也拖不得了,所以他忍着心疼暂时不给豆送钱,为的是把她拖在西安。
……
柳豆终于从天桥的另一端升上来,那毛茸茸的脑袋从天桥刚刚探出,第五鼻子就酸了,他偏了下头吸了下鼻子。
这算什么,一个大男人家,动不动就眼圈红!他在心里骂自己。
他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可那股子酸劲儿他把控不了。
他从小到大没这么爱酸过!
豆没有看到天桥另一端的第五,她背着背包在天桥中央的小摊前驻足,挑挑拣拣一阵,再向前走时,手上多了一个白纸卷成的筒。
她一边走一边吃那纸筒里边的东西,纸筒往嘴边一送、头一仰,象喝矿泉水一样将纸筒中的东西送进口中。
第五吞咽着干涸的喉结,眼目端端地望着小小的豆由远及近的走来,她正专心着纸筒里的‘零嘴’。
她仰头往嘴里送一遍,低头向纸筒里看一遍!
看上去她是把那点‘零嘴’稀罕的紧!
她又一次捧着纸筒仰头时,四目相碰了。
举着纸筒的手顿住了,一颗绿色的豌豆从筒沿滑出,掉在她脚面上,又蹦到地上。
纸筒缓缓从嘴边移开。
第五没有看到他来时担心的或厌恶或仇恨的表情。
豆没有这样的表情!
她只是若有所思的略略把脸歪向一边,偏着脸咬着唇,似在盘算什么,还不时别起眼睛看他。
没错,是在思忖盘算着,眼里还有点‘贼’。
第五看着她眼里的贼光,不敢说话,只艰难的咽喉结。
站立一时,豆仿佛思量好了,她眼睛盯着第五慢慢转回身,向前走,走几步,掉过头看第五,是要让他跟上。
第五慌忙随过去,中间隔着点距离,俩人一前一后,下了天桥,顺甬道往前,在公交站牌停下。
过一阵公交驶来,第五随豆上车。
在车速的一闪一晃中豆站的直直的,眼睛向着窗外一动不动。
第五定定看着她,眼睛里看到他俩乘公交打胎时,她那泛青隐忍的脸。
他抿紧嘴心如刀绞。
一路上,他看着豆,豆看着窗外,俩人无声无息。
公交走的很远,一直到了郊外,豆微微蹙着眉心,她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所以她往很远的地方去。
在一座庞大却废弃很久的铁架大桥边,柳豆下车,第五跟下去。
柳豆向空旷的大桥上走去,边走边把双肩背着的背包换成单肩挎了,兀自往大桥深处走。
第五在三五步开外随行,眼睛定定跟着豆的后背,桥上风很大,她的衣摆发梢统统向一边甩拂。
桥深处路封了,巍峨山脉近在眼前,豆驻脚转过身来。
第五马上住脚,他不敢再往豆近处走,他知道她不会喜欢!
可豆却向他来了,大风把她薄薄的身子吹得要飘起来。
她走了三五步,走到第五脸前,她脑袋就在他下巴下了,他浑身一紧。
豆没说话,她看着第五颈间的一粒晶扣,第五出来时是精心拾掇过的,身上淡淡的香。
看着那枚晶扣,豆轻轻蹙眉,又在思忖盘算。
她咬着腮,脸颊上陷下一个坑,仿佛决心又决心。
忽然她抬头,巴巴的看着第五。
她眼目巴巴的,没错,眼目巴巴的,第五一愣,心紧住了,十分紧,是紧张!
“五哥!”
轻轻的、虚虚的,豆叫了一声。
第五浑身一凌,猝然喘不上气来。
不止他一人被这“五哥”二字惊煞!
亲口喊出这一声的豆,更是自己把自己惊死了,她直想闭眼缓一下,但她没有。
她没有,她反倒是再往第五身上贴了贴。
大风从他们中间呼啸穿过!
她戴着毛手套的手贴到第五胸口,小声的说话:“五哥,你让武大楚给我送了那么多东西,我知道你对我好,你人好,你心好……”
她已经贴到第五身上了,可她还是一个劲继续往上贴,第五无措的几乎要后退。
“五哥,你帮我,我不要你杀人,我只要你惩罚他们,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惩罚他们五哥,我知道你是好人,你会帮我的五哥!”
她央央的说着,第五被她挤的往后撤了撤身,但撤的很少,脚往后撤,心不想。
他换不上气来,说不出话来,脑子里什么都不知道,又空又大又白,他几乎有些疲软无力,两手向两边扎着,放不下去,也不能放到豆身上去,只投降一样扎着举着!
“我只要你惩罚他们,总是有办法的,不会连累你的五哥,五哥,”
豆哆嗦着把手摸进背包,“五哥,我有办法,不会连累你!”
她从背包掏出一张哆哆嗦嗦的纸来:“有两种药!digoxigenin和Ethinylestradiol!五哥,你看,这两个药,这两个药一起……连续七日摄入人体,天天5克,不间断摄入,那里就萎缩!不知不觉萎缩!只要把它溶进水里,放进菜里,掺进任何入肚的东西里,……你不会受牵连你不会坐牢!五哥,你帮我,你只要把他们找来,拖住他们,五哥……”
她眼睛闪着幽幽的黑光,声音低低的,象在说着天大的秘密,偷偷的、急急的,口齿把字咬的实实的,唯恐说的不够清晰。
说完,她眼目巴巴眼目忡忡的仰脸看第五,看他的反应。
第五痛苦的皱紧了脸,他摇头,摇头!
“没有豆,没有……”第五是终于喘上一口气,但意识很混乱。
他只知道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豆她病了,她病的很厉害了,自己怎么能把她害成这样!
他不能原谅自己,他恨不能自己把自己狠狠揍一顿,揍的头破血流。
他摇着头举着手,身子向后退。
“是你啊……”豆凄厉的一声叫,响炸了一颗小炮仗!
但她又及时降下来:“是你啊,五哥,是你把我带到了那里,是你把我扔到那群人里啊,你是有良心的,人人都说你是有良心的,他们人人都说你心好,你帮我,五哥,你不帮我你能心安吗,你不帮我你能睡着觉吗,我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了,我招谁惹谁了,你让他们那样糟蹋我!你知道我多疼吗,你知道我整夜整夜睁着眼吗……”
“豆,”第五哽咽了,口更拙了:“我带你去看医生,我带你看最好的医生,豆你……”
“我没有病!”尖厉刺耳的一声,豆的身体从他身上弹开,她手上的纸飞了,在空中呼啦呼啦随风翻卷。
她喘着粗气,竭力压住自己的激动,换回央央弱弱的声音:“五哥,你帮我,你帮帮我,五哥,我,我给你……”
“我给你……”她重新往第五身上贴过来,整个人象一片纸一样粘到第五战栗的身体上。
她在他下巴下颤颤仰起白白的小脸,黑眼睛张的深深的,看着他赤红的眼睛,她说话,她耳语一般的说话。
“我的伤平了,我的身体又好看了。”
她水汪汪的大眼睛凝视着第五,右手摸索着自己的衣扣,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一一解开,“你看!五哥你看!”
一大片光洁瓷白的小肩膀‘刷’地裸露在嗖嗖寒风中,白的刺眼,颤的扎心。
第五愣成一块铁疙瘩。
“你看,五哥,我好了,我没疤了,我好看了!你喜欢的,我给你!”
‘哇’的一声,第五哭了,孩子一样大张着嘴。
他一把扯起豆的衣服死死将她抱在怀里,放声大哭……
风很大很大,大桥地势空旷,风声撞在铁桥框架上簌簌呜咽,第五哭的悲天恸地。
许久许久,哭够了,嚎够了,他没有办法劝慰豆,豆的心病得慢慢医,他抽噎着哄慰:“我做,我做,豆,我做……”
……………………………………
冬天的傍晚,六点钟天就黑尽。
两个人摸黑回了市区,市区灯火通明。
“吃饭吧,啊?”第五的声音仍然沙哑:“到哪吃呢?”
他从来自说自话,没有征询别人意见的习惯,可现在变了,小小的豆比天大!
“柴街巷有三块钱一碗的面。”豆说。
第五拧过头来看她,十分惭愧的看着她。
三块钱一碗的面,这话叫他惭愧,她当他有多么惜钱,这是过去被她记下的形象。
第五什么都说不上来,他看着豆,伸手攥过豆的小手到路边拦车,她的手虽然戴着厚厚手套依然很小很小,这也让他第五难过。
他紧紧的攥住这只小手。
他们来到海龙湾国际大饭店。
“我的脚,暂时还不灵便,踩汽车离合器,还不行。”
在卫生间冲了把脸,到餐桌坐下后,第五向豆解释没开车的缘故。
“以后不要再坐公交了!”
他小心翼翼的说话,有点字斟句酌,生怕叫豆感到肉麻,生怕豆为自己的关心感到害臊。
说着话钱包已摸在手上,抽出一只卡递给豆:“别打工了……”
话还没说全,柳豆就把卡接走了,她揪开背包的粘扣,掏出电话本,将卡仔细掖进去。
然后抬头吧嗒眼看第五,她说:“那个药大量买的话,得有医生药方。”
她的眼又黑又深,在餐厅华璨晶莹的灯光下,熠熠发光,叫人看了挪不开眼睛。
第五低了低头。
这个话很折磨他,可他让自己十分耐心的听,不厌其烦的听!
豆说那个药可能有苦味,怎样怎样掩盖它的味道,用啤酒或许不易被察觉;她说真不好办,除了苦瓜,几乎没有发苦的食物;她说结合阿司匹林会加速药效……
菜上来了,她的声音戛然而止!甚至停的有些突兀!
她褪下右手的手套,笨笨的捉起筷子,万事靠边,一声不吭,认认真真的吃饭!
第五看她吃饭,很正常的吃饭,却总有一种怪异,是什么呢?
是一种饿极!是一种平静的争先恐后。
对的,就是争先恐后!
他看出来,豆和他得了同样的病。
他们得了一种不算病的病,饿病!
天天不到吃饭时间他们就开始饿,上顿没吃完,就开始想下顿。
端上来的饭,哪怕一粒米,都不舍的丢弃。风卷残云,肚子成了个无底洞,多少都吃的下。
总吃的眼前一干二净。
山林十日让他们得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毛病!
豆还好,表面看去还算吃的文雅,静悄悄,一口一口入肚。
看着一本正经吃饭的豆,第五眼睛涩了。
他吞了吞酸涩的喉结,轻轻搁下筷子。
他持续两个月的‘饿病’,在这一刻痊愈了。
一段情的伤痛要另一段情出现才可治愈,一处病痛的折磨要另一处病痛的生出才可转移。
心上害了病,其它腿脚头肚各处疾病全不是病了。
他的‘饿病’就是让心中害起的一阵‘心疼’给赶跑了。
他燃起一支烟,静静的看着豆吃饭,过一阵给她夹一筷头,嘱她好好吃、慢慢吃。
他觉得自己忽然长大了!
他静静的看着豆,他看着豆的眼神是疼爱的眼神,抑或是一位贫寒的家长,正饿着肚子,看自己孩子大快朵颐。
豆热了,用左手背拭一下额头。
“这么热,把手套摘下吧!”他见豆的左手仍戴着手套,劝她摘下来。
豆不肯,傍晚从郊外返城时,他要看她的手,她也不肯,她不肯他不敢多嘴!
可这时他又犯上心急来,其实他也真不敢看她的手,那断了的无名指当时简单处理了一下,虽然帐篷女人说上的药是祖传,可他不相信那截指骨能长好,八成是成了断指,他真的不敢看。
他不敢看是他怕那股子疼,那股钻心钻肺的心疼,但他心上着急,终究得面对,他心跳着说:“豆,手上的问题大不大,明天到医院看看好吧!”
豆停住了吃饭,抬头看他,若有所思的看他,然后看自己的左手,腮边鼓鼓的。
她没有说话,低回头去,眨着眼睛,轻轻咀嚼,神情恍惚。
第五不再多言。
吃过饭再打车时,豆开始紧张了,垂着头咬腮上的肉,眼睛游移怯懦!
第五知道她紧张什么,她紧张他们将要去宾馆。
第五让出租车到学校。
“豆,学校宿舍放假了也让住啊?”
其实学校最近正在清房,但柳豆这时说:“让的!”
好多事情做起来比想着难多了,她这时在想,如果真的再跟第五上床,她不如死掉!
-------------------------